
鸿爪集
¥ 40 九五品
库存49件
陕西西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郭鹏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
上书时间2012-02-11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8天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 该书是方志学者郭鹏20多年间在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文章选集,包括散文杂文、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地方志研究、书序书评、诗、楹联、附录资料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不少独到见解建树。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名书法家为其题书名,并题字;陕西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马家骏(现居上海)、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董建桥、陕西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王蓬为作《序》。该书内容品位很高,极具研究价值、收藏价值。《鸿爪集》自 序 郭 鹏 我注定是笨人一个了:右手掌是横断纹。据相学家说,横断掌纹是笨人的体相。因此,几十年来我从事着一个笨人的事情——爬格子,看来是命中注定的,即使想努力改变这个命运也难。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究竟爬了多少格子,只知道每天不写点东西就觉得心里空空的,象是这一天白过了似的。头发爬白了,眼睛爬花了,腰爬疼了,背爬弯了,但恶习难改,只有坐在格子前,才觉得有事可干,才觉得是在干正事。柜子里到处是发表过的和未发表过的格子,是各种报纸杂志的样稿、是划满红色蓝色改正符号的校对稿。近些年,虽然换了个汤头,把白纸格子换成了电脑屏幕,但打出来的字,仍然是在格子里。 我装在格子里的,多是些大多人并不爱看的废话,实话实说,援引陈年老账,谈不上文采;甚至说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自己以为有理,其实也不尽然。只是自己不说出来写出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有些是工作中生活中的感悟,有的则是读书的笔记体会整理,以及一些朋友给面子,请对其大作说几句话(谬名曰《序》)等,于是便有了这本杂七杂八的册子,聊存这些年来爬格子的记录而已,也就是在雪地上留下些乱七八糟的爪痕。随着时间的飞逝,这爪痕自然就融入大地,变得了无踪影了。 这些年,还有数不清的发言呀,讲话呀(我不论在什么地场合发言、讲话都自己撰稿,从不烦别人代劳),总结呀,学习体会呀,地方志审稿意见专业培训稿呀,信函呀,草拟的文件呀,等等,我也说不清有多少了,总之是不少,但自认为保存价值不大,没有收录入本书,也算是为了节省的纸张吧!再者,我1984年以后发表地方志研究文章若干篇,1990年,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处曾出版过我与李佩今先生合著的地方志论文集《地方志与国情教育》, 所以,这里就不再收进本集子了。 我向来对书的看法是:书是特殊的东西,对甲可能是废纸,对乙可能是宝贝,世界上从没有一本书是人人都爱看的。有的人视如垃圾,弃如草芥;有的人视为奇货,百年珍藏。我近20年来爬过的格子(主编的书、以及拙著、文章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下千万字。这本小册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算是敝帚自珍,我也从不奢望我的“敝帚”人人爱看,只要有人看就行,哪怕是以鄙视甚至批驳的眼光来看。 朱熹老夫子曾写过一首七绝:“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时了,不如抛却去寻春。”看来老夫子是曾下过决心不爬格子了,但最后至老至死还是没有摆脱爬格子的命运。不过他的格子爬得好,爬出了名,直至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提起他的名字还如雷贯耳。我们虽也爬格子,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这本册子之后,格子肯定还是要爬的,这条路走惯了,免不了还要走下去,爪迹难免还要留在雪泥上。至于这些爪痕好看不好看,能留多长时间,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郭鹏2005.6.24 《鸿爪集》序言 董健桥 (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 我知道郭鹏远比认识他要早。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搞地方志工作,尽管原先具备一些关于地方志的基本知识,但从无进行过理论上的研究,更无实践方面的经验,要尽快“入门”,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习。于是对当时的各地各级地方志期刊和有关著述甚为关注。在阅读过程中,一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级期刊和有关著述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名字,就是郭鹏。 我当时并不知道郭鹏是谁,但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他的文章一般文字不长,但很结合实际,一篇文章往往就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具体操作很有用,而且论述清晰,文字干净,逻辑性强,给人的印象很深。后来发现他的文章多与陕西有关系,估计他是在陕西工作的同志,问了当时省志办地县志处处长解师曾,老解告诉我:“郭鹏就是我们佛坪县志办的主任嘛!”从此,我知道我们陕西方志界有个郭鹏。 我当时还在省志处工作,和市县同志接触较少,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郭鹏见面。90年代初,老解退休,我接任地县志处的工作,此时郭鹏也已经完成了《佛坪县志》的编纂,调到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第一次和郭鹏见面,是在宝鸡的一次会议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见面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指着他说:“你就是郭鹏?”他指着我说:“你就是董健桥?”遂开怀大笑,一见如故。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有书信、电话往来,有时说说工作,有时说说业务,有时拉拉家常,有时倾诉烦恼,也有时仅仅互致问候。他对工作的热情、对地方志业务的浓厚兴趣和深入钻研以及想干一番事业的执着愿望,常常使我深受感动。 汉中地区志办当时面临着很繁重的工作任务——多数县的志书还没有完成,业务指导和审稿工作量很大;还要适时启动《汉中地区志》的编纂。调郭鹏到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事实上,他在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以及后来创办并逐年编纂《汉中年鉴》所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在汉中是空前的、永垂史册的。 据我所知,《汉中地区志》的启动工作,由于种种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当时并不顺利。而这一阶段,全省其他地市的地市志编纂工作却蓬勃开展,《汉中地区志》的工作一下子落到全省的后边,郭鹏心急火燎却无可奈何,我上面说的“有时倾诉烦恼”,就是他和我那一段交谈的主要话题。 省志办对地市县修志工作只有业务指导的职能,对诸如人、财、物及具体工作规划等重大问题并无决策的权力,对《汉中地区志》工作的一度停滞,除了向地委、行署提出建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这一段时间,全省各地市县志稿大量完成,纷纷送省终审,省志办审稿压力很大,我想,让郭鹏就这么“闲着”,实在是浪费资源,就请他作为省志办的特邀审稿员,参与了对《志丹县志》、《镇巴县志》和《延安市志》的终审。他的审稿报告结构严谨,逻辑严密,问题分析准确,解决方案可行,对提高这几部志书的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省志办审稿委员会和这几部志书的编纂单位都很满意,也使我对他的业务水平有了更多的了解。 《汉中地区志》的编纂工作在各方努力,特别是汉中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终于于1995年正式启动,1998年郭鹏被任命为主任、主编,他随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延续汉中自清嘉庆年间编纂《汉中府志》以来中断了二百年的历史记录,且工程浩繁、意义深远的工作中去。期间,省志办在宝鸡召开有各地市同志参加的业务会议,省志办滕云主任问我:“郭鹏怎么瘦成这个样子?”我说:“《汉中地区志》‘动工’了”。这就是那个时期的郭鹏。 郭鹏从事地方志工作二十多年,在主持完成近百万字的《佛坪县志》和三百六十余万字的四卷本《汉中地区志》两部大部头著作外,还有很多专著和文章发表。在我看来,其中在地方志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作为范文发表在1990年第2期《中国地方志》的《佛坪县志?总述》。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总述》(或《概述》)是一部志书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写的部分。说它重要,是因为《总述》列于全志之首,是全志的纲领,纲举目张,它把握全局,总揽全志,起着正确引导读者深入研究一地历史和现状的导读作用。一篇有个性、有特色、有文采、有风韵的好的《总述》,不但能够吸引读者,而且读过之后,即使不去阅读全书,也能对当地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特色有一个概括、宏观的认识。所以,《总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说它难写,是因为《总述》作为一部志书的最高层次的文字,要在一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字的志书的基础上,提炼出最基本、最富有特色的内容,而且既要跳出各分志的小圈子,又要统揽全志,高屋建瓴,实在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没有对地情的深刻研究和总体把握,没有对历史和现状资料的充分占有,没有与历史实际相一致的逻辑架构设计和精炼、准确并富有文采的文字功力,是很难高质量地完成的”。 《佛坪县志?总述》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后,反响热烈,被方志界认为是《总述》(《概述》)写法的代表性派别之一。据我所知,《中国地方志》创刊二十多年来,全文发表一部县志的《总述》,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个人对这种写法也是颇为欣赏,多次在业务或审稿会议等场合表示了对这种写法的推崇。2005年,《汉中地区志》出版,资料丰富翔实,记述严谨准确,编排科学合理,从文字到图照,从内容到装帧,其质量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都堪称上乘佳志。 郭鹏同志以他对事业的执着、坚韧和聪明才智以及多年来的辛劳和无私奉献,为汉中的地方志事业、地方历史研究和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应得的回报。他多次被评为陕西省或汉中市地方志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其事迹被多家媒体广泛传播;1998年晋升编审职称,任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2005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表彰的“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是我省地方志工作开展二十多年来本系统唯一的省部级劳动模范。 逝者如斯!郭鹏把一生美好的时光交付给了地方志事业,在面临人生的又一个转折——退休之际,他把自己多年来的作品汇编成集,命之曰《鸿爪集》。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人生记录,这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文字,正是郭鹏治学乃至人生的心路历程。 《鸿爪集》按内容来说分作了七个部分:一为《散文?随笔》,二是《地方史研究》,三为《地方志研究》,四是《宗教研究》,五是《序跋?评论》,六为《诗?联》,七是《附录》。不计楹联和附录,共137篇(首)。我有幸得以先睹,时时为其感动。其文字优美,情真意切,论说雄辩,考证严谨,篇篇体现着作者的“真性情”。文如其人,此言不谬矣! 《鸿爪集》付梓之际,郭鹏亲赴西安,当面把全书清样交给我,嘱我为序,使我颇感吃惊。这部凝聚着他多年心血,有着许多精当见解的著述,对于他本人以及对地方史志有兴趣的读者的意义和价值,自不必说。就我来说,论年龄,郭鹏是我的学长;论资历,他投身地方志工作比我早得多;论成就,必将传世的《汉中地区志》和《佛坪县志》,令我只能望其项背,我何以能为他这部书作序?遂予婉拒。但郭鹏说:“请你作序,在于我们二十年的相交相知,在于你对我工作上的一贯支持和对我本人的了解!”这番话,与当年宝鸡市志办的同志嘱我为《宝鸡市地方志工作文集》作序时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不禁令我大为感动!屈指算来,我从事地方志工作二十年,在这个“艰苦、辛苦、清苦”的阵地上摸爬滚打,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虽无权无势无钱,却也服务了社会、充实了自己,尤其是结交了省内外一批像郭鹏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实乃人生之幸事!因此,郭鹏所嘱,不容推托,遂欣然命笔,写下以上文字,以略表心迹和对《鸿爪集》出版的祝贺! 是为序。 二OO七年二月于西安(注:作者董健桥是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 《鸿爪集》序 马家骏(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丁亥春,我在珠海,见到孤鸿,于是有诗句:“伶仃洋洒雨,孤鸿瘦伶仃”。晚上,西安来电说,郭鹏由汉中给家中打来电话。不几日我回到西安,见有十天前的“特快专递”,取回来一看,原是郭鹏的《鸿爪集》的清样。厚厚的四百多页,它可一点也不瘦,这是个丰满的鸿的厚蹼。于是,就读了起来。 郭鹏,今年退休前是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最近10年来主要从事《汉中地区志》和《汉中年鉴》的主编等工作。他是我“文革”前教过的最后一届大学生。1965年下半年,我给他所在的班讲过《文艺理论》课。次年他们去参加“四清”,夏天回来时校内大革文化命,一团混乱。郭鹏有空就偷着读书,以补充只读了半年大学课程的亏欠。这和那些搞派性、甚至打砸抢的红卫兵迥然不同。他毕业后,分配在秦岭深山的佛坪县工作。但他非常勤恳,踏实读书。他为人诚恳老实,谦虚谨慎,在编辑地方志这种繁琐工作时,认真努力。终于做出了成果。就从全国数十万史志工作者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全国“十杰”来说,便可想而知他的成就了。同时,他还做出了其他的开拓性工作,出版了不少的书籍。我对他的《佛坪县志》、《〈佛国记〉译注》、《寒山诗注释》写过评论。这次,他要出版他的文集,让我写一篇序言,我自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 这部文集是他出版了许多专集之后的一部书,这部书的总的特点是:它异常的丰富。其中有散文随笔、历史研究、地方志研究的成果与心得,有宗教研究的文章,有对别人的书所写的序跋和评论,有他创作的诗词和楹联等等。在附录中,列入了他人写郭鹏的文字,以及郭鹏著作的目录。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这部书包含了郭鹏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他是怎样从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位史志专家的。他的成长过程,很有启发意义。安徒生说过:你只要是个天鹅蛋,就是生在鸭窝了,丑小鸭也会成为飞到高空的美丽天鹅。但是在人类,却需要个人的努力。郭鹏19岁来读陕西师范大学,我从给他当老师到以后我们成为忘年交的好朋友,整整过了40年了。他们六九级三班,做出显著成绩的,他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时代环境,大家是共同的,但是,有无成就,和成就大小,全在个人的努力。我希望从山村走出来的年轻人,都从郭鹏身上受到一些启发。著名女作家肖凤在对我的书评论中曾说:“从您这位学兄的文章中,也认识了您的学生郭鹏,像您这样的先生,必然会教出像他那样有情有义的学生,有了这样的学生,就是做先生的幸福与安慰吧。……”学生的有成就,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出郭鹏的足迹和精神。至于我引他以为自豪,是其次的事了。 《鸿爪集》不仅十分丰富,而且许多地方有自己的创见。诗词楹联属于艺术创作,是个人特色的东西就不必说了。单就书中的史志文章和研究史志的方法论文章而论,就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一家之言。书中不少考据文章,事实确凿,有数字,有照片,有文献做支撑,有的还有实地考察。据此,自然会发前人所不曾发的言论。给人新颖的见解与知识。书中那些史志研究的方法论文章,是郭鹏多年编写县和地区(市)的方志、审查其他地方志的经验积累,是他工作中有独到之处的心得提炼。这对于其他地方志编写人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郭鹏是学文学的,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搞了20多年史志工作,此外他又热衷于佛教文化的研究,从事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行政工作。因此,在郭鹏身上,文史哲三者是综合在一起的,理论与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看问题就会更聪睿深刻;有了历史学家的目光,就会不去空谈,而是凭事实说话;有了文学和诗人的修养,言谈与文字便可以无远弗届。因此,读郭鹏的这本书,读者会思想上受到启发,学识上得到新知,文词欣赏上也是对美文的艺术享受。多年行政领导工作经验,使他在工作运作起来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并不感到特别吃力。 一本文集,是多篇不同文章的集合,自然文章之间会参差不齐,真要挑这本书的毛病,那挑家是不会徒劳的。但我向来的做法是:读一本书只从自己受益方面去多多考虑,注意吸收;而对于那些瑕疵,只要无伤大雅,不涉及原则,就可不必去花费心思劳神了。如果为了再版时修订,读者不妨给作者提出来,这种好事是会受欢迎的。 2007年3月22日于陕西师范大学(注:本文作者马家骏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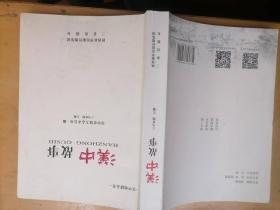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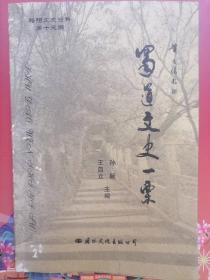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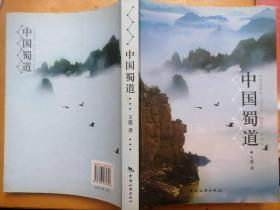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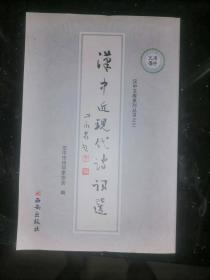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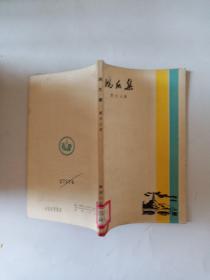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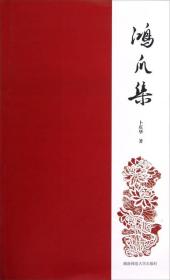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