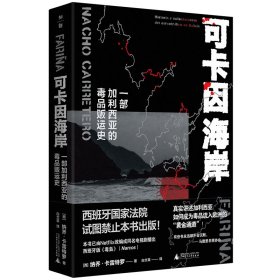
正版✔可卡因海岸:一部加利西亚的毒品贩运史(西班牙国家法院试图禁止本书出版!)纳乔·卡雷特罗,白文革✍本书已由Netflix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西班牙版《毒枭》(Narcos)。一部勇气可嘉的调查记者手记,用电影的方式,真实讲述加利西亚如何成为毒品流入欧洲的“黄金通道”!正版全新书籍现货如需其它图书请联系客服
全新正版书籍,假一罚十,节假日正常发货~专业文史书城,如需其它图书请联系客服
¥ 68.8 7.8折 ¥ 88 全新
库存888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纳乔·卡雷特罗,白文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76241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精装
定价88元
货号3284727
上书时间2024-12-0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编辑推荐】
西班牙国家法院试图禁止本书出版!
本书已由Netflix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
西班牙版《毒枭》(Narcos)。
位居西班牙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首位超1年。
在西班牙累计销售突破150000册。
已翻译成10多种语言,版权售出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家。
真实讲述加利西亚如何成为毒品流入欧洲的“黄金通道”!
在西班牙出版后,本书因直指毒品交易背后的腐败官员而一度被迫下架。书中揭露的庞大的毒品贩运网络、毒品泛滥的严重程度,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作者呈现了一部犯罪题材的动作惊悚大片,试图用电影的方式记录下这一切。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所有的真相,才能阻止毒品瘟疫的蔓延。
【内容简介】
西班牙加利西亚,那里的狂风海岸被罗马人认作世界的尽头,在希腊人眼中,那是卡戎将灵魂运往阴间的地方。自中世纪以来,加利西亚的“死亡海岸”吞没了无数往来船只,而走私也成为当地人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20世纪末,大西洋对岸的毒品涌入,进而蔓延到欧洲。
20世纪90年代,80%的可卡因通过加利西亚海岸登陆欧洲。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加利西亚还拥有成为一个新西西里岛所有的必要条件:落后的经济、走私的传统、大众容忍甚至崇拜罪犯、诡异的政治氛围和社会规则……那里有形形色色的西班牙式毒枭,他们或脚踏木屐,乔装成粗鄙的渔民,或衣着华丽,试图成为“教父”般的人物;那里也有道貌岸然、唯利是图的腐败官员,充斥着暴力及与之相抗的紧张扫毒行动,更不乏一则则由毒品引发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加利西亚为何会变成毒品进入欧洲的门户?通过采访瘾君子、走私犯、犯罪集团头目、缉毒局特工、法官、抗议者、普通老百姓,作者带我们一步步接近让人难以置信的真相。这本书无疑是对毒品在欧洲中心地带肆虐和毒枭暴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记录。
【目录】
引 言
第—章 穿过陆海江河
第二章 烟草时代
第三章 大飞跃
第四章 加利西亚黑手党
第五章 黑帮大佬
第六章 白粉浪潮
第七章 “海蟹行动”
第八章 斗争在继续
第九章 仿效黑手党
第十章 全力出击
第十一章 一代新人换旧人
第十二章 白粉踪迹
【文摘】
穿过陆海江河
那片海:死亡海岸的神秘传奇
学生时代我们曾做过测量计算,但结果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加利西亚居然拥有1498千米的海岸,比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还要长,甚至超过了巴利阿里(Baleares)群岛的总长度。放大之后可以看到,海岸线曲折迷离,它由无数海岬和众多深邃的小港湾组成,可谓是神出鬼没的理想之地。其周遭延绵不断的陆架和岩石,似乎就是专为搁浅船只而设计的。其中有一段海岸,被称为“死亡海岸”(Costa da Morte),而我们的故事即将在死亡海岸展开。
该区域大多数乡村与城镇蜷缩在海岸之内,躲避大西洋狂风之虐,曾几何时,城乡之间互动的形式就是渔夫行会之间的你争我抢。在偏僻的加利西亚,人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口音,令其他西班牙人觉得晦涩难懂。菲尼斯特雷角(Cabo Fisterra)是皇冠上的宝石:在古罗马人眼中,它是世界的尽头;在希腊人眼中,它是冥府渡神穿越冥河的起点;它同时也是基督教卡米诺·德·圣地亚哥(Camino de Santiago)朝圣之路的开端。而对当今的大多数游客而言,它只是一个伸向大西洋的风光旖旎的海角。无独有偶,这里也是一个绝佳的携运走私物品的陡峭海崖。
死亡海岸,北起拉科鲁尼亚市(A Coruña),向西南蜿蜒曲折至菲尼斯特雷以南,这一带的居民一向靠海吃海。除了打鱼和贸易,他们还依赖过往的商船过活。但他们并非总是坐等科尔米(Corme)、拉赫(Laxe)、穆希亚(Muxía)、卡马里尼亚斯(Camariñas)等重要港口的船只送货上门,他们通常会选择突袭抢劫过往船只,或只需密切关注任何可能被冲上岸边的失事船只残骸。
加利西亚到底吞噬了多少船只?要试图弄清楚这一点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单凭”当地人称,自中世纪以来,已经有927起在册的沉船案例。一位名叫拉斐尔·勒迈(Rafael Lema)的研究人员对这些故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并将之汇编成《死亡海岸,梦想与沉船之乡》(
Costa da Morte, un pa
ís de sueños y naufragios
),对其中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进行了收录。
19世纪末,英国商船岩羚羊号(Chamois)在拉赫附近搁浅。当地有传言说,一个渔夫前去援助船员,在靠近失事船只时,他大声呼喊,问船长是否需要帮助。船长以为来人是问这艘船的名字,就回答说“岩羚羊”,结果出现了神奇的语言“短路”:渔夫以为他想说的是这艘船上的货物是牛(bois,加利西亚语的意思是“牛”),于是急匆匆地赶回岸上,并告知了他的乡亲。不消片刻,他们就成群结队、全副武装地乘船出现在了那些浑身湿透、神情惊骇的英国人面前。
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一艘名为普里阿摩斯号(Priam)的商船搁浅,从船上漂到海滩上的金表银表在短短数个小时内就不翼而飞。一架三角钢琴也被冲到了海滩上,当地人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可方物,还误以为是另一个宝箱,于是将之大卸八块来探寻宝物。
流传的所谓孔波斯特拉号(Compostelano)故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沉船事件。该船游刃有余地进入拉赫湾,在即将登陆之际,误打误撞到了卡瓦纳(Cabana)海滩附近的一片沙洲。据说当地人下去查看时,在船上只找到了一只猫,并未发现任何船员的踪迹。
1890年发生了一起无比惨痛的事故,英国的巨蛇号(Serpent)在卡马里尼亚斯附近沉没,500名船员丧生。他们的坟墓就矗立在附近海滩和悬崖之间的英国公墓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多年前,船长号(Captain)曾在菲尼斯特雷遇难,400多人无一生还。
海难的惨状多种多样,溺死人只是其中一种形式。1905年,满载手风琴的巴勒莫号(Palermo)在穆希亚附近遇难。据传,那晚吹向陆上的微风带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般的生物。
1927年,尼尔号(Nil)在卡梅尔(Camelle)附近搁浅,货舱里装满了缝纫机、布匹、地毯和货车零件。船主所做的件事情就是雇用一些当地人来看守货物。但这种做法却被证明是大错特错:未被雇用的当地人蜂拥而至,不消数日,船舱就被洗劫一空。尼尔号还碰巧装运了几箱炼乳。有记载称,当地人之前从未见过炼乳,将其误认为油漆。他们把炼乳带回家,在房子上一阵涂抹,结果被大量苍蝇侵扰。
人们记忆之外的例子还包括西班牙无敌舰队1596年骇人听闻的海难:25艘船沉没,1700多人丧生。当时的报道描绘了为凄惨的画面:数道闪电划过长空,照亮了悲惨的水面景象,那里漂满尸体、船只七零八落、人们在吞噬一切的海浪中哭爹喊娘。
19世纪,复仇者号(Revendal)、爱尔兰胡德号(Irish Hood)和悍狼号(Wolf of Strong)这3艘英国船在死亡海岸沉船,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船上水手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尸体,水手们的命运就此葬送在当地的拾遗者和陆上的海盗手中。这些人的任务就是让船只偏离航道,然后上船洗劫,他们会在悬崖顶位于战略要地的灯塔边点燃火堆或悬挂火把,船只一旦搁浅,他们就划船而来屠杀船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英国人,很快消息就传到了那些海岸。19、20世纪之交,皇后维多利亚·欧珍妮(Victoria Eugenia)的朋友,作家安妮特·米金(Annette Meakin)对这些报道感到惊愕,想出了“死亡海岸”(Coast of Death)这一引人注目的称谓,从此被人们记住。英国报纸很快就开始刊登有关这一可怕地区的文章,而马德里的新闻界也正是从中得知了这个故事,并将“死亡海岸”回译成了加利西亚文——Costa da Morte,对其大肆渲染。威斯敏斯特立即向西班牙发出请求,要求当局采取措施打击“这些海盗黑手党”。
拉斐尔·勒迈指出:“从来就没有什么黑手党。”他认为,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而当地的传说也不过如此:“文献中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存在任何海盗组织有计划地出没并掠夺船只。”尽管沉船的故事众说纷纭,但它们仍然给人一种感觉:几百年来,死亡海岸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就是在那些轻易获得而通常无须偿付的货物基础上形成的。
那片地:狭长的边境带,黑市的肇始
当船只在死亡海岸被抢劫(或据称被抢劫)时,那些内地人就可趁机大捞一把。这一事实不容争辩,也没有那么神秘:从医药到硬通货,从食品到电器,从金属到武器和移民的托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色商品都穿越了那个狭长边境带(a raia seca,干旱地带/边境),也就是所谓的加利西亚和葡萄牙交界区域。
在这些纬度上,葡萄牙—西班牙边界是出了名的分散。两国之间自古存在着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重叠,却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就在19世纪,居住在偏远的维林(Verín)和查韦斯(Chaves)村落之间的一些居民,都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公民,而且也没人把这事放在心上。这种无国籍状态的例子莫过于一个叫作杂居区(Couto Mixto)的地方。
杂居区是一块地处边远的三角形地带,占地27平方千米,那里崇山峻岭,由圣地亚哥(Santiago)、米乌斯(Meaus)和鲁比亚斯(Rubiás)三个村落组成。这一荒凉的地区在中世纪时被称为“谋财害命之地”。同样的地位也被赋予了其他一些地区,它们要么是位于偏僻的边境地带,要么是被瘟疫或战争摧毁的人烟稀少的地区,而后由于释放到那里的囚犯得以重新繁衍。11世纪时,大约1000人在杂居区安顿下来,后来这个地方被当作一个自治区管理。无论是葡萄牙伯爵领地还是加利西亚王国都放弃了对其的任何所有权,这使那里的人民处于被遗忘的边缘。
12世纪初,在加利西亚被莱昂王国(León)和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吞并后,杂居区缺乏身份界定的奇特情形就变得更加明显。自13世纪以来,由于葡萄牙王国和西班牙王国都没有对该地区提出主权要求,那里的居民实际上开始作为独立的国民自行其是: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不缴赋税,免征兵役。鉴于没有关于该地区的正式条约,各方都接受了该地区事实上的自主。这样一来,杂居区也就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处于三不管的状态,羽翼未丰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和葡萄牙财政警卫队(Guarda de Finanzas)之流对其不屑染指。那所谓的将其一分为二的“专线”便成了走私犯的天堂。
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模糊状态一直持续到1864年,那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一项边界协议,作为《里斯本条约》的一部分:所确定的边界为,从米纽河河口(desembocadura del Miño)到瓜迪亚纳(Guadiana)的卡亚河河口(desembocadura del Caya),直穿杂居区中间,不偏不倚。由此宣告了独立长达8个世纪的这个加利西亚版的安道尔的终结,同时也成为鲁道夫·冈萨雷斯·韦洛索(Rodolfo González Veloso)所拍摄电影《拉亚诺斯:后一个自由的加利西亚人》(
Rayanos: los
últimos gallegos ind
ómitos
)的主题。
按照官方的说法,该条约确定的边界,今天仍将西班牙的奥伦塞省(Ourense)与葡萄牙分开。许多家庭被一分为二,但仍有很多人无视这项法令,因涉及财产,一如既往地遵守以往的边界划分。有些地方,乡里乡亲召开年度会议,根据作物需求或已建成的新建筑来决定新的边界。所以,尽管当局强行设置了一个边界,当地人却按照自己的协议行事。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后,边境开始有人把守,当局试图结束迄今为止仍存在的互相渗透,并正式宣布所有货物的进出口都是非法的。牧羊人是被允许未经边境哨所登记而过境的人。有些人,一旦穿过那狭长边境带,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死板的新边界也将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了明显划分。在战后的西班牙,加利西亚等农村地区陷入贫困,而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则相对较高。加利西亚人不仅要在没有药品和汽油的情况下过活,而且还面临食品、电力和机器零件等各种物品的短缺。咖啡和打火机成了奢侈的紧俏货。加利西亚人透过油灯的光向外望去,在不远处就能看到葡萄牙家家户户用电灯泡照明。这是有史以来人们次齐心协力进行走私活动的背景,一种由边界两边地区不平等造成的结果。
那时候人们开始偷运食品、药品、机器、机械零件和武器。偷运货物的人每捆食品要收49比塞塔(peseta),每捆金属或工具要收300比塞塔—这个数目大概是一个普通加利西亚人的月收入。
货物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穿过狭长边境带,部分原因是走私者与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串通。在当地的酒馆里,走私者与警卫队员共饮着一大杯酒,玩着多米诺骨牌游戏,看上去没有丝毫不正常。当局可以从这种安排设置中渔利,这一权宜性的结合一直延续到现在,直至该地区成为烟草和毒品走私的重灾区。
只有在马德里官员访问期间这类活动才会偃旗息鼓。往来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列车开始以正常的速度行驶,而不是以通常每小时15千米便于移交货物的速度运行。马德里官员在附近转悠时,人们会从窗户上取下白色的手帕示警—海岸不再安全。于是人们会消停几天,之后,随着官员们安全返回西班牙首都,当地人便可再次获得葡萄牙人从巴西带来的青霉素,以及咖啡、火腿、腌鳕鱼和食用油。穿越边境的甚至还有英国头巾,专门为加利西亚的奥伦塞和比戈(Vigo)集镇上的名媛淑女装点门面。显而易见,走私非但没有被人唾弃,反而是一种值得尊重,甚至能赢得威望的活动。在加利西亚的战后大萧条时期,走私贩运也成了一种生存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地区成为钨的国际来源地,在德国军备制造中,钨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金属。狭长边境带的专业矿工义无反顾地将钨出售给当时被称为“金发贵族”(los rubios)的纳粹特使,价格一度堪比黄金。二战前,每千克钨价值13比塞塔,但第三帝国的大量需求使其价格飙升至每千克300比塞塔。当时,几十个奥伦塞家族一夜暴富。当地的这种繁荣为加利西亚作家赫克托·卡雷(Héctor Carré)的小说《淘钨热》(Febre)提供了素材:加利西亚边境被描绘成一个黄金国(El Dorado),矿工们争先恐后地淘钨。事实上,在纳粹进入这一地区的同时,坚持反对佛朗哥(Franco)的抵抗斗士也正隐藏在加利西亚的山上;他们从当地人手中购买禁运的葡萄牙物资,从而成为当地人收入的另一个来源。近,人们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兴趣再度高涨,这是因为加利西亚议会和波尔图(Oporto)的旅游学院在携手揭秘钨的走私路线,这可谓是令人拍手称赞的“壮举”,尤其是在加利西亚这样一切都可成为过眼烟云的地方。
那条河:狭长的潮湿地带,走私贩运的雏形
当奥伦塞人用山路运输货物时,蓬特韦德拉(Pontevedra)的人也没闲着,他们走水路,一个叫“狭长的潮湿地带”(a raia mollada)的河口。这是一个几千米宽的地方,由许多小岛和滨海小径组成,在米纽河注入大海的地方形成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边界。
在战后的岁月里,差不多所有有船的人都对走私产生了兴趣。他们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来,装到车上运往内地。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狭长的潮湿地带的走私活动是近代加利西亚所有贩毒活动的雏形,这些初的走私者为走私的基础设施和黑市文化打下了基础,这里后来成为拉丁美洲卡特尔贩毒集团寻找进入欧洲路线时的一个诱人的窗口。你可以想象它在毒枭心目中的样子: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按部就班,而且由来已久,这正是他们要选择的地方。直至今日,加利西亚人仍然是他们愿意选择的商业伙伴。
事情并非总那么像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或者暴力十足,甚至也没有那么伤风败俗。在米纽河下游地区,如同内陆地区一样,战后生活非常困苦,走私活动的出现是对艰难时世的映照。配给制度被强行实施,而各种药品和食品就在几千米外,跨越边境便可获得,走私就成为必然。因此,在《我也是米纽河口的走私者》(
Yo tambi
én fui contrabandista en el estuario del Miño
)一书中,普拉西特莱斯·冈萨雷斯·马丁内斯(Praxíteles González Martínez)用人称向人们举证,由此打开了20世纪40年代通往加利西亚边境地区的窗口。他写道:“人们食不果腹,对边境对面投去艳羡的目光。一箭之遥就是葡萄牙,那里的人们住着白色的房子,开着汽车,用电灯照明。与此同时,我们却用牛油蜡烛挑灯夜读,就连能够认识有自行车的人都算是幸运。”他所描述的这种差别是两群人,一群饥寒交迫,一群乐享着从其非洲殖民地搜刮的战利品。
早有组织地参与走私活动的其实是女人。她们负责看管家畜,在河口小岛上放牧,可轻松地用牛群运输糖、米、油和肥皂等货物。时间久了,她们开始批量运输咖啡、火柴和布匹。迫于回避当局查封的需要,女人们设计了预警系统,首个集体组织的雏形应运而生。
许多加利西亚人之前迫于生计移居到了卡斯提尔和加泰罗尼亚(Cataluña),在那里做季节性的水果采摘员,而走私热潮让他们得以重返家园。不久,男人开始取代女人成为新集体的领袖。随着货物数量的增长,物流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船只和马匹随即被投入了运输的队伍。当时由于肺结核传染病的爆发,青霉素成了摇钱树,供不应求,油水可观。
从一开始,走私者就与国民警卫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些吃官饷的人与普通人一样贫困潦倒,而且几乎总是他们来提出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他们会逮捕个把走私者,并对他们所没收的货物处以价值两倍的罚款。也就是说,如果货物没有什么价值,就能免于罚款。走私者一看到警卫队的身影,就把包裹扔到船外或销毁商品(在那一时期,某些鸡肉走私者会血洗禽鸟)。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20世纪后期,贩毒者从快艇尾部甩掉包裹这一主要形象的前身。
20世纪50年代,情势大改,人们开始走私非必需品。西班牙经济回调,情况已经没那么糟糕,而葡萄牙则进入了萧条期,诸如汽车零件、废金属、铜、锡、电线、橡胶、腌鳕鱼、章鱼、葡萄干和烟草等商品开始双向流转。走私者被称为承运人(freteiros,frete在葡萄牙语中是货运的意思),他们每次代运就能挣到200比塞塔。为了避免误会,同时也为了确保不会上当,那些店老板会在边境上等候。承运人会将货物交到他们手中并换取一枚铝制代币,之后用之兑现。禁运品被社会广泛接受,以至于这些代币在边境两侧的数个城镇都享有货币价值,达到200比塞塔或100埃斯库多(escudo)的程度。众多商家都因收到此物而沾沾自喜,乐不可支。
有时货运的对象是人。由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的殖民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葡萄牙经济开始衰退,大批葡萄牙人都想逃离本国,有些人是因为日复一日的贫困,有些人则是为了逃避征兵。加利西亚的走私者构成了人口贩运新网络的一部分,而米纽河则是该网络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他们收取600比塞塔的人头费,可算是笔可观的横财。
加利西亚人把偷渡者带到河流上游,安置到安全屋,之后再把他们塞进卡车和货车里,运往法国。其中也不乏欺诈案例:有些人冒充走私者,只将偷渡者带到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或巴斯克地区(País Vasco),然后带着钱溜之大吉。撇开这些个案不谈,有报道说偷渡者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患病,这些走私者还会请医生为他们诊治。
起初,贩运人口相对容易,而且节奏也比较稳定,但当官方有所反应时,行动则需精心策划,巧妙安排。偷渡者会被装到空油罐车里、卡车驾驶室后面的休息床下面或是汽车的后备厢里。
有一名参与贩运这些葡萄牙偷渡者的走私者,绰号叫“利托”(Lito)。他记得有一次贩运一个四口之家,那个父亲一路酒不离口。“利托”说:“他吓得不成样子。”那人来到船头走到“利托”跟前,问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是否必须脱帽行礼。“利托”记得那人用葡萄牙语掺杂着加利西亚语唱了一首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起舞翩翩,我们砍掉了萨拉萨尔的头颅,割掉了佛朗哥的蛋蛋”(Bailemos xuntos, sobre as ondiñas do mar, para lhe cortar os collóns a Franco e a cabeza a Salazar)。一度,他狗啃地似的栽到了泥地中。那次贩运让“利托”大伤脑筋。
走私网络蓬勃发展,向新的地区一路蔓延,从河口向上移动,直插比戈和葡萄牙北部之间的陆路过境点。废金属成为主要商品;起初尚可相当公开地贩运,但同样的,一旦官方警惕性提高,走私者也要相应优化他们的把戏。例如,跃跃欲试的比戈青年男子会用废金属做成马甲,穿在外套里面,用轮胎橡胶做护腿。普拉西特莱斯·冈萨雷斯·马丁内斯描绘了一幅当时年轻人的画面:胸前和后背携带着10多千克,腿上又带了20千克,吃力地在比戈的街道上缓缓举步—“像机器人一样,但动作迟缓”。巴士有时会在接近边境时抛锚,司机则一脸懵圈,根本不知道是因为有那么多乘客携带了40多千克的禁运品。
对于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或葡萄牙卫队来说,在米纽浅滩(Baixo Miño)设置一个哨所要远远好过中什么彩票。有故事说,一个年轻的葡萄牙官员被派往了加利西亚边境,他的父亲也曾就职于同一个岗位,而且为人颇为正直,曾设法回避了与走私者的所有联系。这让西葡双方都很尴尬。当儿子来上任时,他父亲之前的赫赫名声,让他颇为忧虑,他担心那些走私者会认为他和他父亲是一路货色。也就是说,他所担心的是得不到自己的那份好处。这位年轻人上任的天就迎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边境的村镇,让黑市商人确信无疑,他跟他父亲完全是两回事。他像所有人一样爱钱爱富,而且他有意从中捞上一把。
【媒体评论】
一个没人讲述过的西班牙故事,一部独特的、“小说式”的纪实作品,但要注意的是,里边记录一切都是真的!
——罗伯托·萨维亚诺,《蛾摩拉:一位意大利反黑记者的卧底人生》作者(Roberto Saviano, author of
Gomorrah: Italy’s Other Mafia
)
这本书为哥伦比亚那些臭名昭著的毒枭的“传奇故事”增添了更多戏剧性内容——揭露了他们的腐蚀性影响远远超出了卡利和麦德林的总部。勇敢的调查记者纳乔·卡雷特罗将这段历史写成了一部动作惊悚大片,书里面充满了耐人寻味的人物。
——威廉·C.伦佩尔,《在魔鬼的餐桌上》作者(William C. Rempel, author of
At the Devil’s Table
)
正如加利西亚海岸已成为一种致命毒物进入欧洲的大门,这本精彩绝伦的书也成为理解欧洲大陆历史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切入点,而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忽视了这一方面。
——诺曼·奥勒,《闪电战:纳粹德国的毒品》作者(Norman Ohler, author of
Blitzed: Drugs in Nazi Germany
)
有些书永远都不会沉默。
——马德里书商协会(Booksellers Guild of Madrid)
【作者简介】
纳乔·卡雷特罗(Nacho Carretero),1981年出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调查记者,也在《世界报》(El Mundo)、《西班牙人》(El Español)等知名西语媒体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西班牙、卢旺达、叙利亚、菲律宾等多个国家。2015年出版《可卡因海岸》,该作品已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
白文革,毕业于河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多年从事英语翻译、审校及教学培训工作,翻译图书30多部,包括《汗血宝马》(Under Heaven)、《战士》(Warriors)、刘震云小说《塔铺》(Ta Pu)等,翻译作品曾多次获奖。
【前言】
引 言
西葡边境(a raia)的老辈人还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老头每天都骑着自行车越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加利西亚(Galicia)边境,肩上总是挎着一个袋子。每次,边防军都会拦住他,问他袋子里装的是什么。老头总是很随和,打开袋子让他们自己找找看,并且叽叽喳喳地说道:“就是煤块。” 边防军虽然很恼火,但还是让他过了境。在另一边也是同样的场景:葡萄牙边防军,当地称他们为卫队(guardinhas),也会先搜查他的袋子,然后才允许他骑车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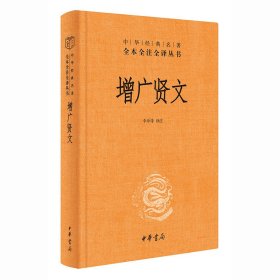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