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击者
全新正版图书 可以开电子发票 有需要的联系客服!
¥ 15.13 3.4折 ¥ 45 全新
库存15件
作者香无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ISBN9787549630301
出版时间2020-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28528552
上书时间2025-01-0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修剪玫瑰的少女、十年一次的流星、死去后的第七天……少年和少女将性命托付于刀尖,在心底为爱人铸了孤坟。人生仿佛一无所有,前程是黑暗连续着的黑暗。
爱和恨意的火花交织着不断迸发,善念与恶毒行走在人间。一个个诡谲的处境,一次次以身探险,情感是深沉而且内敛的,说不出口的爱意从眼角眉梢流淌而出,拥抱的动作仿佛只为了隐藏各怀鬼胎的神情。为了你,我可以杀人,可以救人,我可以为了我自己杀掉你,还可以为了你杀掉我自己。
真相并不重要,甚至在揭露的那一刻让人想要再次掩盖它们。
我们都如此孤独,像浩瀚宇宙的尘埃,追逐光明,旋转在阳光之下。
人生残酷,甚至希望可以一生活在谎言之中,真相揭露的时候,死亡、危机已如影随形。
作者简介香无,原名王立,80后新锐悬疑作家、编剧,善于刻画爱情与人性的罪恶。
至今已发表作品百万字,并凭借《往生刑》《塌方》等短篇悬疑推理小说多次入选《中国悬疑小说精选》《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其中,《塌方》系第二届燧石文学奖“悬疑类•中短篇小说”入围作品。
2016年,短篇小说《往生刑》被改编为同名爱情悬疑电影,葛布主演。
2018年,短篇小说《有求必应》作为原著故事之一,被当年高分网络电影《天方异谈》进行改编,并由著名悬疑作家周浩晖导演。
目录罪人 1
目击者 44
画中人 81
往生刑 113
眸色 154
囚徒 217
情人 250
内容摘要修剪玫瑰的少女、十年一次的流星、死去后的第七天……少年和少女将性命托付于刀尖,在心底为爱人铸了孤坟。人生仿佛一无所有,前程是黑暗连续着的黑暗。
爱和恨意的火花交织着不断迸发,善念与恶毒行走在人间。一个个诡谲的处境,一次次以身探险,情感是深沉而且内敛的,说不出口的爱意从眼角眉梢流淌而出,拥抱的动作仿佛只为了隐藏各怀鬼胎的神情。为了你,我可以杀人,可以救人,我可以为了我自己杀掉你,还可以为了你杀掉我自己。
真相并不重要,甚至在揭露的那一刻让人想要再次掩盖它们。
我们都如此孤独,像浩瀚宇宙的尘埃,追逐光明,旋转在阳光之下。
人生残酷,甚至希望可以一生活在谎言之中,真相揭露的时候,死亡、危机已如影随形。
主编推荐香无,原名王立,80后新锐悬疑作家、编剧,善于刻画爱情与人性的罪恶。
至今已发表作品百万字,并凭借《往生刑》《塌方》等短篇悬疑推理小说多次入选《中国悬疑小说精选》《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其中,《塌方》系第二届燧石文学奖“悬疑类•中短篇小说”入围作品。
2016年,短篇小说《往生刑》被改编为同名爱情悬疑电影,葛布主演。
2018年,短篇小说《有求必应》作为原著故事之一,被当年高分网络电影《天方异谈》进行改编,并由著名悬疑作家周浩晖导演。
精彩内容罪人
起·爱之绊
当我赶到医院时,黄怡然已经不行了。原本就单薄的身子如今更显得无力,整个人像失了所有颜色一样变得苍白。
医生说她中了七刀,和她的父亲一样。不同的是只有后一刀才扎在了致命的地方。而她竟然还拼着后一口气,给我打了告别的电话。
我握着她垂在床单外的手,医生们推着她的病床急匆匆地往急救室里赶,头顶的白炽灯亮得我眼花。她已经有些神志模糊了,却还努力看着我的方向,瞳孔扩散,无法聚焦。
她的手很凉,那是曾经舞动于花瓣中的手,是我无数次碰触过的手,是我千百次凝视过的手,可今天这一切就要消失了。
我一直陪着她跑到了急救室门口,医生狠命拦住了我,她的手指从我手里滑落。我分明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在对我说话,急忙拉住了病床,俯下身,跪在她旁边。她拼命喘息着,像要耗尽生命一样对我开口:“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这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让我之后每每想起,都心如刀绞。
一·雾中谜
清早刚一到队,我就被队长连拖带拽地弄上了车,手忙脚乱地整理着的资料、随身的小本、在学校里被千叮咛万嘱咐要记得带上的手套,还有证物袋。老王把车开得飞快,警笛声啊呜啊呜地鸣响而过,这座城市还在浓厚的湿雾里沉睡着。
“景阳区,死者是男性,被人发现时已经断了气。喏,这是现阶段收集到的资料。”
队长简单给我说了下报案人提供的线索后,递给我个蓝皮的本子。我的睡意瞬间被这个消息赶跑了。
队长比我大二十来岁,是队里资历老、经验丰富、破案数量也多的刑警。他本来就是科班出身,在学校的成绩一直被教官们津津乐道、标榜至今,后来一毕业就进了刑警队,干得风生水起。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据说就会令辖区内的罪犯们闻风丧胆。他有一个老婆和一对现在上大学的双胞胎儿子,家庭幸福美满。
“听说你又拒了上面来的调令?”
老王开着车,对后视镜里的队长发问。队长“嗯”了声,皱着眉一直盯着窗外,像是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我一来这个地方就听说了,其实队长早年跟别人炒股投过资,后来赔大了,被降了职,才到了我们这一片。后来因为考绩高,上面跟他提过好几次,可以升迁离开,但不知为什么,队长却一直拒绝此类的人事调动,坚持留守在我们这个片区。
“队长在这个片区多少年了?”
“十二。”他漫不经心地回了我一句。
老王吹了个口哨,笑起来。
“要是我像你这么能干,早拍拍屁股走了,何苦还跟这些小年轻天天东奔西走地查案子。”
“嗯……习惯了吧,你让我去做别的事我也做不来。”
队长耸耸肩,没说更多的话。我和队长不一样。我刚从警校毕业,能分配到这个地方,一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二也靠了点老师的人脉。绝不是因为从小就抱有什么拯救世界的梦想,而是我觉得除了身体健壮外,自己一无是处,所以不得已才进了刑警队。好歹是公务员行列,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等到了年纪就自动退休,清清闲闲地过一辈子。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走马上任的天,就遇到了杀人案。
景阳区离我们警局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还是清晨,堵车的盛况还没开始,所以到的比预计时间更早了些。现场已经被先去的同事们用黄色警戒线围了起来。队长带着我跨过警戒线进去,看见地上趴着个男人的尸体,身下的血迹已经干涸了,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的,脸侧贴在地面上,双目圆瞪,他的手指弯曲着朝前方伸出,肌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十分僵硬。
尽管在学校里已经见过多次这样的模拟场景,可当真正面对死人时,我还是止不住一阵头晕目眩,盯着那具尸体半天挪不开视线,双腿一个劲地打着颤。如果不是身后还有同事,我可能已经跌坐到了地上。
好在队长并没责怪我的失态,准确地说,他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他长久地伫立在尸体跟前,皱着眉,脸色有些微微发白。过了会儿,他似乎瞥到我,嘴角不自然地动了动,这才回过神,走到尸体跟前蹲下来,取出手帕捂着鼻子,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熟练地轻轻翻弄了下尸体,似乎想从口袋里找出点新的线索。此时,身后传来法医的呼喊声,他抬起头赶紧离开了尸体,举起手连连说着抱歉。仔细听完法医的描述后,老王吩咐我去找现场的人打听打听死者的事情。
我用快的速度离开了那具散发着腐败气味的尸体,并不是害怕尸体本身,只是不愿去接触某些即将查清的事实。
围观的人大多上了年纪。他们清晨赶早出去买菜锻炼,可没想到一回来就看见了这么不得了的事情。我掏出纸笔询问了几个还围在那里的老人。
据他们说,死者姓黄,就住在附近的居民楼里,家里还有个上高中的女儿。我敏锐地发现,没有任何人对他的死表示痛心,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在调查中,我发现了一个似乎知道不少事情的老太太。可不管我怎么询问,她一直言语支吾,不肯跟我说实话,等被我问急了,拎着菜篮子转身就走,边走边对我挥手,像赶苍蝇似的。
“有什么好问的,这种人死了就死了,真是!”
我不死心,一直跟着她追到了巷口。她终于停下来,看着周围没人,叹了口气,摇摇头,有些不满地瞪着我。
“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人,我说你们有什么好查的。”
我愣了愣,赶紧抓着她继续深究下去。
“能说说具体的吗?为什么说他不是人?”
“这男人的秉性我比谁都清楚,我就住在他家楼下,一喝醉酒了就那声音——哎哟。”
老太太的头摇得更厉害,一口接着一口地叹着气。我微微感到有些失望,在本子上写了“邻里矛盾”几个字后,又接着追问下去。
“那您知道谁有可能杀了他吗?比如仇人什么的。”
“仇人?”老太太冷笑一声,“他这种人周围全是仇人。”
“什么意思?”
“这男人嗜酒如命,天天出去鬼混,喝了酒回来就闹得整个大院鸡犬不宁。原来有老婆的时候就打老婆,那么粗的条凳都被他给打断了。可怜的就是他女儿,经常被他打得满院跑。原来他老婆还在的时候情况稍微好点,至少有个人能护着。等他老婆失踪之后,这家伙就变本加厉了。大冬天的也不给他女儿厚衣服穿,还赶着她出来买酒。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又叫又骂的。经常不给学费,整天把女儿关在家里面不让出去。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看着那姑娘可怜,偷偷给她送点吃的,被发现了,她又会挨一顿毒打。就前几天,那姑娘的手臂上又多了块疤。”老太太又叹了口气,使劲地摇着头,“这种人死了才好,活着就是造孽。”
我将听到的悉数记下来,老太太探头看着我的本子,又补充了几句:“你们这些警察,也别费那么大劲去查明犯人。要我说,这种人死了就死了,活该!”
“老太太,这不行,我们是警察。”
我本还想说什么,可那老太太似乎不想再说下去,转身蹒跚离开了。我在本子上把听到的事情全写了下来,回到现场将调查结果报告给了队长。尸体已经被运走了,地上突兀地用白笔画了个轮廓。队长擦着手,告诉我:“死者一共被人砍了七刀,初步死因是失血过多。”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有那么深的仇恨呢?我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又浮现出了老太太说的话,便向队长申请去询问死者的女儿。按照规定,我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前往。可队长认为这是个锻炼的好机会,便命令我一个人解决证词问题。接着,队长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没头没脑地吐出一句话:“别牵扯太深。”
回到家后,我一直想着队长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让我不要对这个案子牵扯太深呢,还是别的什么?
二·花溅泪
第二天我在去见女孩之前,买了束白色的菊花带着。我自以为是地觉得就算父女俩感情再差,应该还是血浓于水。
可在我见到女孩的眼,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她的脸上根本没有流露出半分伤感。
他们的房子隐藏在整个居民区后,背阳,位置很差,冬天潮湿、夏天蚊虫肆虐,所以价格也是便宜的。
他们住在六楼,隔壁是间空房子。
我敲了几声门,过了会儿,里面传来声很轻声的回应。我按照程序,将证件放在猫眼上,等那女孩检验。可没想到,她连问是谁的兴趣都没有,“哗啦”一下把门拉开,扑鼻而来的是门内那股浓郁的酒精味。受害者的女儿就站在我面前,穿着白色的背心和一双淡黄的拖鞋,直勾勾地盯着我,面无表情。
“请问是黄书明家吗?”
我和她对视了半晌,忽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赶紧开口打破了僵局。她点点头,侧身让我进去。
房间里很空,地上散落着废旧报纸和空酒瓶,似乎全被一种衰败的颜色围绕着,充斥着颓废的气息。
女孩让我坐在椅子上,不知从哪里摸出个老旧的搪瓷杯子,给我倒了杯水,紧接着,她随意地抓过一边的小木凳,坐在了我的面前。
我四处打量了下,这个屋子藏不了任何秘密。
“请问,你就是黄书明女儿?”
“是。”
那是我次听见黄怡然的声音。她的声音很细小,和她文文弱弱的外形很搭。海藻似的长发垂到了腰间,没有任何造型,显得有些蓬松,泛出病态的干枯的黄色。
她的脸很白,小小的,下巴很尖,嘴唇很薄,上下两片抿在一起,失了血色——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她的手腕细得像根筷子,我悄悄比了下,感觉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将它们折断。大夏天的,她还穿得比较厚,长衣长袖,加上一双白色的棉袜。
“你父亲的事情——我很抱歉,请节哀顺变。”
“没什么,死了就死了呗。”她顿了顿,“反正我没钱烧他,如果你们警察不弄,就随便丢给医院当教学道具好了。”
我被她话中的冷漠给骇住,一时不知如何反应,嗓子烧得慌,只能不断地喝着已经变凉的白水。长久的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用一种极度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也许还混合着一丝嘲笑。可就在她瞥见我放在一边的花时,眼睛忽然亮了。
“这花,给我的?”
她身体前倾,手指轻轻在花瓣上抚摸了下,又很快缩回去。
“啊,是。”
我有些恼怒被她牵制的感觉,赶紧把花递了过去。她起初不接,只是很小心地埋下头,在花束里深深地闻了闻,用一种几不可闻的声音开口:“真香,我们家很久没有这种味道了。”
紧接着,她的嘴角露出了个淡淡的微笑,可惜一瞬即逝。我的手一直停在半空,她抬起眼盯着我,跟我用眼神再三确定,这才带着莫名的欣喜表情,将花接了过去,拿在手中。我盯着她长时间留恋在花瓣上的纤细手指,继续自己的问题。
“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你,是关于你爸爸的。”
“你问吧。”
她对我的问题毫无兴趣,仿佛注意力都放在了那束花上,时不时低头去嗅一下花香,再带着满足的神色抬起脸。
可她的眼神一直是冰凉的。
“你的姓名?”
“黄怡然。”
“年龄?”
“十七岁。”
“家里除了你和你父亲,还有什么人?”
“原来有个妈妈,后来就没了。”
“我听人说是失踪了?”
“不,被那个人杀掉了。”
我一顿,笔尖在纸张上戳出个不小的墨点。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面容依旧安静,甚至可以说是麻木。她微笑着用指尖挑逗花瓣,微微歪着头。没有刻意修剪的刘海,几缕杂乱的头发随意散落在她的肩膀上,仿佛对刚才的这些对话不屑一顾。
“是……哪个人?”
刚问出这个问题,我就后悔了。因为黄怡然终于把头抬了起来,直勾勾地看了我半晌。那些因为花瓣才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笑容被她很快收藏起来。紧接着,她用一种近似嘲讽的语调“哼”了声,嘴角一翘,咬着牙吐出一个名字:“黄书明。”
我的笔尖抖了抖,在纸上落下个难看的墨点。她一停,那副状若平静的面容下隐藏着某种暗涌。我发现她的手指紧紧握住了花束。过了会儿,她绷紧的脸忽然一松,露出个神秘的笑容对我开口:“说不定啊,那尸体就被那人藏在这个家的某个地方呐。”
那天我没有问出太多有用的东西,就落荒而逃地离开了。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无数凶杀、仇恨、人与人之间难言的龌龊和愤懑,我甚至比一般的人了解得更深。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环境才会造就出黄怡然这样的女孩,可以一边欣赏那束平淡无奇的小花,一边带着冷漠的表情坐在警察面前,面不改色地告诉对方:自己刚被人谋杀了的父亲,在许多年前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将查案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队长,同时申请退出这个案件。见过黄怡然之后,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隐隐作响,吵得整个大脑在闷闷地发痛。
就在我陈述的过程中,队长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报纸,可我知道他在用心听我说话,因为他的视线长久地停留在某一个区间,没有挪动半点。一直等我说完了,他才放下报纸喝了口茶,丢出一个新命令:“明天继续。还有,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你先给我放在一边,先把眼下的事情做好。”
“您的意思是不查死者妻子的事了?”
“这么多的案子,如果不一件件来做,你怎么能确保这不会成为另一个悬案?”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他换了条腿搭着,推了推滑下鼻梁的眼镜,撩起眼瞥着我。
“记住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这种事情以后多得是。等你把眼下这个案子破了,再想别的事情。”
言外之意,我不做还有大把人等着替补上位。我无力跟他辩驳什么。队长对于我而言,一直像是个老师。也许是出于对前辈的敬畏,我没有回应,只是立正对队长敬了个礼,转身准备离开。可就在那时,他忽然又叫住了我,丢给我一张照片,是当时拍的尸体的照片。
“看看,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将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次,摇摇头。尸体的姿势、证物的摆放,甚至连那天早上稀薄的阳光的角度都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报告,我没有发现问题。”
队长从眼镜的上半部分盯着我看了会儿,摇摇头,对我挥挥手。
“拿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
他并没有提示我的打算。我苦恼地回了家,把事情记录下来,将照片贴在分析用的白板上,倒头睡在床上。
黄怡然那双空洞的眼睛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等我闭上眼睛仔细回想时才发现:她其实是个很美的姑娘。
三·心成灰
第二天,我故意等到放学的时间才硬着头皮再次去了黄家。原本计划着还要在门口蹲一会儿,黄怡然才回来,可没想到我刚上楼,门就自动开了,黄怡然木然地站在屋内盯着我。
“我刚才从窗户上看到你了。”
“你逃课?”
“我被退学了。”
“为什么?”
“没钱交学费。”
她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侧开身,放我进了屋。我发现这个女孩永远有让我错愕不及的能力。
“我想跟你谈谈你父亲,还有你昨天说的事情。”
她点点头,照例给我端来一杯水。我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很凉。她却像被火灼了似的,惊吓地往后退了一步。而后,她似乎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尴尬地低下脸,避开我的眼睛,仿佛用了很大力气才抑止住尖叫的欲望,兀自坐在一边的小凳上。
“我没亲眼看到他杀我妈,反正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已经不见了。他说我妈永远不会回来了。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妈妈死了。”
“你怎么能确定?”
“我当然确定。他说要杀我妈和我,说了不止一次。我妈被他打得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估计那天就是手重点,敲在了头上之类的地方。”
“那就是说,你没见着你母亲的尸体?”
“我说了我妈一定死了!你是不是不信我?”
她忽然有些激动,站起身,气呼呼地瞪着我。
“你不信就算了,反正——”她猛地一顿,像是想起什么一样,脸上露出个自嘲的微笑,“反正你们警察都是一个样子。”
我被她的反应刺激了下,咬咬牙,示意她坐回去。
“我不是不信你,我只是想问清楚。那时候你多大?”
“小学。”
“小学——”我心里有些难受,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废话,“你一定很想念她?”
“是挺想的,她在的时候那家伙主要打她,她不见了就开始打我了。”
她的表情又重回木然。夕阳照进窗户,几缕光线似乎无力地在她身后摇曳。她的脸一直背光,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可她的声音迫使我相信,她的内心就是这样想的。我用很大的定力强迫自己不被她的话干扰,继续问下去。
“跟我说说你的父亲,你知道他有什么仇家之类的吗?比如钱或者——”我斟酌了下字句,“感情方面的。”
“有,他外面有女人,那些女人一出现,就会打我,她们骂我是拖油瓶。”
她用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语调陈述着这个事实,双手放在膝盖上,轻轻绞在一起。房间里的酒精味淡了些,地上还是凌乱地堆积着杂物。她安静地坐着,等着我的下一个问题。我忽然觉得,也许在很久以前,这个女孩的灵魂就已经死了。
“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不知道,反正都是他随便找的,陪他玩两天,骗走他的钱就开溜,谁会真的想留在他身边?”她自嘲地笑了笑,“谁会和那个女人一样那么傻,还给他生孩子。”
“你说……你的母亲?”
“如果她当初不生下我就好了。”黄怡然幽幽地说道。我浑身一个激灵,透心的凉意从脚底侵袭了心脏。
“你知道——”我斟酌字句,“父亲”这样的词似乎并不适合出现在这样的场景里,“死者近有没有和人发生过争执?”
黄怡然歪了歪头,盯着我。
“为什么要换称呼?”
“只是觉得——不大合适。”
“不大——合适吗?不大合适……不大合适……”
她的眉心动了动,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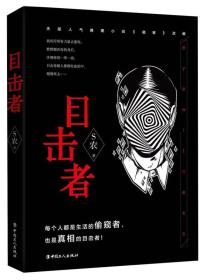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