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者·文学)眼泪
批量上传,套装书可能不全,下单前咨询在线客服!有特殊要求,下单前请咨询客服!
¥ 43.67 6.7折 ¥ 65 全新
库存15件
作者(法)帕斯卡·基尼亚尔 著,王明睿 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244643
出版时间2022-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5元
货号29409181
上书时间2024-11-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842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洛泰尔签署了份法语文本《斯特拉斯堡誓言》。作者从这段历史挖掘素材,描写了查理大帝的两个孙子、私生的王子——孪生兄弟尼哈与哈尼截然相反的命运。哥哥尼哈是秃头查理的史官,是签署誓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人生高光,是成为个用法语书写的人,是担任法语的接生婆。弟弟哈尼则只身一人策马而去,如同这个世界的幽灵一般寻找着一张女性面孔。这张面孔的主人是世间万物的母亲,哈尼想找到她,进而找到自己的源头。哥哥尼哈见证了法语文明的诞生,弟弟哈尼则想找到孕育这种文明的母亲。书名“眼泪”,既代表了法语诞生时令人激动不已的场景,也蕴含着哈尼意欲寻找文明之源而不得的悲伤。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法国文评人奖、法国文化大奖得主,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少年时期曾患自闭症,这对他日后的创作生涯影响重大。其作品以形式碎片化、内容杂糅、思想深邃为特征,代表作有《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符腾堡的沙龙》《秘密生活》等。
【译者简介】
王明睿,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比较文学。译有《音乐课》《距骨》《自杀》等。
目录译 序 001
Ⅰ(蓝莓男子书)
- 马的故事003
- 哈古斯遇上的故事006
- 八音盒009
- 尼哈出世011
- 尼哈的受孕013
- 恋爱中的哈尼016
- 弗拉特·卢修斯019
- 安吉尔伯特修缮过的修道院021
- 大厅里的沐浴场景025
- 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尔·加菲奇战败027
- 阿弗尔河畔维尔内伊的主教会议030
- 被称作“熊之日”的那天033
- 索姆之源035
- 面孔039
Ⅱ(心意难测书)
- 秘密房间043
- 名叫赫德比的猎犬045
- 奥德的女仆047
- 浆果王053
- 敲钟人雨格留在墙上的斑点054
- 圣里基耶之影的来源057
- 圣女维络尼卡在芒通港湾现身060
- 卢维埃的路062
- 默不作声的德欧特莱德转过身,看见了
贝尔特和海滨公爵063
- 关于我们奇迹般的生命064
- 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欣快066
- 瘦瘦的068
- 圣人奥古斯丁的爱情讲道070
Ⅲ(欧洲始于何处?)
- 比利牛斯山口075
- 生育女神077
- 哈尼的爱恋078
- 关于柏勒罗丰王子082
- 蒂格雷河上的灯笼083
- 女眷马车的左侧车轮下085
- 塞壬之歌089
- 关于爱情的脸颊、耳朵和丝绸090
- 捕鱼的鸟092
- 永别了,利姆尼的牝马095
- 塞涅卡之圈098
- 荒野的阵阵声响104
- 卢修斯神父与画像107
- 格兰达洛的阿丽拉111
- 欧洲始于何处?114
- 卢修斯之痛115
Ⅳ(安吉尔伯特诗歌书)
- 达戈贝尔王的三条狗119
- 红布121
- 圣里基耶修道院的起源122
- 挂外套的圣人弗洛朗125
- 雪中的埃皮奈别墅127
- 罗特鲁德129
- 恶131
- 安吉尔伯特的诗133
Ⅴ(罗马历元月十六书)
- 法兰克人的王国139
- 国王的阿尔卑斯山之旅141
- 皇帝的加冕143
- 查理曼之死145
- 历史学家尼哈146
- 丰特努瓦战役148
- 《阿让塔利亚誓言》150
- 《斯特拉斯堡誓言》153
- 不会有任何援助156
- 在暴风雪中出发158
Ⅵ(尼哈离世书)
- 尼哈敏感退隐163
- 尼哈的遗嘱165
- 尼哈之死167
- 萨尔的眼泪169
- 萨尔与哈尼171
- 捕鸟者费尼西亚努的故事173
- 费尼西亚努的教导174
- 爱的奇遇179
- 哈尼在巴格达183
- 乔纳德·勒·苏费185
Ⅶ(圣女欧拉丽继抒咏)
- 她化作一只白鸽飞走了189
- 法国文学的诞生190
- 圣女欧拉丽的生平194
- 圣里基耶修道院的火灾198
- 连着两座城堡的中堂200
- 孩子勒·利梅伊的故事201
- 一只乌鸦的来源204
- 壳状地衣206
- 黑色枯木上的盘菌209
Ⅷ(伊甸园书)
- 夏娃的花园213
- 奥伊塞尔岛214
- 大海216
- 阴郁的山谷221
- 卢修斯神父消失了223
- 母亲的碎块224
- 哈尼听见了死者的笑声227
Ⅸ(诗人维吉尔书)
- 维吉尔239
- 库迈的鸟栏242
- 经桌旁的圣徒约翰243
- 页面247
- 马249
- 死于卢瓦尔河252
- 天空253
- 济韦港口255
Ⅹ(师长书)
- 李义山261
- 捕鸟264
- 往日的雪266
- 费努之死267
- 哈尼之死270
- 弗拉特·卢修斯273
- 色萨利的卢修斯279
- 猫头鹰280
内容摘要842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洛泰尔签署了份法语文本《斯特拉斯堡誓言》。作者从这段历史挖掘素材,描写了查理大帝的两个孙子、私生的王子——孪生兄弟尼哈与哈尼截然相反的命运。哥哥尼哈是秃头查理的史官,是签署誓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人生高光,是成为个用法语书写的人,是担任法语的接生婆。弟弟哈尼则只身一人策马而去,如同这个世界的幽灵一般寻找着一张女性面孔。这张面孔的主人是世间万物的母亲,哈尼想找到她,进而找到自己的源头。哥哥尼哈见证了法语文明的诞生,弟弟哈尼则想找到孕育这种文明的母亲。书名“眼泪”,既代表了法语诞生时令人激动不已的场景,也蕴含着哈尼意欲寻找文明之源而不得的悲伤。
主编推荐【作者简介】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法国文评人奖、法国文化大奖得主,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少年时期曾患自闭症,这对他日后的创作生涯影响重大。其作品以形式碎片化、内容杂糅、思想深邃为特征,代表作有《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符腾堡的沙龙》《秘密生活》等。
【译者简介】
王明睿,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比较文学。译有《音乐课》《距骨》《自杀》等。
精彩内容Ⅰ(蓝莓男子书)
- 马的故事
从前,马儿们是自由的。它们驰骋在大地上,没有人想要得到它们、圈住它们,把它们集成队列、给它们套上绳索、给它们设下陷阱、把它们套在战车上,给它们安上马具、装上马鞍、钉上铁蹄,骑上它们、牺牲它们、吃掉它们。有时候,人们和动物一同歌唱。一方的长久呻吟引起另一方的奇异嘶鸣。鸟儿们从天而降,来啄食残食。残食落在马儿的四条腿之间,它们正抖动着自己华美的鬃毛。残食落在人们的大腿之间,他们仰着头,席地而坐,围着篝火,吃得狼吞虎咽,吃得咋咋作响,大快朵颐,突然有节奏地拍起手来。当篝火熄灭,当歌声不再,人们站起身来。因为人们不似马儿一般站着睡觉。他们擦去阴囊和阳器被放在地上时留下的痕迹。他们重又跨上马,骑行在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骑行在大海潮湿的岸边,骑行在低矮的原始森林里,骑行在时常刮风的旷野,骑行在大草原上。一天,一个年轻人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我来自一个女人的身体,我重又面对着死亡。我的灵魂在夜里于何处消失?它去了哪一个世界?有一张我从未见过的面孔,它困扰着我。为何我又见到了它,这张自己并不认识的面孔?”
他踏马而去,只身一人。
突然,正当他在白昼里奔驰,天黑了。
他俯下身。他惊恐地抚摸着马儿脖子上的鬃毛,还有它温热又颤抖的皮肤。
可天空变得漆黑一片。
骑手拉着缰绳上的铜链。他下了马。他在地上铺开一条毯子,毯子由三张紧紧交织的驯鹿皮制成。他系起毯子的四个角,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保护马儿的脸。他们重新上路了。
空气纹丝不动。
忽然,雨水压将过来。
他们缓慢前行,在嘈杂声和雷鸣般的雨水里,用眼睛寻找道路。
他们来到一座山丘。雨停了。黑暗里,有三个男人被绑在树枝上。
中间的,是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额头上有一顶带刺的王冠,他在嘶吼。
奇怪的是,另一个男人在用灯芯草的朝他嘴边递去一块鹿蹄。与此同时,在他身旁,一个士兵正将长枪刺进他的心脏。
- 哈古斯遇上的故事
后来,过了几百年,有一天,夜幕降临,他独自行走,用笼头牵着身后的马儿来到索姆河岸。幽暗开始笼罩河水,他停下了。
男子发现在一堆板岩上有一只死去的松鸦。
离静静的河水约有十米远。
那里有一棵桤木。
那堆松松的、灰灰的岩石板沐浴着夕阳,上面躺着一只松鸦,展开宽大的翅膀,张着嘴。
马儿喷着鼻息。男子抚摸着遮盖了它脊柱的又长又厚的毛发。
哈古斯是这条河的摆渡人,他把船系在大桤木的树干上。他朝困惑的骑手和僵化的马儿走来,待在他们身旁。他把船篙靠着自己的肩,将自己的目光融进他们的目光。
因为这只死去的松鸦身上有些许古怪。
于是哈古斯鼓足勇气,走向那只长有蓝色翅膀的鸟。
可他几乎立刻就定住了,因为松鸦正在有节奏地扇动蓝黑相间的羽毛。他喘着气,向后转了转身子。他的动作是这样的:有时朝向河岸、小船、桤木的叶子与河水,有时朝向蓟草、被自己的所见吓得动弹不得的骑手,以及一动不动、惶惶不安的马儿。
实际上,松鸦在向后一抹阳光的温热献出自己的彩色羽毛。
它在晒羽毛。
随后,不到一秒钟,它迅速旋转,立起爪子站起身,一下就飞了起来,栖息在河岸摆渡人的船篙。
哈古斯顿时在自己的肩上感到,他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把头朝鸟儿转过去,它在看着他,发出可怕的叫声,又转向骑手,但是身旁已空无一人。骑手和马儿走了,他没有发现他们已经消失了。
忽然,鸟儿重新展开自己蓝黑相间的翅膀,离开了栖息处——哈古斯靠在肩上的船篙——飞走了。
鸟儿冲进了天空。
渐渐地,哈古斯的性情变得阴郁了。他开始对自己在河边的职责不上心了。他把船扔在灯芯草丛里。他任由倾盆大雨侵袭着小船。两个季度后,妻儿厌倦了他的忧伤,焦躁不安地与他交谈一番后,带上行李,走了。哈古斯不再需要家人陪伴,于是也离开了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再和人类说话。他避开刺眼的光线。一切可见的事物都让他害怕。即便是动物的脸,他也会逃避,因为他觉得这些脸在谴责自己。他左躲右闪,不想碰上黄嘴老鹰的眼神,不想遇见燥热之夜在荒野上企图用歌声吸引自己的青蛙的眼睛。
- 八音盒
从前有个略显罗圈腿的男子,他背着一只带有小格子的木盒。他行走在各个村落里。他把盒子放在一块石头上,或是一棵树的树桩上,或是一只箱子上,或是一条长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人们看到了十二个洞。每个洞里都有一只青蛙。晚上,他抬起头,呼喊着凡·西苏,像是一个有脚疾的男子在向天空发出祈祷。“说话吧,凡·西苏!”他叫喊道。又让旁边的一个孩子拿来一只水壶,往每只脑袋上浇水。它们唱歌了。
孩子们和各色人等从田野和林间小路聚集而来,围着他,一个个紧紧地挨着他,想看看盒子里究竟有什么。“如果你们保持安静,”他对他们说,“你们就会听到一种隐约的钟声。”
于是,就连孩子们也不说话了。人们听着缓慢升起的歌声,眼睛湿润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另一个世界里的某个人。有人低声喊着“妈妈!”,心里已双膝跪下、瘫倒在地。他们低低地说着:“妈妈!妈妈!”
- 尼哈出世
从前,尼哈出生的那天,安吉尔伯特伯爵——孩子的父亲,也是索姆湾献给圣人里基耶的那座修道院的院长——在孩子从贝尔特肚子里滑溜溜地出来后抱着他说:“你次抬起眼皮,你褶皱的皮肤如此脆弱,你在光亮中睁开两只湿漉漉的大眼睛,我以父、以子、以灵的名义祝福你。”此时一声新的啼哭响起。在贝尔特的肚子里有一个孪生兄弟:人们能看到黄色的额头在顶着腹部内壁,已经出现在贝尔特发紫的宽大阴唇之间,就在那片金色体毛下面,它们遮住了她一直紧绷到肚脐、快要撕裂的皮肤。安吉尔伯特院长伯爵想抓住他。可这个新生儿浑身湿漉漉的。黏糊糊的小身体四处乱扭,像一条鳗鱼在手里滑动。院长喊道:“你的感觉开始在自然中四下寻找抓手,你张开细小的手指,如此顽强而炽热地紧紧抓住我的大手,我这个在若干季节之前将你孕育的人,现在为你祝福。这张面孔与尼哈相像得连影子都远远不及:他几乎像是倒影一样反射着尼哈!在这张面孔里,尼哈再次降生,这是上帝传达给我们的信号。上帝想让尼哈的日子里有一个同伴,就像他自己有约翰睡在肩膀上!”
说完这些后,他进行了第二次洗礼,给婴儿起名为哈尼。
- 尼哈的受孕
从前,在尼哈出生前的九个月,一天下午,他们躲开他人的视线,藏在黄白相间的忍冬和蓝色的大片藤萝后面,那位叫贝尔特或贝尔塔的皇帝之女,拉着安吉尔伯特伯爵的手,对他说:
“来吧。”
她又说道:
“来吧。我深爱着你。”
她拎起长裙。他进入她的身体。
她享受着。
他自己在那儿体验到莫大的快感,又深深地进去了一次。
她享受着。
这发生在尼哈和哈尼出生之前。萨尔是索姆湾的萨满,她在那时即兴创作了这样一首诗:
“因为,若说鸟儿们爱唱,它们也爱听这歌。
它们爱听白垩峭壁下汹涌澎湃的北海,它们在海浪面前逐渐沉默不语,海浪涌起,又在沙滩上跌碎,滚压着沙滩,垂直的白色岩壁在这侵蚀下化作了沙子。
能吸引鸟儿的,只有港湾沿岸池塘死水里芦苇的窸窸窣窣。
它们向海边牧场和芦苇丛走去,走进深处。它们发出吱吱的叫声,为风在自己身上吹动的歌唱伴唱,以此为乐。”
“就是说,”萨尔说道,“雨啊,
当它落到森林的树叶上,
便让鸟儿的嘴惶恐不安,以此报复。
雨水减慢了它们的变奏,降低了它们放声长鸣的音高。
有时,暴雨和阵雨打断了它们。
啁啾声被哗啦声和轰鸣声彻底取代。”
所有鸟儿都会回应——当它们终于不再作声,即便是这出人意料的安静也是在回应。
所有鸟儿都会因地制宜地转调,场景为它们的奇怪指令组织的动作和特殊共鸣提供伴奏。
当场地置于薄雾,几乎没有琶音会叮当作响。
任何有节奏的连续呼唤在屋顶下都不会响起两次。
在鸟儿的世界里,低音比高音传播得更远——就像我们世界里的痛苦。
慢节奏比快节奏更易辨认。
我,萨尔,我会说:
“鸟儿的示意比你们感受到的忧愁更柔更软。
对我的耳朵来说,它们比人类吐字清晰的语言更容易读懂,只要这些人着了魔、在打转,却不知在承受苦难时该如何面对它,我就会帮助他们。”
- 恋爱中的哈尼
一天,福音传教士马太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1句中写道:“In illo die, Iesu, exiens de domo, sedebat secus mare.”(一天,耶稣走出屋子,坐在海边。)一天,哈尼走出屋子,坐在海边。突然起了风,卷起了沙子。他十三岁。有条船停在那儿。他登上船。他升起桅杆上的船帆。他朝着西边径直而去,又转向北方,松开了船舵。他睡着了。于是他航行了许久。他跨过了大海。他在阿克洛登上岸。在阿克洛港湾,哈尼遇见了一位住在岩石下的圣人。
哈尼在沙子上画下一副面孔,向圣人问道:
“您认识这张脸吗?”
但隐士回答他说:
“我不认识这张脸。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的身体、不认识你的脸,我只是刚才在石头小屋门口看见你在停船,看见你借着一根绳子从小艇上下来,摇摇晃晃,把小船拖到海盐泥浆里和岸上破贝壳的碎片上。”
“因为我在找那个长着这张脸的女人。这就是我旅行的目的。对我来说,我自己的脸并不重要。因为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脸早就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了。”
813年,贝尔塔(贝尔特,哈尼的母亲)公主在她父亲位于埃克斯拉夏贝尔的新宫殿里说:
“我觉得他的头脑变得空洞洞的。当毛发沿着他的大腿生长、占领他的脸颊,爱情就令他心神不宁。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产生了幻象,可我知道有一个不属于他的身体登上了他的大脑。至少,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个形象爬上了他的头脑,紧紧攥着它。当黎明到来,当他从床上起身,这形象也没有消退。从这时起,他再也不愿看见自己的兄弟。这个形象变成一种狂热,强烈到他再也听不见人们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他想找回这张脸。只要面对着我的儿子,看到他现在的模样,没有人不会为之震惊。他在爱着某个人。”
在双胞胎中较小的、名叫尼哈的孩子面前,贝尔特正是这样评价了儿子的出走。因为,在双胞胎中,早孕育的是后出来的。哈尼,作为尼哈的另一种写法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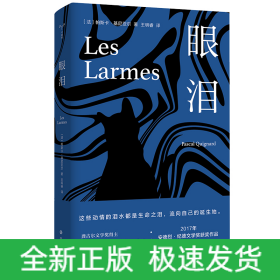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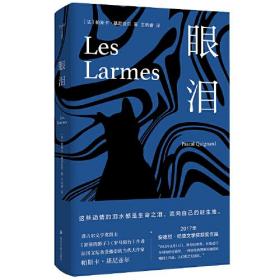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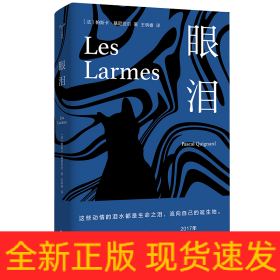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