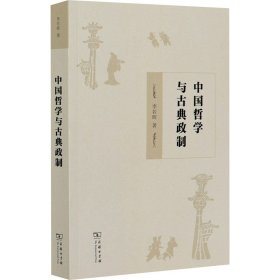
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1.54 6.1折 ¥ 6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李若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81754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2160554
上书时间2024-05-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李若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学、古典语言文献研究。
目录
绪论 自然与尊严 :道家思想内核及其普遍意义
节 道无形
第二节 精神专一
第三节 比于赤子
第四节 赡足万物
第五节 尊道贵德
章 何谓中国哲学
节 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第二节 中国哲学与中华文明之未来
第三节 熔经铸子:中国哲学的根与魂
第二章 如何是中国哲学
节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第二节 早期中国的“物”观念
第三节 老子传记及其思想:以《史记·老子列传》为中心
第四节 虚妄的“道体”:思想变迁下的经典诠释
第三章 古典德性政制
节 仁智勇三达德之变体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节 循必然以窥天道:试析阴阳家理论的逻辑结构
第四章 解经与治国
节 合内外之学:以战国至西汉儒道经学之互动为中心
第二节 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第五章 观念与行为
节 东周诸侯称王与中华正统观念之形成
第二节 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运作:重论费孝通双轨政治
第三节 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结语 中华政制要论
节 《尧典》五教
第二节 儒法五伦
第三节 身份社会
第四节 天下为公
第五节 家国一体
第六节 小结
征引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以忠臣为嘉宾,以卿相为师友,这是秦制之外,中华古典政制的另一种选择。
作者自道家入手论中国哲学,倡言熔经铸子,成就中华文明之魂魄;以仁智勇三达德说古典德性政制之大义,探究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历史道路。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中华古典政制以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为框架融摄外来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君权与相权相分保障天下为公,以治权在下培养道德责任。中华文化也得以遍采其长,熔铸伟辞。
主编推荐
本书体现了李若晖教授一贯的研究风格,经子并重,尤其精熟于道家,史论结合,注重小学功夫和逻辑分析。其开篇“自然与尊严:道家思想内核及其普遍意义”一节,“道无形”“精神专一”“比于赤子”“赡足万物”“尊道贵德”五种勾勒,足以规模全体,是当代道家哲学研究论说的扛鼎之文,而其后的《老子列传》研究,史论之战国至西汉儒道经学之互动、东周诸侯称王之故事,解经之《鹿鸣》传笺等,均极见功力。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教制度之互相建构的很好作品。
精彩内容
第四节 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下为公也深入人心。体现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便是宰相制,尤其是唐宋中书政事堂制。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明确以政事堂制度约束君主。《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列传》载其上疏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可谓对君相分权制度的完美阐述。南宋宁宗绕开中书,以内批将朱熹逐出临安,监察御史吴猎上奏,痛陈“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于是钱穆由秦汉以下政府之构成,讨论中国古代政体之性质,认为中国有一种自适国情之政制,“即所谓公忠不党之民主政治。‘公忠不党’者,乃超派超党、无派无党,或虽有党派而党派活动在整个政制中不占重要地位之一种民主政治,亦即所谓‘全民政治’。”并且,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一种政制:“若论中国传统政制,虽有一王室,有一最高元首为全国所拥戴,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既非王室宗亲,亦非特殊之贵族或军人阶级。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进而,钱穆因汉初帝王将相多出自平民,因而称汉初政府为“平民政府”;又以“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而称昭宣元成一段之政府为“士人政府”:这两者构成钱氏“全民政治”的具体历史形式。
徐复观则对钱氏所谓“平民政府”、“士人政府”提出批评。对于“平民政府”,徐复观说道:第一,“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大陆上幼稚地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第二,“所谓代表一般平民的问题。”一个史学家应了解政治观念必须通过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然受到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不了。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民的根源。”至于“士人政府”,徐复观反驳:“我们称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宣元以后的儒生多受宦官外戚打击,“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总结徐氏的观念,可以归结为:政府的性质应由其行为即施政来判断,政府的行为不取决于政府人员的来源,而取决于政府机构本身(的组织方式)。
张君劢甚且著专书《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对钱穆之论进行全面深入批评。张君劢对钱说之总体评论为:“吾读钱著深有所感者,其书名曰‘传统政治’,意在探讨旧历史之真相,然其衷心所崇拜者,实为现代西方政治。其称宰相为副皇帝者,以西方责任内阁 总理为背景者也。其称士人政府为平民政府者,以现代人民参政为背景者也。其所以重六部而抑九卿者,以现代西方内阁中各部为背景者也。钱著名曰‘探讨旧历史之真相’,而实对于旧历史上吾国之长处,为方今西方所无者,从未略举一二项……钱著不举自己之特长,独于西方今日所争所尚者,特造为副皇帝、士人参政之名以阴射之,实则,在名实两方面均不相符合。其所以如此,乃钱先生内心上之自卑感有以致之也。”至于钱穆“平民政府”之说,张君劢论曰:“钱先生心中想像西方政制中贵族平民对立之状,乃择所谓平民政治之名,以明吾国不容贵族政治之存在。夫去贵族而代以平民,自然为一种进步。然在吾国除至尊之皇室外,其他人一律平等,无所谓平民非平民。如是平民云云,乃仅为自西方政治辞典中所采用之名辞,而无其他贵族平民对立之实质者也。”“平民政府”必须相对于“贵族政府”才有意义,系指在存在着贵族势力的情形下,将贵族排除出政府,而任用平民。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春秋战国之交可算是平民取代贵族进入政府。严耕望详考史籍,认为秦“宗室贵族势力极盛,大庶长尤为其领袖,时操废立之权……成公以前,贵族权重;穆公雄才,外拓国土,内抑贵族而巩政权,是以父子相传,位宁八世,厉公以后,贵族复强,迄乎孝公,亦已八世;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脆弱可知矣。”商鞅变法之后,军功爵制使得平民大量进入政府,导致“宗室亲贵起与客卿斗争不遗余力,是以孝公既殁,车裂商鞅,穰侯相秦,疾拒游士,及文信失势,贵族更乘机谋议,一切逐客……秦史传统,君主与贵族斗争至烈,雄主以客卿为爪牙以与贵族搏斗,贵族之势既夺,君主之威既隆,则客卿自亦因缘得势耳”。但是由此造就的政府,却并非平民主导的政府,仅是专制君主主导的政府任用平民办事而已。平民没有政治背景,只能仰赖君主的威势,哪怕身居高位,也可为君主随时去除。张君劢云:“以云士人在各朝参加政局者,其最大难题,莫过于与专制君主之相处,乃至与帝王有关系人物之相处……越王勾践之于大夫文种,秦惠文之于商鞅,人臣之生死,皆决于君主一时之喜怒而又显然矣。及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吕不韦徙蜀 自杀。汉高祖威加海内,杀黥布、彭越、韩信诸叛将,固不足怪,乃至发纵指示之功臣如萧何者,亦复投之狱中。其他创业之主如唐太宗者,平日固倚李勣为长城,于其临死之前,乃遗诏太子曰:‘如勣不受命,当杀之。’宋太祖惩五代诸臣之廉耻道丧,乃立不杀士大夫之戒,可谓得为君之体。至于明太祖之杀功臣,较诸前代尤惨酷矣。”《汉书》卷八《宣帝纪》,宣帝系由平民登立为帝。但在登基之前,“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师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可见汉政府并不以“平民政府”自居,甚且忌讳以庶人为天子。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早年的贫穷并不必然导致关心民生疾苦,反而极有可能导致极端的贪婪。灵帝已是帝王之尊尚且如此,又何怪乎贪腐横行。正是基于此,我们反思钱穆所谓“全民政治”,平民进入政府是否必然保障政府关心平民?徐复观的反驳显然极有道理,“陈世美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为了自己向上爬可以抛妻弃子,又怎能指望如此之人为民请命呢!
至于“士人政府”,张君劢指出:“所谓士人,指读书人或士大夫言之,政治托之于读书人,自为一种长处。然历代以来,不读书不识字之人,占全国人十之八九,此十之八九即为不得预闻政治之人。彼西方国家中识字者,居十之八九,尽行使钱先生所谓间接民主而以为不足取法,我中国十分之一之人民,得因考试入官,而钱先生择美名以名之,曰直接民权。不知其所称许者,乃士大夫之做官权而已,何民权可言哉!”再进而言之,士人经由科举进入政府便可称为“士人政府”吗?张君劢认为:“吾国由考试中选拔之文官所造成者,为官僚政治。其人职在奉令承教,自己无所主张,在法规之内,习于舞文弄法,上下其手,以便自己升迁,或且奉迎长官之意,蹂躏百姓……如是文官制,可以视同人民参政乎?可以代替民意机关乎?盖不待辨而自明矣。”再从政府行政来看:“吾欲问钱先生者,所谓士人政府之政策之预备,事先有何调查,有何报告书乎?政策之决定,既由君主裁可,而何以立朝者各有主张乎?究竟谁有权赞成,谁有权反对,其准绳安在?如此一国三公我谁适从之局中,何制度可言乎?何种传统可为后人遵守者乎?”第五节 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以养成道德承担,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在科举制下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襄王述周公封建,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宗族拱卫国家的观念。此后这一观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一统六国称帝之后,“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可见虽然天下大势已由封建变为郡县,但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的观念仍然牢不可破,且并非仅仅是几个不识时务的儒生的谬见,而是秦朝多数大臣的共识。
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再也无力授田。“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民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格局,不是贵族政治,不是门阀政治,也不是国家直接控制编户齐民。唐末五代,由流民武装建立的政权不能直接掌握土地,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而作为经济上的主体力量,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或者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于是出现了叶适所谓的‘民与君为二’的格局。也可以讲,这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格局,或者说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分离的格局。”宋儒往往将唐之亡归因于世族消亡,因此救弊之法就是重建宗族。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宋儒最终构造出了有别于六朝世族的平民宗族。在户等上,有田者为主户,无田者为客户,均为编户齐民,身份相等。基于契约的佃农对于地主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避免了地主的贵族化。因此宋以后的家族囿于一隅之土,纵使族人获致高官,也仅仅是以个体身份入仕,其家族绝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治力量。成为宋以后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基础。
当近代国家危亡之际,孙中山于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一节,强调:“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至于合群之法: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此外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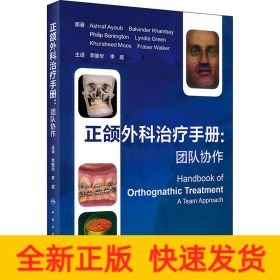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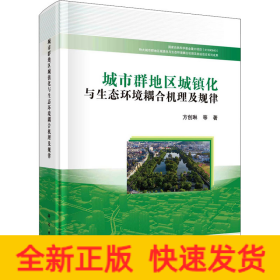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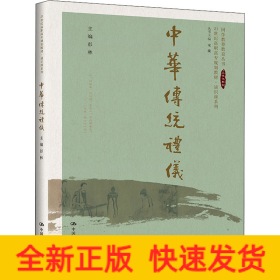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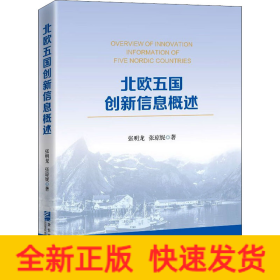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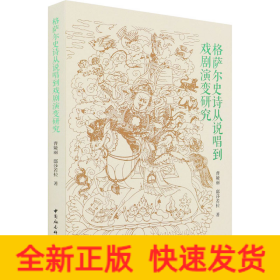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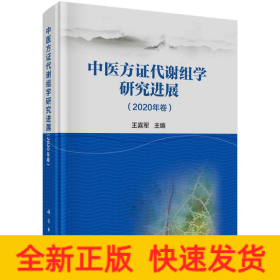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