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鸿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7.82 4.2折 ¥ 42 全新
库存10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艾姬
出版社湖南文艺
ISBN9787572618574
出版时间2024-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2元
货号32087650
上书时间2024-07-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主编艾姬,资深图书策划编辑,拥有8年青春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经验,策划出版过《哑舍·零》等畅销百万册的图书作品。
内容摘要
这是一本双女主古风BE短篇集。讲述了在古代背景下,处于各种封建制度与父权制度压迫下的不同身份的女性,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与不平等对待,彼此守望相助,携手冲破命运与社会的桎梏,追求自由独立的人生,共同成长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个个形象鲜明的女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足智多谋的闺阁小姐、坚毅果敢的家族继承人……通过数个女性彼此互助的动人故事,展现出不一样的女性风采,这些女性在各种压迫之下迸发出的反抗力量,描绘着黑暗现实中闪光的人性★精美随书赠品:(1)人物镭射圆扇×1;(2)古风诗卡×2;(3)“诀别”海报×1;(4)首刷特典镂空纪念卡×1
精彩内容
但琼花无恙文/倪光纵使普天之下,有再多人匍匐于慕容韫足边,却唯独沈喑,能做她的恶犬,亦做她的不二之臣。
护国长公主×乞儿小侍卫一
沈喑被捡回去的时候才九岁。
九岁的小乞丐,扑在泥里,同一群比她不知大了多少的老乞丐抢吃食。那吃食也不过是块发了霉的烧饼,被泥水浸湿了,又被无数肮脏的手抢来夺去。
侍卫将沈喑提起来的时候,她正将那块饼塞到嘴里。饼太硬,她就梗着脖子往下咽,一张脸被泥糊得不辨五官,唯有一双眼睛,亮得似燃着一把火。
她很轻,比一只猫重不了多少,乖乖蜷缩在那里,人畜无害的样子。侍卫放松了警惕,却在下一刻就被她狠狠一口咬在了手腕上。
侍卫吃痛松了手,沈喑落地要跑,却又撞入了一个怀抱中。
那时节刚刚入春,春寒料峭,肃杀的风自漠北一路吹到了江南,墙角几枝桃花开得伶仃单薄,零落的影子横斜在青色的衣角上,映出那人一双闲散昳丽的凤眸,挺直的鼻梁上,印着一颗淡淡的朱砂红的小痣,端的是一副薄情寡恩的美人相。
这样的美人儿,沈喑过去从没见过,似是将自己衬成了脚边的泥,离得近了,都觉得玷污了她。
可美人儿的脾气很好,被她撞了也不生气,反倒问她:“你跑什么?”沈喑警觉道:“那块饼是没人要,我才吃的。”美人儿耐心道:“我不是要抢你的饼——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往后,便再也不会挨饿了。”沈喑出生时便遇到干旱,往后的九年人生,多在颠沛流离。她是女子,又无父兄庇佑,若不是天生凶悍,早就死在了逃荒的路上。往日不是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了的人,尸骨如今已经腐朽。
所以她只道:“那你现在先给我两个馒头。”——就算是骗她,她也要做个饱死鬼。
那人便笑了,望着她的眼神带着点极淡的怜惜与遗憾。
后来沈喑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是走了大运。
那桃花下的美人儿便是大靖长公主慕容韫,亦是她未来要效忠一生的主子。她被带了回去,一日三顿,顿顿有肉,她初时还觉得是在做梦,狼吞虎咽吃了,当晚就闹起了肚子。
太医诊治,她是猛地饕足不好克化,需要再好好饿两顿。她原本恹恹的,闻言差点跳起来:“你这老匹夫,胡说八道什么!”太医不和她计较,她却凶得要命,要拿枕头砸太医。第二日,她就被送到了慕容韫面前。
那时正是早膳时间,她乖乖站在那里等着。慕容韫不过片刻便走了出来,因在自己宫中,只穿着件家常的衣裳,流水似的长发沿着肩头蜿蜒落下,赤裸的足踩在细密的地毯上,竟比白玉更要耀眼。
她看得有些呆,只觉得这位公主,从头至尾,无一处不美。在她面前,自己就像是一只蝼蚁,又怎敢亵渎神明?
可慕容韫坐下之后,却问她:“太医让你饿着,是为你好,你做什么打他?”她更呆了:“您……您怎么知道?”慕容韫没有回答,只看了她一眼,旁边的大宫女提醒她:“公主让你坐下。”她连忙坐下,却又不敢动,慕容韫便道:“喝粥。”她连忙捧着碗就往嘴里倒,慕容韫却又说:“慢点,一口一口喝。”慕容韫风流天成的凤眸,望人时总有种睥睨之意,明明应当权杖天下,却只是认认真真地看着她喝粥。
她无措到了极点,喝得束手束脚。等她喝完,慕容韫这才收回了视线:“往后每日,都来我这儿用膳。”这是天大的荣耀,一个小乞儿,竟能与公主同席。
两人一张圆桌,她总觉得自惭形秽,连筷子都不敢动,慕容韫便亲自替她夹菜。她吃饭免不了狼吞虎咽的毛病,可只要慕容韫看她一眼,不必开口,她就知道自己该慢一点。
日后回忆,那竟是人生中难得的温情时刻,雕花的窗外,日光投进屋内,映得檐下一瓶折枝梨花落下斑驳的影。
慕容韫的背脊永远挺得笔直,雪白秀丽的面上神色沉静,似一枝牡丹,生来便要这盛世做她裙下的点缀。偶尔抬眸,闲闲扫过她时,她心中总是有一点无措,却有更多的快乐。
纵使普天之下,有再多人匍匐于慕容韫足边,却唯独沈喑,能做她的恶犬,亦做她的不二之臣。
二慕容韫一直陪着沈喑吃饭,硬是替她改掉了吃饭狼吞虎咽的坏毛病。
作为大靖的大长公主,慕容韫原本是被当作皇太女看待,十年前,太子降生,原本被委以重任的慕容韫一下子处境尴尬起来,还好皇帝疼她,特意将兵权给了她,又赐了她“护国长公主”的头衔。
如今天下并不太平,连年的水旱蝗灾,整个大靖哀鸿遍野,往年的盛世光景不再,竟显出了岌岌可危的征兆。
皇帝年迈,身子骨弱,治国的重担便到了慕容韫身上。多少次吃饭时,急奏传来,慕容韫便要匆匆起身。
沈喑年纪小,却也知道利害,慕容韫走了,她便跟着侍卫一道练武。侍卫都是精心挑选的好手,见她用心,忍不住笑了:“你一个小姑娘,练这个做什么?公主宠你,等你大了,替你许个好人家。”沈喑却说:“我不嫁人。”“你不嫁人要做什么?”“我要跟着公主。”侍卫们便笑了,都说她有志气。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不是有志气,她只是要跟着慕容韫。
慕容韫是这天下间最了不起的人,她便不能只做个闲人,否则哪里配在她身旁有一席之地?
她没有天分,便要下苦功,旁人练一个时辰,她便练两个时辰。到了夜里,下人房中禁燃烛火,她便借着月色、雪光,艰涩地将书上的字背到心里。
连慕容韫都劝她:“过刚易折。你年纪小,何必这样苛责自己?”可她知道,自己不像慕容韫天生聪颖,若不笨鸟先飞,哪里能够得偿所愿?
这样的勤奋,终于让她成了慕容韫身边的一把好手,那些教授她的侍卫早已不是她的对手,纵使是饱读诗书的学士,也为她而啧啧称奇:“若你非女子,当在朝堂上有一番作为。”她哪里需要什么作为?她的一切,都是慕容韫赠予的,她所图所求,也不过慕容韫的回眸一顾罢了。
沈喑十五岁时猛地开始抽条,她长高了个子,往日的衣衫都短了不少,借着铜镜自照,能望见一张秀丽的面孔,眉眼都是浓的,只唇色是淡的,眼角尖尖,像是狐狸。
那一日慕容韫正在批阅奏折,她站在旁边磨墨,窗外大雪纷纷,落得满殿都是冷月似的反光,慕容韫漫不经心扫过她时,手中的笔忽然停在那里。
一颗很大的墨汁滴落在奏折上晕开了,慕容韫眼底藏着喜怒不辨的光,望着她,似是透过她,看向一段求而不得的过往。
她听得慕容韫喟叹似地呢喃:“阿寿。”声音清冷,却又缱绻。
她大着胆子抬起眼睛:“公主,您在喊谁?”听到她声音的一瞬,慕容韫眼底的光熄灭了:“一个故人罢了。”她又问:“我很像您那位故人吗?”慕容韫似是没有预料到她会问这个,唇角翘起,却又叹息道:“你同她……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若无半点相似,她又怎会看自己看得出了神?
只是沈喑没有再问,她知道自己能在慕容韫身旁,已是叨天之幸,又怎敢去奢望更多?
那夜之后,慕容韫便离了宫,却没有将她也带上。别的侍卫都说是公主疼她,出这一趟差事辛苦,特意将她留下。可她知晓,一定是慕容韫不肯看到她。
伤心是有的,更多的却是好奇。那个叫“阿寿”的人,究竟是什么模样,才会让慕容韫在某个发现自己与那人相似的瞬间,这样失神。
那年春天是个难得的好天候,慕容韫回来时,沈喑特意守在门口等着。枝头的梨花簌簌而落,盈满了衣襟,她远远看到慕容韫的凤辇落下,里面出来的,除了慕容韫,还有另一个人。
那是个极为小巧纤细的少女,穿着一袭梨花白的裙子,裙角用银线绣了花纹,走动时,如水光潋滟,越发衬得一张面容如雪般晶莹清丽。
少女俏生生立在那里,沈喑竟一时不敢上前,还是慕容韫看到了她,唤她说:“躲在那里做什么?”沈喑这才慢慢地走了出来,听到少女问慕容韫:“阿韫,这人是谁?”慕容韫回答说:“这是我同你提过的沈喑。”“原来是她。”少女含笑望向沈喑,声音天真娇嫩,“我叫阿授,九文山山主的女儿,沈喑姐姐,往后,请多多指教。”她竟然叫阿授!
公口中念叨的人,竟是这样一个少女。
沈喑僵在原地时,慕容韫已经被少女缠着走了,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顾得上同她说。
远方的夕阳即将落下,仿佛一捧很小的、即将熄灭的灰烬。树梢的梨花落尽了,满地都是狼藉的白。皇城内渐次亮起了灯火,最高处慕容韫的宫室内,流水一样送入各色珍馐——那都是为了宴请阿授。
阿授手松,一掷千金,人人都得了赏赐,大家都为贵客的到来而欢呼雀跃。夜里,下人房中,侍女们争相攀比着阿授赏给她们的首饰,有人问沈喑:“公主那样宠你,阿授小姐也一定送了你大礼吧?”见沈喑不语,有人小声说:“可我听说,阿授小姐不喜沈喑,还和公主吵了一架。公主为了哄她,答应明日带她去玉清池赏琼花呢。”“啪”的一声,是沈喑不小心握碎了一只白玉的发簪。血沿着掌心滚落下去,可沈喑却不觉得痛,只是惊讶,看起来温润无害的玉石,原来也能伤人。
宫中唯有一处有琼花,相传三百年前,有仙人乘风而来,助大靖定鼎于此,后仙人溘然长逝,化作琼花,三百年未曾凋谢。
沈喑以前也曾好奇过这样的传闻,同慕容韫提过一次,想要去看看。那一次,慕容韫却大发雷霆,沈喑这才知道,这片琼花,竟是慕容韫的禁忌。
禁忌在有些人面前,也并不算什么。
只是她沈喑,并非能让慕容韫破例的那个人罢了。
三九文山作为国教所在,一向地位崇高,在历任山主面前,甚至连皇帝都要垂首行礼。作为山主之女,阿授说是公主也不为过。
她一来到宫中,便住进了慕容韫的寝宫。沈喑按照往昔的时辰,来找慕容韫用膳时,便看到阿授正坐在她原本的位子上,言笑晏晏地缠着慕容韫说笑。见到沈喑,阿授脸上的笑容立刻淡了下去,问慕容韫:“她来做什么?”慕容韫说:“她一向是同我一道用膳的。”阿授桃花似的眸子弯了弯,撒娇说:“可我在家中,爹爹一向只许我同他一道用膳。阿韫,你是公主,可以陪我,可是沈喑姐姐……”这话说得隐晦,却不外乎是说沈喑身份太低。
沈喑不语,只是垂下头去,殿内安静了许久,她终于听到慕容韫说:“你先下去,若有什么喜欢的菜,要小厨房做来给你。”沈喑的心往下沉去,沉到了看不见的地方。那些曾给她的优待,在旁人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间,便被收了回去。
幼时的三餐不继,让她留了一身的病,全靠慕容韫替她细心调养,如今不过不按时吃饭,胃便又隐隐作痛。
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沈喑转头,看见一张娇嫩的面容。阿授站在她身后,怀里抱着一捧花枝,那花格外皎洁,花瓣如透明的一般,唯独在花心处,泛起一点潋滟的红。
阿授笑着问她:“认得这是什么花吗?”沈喑不语,阿授便继续道:“这便是琼花了。阿韫带我去看,见我喜欢,便替我摘了,让我插在瓶中。沈喑,听说你之前也曾想去看琼花,你知道,阿韫为何不肯带你去吗?”“我不想知道。”见她开口,阿授笑意更浓:“其实你在意得不得了吧?沈喑,你不过是一介乞儿,能在阿韫身边这样久,已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琼花是仙人之躯所化,哪里是你这样下贱的人能够染指的。就像阿韫,看起来离你很近,可她是天边的云,你却不过是她足下的泥。”阿授的声音娇甜软糯,带一点南音,格外动人,哪怕说着这样的话,眉眼间仍是含笑。
一等一的天真烂漫,也是一等一的残忍。
胃疼得更加厉害,却又似乎不只是胃,更像是牵扯着五脏六腑,都在隐隐作痛。沈喑额上疼出冷汗,背脊却仍挺得笔直。
“那又如何?”阿授一愣:“什么?”“我出身是不如你高贵,可过去数年,都是我陪在她的身边。你知道她每日用膳后喜欢小憩一炷香的时刻吗?你知道她批阅奏折的时候只喝雀舌茶吗?你知道她从不用龙涎香,只用梅香……”阿授气道:“你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只要我想,我能将九文山的一切都给她!”“她是护国长公主,生来便要守卫大靖,真的会喜欢一个将皇权踩在脚下的人吗?”眼前一阵阵发黑,沈喑用指尖刺入掌心,苍白着脸微微一笑,“况且,阿授小姐,你有朝一日,注定是要嫁人的。可我却能一直陪在公主身旁,死生不离。”阿授终于忍不住,自袖中拿出一柄长剑,指向沈喑:“你这贱仆怎配!”沈喑眼角的余光看见了远处的影子,她明明能躲,却没有躲开,任由那锋利的兵器刺向了自己。
剑入胸膛,再往前半寸便是她的心脏,却止步于此。
漫天飞舞的琼花花瓣间,慕容韫神色冷厉肃杀,将沈喑单手抱在怀中。沈喑吐出一口血来,望着慕容韫,忽然无声地笑了。
这一次,是她赌赢了。
再睁开眼时,沈喑望见床头的花瓶里插着几株木兰花,慕容韫正坐在一旁,垂眸批阅奏折。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去,怕她睡不安稳,屋内没有点灯,唯有窗外的月色透了进来,冷冷地落了满地。
她觉得口渴,沙哑着声音问:“公主,您怎么在这儿?”慕容韫闻言抬起眼睛,自一旁倒了杯温热的水递到她嘴边,等她喝了才淡淡道:“怕我一眼没看到,你就死了。”她被呛了一下,听到慕容韫叹了口气:“阿授的武功不过平平,那长剑却是九文山的神器,你如今寒气入体,不知要调养多久才能痊愈。沈喑,为了赌气,值得吗?”慕容韫难得这样喊她,语气中竟有了鲜明的怒意。她忍不住要笑,一双眼睛亮得像是星星:“公主,您是生气了吗?”慕容韫被她问得一顿:“我是气你不知道珍惜自己。”她笑得越发开心,将脸埋在慕容韫的掌心里,梦呓似地轻声说:“能被您护着,我便是死了,也觉得开心。”她看不见慕容韫的神情,也不敢去看,生怕她会抽出手来,弃她于不顾。
还好她没有。
“我不会让你死的。”慕容韫的声音似是泠泠的泉,泉水一滴一滴,落入她的心底,“沈喑,你信我。”屋内安静至极,听得到一朵花开的声音,木兰花在夜色里,乍然望去,也似琼花。慕容韫的掌心冰凉,被她的泪淌过时,却带着一点脉脉温情。
她这条命,本就是慕容韫捡回来的。她掌着她的生杀大权,要她生死、要她枯荣。
心口的伤隐隐作痛,痛中也生出快意,这一生她注定为慕容韫而生,为慕容韫而死,哪怕伤痕累累,也不觉有悔。
四因着受伤,沈喑在慕容韫宫中住下了。
听说阿授发了极大的脾气,将整个屋子砸了个粉碎,却没有闹到她的面前。新来的小婢女和她悄悄说:“是公主吩咐,不许阿授小姐来打扰您。”这一局,是她胜了,哪怕胜得惨痛。
九文山上积雪皑皑,山主赠予阿授的那柄剑由千年玉髓铸造。太医诊治,往后余生,她体内的寒毒都无法排除干净,每到天冷,骨缝都会透出阴冷的寒气,折磨她,不死不休。
因着她怕冷,慕容韫特意赐了她一尾狐裘,雪白的毛皮,三寸的出锋,轻轻一吹,便盈盈地颤了起来。
小婢女来通风报信:“这是九文山特意将豢养的三尾狐剥了皮,送给公主,没想到公主转手就给了您。阿授小姐气得要命,和公主大吵一架,哭着跑了出去。”这样的盛宠,她听了却也没有多少得色。九文山一脉向来桀骜,对待朝廷从不肯俯首,如今为了阿授,刻意讨好慕容韫,慕容韫却这样不留情面……窗外忽然响起连绵的钟声,自皇城最深处的銮殿内,一路蔓延至方圆百里的京师之中。无论殿内殿外,所有人都惊在原地,不知是谁,忽然发出了一声悲鸣。
“陛下——”那是丧钟,只为当朝天子而鸣。
皇帝驾崩,幼帝登基,慕容韫作为大长公主,风雨兼程赶回京中。
她回来时,已经是三日后,那日下了大雨,浇湿了窗外满枝早开的杜鹃。慕容韫进屋时,身上还带着沉沉的水汽。
雨将天地都淹没,她的长发湿漉漉地黏在脸上,整个人如同艳鬼,锋利而凄艳。
沈喑连忙起身,要她坐下,又拿被子将她裹了起来,她没动,只是那样静静地垂着眼睛,忽然喊她:“沈喑。”她连忙道:“我在。”“沈喑……”慕容韫问,“你还记得你爹娘吗?”沈喑出生时,母亲因为难产去世,父亲含辛茹苦地养育她,却死在了逃荒的路上。她沉默了一会儿,她以为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可原来那些面目,还都历历在目。
“记得。”“我走之前,父皇将我喊到御书房,他赐了我一幅字,上面写着‘审慎’二字。我知道,这是他在暗示我,我在朝中,势力过大,对太子影响不好。我要跪地谢恩时,他却又拦住了我。父皇要用我,却又要防备我,他是帝王,亦是父亲。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沈喑……”慕容韫一遍又一遍地喊她的名字,似乎借着这两个字,来汲取一点力气。
“我却忽然想不起来,父皇究竟长的什么模样了。”天家无父子,可曾几何时,她也是被抱在怀中娇宠的公主。只是时移世易,天子有了更为怜爱的幼子,难免要为幼子筹谋。曾经放在心尖上的女儿,如今却成了皇权的阻碍。
所以提防,所以拉拢,所以已经许久未曾抬眸去看,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何等模样。
窗外雷声滚滚,春日惊雷处,旧日光阴也短。慕容韫的指尖冰冷,将头靠在她的肩上,她能感觉到,有滚烫炽热的水珠滚落,那是不能被任何人看到的,独属于天之骄女的尊严。
她紧紧地抱住她,似是抱住她无人可诉的痛楚。
在最难过的时刻,慕容韫想起的,终究是她,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阿授。
“公主。”心被慕容韫的一颗泪灼烧,她轻而坚定地说,“我会一直陪着您的。”那是十六岁的沈喑,所能许下的最庄重的承诺,日后年年岁岁,回忆起这一刻时,她都会想起那一颗泪,想起窗外滚滚的雷声和被打落满地的杜鹃花。
可无论如何,她都无法想象,许久之后,光阴翻涌,青史成灰,她于烟尘滚滚的史书之上,留下的一笔,却同慕容韫没有分毫干系。
五沈喑于史书上留下的第一笔,是她十七岁时,被新登基的天子下了圣旨,迎娶入宫。
她以乞儿之身,先侍奉于大长公主,后入宫不过半载,便一路扶摇直上,成了仅次于皇后的贵妃。皇帝对她恩宠不绝,十数载间,令她独宠于后宫。
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曾作猜想,她定是国色天香的艳姝,抑或是倾国倾城的狐媚,却无人知,沈喑初入后宫时,不过是一名小小的答应。皇帝不喜她,看到她便皱了眉:“这就是所谓的国色天香?倒也不过如此。”“陛下坐拥天下,富极四海,自是瞧不上奴婢的粗俗样貌。只是奴婢侍奉大长公主身侧数载,常听公主感叹,陛下之聪颖勤勉,远非常人所能及。奴婢愚钝,或许在陛下身侧,也能学到一二。”她身上只着了素白纱衣,肌肤在烛火下如同莹莹的雪,她微微抬起眼睛,尖尖的下颌抵在胸前,似是一只狐狸。
小皇帝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上有些失了神,顿了片刻,他冷笑一声:“巧言令色。”那夜红烛垂泪,天还未亮时,她便被送回了自己的住处。小婢偷懒,并未替她准备热水,她便就着冷水,将自己收拾妥帖。窗外的月是半弯的,落下清冽的光,留下满地清霜,她看着镜中自己身上狼藉的痕迹,忽然无声地笑了一下。
身体骗不了人,哪怕对她再多鄙薄,天子到底是为她着迷的。
她感激自己有这样一张面孔,男女之间的情爱,多因色而起,天子后宫空虚,她足以艳冠后宫。天子常召幸她,从不许她留下过夜,未到天明就差人送她回来,再到后来,亲自替她选了离自己最近的宫室,只为想到她时,便能见到她。
日子流水一样过去,十七岁的末梢,她已升为贵妃。天子怕委屈了她:“皇后乃是先皇所赐,无过不可废。可是喑喑,你要知道,在朕心里,唯有你一人。”若是旁人,早已感激涕零,她心中却无悲无喜,只是柔声道:“只要陛下心在臣妾这里,贵妃还是皇后,又有什么区别?”天子爱极了她的谨慎温柔,待到天明,方才离去。她抽了珠钗,拨弄炉中的残香,寻了一块丢到冷酒里面仰头喝下。
旁边忽然有人问她:“这是令人体寒的方子,女子饮了不易受孕。贵妃娘娘难道不想母凭子贵?”这声音明媚,带着南音,正是阿授。
她的神色淡了下去:“与你无关。”“怎会与我无关?阿韫正在边关,朝堂之上,再无一人敢为她言。如今你正得圣宠,若是诞下龙子,皇帝必龙心大悦,到时你可以趁机求皇帝将阿韫放回来!”阿授冷冷道,“还是你心中,其实并不愿见到阿韫?”一年前,先皇驾崩,恰逢边关大乱,天子初登大宝,便连发十二道诏令,责慕容韫亲往抵御外敌,却又生怕慕容韫拥兵自重,不但不给粮草军需,甚至连甲胄战马,都苛刻至极。
朝中不是无人为慕容韫说话,却被小皇帝一个个呵斥贬谪,待到如今,朝中早已无人敢仗义执言。
杯中残酒被泼在地上,徒留一点伶仃的香气,沈喑轻笑一声,抬眸看向阿授:“怎么,我入了宫还不够,一定要我怀了孩子才行?”阿授脸色一变,可沈喑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乞儿,并不畏惧她。
“我自有主意,还容不得旁人指点。阿授小姐在九文山惯了,难道不知道,当朝天子对你们,也并无什么好感?”阿授猛地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她却只是合上眼睛:“本宫倦了,退下吧。”“沈喑,你真是变了。”阿授难掩面上的复杂神色,“我当初还以为,你入宫是真的一心为了阿韫,可如今看来,你分明乐在其中。”沈喑眼睫轻轻一颤,心里却并不起分毫涟漪。是做慕容韫身边一个小小的婢女,时刻忧心于被人替代要快乐,还是如今在后宫之中做万人之上的贵妃来得更逍遥自在,或许,连她自己都分不清了。
那年她生辰时传出喜讯,已怀有三月身孕。皇帝特意下旨为她举办最盛大的生辰宴,自她得宠便称病不出的皇后也难得出席,送了她一幅百子千孙图作为寿礼。半月后,她小产血崩,救了三日方才活了下来。
皇帝震怒,严令彻查,发现原来是那副百子千孙图上涂满了致人小产的药材。皇后被废,一家人被贬谪流放。后宫之中人心惶惶,而她在生死关头挣扎许久,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屋内烛火通明,却唯有伶仃的光落入眼中,仔细分辨了才知道,竟是有人将手悬在她的眼上,免得她被火光灼痛了双眸。
她怔怔地看着那只手,望见手上狰狞的伤痕,忽然眼泪就滚了下来。
两人都变了,不过两年未见,回首时,都不似前尘。慕容韫瘦了许多,唯有一双眼睛,仍旧亮若寒星,却在望见她时,盈着难以言说的温情。
“疼吗?”这次小产,她血崩不止,身下的毯子濡湿了一条又一条,血从身体里流淌走,人的感觉原来是那样麻木而平静。她躺在那里,能听得到身旁御医们惶恐的声音,明明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却一点也不害怕,她只是遗憾,连最后,都没有见到慕容韫一眼。
可还好,她挺过来了。
原本是不疼的,可被问了,似是整个人都娇气了起来。眼尾滚下眼泪,她哽咽着说:“疼,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你,就疼得厉害。”慕容韫手指的皮肤不比曾经细腻,替她将眼角的泪拭了,哄她说:“你现在身子不好,哭多了伤眼睛。”她颤抖着手按住慕容韫的指尖:“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边关风大,能望得见极好的月亮,一到天晴,夜里天幕一尘不染。若你看了,也定会喜欢。”那些苦楚,到了她的口中,不过是这样风花雪月的事。她被逗笑了,眼泪却大颗大颗滚下来,将慕容韫的手指都沾湿了。
“回来了,就不要走了好不好?”慕容韫手指微微一颤:“边关事紧,离不开我。”“就当是为了我。”“沈喑……”慕容韫说,“我是为了你回来的。”这是多么大的殊荣。
这些年,她守在边关,寸步不离。如今却因她小产,一路跑死数匹骏马,三日之内便赶了回来。
这样的风雨兼程,不过为了见她一面。枕边摆着的花已经微微枯萎,能够嗅得到淡淡的香气,花瓣上还沾着一点黄沙,是被她捂在怀中,自边关带回给她。
她的眼泪淌得更急,死死抓着慕容韫的手,哀哀祈求:“公主……”慕容韫眸底现出几分恍然:“是他要你做的?”她哭得说不出话来,慕容韫又要替她擦泪,手刚刚抬起,就无力地垂下。炉中燃着的,本是千金难得的安神香,却不知何时,被替换成了软骨散。她是如凤凰一般桀骜的女子,哪怕孤身抵京,皇帝仍对她心存忌惮,所以设下这样的计谋,只为将她彻底困囿于宫闱之中。
而她只是一枚棋子,有孕、小产,不过是掌权人惺惺作态。
“别哭,我不怪你。”慕容韫倒下时,还怕会压到她,只虚虚地倚在床边,离得太近,倒似温情脉脉,“沈喑……”慕容韫叹了一口气:“下次,不要再用自己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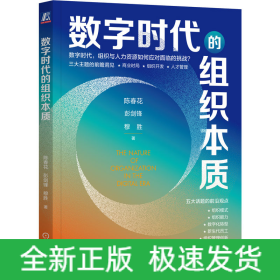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