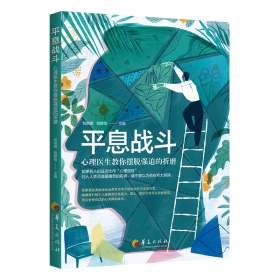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4.98 4.2折 ¥ 59 全新
库存10件
作者包祖晓主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22202433
出版时间2022-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9元
货号31437918
上书时间2024-05-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第一章强迫诊治过程中的困境与出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都能量化,不是所有能量化的事都有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强迫是种古老的现象,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问题,与某些动物行为相似,有返祖现象或原始行为。因此,不管现代医疗科技如何发展,各种与强迫有关的仪器、药品如何层出不穷,单纯运用医学上的方法是很难彻底治愈强迫的。就如下文中的例子所示。
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某来访者,男性,17岁,高中学生,患强迫障碍多年,曾在多家医院进行过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后服用过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经典的抗强迫药物,甚至连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也用过,但效果有限。期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疗效亦不佳。此后中断治疗。数月后一次因来医院看咳嗽问题顺路来心理卫生科看望一下就诊过的医生。当医生问他现在状况如何时,他说:“强迫已经没有了”。当医生好奇地请他谈谈经验时,他说:“自从上次离开医院后,无意中读到了托尔斯泰的书,发现写得太好了,就一门心思沉浸到里面,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强迫念头不来捣乱了。”这是作者曾经遇到过的强迫障碍案例。许多时候,包括作者在内的医生们绞尽脑汁地对强迫者进行医学干预,但收效有限。
许多研究证据表明,大部分药物治疗强迫症的平均有效率不超过60%,典型症状的减少平均不超过50%。在治疗相当长的时间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继续深受强迫症状的折磨。
作者以为,药物在强迫的治疗中充其量起到了“游泳圈”或“拐杖”的作用,是一种对症治疗,无法起到像抗生素杀灭细菌那样根治疾病。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药物所起的作用是把强迫症状压制下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把症状隐藏或掩盖起来,甚至可能把人变得“迟钝”或“麻木”,让我们感觉不到冲突、恐惧和焦虑。如果停药,许多时候症状会马上冒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
边维尔早在1771年就已认识到药物/物理疗法治疗心灵痛苦的作用有限,他在《论女子淫狂》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C.A.Ross在1989年批评道:“为数众多陷入绝境的患者多年来一直接受无效的药物治疗,不断遭受二次创伤。”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更是尖锐地指出:“痛苦和不满是我们心灵旅程的自然组成部分,否定它们就是否定成长。可是,医药产业却藉人生中极为正常的苦恼和不满牟利,研制出一大堆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设法麻痹我们,使我们感觉不到苦恼和不满。”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强迫症药物治疗之外的疗愈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并没有否定药物能缓解人的强迫思维、焦虑情绪等症状,只是在强调:从长远的角度看,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我们不应强行对他们进行药物干预。正如斯坦恩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所提出,如果产生强迫症症状的人自己不求助的话,不应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就需要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考虑,”他说道,“之所以这么多人产生了强迫症状却没有得到治疗,其原因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完全对付得过去。”他继续说道:作为心理健康专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干预的认识,让他们了解自己随时可以得到这种服务。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有义务帮助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减少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我就怕大家会忘记,社会中大多数产生强迫症状的人,不管其情况是可以被诊断出的,还是被认作是在阈值以下的,抑或是在两者之间的,他们都还不是病人。因此,提出我们应当花费更多努力去找出这些个体,对他们加以治疗就意味着我们自认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何时需要我们的帮助。
从另一角度说,斯坦恩通过这段话在强调,对于强迫的疗愈来说,我们需要关注医疗以外的内容。
需要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既然这些行为对实施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苦痛,那么他们产生苦痛的过程就相当关键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强迫症是群体、文化和家庭造成的。如果你的行为——比如说一丝不苟地把物品摆放整齐——被认作是古怪的,那你就会因此感到痛苦。反之,如果别人认为这是泥瓦匠大师才具备的手艺,有自己的用途,那你就不会因此感到痛苦了。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残障与人类发展系、医学教育系教授莱纳德·戴维斯针对临床性强迫明显泛
目录
第一章 强迫诊治过程中的困境与出路
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都能量化,不是所有能量化的事都有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强迫是种古老的现象,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问题,与某些动物行为相似,有返祖现象或原始行为。因此,不管现代医疗科技如何发展,各种与强迫有关的仪器、药品如何层出不穷,单纯运用医学上的方法是很难彻底治愈强迫的。就如下文中的例子所示。
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
某来访者,男性,17岁,高中学生,患强迫障碍多年,曾在多家医院进行过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后服用过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经典的抗强迫药物,甚至连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也用过,但效果有限。期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疗效亦不佳。此后中断治疗。数月后一次因来医院看咳嗽问题顺路来心理卫生科看望一下就诊过的医生。当医生问他现在状况如何时,他说:“强迫已经没有了”。当医生好奇地请他谈谈经验时,他说:“自从上次离开医院后,无意中读到了托尔斯泰的书,发现写得太好了,就一门心思沉浸到里面,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强迫念头不来捣乱了。”
这是作者曾经遇到过的强迫障碍案例。许多时候,包括作者在内的医生们绞尽脑汁地对强迫者进行医学干预,但收效有限。
许多研究证据表明,大部分药物治疗强迫症的平均有效率不超过60%,典型症状的减少平均不超过50%。在治疗相当长的时间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继续深受强迫症状的折磨。
作者以为,药物在强迫的治疗中充其量起到了“游泳圈”或“拐杖”的作用,是一种对症治疗,无法起到像抗生素杀灭细菌那样根治疾病。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药物所起的作用是把强迫症状压制下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把症状隐藏或掩盖起来,甚至可能把人变得“迟钝”或“麻木”,让我们感觉不到冲突、恐惧和焦虑。如果停药,许多时候症状会马上冒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
边维尔早在1771年就已认识到药物/物理疗法治疗心灵痛苦的作用有限,他在《论女子淫狂》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C.A.Ross在1989年批评道:“为数众多陷入绝境的患者多年来一直接受无效的药物治疗,不断遭受二次创伤。”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更是尖锐地指出:“痛苦和不满是我们心灵旅程的自然组成部分,否定它们就是否定成长。可是,医药产业却藉人生中极为正常的苦恼和不满牟利,研制出一大堆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设法麻痹我们,使我们感觉不到苦恼和不满。”
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强迫症药物治疗之外的疗愈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并没有否定药物能缓解人的强迫思维、焦虑情绪等症状,只是在强调:从长远的角度看,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我们不应强行对他们进行药物干预。正如斯坦恩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所提出,如果产生强迫症症状的人自己不求助的话,不应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就需要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考虑,”他说道,“之所以这么多人产生了强迫症状却没有得到治疗,其原因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完全对付得过去。”他继续说道:
作为心理健康专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干预的认识,让他们了解自己随时可以得到这种服务。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有义务帮助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减少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我就怕大家会忘记,社会中大多数产生强迫症状的人,不管其情况是可以被诊断出的,还是被认作是在阈值以下的,抑或是在两者之间的,他们都还不是病人。因此,提出我们应当花费更多努力去找出这些个体,对他们加以治疗就意味着我们自认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何时需要我们的帮助。
从另一角度说,斯坦恩通过这段话在强调,对于强迫的疗愈来说,我们需要关注医疗以外的内容。
需要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
既然这些行为对实施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苦痛,那么他们产生苦痛的过程就相当关键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强迫症是群体、文化和家庭造成的。如果你的行为——比如说一丝不苟地把物品摆放整齐——被认作是古怪的,那你就会因此感到痛苦。反之,如果别人认为这是泥瓦匠大师才具备的手艺,有自己的用途,那你就不会因此感到痛苦了。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残障与人类发展系、医学教育系教授莱纳德·戴维斯针对临床性强迫明显泛滥现象所写。他在《强迫症历史》一书中提出,“强迫思维和强迫症最好被认作是一种疾病实体,其定义是临时的、不固定的,随着文化及历史变迁而变化,人们有时候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有用的,而在其他时候则认为它是有害的、可怕的。”他还说,“狄更斯的多产说明他的写作具有强迫性;我们在电影里要求情人对对方爱得死去活来,对不要命的运动员和一根筋的音乐家也都高看一眼,这些都是强迫症的倾向。”
是的,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强迫特点。例如,达尔文、弗洛伦·南丁格尔、约翰·班扬、塞缪尔·约翰逊、马丁·路德、温斯顿·丘吉尔,等等。
然而,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表示无法苟同上述观点,说戴维斯把所有不同类型的强迫行为全都绑在了一起。这样就把一般意义上的执念和临床意义上的强迫症混淆了,结果是稀释了后者的严重性。
作者以为,戴维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在强调强迫的临床治疗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上文这位强迫来访者的治疗经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观点。
从进化的角度分析,强迫症的某些特征比较原始,是动物性的表达。例如,水鼩就具有类似某些强迫者的刻板行为——严格按既定路线行走。据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茨观察,水鼩的行动路线“就像铁轨限制火车一样限制着它们的行动范围”。他观察到,水鼩在路线上遇到有石头挡在前方就会跳过石头,然而石头被拿走以后它们还是会在原来的位置跳起来。同样的,狗追逐自己尾巴的现象、鸟类强迫性梳理羽毛的现象都具有强迫症者的行为特征。
精神分析理论也提示,如果小孩在肛欲期(又称肛门期,约1-3岁进入)得不到满足便会很容易在长大后出现肛门性格(又称肛门神经症)。这类人往往表现出:吝啬、顽固、倔强;有洁癖;喜欢收集和囤积东西(把凌乱的房间、杂乱的抽屉和壁橱看作充满粪便的肠子,并乐于让这种混乱滋生蔓延);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和金钱;具有完美主义人格。而这些表现恰恰是强迫的主要临床特征。
因此,强迫症可能不仅仅是人的某种基本功能出现故障,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也许它并非一无是处,可能在人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例如,强迫行为的主要表现清洗、清洁、检查等在过去都可能是生活的策略,是早期人类或是更古老时期的哺乳动物赖以生存的自我保护习惯。再如,梳洗行为可以巩固群体内部的联系,防止疾病;对后代、配偶、领地和储备加以检查则能保障安全。弗洛伊德在《强迫行为与宗教实践》中甚至提出,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强迫行为和宗教信仰者所表达出的虔诚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强迫行为可能会起到宗教信仰所起到的宁心安神作用。Larry Eisenberg所说的“为了心理的宁静,妥协是通用的方式”,表达的也是这种观点。
综上所述,强迫问题不仅是医疗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人生问题。因此治疗时也必须把其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加以解决。下面再借电影《尽善尽美》来强调一下“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叫梅尔文的强迫症老头整天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他的第62部书,生活枯燥乏味,不愿意与任何人交往,还有让人不可理解的洁癖。他对生活及周边事物始终采取冷漠应对,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从不关心包括他的心理医生在内的任何人的变化。每次锁门他都怕没有锁牢,几乎每次都要重复锁五次。他每天唯一的活动是中午都会去同一家餐馆去吃饭,在这家餐馆里,只有唯一的一位名叫卡罗尔的女招待愿意为他服务。在强迫症的影响下,他将同性恋邻居西蒙的丑陋的小狗扔到垃圾堆里,并屡屡侮辱性格活泼而又温和的西蒙。
然而,正是在卡罗尔和那只丑陋的小狗的不断影响下,梅尔文走出了强迫。当西蒙因为被抢劫犯殴打而住进医院时,他不得不去照顾那只丑陋的小狗……在长时间的陪伴中,梅尔文竟然被这只小狗感化,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西蒙出院的时候,梅尔文是那么舍不得小狗离开,甚至还因为小狗的离去而流泪。从此以后,梅尔文开始关注他周围的人和事,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他所说,他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生活状态中去了。固然现在的生活状态没有以前的自由任性,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现在的生活更富有人情味。最终在追求卡罗尔的过程中不断被她的天真的热情影响,不断改变自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内容摘要
第一章强迫诊治过程中的困境与出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都能量化,不是所有能量化的事都有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强迫是种古老的现象,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问题,与某些动物行为相似,有返祖现象或原始行为。因此,不管现代医疗科技如何发展,各种与强迫有关的仪器、药品如何层出不穷,单纯运用医学上的方法是很难彻底治愈强迫的。就如下文中的例子所示。
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某来访者,男性,17岁,高中学生,患强迫障碍多年,曾在多家医院进行过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后服用过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经典的抗强迫药物,甚至连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也用过,但效果有限。期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疗效亦不佳。此后中断治疗。数月后一次因来医院看咳嗽问题顺路来心理卫生科看望一下就诊过的医生。当医生问他现在状况如何时,他说:“强迫已经没有了”。当医生好奇地请他谈谈经验时,他说:“自从上次离开医院后,无意中读到了托尔斯泰的书,发现写得太好了,就一门心思沉浸到里面,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强迫念头不来捣乱了。”这是作者曾经遇到过的强迫障碍案例。许多时候,包括作者在内的医生们绞尽脑汁地对强迫者进行医学干预,但收效有限。
许多研究证据表明,大部分药物治疗强迫症的平均有效率不超过60%,典型症状的减少平均不超过50%。在治疗相当长的时间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继续深受强迫症状的折磨。
作者以为,药物在强迫的治疗中充其量起到了“游泳圈”或“拐杖”的作用,是一种对症治疗,无法起到像抗生素杀灭细菌那样根治疾病。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药物所起的作用是把强迫症状压制下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把症状隐藏或掩盖起来,甚至可能把人变得“迟钝”或“麻木”,让我们感觉不到冲突、恐惧和焦虑。如果停药,许多时候症状会马上冒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
边维尔早在1771年就已认识到药物/物理疗法治疗心灵痛苦的作用有限,他在《论女子淫狂》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C.A.Ross在1989年批评道:“为数众多陷入绝境的患者多年来一直接受无效的药物治疗,不断遭受二次创伤。”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更是尖锐地指出:“痛苦和不满是我们心灵旅程的自然组成部分,否定它们就是否定成长。可是,医药产业却藉人生中极为正常的苦恼和不满牟利,研制出一大堆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设法麻痹我们,使我们感觉不到苦恼和不满。”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强迫症药物治疗之外的疗愈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并没有否定药物能缓解人的强迫思维、焦虑情绪等症状,只是在强调:从长远的角度看,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我们不应强行对他们进行药物干预。正如斯坦恩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所提出,如果产生强迫症症状的人自己不求助的话,不应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就需要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考虑,”他说道,“之所以这么多人产生了强迫症状却没有得到治疗,其原因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完全对付得过去。”他继续说道:作为心理健康专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干预的认识,让他们了解自己随时可以得到这种服务。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有义务帮助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减少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我就怕大家会忘记,社会中大多数产生强迫症状的人,不管其情况是可以被诊断出的,还是被认作是在阈值以下的,抑或是在两者之间的,他们都还不是病人。因此,提出我们应当花费更多努力去找出这些个体,对他们加以治疗就意味着我们自认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何时需要我们的帮助。
从另一角度说,斯坦恩通过这段话在强调,对于强迫的疗愈来说,我们需要关注医疗以外的内容。
需要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既然这些行为对实施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苦痛,那么他们产生苦痛的过程就相当关键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强迫症是群体、文化和家庭造成的。如果你的行为——比如说一丝不苟地把物品摆放整齐——被认作是古怪的,那你就会因此感到痛苦。反之,如果别人认为这是泥瓦匠大师才具备的手艺,有自己的用途,那你就不会因此感到痛苦了。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残障与人类发展系、医学教育系教授莱纳德·戴维斯针对临床性强迫明显泛滥现象所写。他在《强迫症历史》一书中提出,“强迫思维和强迫症最好被认作是一种疾病实体,其定义是临时的、不固定的,随着文化及历史变迁而变化,人们有时候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有用的,而在其他时候则认为它是有害的、可怕的。”他还说,“狄更斯的多产说明他的写作具有强迫性;我们在电影里要求情人对对方爱得死去活来,对不要命的运动员和一根筋的音乐家也都高看一眼,这些都是强迫症的倾向。”是的,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强迫特点。例如,达尔文、弗洛伦·南丁格尔、约翰·班扬、塞缪尔·约翰逊、马丁·路德、温斯顿·丘吉尔,等等。
然而,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表示无法苟同上述观点,说戴维斯把所有不同类型的强迫行为全都绑在了一起。这样就把一般意义上的执念和临床意义上的强迫症混淆了,结果是稀释了后者的严重性。
作者以为,戴维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在强调强迫的临床治疗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上文这位强迫来访者的治疗经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观点。
从进化的角度分析,强迫症的某些特征比较原始,是动物性的表达。例如,水鼩就具有类似某些强迫者的刻板行为——严格按既定路线行走。据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茨观察,水鼩的行动路线“就像铁轨限制火车一样限制着它们的行动范围”。他观察到,水鼩在路线上遇到有石头挡在前方就会跳过石头,然而石头被拿走以后它们还是会在原来的位置跳起来。同样的,狗追逐自己尾巴的现象、鸟类强迫性梳理羽毛的现象都具有强迫症者的行为特征。
精神分析理论也提示,如果小孩在肛欲期(又称肛门期,约1-3岁进入)得不到满足便会很容易在长大后出现肛门性格(又称肛门神经症)。这类人往往表现出:吝啬、顽固、倔强;有洁癖;喜欢收集和囤积东西(把凌乱的房间、杂乱的抽屉和壁橱看作充满粪便的肠子,并乐于让这种混乱滋生蔓延);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和金钱;具有完美主义人格。而这些表现恰恰是强迫的主要临床特征。
因此,强迫症可能不仅仅是人的某种基本功能出现故障,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也许它并非一无是处,可能在人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例如,强迫行为的主要表现清洗、清洁、检查等在过去都可能是生活的策略,是早期人类或是更古老时期的哺乳动物赖以生存的自我保护习惯。再如,梳洗行为可以巩固群体内部的联系,防止疾病;对后代、配偶、领地和储备加以检查则能保障安全。弗洛伊德在《强迫行为与宗教实践》中甚至提出,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强迫行为和宗教信仰者所表达出的虔诚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强迫行为可能会起到宗教信仰所起到的宁心安神作用。LarryEisenberg所说的“为了心理的宁静,妥协是通用的方式”,表达的也是这种观点。
综上所述,强迫问题不仅是医疗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人生问题。因此治疗时也必须把其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加以解决。下面再借电影《尽善尽美》来强调一下“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的重要性:一个叫梅尔文的强迫症老头整天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他的第62部书,生活枯燥乏味,不愿意与任何人交往,还有让人不可理解的洁癖。他对生活及周边事物始终采取冷漠应对,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从不关心包括他的心理医生在内的任何人的变化。每次锁门他都怕没有锁牢,几乎每次都要重复锁五次。他每天唯一的活动是中午都会去同一家餐馆去吃饭,在这家餐馆里,只有唯一的一位名叫卡罗尔的女招待愿意为他服务。在强迫症的影响下,他将同性恋邻居西蒙的丑陋的小狗扔到垃圾堆里,并屡屡侮辱性格活泼而又温和的西蒙。
然而,正是在卡罗尔和那只丑陋的小狗的不断影响下,梅尔文走出了强迫。当西蒙因为被抢劫犯殴打而住进医院时,他不得不去照顾那只丑陋的小狗……在长时间的陪伴中,梅尔文竟然被这只小狗感化,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西蒙出院的时候,梅尔文是那么舍不得小狗离开,甚至还因为小狗的离去而流泪。从此以后,梅尔文开始关注他周围的人和事,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他所说,他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生活状态中去了。固然现在的生活状态没有以前的自由任性,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现在的生活更富有人情味。最终在追求卡罗尔的过程中不断被她的天真的热情影响,不断改变自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主编推荐
谨以此书献给罹患强迫并正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献给从事强迫治疗的医护人员本书从新的视角对强迫及其治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纠正了有关强迫诊治过程中的误区;详细介绍了诊治强迫所需要的检查和评估,对于容易导致强迫的疾病进行了整理;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在论述强迫症常规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方法之外,深入探讨了强迫治疗中的深层次问题;并附以大量的临床治疗案例。本书内容通俗易懂,不仅适合强迫者及其家属阅读和使用,还可供健康保健人员、临床医护人员、精神/心理卫生工作者阅读和使用,对健康人群和高“压力”人群的修身养性也很好合适。包祖晓医学博士认为强迫首先是生活或者是人生问题,然后才是医疗问题,我们需要把强迫问题还原回生活/人生问题去加以解决。包医生说强迫症很好顽固、症状多变、患者的痛苦体验很好深刻,但传统医学疗法的疗效有限。如果强迫者能综合运用本书中介绍的治疗方法去疗愈,唤醒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自愈力,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治愈强迫,而且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成长。
精彩内容
第一章强迫诊治过程中的困境与出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都能量化,不是所有能量化的事都有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强迫是种古老的现象,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问题,与某些动物行为相似,有返祖现象或原始行为。因此,不管现代医疗科技如何发展,各种与强迫有关的仪器、药品如何层出不穷,单纯运用医学上的方法是很难彻底治愈强迫的。就如下文中的例子所示。
药物对强迫的治疗效果有限某来访者,男性,17岁,高中学生,患强迫障碍多年,曾在多家医院进行过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后服用过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等经典的抗强迫药物,甚至连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也用过,但效果有限。期间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疗效亦不佳。此后中断治疗。数月后一次因来医院看咳嗽问题顺路来心理卫生科看望一下就诊过的医生。当医生问他现在状况如何时,他说:“强迫已经没有了”。当医生好奇地请他谈谈经验时,他说:“自从上次离开医院后,无意中读到了托尔斯泰的书,发现写得太好了,就一门心思沉浸到里面,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强迫念头不来捣乱了。”这是作者曾经遇到过的强迫障碍案例。许多时候,包括作者在内的医生们绞尽脑汁地对强迫者进行医学干预,但收效有限。
许多研究证据表明,大部分药物治疗强迫症的平均有效率不超过60%,典型症状的减少平均不超过50%。在治疗相当长的时间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继续深受强迫症状的折磨。
作者以为,药物在强迫的治疗中充
相关推荐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保定
¥ 37.00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泰安
¥ 34.71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保定
¥ 31.57
-

平息战斗 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烟台
¥ 36.78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北京
¥ 35.02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北京
¥ 59.00
-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无锡
¥ 41.30
-

平息战斗 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北京
¥ 34.10
-

平息战斗 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保定
¥ 32.00
-

平息战斗 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
全新北京
¥ 34.10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