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障碍阅读·彩插励志版《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0.03 0.1折 ¥ 14.8 全新
库存144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海伦·凯勒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68121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4.8元
货号31175262
上书时间2024-09-0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海伦·凯勒(1880—1968),美国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188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在人生最初的十九个月,海伦还是一个健康的婴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六岁时,安妮·莎莉文担任她的家庭教师,从此成了她的良师益友。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海伦成功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女子学校,后又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190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她写出了第一本书《我的生活》,它不仅给聋盲人带来了希望,而且给千千万万健康人带来了鼓舞。海伦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让她对其他残障者的情况更加同情,促使她一生都致力于慈善事业。1906年,海伦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盲人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为盲人服务的社会工作。她到优选各地发表演讲,为盲人、聋哑人筹集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访问多所医院,慰问失明士兵。同时她还为贫民及黑人争取权益,呼吁世界和平。她崇高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1964年海伦被授予美国公民优选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次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
目录
\\\\\\\\\\\\\\\\\\\\\\\\\\\\\\\\\\\\\\\\\\\\\\\\\\\\\\\\\\\\\\\"我的生活 1
生命之初 2
顽皮的盲童 7
走出“埃及” 15
我的老师 19
亲近自然 25
“爱”是什么 29
思想的珍珠 33
圣诞快乐 42
行走在波士顿 45
大海历险记 50
山林秋思 53
踏雪寻欢 58
跳跃的语言 61
霜冻王 67
驱除阴霾 76
语言之美 81
灿烂的日子 84
学在剑桥女子学校 88
漫漫求学路 95
迷失“雅典” 101
阅读的乌托邦 110
我的七彩人生 123
一生的朋友 136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45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46
附录:老师眼中的海伦 163
初识小海伦 164
与海伦独自生活 171
奇迹发生 175
Water 178
思想的颜色 185
海伦参与的“第一个圣诞节” 190
不一样的海伦 194
延伸阅读 206
★本书名言记忆 206
相关名言链接 208
作者名片 209
名家点评 210
读后感例文 211
知识考点 214
参考答案 222\\\\\\\\\\\\\\\\\\\\\\\\\\\\\\\\\\\\\\\\\\\\\\\\\\\\\\\\\\\\\\\"
内容摘要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作家海伦·凯勒所著的自传体散文集,讲述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书中不仅对海伦·凯勒的成长经历及求学生涯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还透过“三天光明”的情景设定,来描述海伦·凯勒对普通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体会以及对人生的多重感悟。海伦·凯勒虽然失明、失聪,但她学会了阅读、识字,还顺利进入大学学习。这部作品将带我们走进海伦·凯勒的世界,了解她不平凡的学习、成长过程。
主编推荐
本书主要讲述了海伦·凯勒传奇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海伦从小聪明伶俐,并且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然而当她十九个月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海伦连日高烧、昏迷不醒。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黑暗无声的世界让她变得暴躁、任性。幸运的是,安妮·莎莉文老师来到了她身边,燃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莎莉文老师用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海伦了解和认识世界,将海伦不能感知的事物,通过独特的语言投入她的脑海。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海伦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她掌握了手语、盲文、唇语,学会了阅读、写作、与人交流,最后甚至成功考入了大学。海伦凭借顽强的毅力,付出超越常人几倍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她的经历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努力实现生命的价值。本书收录了海伦·凯勒的处女作《我的生活》、散文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及附录《老师眼中的海伦》。《我的生活》部分主要是海伦·凯勒的自述,对她的成长经历及求学生涯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部分透过“三天光明”的情景设定,来描述她对普通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的体会以及对人生的多重感悟。《老师眼中的海伦》部分以莎莉文老师的视角来讲述海伦·凯勒在接受教育后的变化过程,让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感受莎莉文老师对海伦的影响。让我们徜徉在作者朴实的语言世界中,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内心,真切地去感受那份坚强与善良。
精彩内容
\\\\\\\\\\\\\\\\\\\\\\\\\\\\\\\\\\\\\\\\\\\\\\\\\\\\\\\\\\\\\\\"我的生活生命之初“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备受家人的宠爱。“我”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能发出像“你好”“茶”“水”等简单的词的读音,“我”对许多事物充满好奇,甚至渴望模仿别人的行为。可是有一天,当“我”醒来,发现自己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时,“我”陷入了无尽的悲伤……我带着某种敬畏,我开始记录下我过去的生活。我仿佛是带着一种迷信的犹豫,揭开了那缠绕着我童年时代的金色薄雾似的面纱。撰写自传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当我试图将我早期的诸多印记分门别类时,我发现经过衔接过去与现在的几多岁月之后,事实与想象似乎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现在可以说是成年后的我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孩提时代的经历。回顾我生命最初的阶段,一些画面依然在我脑海中鲜活生动,但是“囚狱般的阴影笼罩着剩下的记忆”。此外,童年许多的快乐和悲伤已经褪色。而在我的早期教育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在我不断成长的兴奋中被逐渐淡忘。所以,为了不那么单调乏味,我将在一连串粗略的勾画中,试图只呈现那些对我来说最有趣、最重要的情节。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塔斯甘比亚——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
我的父系祖先,是定居在马里兰州的瑞士移民凯思帕·凯勒。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曾是苏黎世的第一位聋哑教师,出于机缘巧合,他竟然写了一本关于聋哑人受教育的书,有句话是颇有见地的:“一个国王的祖先中不一定没有一个奴隶;同样,奴隶的祖先中也不一定没有人当过国王。”我的祖父,凯思帕·凯勒的儿子,来到亚拉巴马州这片广袤的土地,最后定居下来。我曾经听说祖父每年都要从塔斯甘比亚镇骑马到费城,购置农场所需的农业用品。我的姑妈一直保存着许多当年祖父写给家里的书信,信中描述了这一旅途中迷人而生动的景象。
我的祖母是拉法叶一个副官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是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地方长官亚历山大·斯泼茨伍德的孙女。她也是罗伯特·E.李的堂姐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一名同盟军上尉,而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很多。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和苏姗娜·E.古德希婚后许多年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利。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纽伯利港,后搬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他加入南方军队成为一名陆军准将。他和露茜·海伦·埃弗雷特结了婚,露茜和爱德华·埃弗雷特、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博士同属于埃弗雷特家族。战争结束后,举家迁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直到那场剥夺了我视觉和听觉的疾病来临前,我们居住的地方很小,仅有一个方形的大房间和一个供仆人睡觉的小房间。在南方,人们习惯在自己的家园旁边加盖一所小屋以备不时之需。内战结束后,父亲也盖了一所这样的小屋,在他和我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在那里。小屋完全被攀缘的葡萄藤、蔓延的蔷薇和金银花覆盖了。从花园里看,它像极了一个用藤蔓搭成的凉亭。小小的走廊在满眼的黄色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景致中被隐藏起来,成了蜂雀和蜜蜂最喜爱的领地。
我们一家居住的宅院,离小凉亭只有几步台阶。它被叫作“绿色常春藤”,因为房子和周围的树、栅栏都被美丽的英格兰常春藤包围着。这个老式的花园是我儿时的天堂。
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我常常沿着坚实的黄杨木篱笆,凭着自己的嗅觉,感受那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心绪不宁之时,我也会去那儿,把灼热的脸颊藏在那清凉的树叶和草丛中,寻求慰藉。完全将自己沉浸在花的海洋里是多么愉悦啊,我幸福地漫步到一处又一处。忽然间,我来到一株美丽的葡萄藤下,凭着它的花和叶子,我认出了这就是花园尽头缠绕着那倒塌了的亭子的那一株。这儿还有绵延的铁线莲(别名铁线牡丹、番莲等,有“藤本花卉皇后”的美称),低垂的茉莉和一些香气扑鼻的被称作蝴蝶百合的花儿,因为它们易碎的花瓣就像是蝴蝶的翅膀。但在所有的花中还是蔷薇最可爱。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花房里发现如同在我南方的家里一样,爬满如此令人心醉的蔷薇。它们那长长的藤一串串悬挂在门廊上,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的芳香,没有丁点儿尘土的味道;而在清晨,经过朝露的洗礼,它们是如此柔和,如此纯净,我禁不住好奇:上帝花园里的水仙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初始是如此简单,就像其他的每一个小生命一样。我来,我看,我挣扎。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婴儿的到来一样,为了给我起名儿总是争论不休。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是不能随随便便起名字的,每个人都这么强烈地认为。父亲建议用米尔德里德·坎贝这个他非常崇敬的祖先的名字,并且拒绝参加更多的讨论。后来还是母亲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希望我以她母亲婚前的名字命名,就是海伦·埃弗雷特。但是在带我去教堂的途中,父亲兴奋得忘记了这个名字,这很自然,因为这个名字是在他拒绝参加的讨论会上决定的。当神父问他为这孩子起什么名字时,他只记得要以我外祖母的名字为我命名,于是,他给这个孩子起了“海伦·亚当斯”的名字。
据说,当我还不会走路时,我就已经显露出一种好学而又自信的气质。看见其他人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渴望去模仿。在六个月时,我能发出“''''''''”〔Howdoyoudo(你好)〕的音,并且有一天因为我十分清楚地说出“茶,茶,茶”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甚至在我生病以后,我还记得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所学到的其中一个单词,那就是“水”,在所有其他语音完全丧失后,我还能继续发出这个单词的一些音。而当我学会拼写这个单词时,我就停止去发出这个“wah-wah”(不完整的“水”的发音)的读音了。
他们告诉我,我一岁的时候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抱出浴缸,放在膝盖上,而我突然被那些在阳光底下、在平滑的地板上舞动的树叶摇曳的影子所吸引,我从母亲的膝盖上滑下来,几乎是跑向它们。等这一股冲力用完,我就摔倒了,哭着要母亲把我抱在怀里。
这样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伴随着知更鸟和模仿鸟悦耳歌声的短暂的春天,一个果实丰硕、蔷薇花盛开的夏日,一个满是金色和深红色的秋季匆匆而过,把它们的礼物留在一个热切喜悦的孩子的脚下。之后,在沉闷的二月里,随之而来的疾病使我失去了听觉和视觉,又将我推入新生婴儿般的蒙昧无知中。他们称之为急性胃部和脑部充血。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然而,一天清晨,高烧突然神秘地消退,就像它发生时一样。那个早晨全家为此惊喜万分,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医生也没有意识到我将再也不能看、再也不能听了。
如今,我依然对那场大病有着模糊的记忆。我尤其记得母亲在我焦急痛苦之际给我温柔的抚慰。我还记得,疼痛和迷乱将我从半睡中搅醒,把又干又烫的眼睛转向墙壁,离开那些我曾经喜欢的光线,这光线在我眼中变得黯淡了,而且日益黯淡。但是,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如果真是记忆的话,别的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倒像是一场噩梦。慢慢地,我逐渐习惯了围绕着我的寂静和黑暗,并且忘记了那曾经的不同,直到她——我的老师的到来,带我放飞了自己的灵魂。但是在我生命最初的十九个月里,我已见过宽阔无垠(没有边际。垠,yín)的绿色田野、明亮的天空,还有花草和树木,它们都没有被那个随后而来的黑暗吞噬掉。如果我们曾经看见过,那么“白天就是我们的,包括白天展示出来的一切”。
顽皮的盲童行走在黑暗无声的世界中,“我”感受到了孤独,开始变得暴躁、固执。但是家人和朋友们依旧爱护着“我”:母亲用自己的方式让“我”学会用简单的手势与人沟通;父亲总是尽力给“我”最好的东西;玛莎·华盛顿永远迁就“我”,陪“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世界。
我无法回忆起在我生病后最初的几个月都发生了什么。我仅仅知道我坐在母亲的膝盖上或当母亲去做家务时拽着她的裙摆。我的手感觉每一样东西,注意每一个动作,用这种方法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很快,我感到一种要与他人沟通的需求,并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笨拙的动作。摇头意味着“不”,点头表示“是”,拉意味着“来”,而推则意味着“去”。如果我想要的是面包呢?我就模仿切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要我的母亲在用餐时做冰淇淋,我就做出打开冰箱的手势,颤抖着,表示很冷。此外,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了很多。当她让我拿什么东西给她时,我总能明白她的意思,我会跑到楼上或是她指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确,在漫长的黑夜里我得到的光明和快乐,完全归功于母亲爱的智慧。
我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店里拿回来的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放起来,并且能从中分清自己的。我也知道母亲和姑妈梳妆打扮是要出门,我总是请求跟着她们出去。当有很多客人时,我总是被带出来见他们;当客人离开时,我向他们挥手告别,我依稀记得这些手势表达的含义。一天,一些先生们拜访母亲,我感觉到前门的开合和其他声音,便知道他们到了。突然一闪念,在任何人可能阻止我之前,我跑到楼上,穿上一件我自以为得体的裙子。站在镜子前,就像我曾经看到别人的那样,在头上抹发油,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粉。然后,我将一副面纱用针别在头上,遮住我的脸并垂落搭在肩上。然后,我匆忙地在我细小的腰部套上一件大大的裙撑,让其悬垂于身后,几乎贴在裙子的褶边上。如此不伦不类装扮一番,我就下去帮着招待客人。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意识到与别人不同是什么时候,但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我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想做任何事时,不像我那样用手势,而是用他们的嘴交谈。有时我站在两个正在谈话的人中间,触摸他们的嘴唇。我无法理解,并因此感到恼怒。我嚅动我的嘴唇,疯狂地打着手势却毫无结果。
我想我当时是知道自己有多淘气的,我踢了爱拉——我的保姆,我知道那伤害了她,而当我平静下来后,我有一种类似愧疚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种感觉有没有让我在之后感到不称心的时候,行为稍微收敛一些。
在这些日子,一个黑人女孩儿玛莎·华盛顿(我们厨师的孩子)和一只虽老但曾经相当出色的猎狗贝莉常伴我身边。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在我使唤她做事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在她面前飞扬跋扈(骄横放肆。跋扈,báhù)使我感到满足,她一般则顺从我的粗暴,而不是冒险和我面对面起冲突。我体格健壮,个性积极主动且不计后果。我十分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且总是喜欢我行我素,即使要为此打上一架也在所不惜。我们在厨房里度过了许多时光,捏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磨咖啡,为争抢做蛋糕的碗而争吵不休,并给一群围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它们大多非常驯服,会吃我手中的食物,并让我抚摩它们。一天,一只大雄火鸡从我手上抢走一个西红柿,叼着逃跑了。也许是受到火鸡阁下成功的启发,我们偷走了厨师刚做好的蛋糕,躲到堆放木料的地方,吃得一干二净。之后我就生病了,我想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有只珍珠鸡喜欢在隐蔽的地方筑巢,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深草丛中找寻它下的蛋。当我想去找蛋,却又无法告诉玛莎·华盛顿时,我就将手摊开放在地上,示意草丛里有某种圆形的东西,这时玛莎总能明白。当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鸡窝时,我从不允许她拿着蛋回家,通过明显的手势让她明白她有可能摔坏它们。
储藏玉米的货仓、养马的马厩(饲养马的房子。厩,jiù)和挤牛奶的院子,对玛莎和我来说是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当挤奶工挤奶时,他们会让我把手放在母牛身上,我也因为好奇而经常被牛尾甩打。
为圣诞节做准备对我而言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当然,我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是我喜欢这种充满整个屋子的令人愉快的香味以及能使玛莎和我保持安静的精美食物。很抱歉,我们总是很碍事,但这丝毫没有打扰我们的快乐。我挂起了我的长筒袜,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然而我不记得这种仪式曾让我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好奇心要在天亮前醒来去找寻我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对恶作剧有强烈的爱好。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儿坐在阳台上。一个皮肤像黑檀木一样黑,用鞋带将绒毛般的头发绑成一个个小辫子,看上去她的头就像长满了螺丝锥。另一个皮肤白皙,有着长长的金色鬈〔quán,(头发)弯曲〕发。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大两岁或是三岁。年幼的那个孩子看不见东西——那就是我,而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在忙着剪纸娃娃,但是我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开始剪碎我们的鞋带,剪掉所有我们可以够得着的金银花的叶子,之后我将注意力转向玛莎螺丝锥般的头发。起初她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服从了。考虑到依次轮流才算公平,她抓着剪子剪掉了我的一缕鬈发,要不是母亲及时制止了她,她将剪掉我所有的头发。
我的另一个伙伴,我们的狗贝莉,又老又懒,喜欢在火炉旁打瞌睡,却不愿和我们玩耍。我十分费劲地去教它手语,但是它既迟钝又没兴趣。它有时候会突然惊起并且兴奋地颤抖着,然后像一只瞄准了猎物的猎犬一样严肃机敏。我那时还不了解贝莉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但是我知道它不会照我的话去做。这让我感到恼怒,因为我的手语课通常就像是只有一个人的拳击赛,没有对手,被迫终止。贝莉起身,伸一个懒腰,轻蔑地嗤两下鼻子,就到壁炉的对面又趴下了。我感到厌烦和失望,就又去找玛莎了。
幼年的许多事情深植在我的记忆里,尽管都是独立的片段,但对我来说却异常清晰。这使得我在寂静、漫无目的、没有光的生活中仍能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在围裙上,我将它搁在起居室里壁炉一闪一闪的炉火面前,展开晾干,这条围裙干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于是我挨得更近,把围裙放在火炉上面。火苗迅速蹿(cuān)起来,火焰团团围住我,以至于不到一会儿我的衣服全被烧着我发出恐的叫声,老保姆维尼闻声赶了过来。她拿了一条毯子裹住我,几乎让我窒息,但火却被扑灭了。除了我的手和头发,其余地方没有被烧得很厉害。
大约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在了储藏室里,因为人们都在其他屋子干活儿,她被迫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她拼命地敲门,而我则坐在外面走廊的台阶上,感受着重重敲门带来的震动,高兴得开怀大笑。这次严重的恶作剧使我的父母确信,我必须尽快地受管教。在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到来之后,我寻找到一个机会把她锁在她的屋里。我拿着母亲让我交给莎莉文小姐的东西上楼,然而在我交给她后,立即将门砰地关上,锁上,并将钥匙藏在大厅的衣柜底下。我没有被劝诱说出钥匙藏在哪儿。父亲不得不搭了一个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这让我开心极了。几个月后,我才交出钥匙。
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从这所藤蔓覆盖的房子搬到了一所新的大房子里。家里包括父亲、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之后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初清晰的记忆是我一路经过成堆的报纸,来到他的旁边,发现他独自一人在面前举着一张纸。我怀着巨大的困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他的眼镜,认为这样有助于揭开这个秘密。但是好几年我都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纸是做什么的,明白父亲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父亲亲切而宽容,热爱他的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很少离开我们。据说,他是一个好猎手,也是一个神枪手。除了家人,他最爱的就是狗和猎枪。他也十分好客,极少不带客人回家,以至于成为一种癖好。他尤其骄傲的是这个大花园,据说,他在里面栽种了全镇最好的西瓜和草莓,并且总是把最先熟了的葡萄和精挑细选的草莓摘给我。我记得他领着我穿过一棵棵果树、一簇簇藤蔓时亲切地抚摩我,他对任何让我高兴的事都饱含热情。
父亲还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在我学会了语言之后,他常常将他的最有趣的奇闻逸事笨拙地拼写在我的手上,没有什么比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复述这些故事更使他快乐的了。
1896年,我正在北方享受夏天最后的美丽日子,突然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得病时间不长,短时间急性病发作后,就与世长辞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巨大的悲痛——也是我的第一个关于死亡的人生体验。
我怎样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跟我亲密无间以至于谈论她似乎有点儿失礼。
很长一段时间,我将我的小妹妹视作入侵者。我知道我已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宠儿,我的心中充满了嫉妒。她经常坐在母亲的腿上,而那是我过去常常坐的地方,并且似乎抢走了母亲所有的关爱和时间。这让我很受伤,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甚至感觉受到了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很宠爱却又经常受我虐待的洋娃娃,我给它取名“南茜”。唉,它是我发脾气和情绪不稳定时无辜的牺牲品,以至于它浑身变得一塌糊涂。我有许多会说话、会哭、会眨眼的洋娃娃,然而我从没像喜爱可怜的南茜一样爱过它们中的一个。南茜有一个摇篮,我经常花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轻轻晃动它。我非常警惕地保护着南茜和摇篮,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竟然舒服地睡在摇篮里。鉴于当时我对我妹妹还没有建立起亲情的纽带,所以感到十分生气。我冲向摇篮想要翻倒它,要不是母亲在她落地之前抱住她,这个小婴儿可能就被摔死了。所以说当我走在双重孤独的谷底时,我对充满爱意的言语、动作和友谊中包含的温柔情感都知之甚少。但是后来,当我重新建立起人类固有的情感,米尔德里德和我开始心灵相通时,我们常常会手拉着手去任何地方玩耍,尽管她不明白我的手语,而我也不懂她孩子气的话。
走出“埃及”“我”一直待在黑暗无声的世界里,渴望拥有更多表达自己的方式。大约六岁时,“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前往巴尔的摩看病。“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出行,让“我”逐渐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知识和爱。
此时,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渴望与日俱增。我那有限的手势变得越来越不够用,随着表达自己失败而的是一种情感的爆发。我感觉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我,我做了疯狂的努力让自己挣脱。我斗争——不是因为这种斗争对事情有所帮助,而是我内心中反抗的精神很强烈;我经常失声痛哭,弄得精疲力竭(精神非常疲劳,体力消耗已尽,形容极度疲乏)。如果碰巧母亲在附近,我会扑到她怀里,太过痛苦以至于忘记了发脾气的原因。可没过多久,这种想要与人交流的愿望变得如此急切,以至于这种爆发每天都在随时随地发生。
我的父母陷入深深的悲痛和不知所措中。我们住的地方离任何盲人或聋人学校都很远,而且似乎没有人愿意来塔斯甘比亚这个偏远的地方,去教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确实,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怀疑我是否能受教育。母亲仅有的一点儿希望来自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等)的《美国札记》。她读了他的关于劳拉·布里奇曼(最早成功受到教育的聋哑盲人之一)的记述,并模糊地记得她又盲又聋,仍然接受了教育。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因为她得知那位发明教育聋哑人和盲人方法的豪博士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他的方法也很可能就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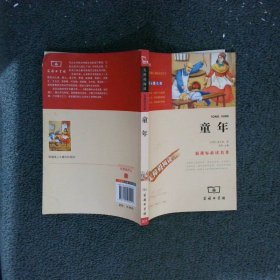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