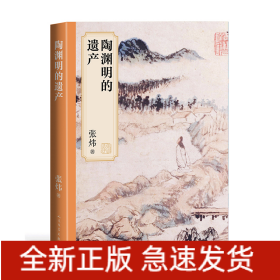
陶渊明的遗产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9.6 5.9折 ¥ 50 全新
库存8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张炜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81094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0元
货号31827225
上书时间2024-05-2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0余部;诗学专著多部;诗歌作品《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
近作《独药师》《我的原野盛宴》《寻找鱼王》《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内容摘要
《陶渊明的遗产》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对陶渊明多年研读、体悟的结晶。在本书中,张炜先从“魏晋这片丛林”说起,将读者带入陶渊明所身处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的魏晋时期。我们由此触摸到陶渊明挣脱官场、投身田园与农事所蕴含的丰厚意义:在“文明法则”与“丛林法则”之间,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坚守。张炜还通过与高更、梭罗、荷尔德林、彭斯、维吉尔、托尔斯泰、蒙田及屈原、庄子、王维、“竹林七贤”、孟浩然等诸多艺术家的对比,将陶渊明置于广阔的价值参照系中。在文明史上众多相似与不同的比照下,陶渊明的光辉分毫未见,而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孤高标本。此外,本书还捕捉到陶渊明人生中众多的生命沉思,并揭示其深刻的哲学意蕴与诗学价值,颇能给当代人以巨大启发。
精彩内容
海拔高度像陶渊明这样真实地描述和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极度艰辛的生活,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比如说杜甫困守长安时写下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史之乱后,他全家逃难到甘肃同谷,写下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甚至描述了他在山里白头乱发争抢橡栗的狼狈相。还有《复阴》这首诗里写道:“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陶渊明和杜甫一样,他们的许多诗就像日记一样,用以记录个人的度日方式和发生的某些事件。生活怎样,就怎样入诗,这是显见的。从文本上看,陶渊明是呈现多,表现少。他直感直述之外,现实经验很难把握的那部分,诗里就较少出现。实事实写,让经验紧紧地跟随,而不是过多地引申和想象。诗人更多地写了普通人的普通经验,让人在阅读中可以充分而直接地参与其中,这就与其他诗人的表达有所不同。比起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诗人所表达的那种经验、况味,陶诗更容易与一般人的心得体会同步。我们同样对一种艺术发出惊叹,发出赞美,原因却是很不一样的。
陶渊明的诗更让人产生一种亲和感,就好像他在我们身边、左右、中间。如果说李白好像在台上表演,而陶渊明则和我们一样,是坐在观众席上的。谢灵运、杜甫、李商隐、苏东坡等,都离我们稍稍地遥远,他们都站在高处,而陶渊明就立在我们身侧,和我们一起笑谈耳语:“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饮酒二十首·其九》)陶渊明时刻都把自己置于普通人的地平面,这不仅是因为其生活地位造成的,也不仅是日常的艰辛所致。像古代的其他许多诗人生活都很艰苦,但他们并不会因为现实境况的苦与累而放低自己诗中的身段。他们仍然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高处,许多时候形同精神贵族。李白对“谪仙人”之号多有认同,甚至都不是人间之子,高为天人了。李白是踏云而行的天人,杜甫是行走大地的旅人,陶渊明则是匐匍泥土的农人。苏东坡是公认的大才子,一度官居京城,属于一个从庙堂到民间的人,是一个从上面下来的人,这一点让人始终难忘。事实上现实中的人不会忘记诗人身份的特异,后来的读者也始终会得到这种提醒。这种身份记忆即便不在诗人的作品中直接留存,也会从文字间洇渗出来。不同的经历会洋溢出不同的气息,这是很难遮掩的。
比较看,陶渊明的农家生活是更为自然的和日常的,他的诗歌也是如此。与平时的生活一样,陶渊明的诗歌从风韵到辞章都不那么耀眼和显著。一般来说诗的标签总是贴在诗人身上的,而陶渊明的标签却大多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也算一个特例。
陶渊明的朴实无华到了这样的地步: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表达上,他给人的外部观感都没有多么“高”,其“海拔高度”似乎都与大众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其内在质地与大众的区别。从经济地位而论,陶渊明后来甚至还低于一般人,而其生命质地的优异,却始终远远高出一般人。
这里的“海拔高度”更多地是指做人姿态、心理态势,是给人的日常观感。
陶渊明精神生活的内质与诗的高度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伪常人”。他务农,但许多时候并不是农民的心理。李白很少干过正常人的事情,苏东坡严格讲也没有干过多少,杜甫由于生活窘迫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他的“心理海拔”却始终很高。只有陶渊明在实际生活和“心理海拔”上,都让人觉得是常人的高度,甚至还低于常人。从这个角度去透视他的人生和艺术的奥秘,似乎能察觉到一点什么,令人怦然心动。
金句?要研究“丛林法则”,就必须弄清它的“食物链”。在丛林中,“食物链”的顶层是狮子虎豹,再往下是豺狼鬣狗,最后一级就是兔子鼹鼠这类吞食草虫的小动物了。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期,位于“食物链”最顶端的嗜血动物,就是桓玄和刘裕之类的大军阀。夹在食物链中间的各种“动物”要自保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入伙,进入嗜血的强势集团,一起狩猎,共享猎物;另一个办法就是结伙,像野狼和鬣狗那样。
?诗人将无比的愤怒与勇气留在了诗中,而且借古喻今,小心暗喻,是足够谨慎了。这当然是必要的,是在一种特殊时势下的特殊表达。当时风行的玄与佛,清谈与任诞,不过是一个严厉时代酿出的另一杯酒而已,对一个具有深刻责任感的诗人,真是苦到了无法下咽。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可能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养生”,没法“逍遥”也没法“安命”。
?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博斗下去。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倔强地存在下去。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
?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谜底又在哪里?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存在于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做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显得朴素天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可操作的”。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
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苦难对于陶渊明是无边的,这无边苦难所放射出的精神的光辉,都是后人站在遥远之地才能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讲,这既是一笔了不起的遗产,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和感动。这是诗人必将付出的人生代价,也是他用整个生命做出的贡献。陶渊明被一种文明培植,这使他不得冲入“丛林”,没有以自己的动物性展开一场生死对决。
?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陶渊明在“丛林”之中、在“丛林”边缘所不得不回答的尊严问题,入世出世问题,如何生存、怎样战胜自己的懒惰和懦弱等等一系列大问题时,留下了宝贵的“遗言”。从这个角度去看诗人的全部文字,是最具价值和意义的。
?陶渊明最后可以饿死,可以穷困而死,但其思想信念和精神却没有溃散。他始终是一个“挺住”的灵魂。在激荡的时代横流里,他是一座没有冲毁的个人岛屿,而不是一滩溃散的泥土。他没有在时代的水流里面变为一汪浑水的源头,而成为一块使周边水浪清澈流过的岩石。
?我们对诗人如何判断?我们最欣赏的当然还是他敢于对“丛林法则”说“不”。无论遇到多大的诱惑,面临多少不可解脱的痛苦,即便饿死,也仍旧要说出这个“不”字。
这就是“挺住”,这就“意味着一切”。他靠什么挺住?既非对神的信仰,那就一定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是生存的本能。最重要的,还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有业已形成的自然观和文明恪守力。他是一个直到最后都未能放弃原则、未能丢失尊严的人。他可以失去生命,但他没有被打败。如此,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看成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被后人强调得太多,所以也就放大了。因为这句话说得那么坚毅、解气,算是掷地有声。我们后来人在陶渊明这次痛快的发泄面前,会有同样的快感。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个人做出如此酣畅淋漓、斩钉截铁的社会宣示,背后肯定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他一定长时间竭尽全力,用生命一点点构筑起强大的底部支撑力,最后才完成了这个具有经典意义的转身。
?作为一个诗人,陶渊明的诗文歌赋艺术之所以充满魅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长于细节描写,能够囊括蕴含许多极小的、动感很强的局部。这作为一个诗人和散文家是较难做到的,因为这往往不是他们的本领,而是小说家的擅长。
?陶渊明对于死亡的反复咏叹,已经成为医治个人不幸的一味良药。对于一个几近绝望、十分痛苦的诗人来说,切近的死亡之思甚至可以看成是他挖掘的一道人生“掩体”,用以抵抗生活的黑暗。
陶渊明显然需要这样的一道掩体,因为他与自己的人生危运常常进入超乎一般的对抗阶段,他想喘息,想生存,甚至想到了最后的胜利。
?自我完成的、相对独立的个人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自足的,而不过分依赖于其他的存在而存在。很多所谓的反抗者离开了其冲撞和抵抗的对立面,自己便自然地消失和瓦解。然而陶渊明不是,他的整个人,他的作品以及品格要义,离开了魏晋还仍然存在,离开了那种所谓的强权、篡晋的士族势力,离开了那个黑暗的时世,也仍然存在并且同样饱满,常温常新。因为他具有强大的个体意义和个体内容。
?鉴定现代精神世界正在发生的灾变,也许可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章作为一片试纸,取来放进心中,然后仔细观察它的颜色如何变化。
?陶渊明真是一个运用“减法”生活的典型。他先是把心债减下来,把欲望的两手放下来,于是一切都减下来了;特别是,这种减法表现在了艺术方面,造就了他极平实简单又极微妙的诗章。
?原来我们刚开始获取的只是一种极外部和极粗疏的表象,陶诗那种内在的准确和精微,那种诡谲特异之美隐藏得竟是如此之深。这正是一种更为深切和老练的旷达与自信,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万物的卓越,是心手高度一致的诗人才有的火候。诗人用极微的动作调拨的,是最精细的奥妙。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