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一罚四】意外旅行团(爱尔兰) 席亚拉·格拉蒂著
集团直发,全新正版书籍,假一罚四,放心选购。可开发票
¥ 22.6 4.5折 ¥ 49.8 全新
库存20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爱尔兰) 席亚拉·格拉蒂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1159911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9.8元
货号3510900
上书时间2024-06-30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席亚拉·格拉蒂,靠前畅销书作家,被誉为“爱尔兰的乔乔•莫伊斯”。她34岁开始从事写作,擅长用幽默、俏皮的文字书写温暖人心的故事,处女作一上市便惊艳四座。她已出版7部文学作品,曾入围言情小说家协会2015年当代言情小说奖。本书版权已卖至美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等地。目前,她与丈夫、三个孩子、一只狗生活在都柏林。
目录
《意外旅行团》是一本公路主题的女性治愈小说。女主角特里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 但为了陪伴好友艾瑞丝, 她毅然决然带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爸爸, 开启了一趟意外之旅。旅途中的一连串奇遇, 让特里尝试了很多不曾想过的事, 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婚姻生活、亲子关系, 逐渐探寻出真正的自我。这部小说通过有笑有泪、惊喜连连的公路故事, 歌颂真挚而美好的友谊, 展现陪伴的力量, 为女性读者带来身心的治愈和深切的感动, 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内容摘要
58岁生日这天,艾瑞丝失踪了!
这接近不在特里的计划内。她为艾瑞丝准备了蛋糕,给艾瑞丝的朋友打了电话,从养老院接上了痴呆的父亲,兴冲冲来到艾瑞丝的家,打算为她庆生。可是,房间里一切都静止了,衣柜、浴室空空如也。一张轮渡预约表躺在电脑里,两只白色信封上面是艾瑞丝又大又浮夸的字迹:
我最最亲爱的特里,
你要知道的件事,是你什么也做不了。我已经下定决心。艾瑞丝已经下定决心,特里却还抱着一丝侥幸。意外之外,特里带着父亲,追上艾瑞丝,驶向未知的旅程……
主编推荐
★如果你曾为《一个叫欧维的男人》落泪,这本书会带你驶向新生。“爱尔兰的乔乔•莫伊斯”又一部治愈新作。书中将生死、友情、亲情、婚姻等深刻的命题,用一场六天、四国的公路旅行串联起来,充满治愈力量。
★女人对女人的陪伴,是男人不可替代的。得知自己的好友在58岁生日当天只身前往瑞士安乐死,作为好友,你能为她做些什么?55岁的家庭主妇特里抛下丈夫和孩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趟意外之旅。即使不能说服好友回心转意,至少还可以忠实地陪伴她。
★突破人生瓶颈,才能看到更辽阔的人生。感受不到爱意的婚姻、单向依赖的家庭以及厌倦当下而不知未来在哪儿的自我缺失,正是家庭主妇特里面临的生活困境。一趟旅程让她走出舒适圈,探索更多可能性。
★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主妇、一个生命即将开始的硬化症患者,加上一个老年痴呆的老头儿,意外地开启了一趟“穷途末路”之旅。没带行李、路边摔伤、出车祸、激烈争吵、悬崖边犯病,他们该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状况?又有什么样的意外惊喜?
精彩内容
第1条先打转向灯艾瑞丝?阿姆斯特朗失踪了。
也就是说,她不在她原本应该在的地方。
我劝自己不要担心。毕竟,艾瑞丝是个成年女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照顾好,何况她的自理能力强过很多人。
我确实容易杞人忧天。问问我的女儿们,问问我的丈夫,他们会告诉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可担心的话,我就会万分担心。要是我没什么事儿可担心,就会觉得自己肯定是忽略了什么东西,当然了,这么说有些夸大其词,虽然我觉得这是大实话。
而艾瑞丝呢,她会告诉你她打算做什么,然后迈开步子,马上去做。她就是这种人。今天是她的生日,她的五十八岁生日。
“人们把生日视作一个契机,可以借此哄骗女人们,说她们在眼下这个年纪看上去光彩照人。”在我提议庆祝生日时,艾瑞丝这么说。
可这是实话,以艾瑞丝的年纪来看,她确实光彩照人。但我没这么说,我说的是:“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庆祝一下。”“我会用天鹅式或者下犬式这类带着兽性的方式来庆祝。”艾瑞丝说道。之前她告诉我,她已经预约好入住一家瑜伽疗养院。
“可是你讨厌瑜伽啊。”我说。
“我以为你会高兴呢。因为你总是告诉我,瑜伽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MS)的人很有好处。”我今天的计划是去看看爸爸,然后给威克洛的瑜伽疗养院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会带上给艾瑞丝的生日蛋糕开车过去。这样,他们就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了。艾瑞丝当然不愿小题大做,可每个人都应该在过生日的时候吃上一口蛋糕。
然而,当我抵达养老院时,我的父亲正同一名经理一起坐在等候区。他坐在椅子上,脚边的地板上放着他的旧旅行包,边缘处略有磨损,但完全能用。
“一个星期。”经理说。据说这是专业灭虫人员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害虫,他是这么说的,我由此认为,他说的是大老鼠,如果只是小老鼠的话,他就会直接说是小老鼠,对吧?
我父亲住在硕鼠出没的养老院里,他在那里玩填色游戏、输掉宾果游戏、唱歌,等着马上会从商店回来的我妈妈。
“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爸爸转去另一家养老院。”经理提供了备选方案。
“不用,我会带他走。”我说道。我也只能这么做了。曾经,我以为我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家照顾他,就像多年来妈妈做过的那样。我觉得我扛得住。坚持了半年之后,我不得不把他送进养老院。
我把爸爸的旧旅行包放进后备箱,紧挨着生日蛋糕。我用蓝色的糖霜做海,用灰色的糖霜做岩石,又在岩石上用糖霜画了个简笔小人儿艾瑞丝。她每天都去高岩游泳。即便是十一月,即便是二月,她天天都像是游在七月天里。我想,她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个蛋糕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好,远远超出了烹饪书上的预估时间。布兰登说,这都是因为我精益求精。可是,这蛋糕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出于一个完美主义者之手。蛋糕歪歪扭扭的,重心不太稳,仿佛经受了恶劣天气的摧残。
我为爸爸系好副驾驶座上的安全带。
“你妈妈在哪儿?”他问。
“她马上就从商店回来。”我答道。我早已不再一遍遍地告诉他,她已经不在了。这个消息每次都让他非常难过。他脸上的悲痛是那么明显,那么生动,一如我自己的悲痛再现。我不得不看向别处,闭上双眼,把指甲深深嵌进手上的皮肉里。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
“先打转向灯。”爸爸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每当念诵交规时,他就会这样。他记得所有交规。在你的大脑中,肯定有某些封闭区域是阿尔茨海默病无法闯入的。
他下达指令时,我照做了,然后在出发前给瑜伽疗养院打了个电话。
但是艾瑞丝不在那里。
她压根儿没去。
事实上,接线员说,他们那里并没有艾瑞丝?阿姆斯特朗的预约记录。这名接线员语调平稳,一听就知道每天都在练习瑜伽。
艾瑞丝之前叮嘱过我,这星期都别给她打手机,因为手机会关机。
我打了她的手机。
果然关机了。
我开车去了她在菲尔特里姆的小别墅。每一扇窗的窗帘都放了下来,整栋房子看起来就是一个女主人已经离开的房子。我把车停在了路边,这里之前总是停着她的老捷豹。出事故之后,艾瑞丝很快就恢复了视力,受伤的只是她撞上的灯柱,但是她的医生不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艾瑞丝说她并不想念那辆车,但是她问我,能否帮她把钥匙还给买了这辆车送她的男人。她说她有个会议,走不开。
“一辆车而已。”她说,“这个本地出租车司机长得像丹尼尔?克雷格,做爱的时候从不说话,熟悉城里的每一只老鼠。”“等我一分钟,爸爸。”我边说边推开了车门。
“别着急,亲爱的。”他说。他以前从来不叫我“亲爱的”。
前院的青草近期才修剪过,清清爽爽。我站在门口,按下门铃。无人应答。我又扫视了一下花园。现在是五月。上个星期,樱桃树的枝上才鼓起累累花苞,今天,浅粉色的花朵便一簇簇怒放。它们温柔而脆弱的美,让人平静,也叫人感伤,因为花瓣很快就会凋落。一个星期左右,花瓣就会纷纷散落在草地上,如同新娘和马夫离开后教堂院子里潮湿而泥泞的五彩纸屑。
虽然确信艾瑞丝不在家,我还是叩响了门。
她会在哪儿呢?
我给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打电话,电话转到艾瑞丝的办公室,但是接线员告诉我的我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艾瑞丝不在,要去度假一周。
“是你吗,特里?”她问道,声音里有些许困惑,她想不通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没错,瑞塔。不好意思,你别在意,我忘了。”忽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艾瑞丝就在房子里。她摔倒了,肯定是。她倒在楼梯脚下,神志不清。她可能已经昏迷了很久,或是好几天。这种担心让我如同触电,并非所有担心都会如此,有些担忧会让我说不出话,或者浑身僵硬。屋侧入口处的木门锁上了,于是我把垃圾桶拖过来,抓住桶沿,双手一撑爬上盖子。人们认为高是一种优势,但在我1.78米高的身上,我必须说,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优势。事实是,我太高了,很难跪在垃圾桶盖子上,实在不知道该把我的胳膊、胳膊肘和膝盖放在哪里才好。
我抓住了门梁,几乎是把自己从门上甩了过去,膝盖蹭在了墙上,中间还有那么一秒钟的迟疑,在放手之前,我尽可能让自己落得远一些。最后,我降落在侧通道上的一堆杂物里。我本该做得更好。女儿们总是借我的身高去够这个够那个。等我从这里出去,就去干点儿什么,游泳、跑步、普拉提,都行。
艾瑞丝后院的棚子已经清理干净,园艺工具沿着墙面挂了一排,角落里是盘绕整齐的软管,那半桶油漆多年前封口处就锈迹斑斑了,如今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确实建议她好好归置一下这些东西,认认真真归置,否则很容易失火。然而,我还是不敢相信她竟然真的动手做了。
哪怕是棚屋山墙上的小窗户也不再布满蛛网。透过这扇窗,我看到一方浅蓝色的天空。
备用钥匙放在倒置的罐子里,就在棚屋里;我跟她说过,我觉得安全意识这么差很危险,而她全然不放在心上。
我又回到停车道上,看了看爸爸。他还在车里,还坐在副驾驶座上,跟着我放给他听的法兰克?辛纳屈的CD——《夜晚的陌生人》——唱歌。
我打开房门,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一片寂静。
“艾瑞丝?”一片寂静之中,我的声音显得很大,我的呼吸拦截了微小的尘埃,它们在死寂的空气里打着旋儿上升。
我穿过走廊,来到厨房。墙上凌乱地挂满了镶嵌在木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每一张脸几乎都是老人的脸,所有人都去过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他们去的时候,艾瑞丝便会询问是否能给他们拍一张照片。
我爸爸的照片就挂在走廊尽头。他的眼中有一道光,可能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阳光。他骨架好看的脸被包裹在头盔般整洁的银发里,从这张脸上仍旧能看出往日的英俊,那会儿他的头发还很浓密。
他看起来很开心。不,远不只是开心。他看上去很清醒。
“艾瑞丝?”我伸手推门,厨房门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响。喷一点儿WD-40防锈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厨房里有一种化学品的酸味。要不是我有所了解的话,肯定会以为是某种清洁用品。厨房表面上非常整洁。料理台上什么都没有,厨房的桌子上也空无一物,那里平时堆满了艾瑞丝的书和文件材料,有时候为了找东西,她就把手提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倒在桌子上。桌子是硬橡木质地的,我坐在这张桌子边吃过很多次饭,几乎没看见过它的真面目。如今,砂纸和清漆终于让我看清了它的样子。
起居室里,窗帘严丝合缝地放下来,沙发上的靠垫似乎变得更圆更大,在我的房子里这没什么好稀奇的,但在艾瑞丝的房子里非常显眼。艾瑞丝很喜欢这张沙发,有时候她甚至睡在沙发上。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一次我打来电话,那是一大清早,她完全没想到会是我。我去艾瑞丝家时会先打电话而不是按门铃,也只有在去她家时我才会这么做。我来的时候,她烧上了水,煮了一壶浓浓的咖啡。那时爸爸刚刚来到我家,一个星期还没过完。
她说她在沙发上睡着了,当她看到我盯着散落在沙发上的毯子和枕头时,便解释说,她是在看《驱魔人》的时候睡着的。
但我觉得那并不是她睡沙发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楼梯。有时候,在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办公室里,我能看到她必须使用拐杖才能上楼。那是棍子,她说。她讨厌等电梯,爬楼的时候总表现出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但是肯定不轻松,怎么可能轻松呢?
再说了,谁会在看《驱魔人》的时候睡着?
“艾瑞丝?”我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惶恐。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
或许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切井井有条,所有东西都被收起来了。
我走上楼梯,平台处挂了更多照片,卧室门全部紧闭着。我敲了敲艾瑞丝的房门:“艾瑞丝?”无人应答。于是,我打开了门。房间很暗,勉强能看清床的轮廓,随着我的眼睛渐渐适应暗淡的光线,我发现床已经清理干净了,枕头在床头整整齐齐堆了两摞。床头柜上没有书。或许她把书带走了,带去了瑜伽疗养院。
但是她并没有去瑜伽疗养院。
我的喉咙深处酝酿出一丝恐慌的味道。平常,她的衣柜门总是开着,因为衣柜里的衣服乱作一团,门根本关不上,但此刻柜门是关上的。地板在我的体重压力下嘎吱作响。我伸出手去,握住了门把手,猛地拉开衣柜,好像我并不害怕里面可能有什么。
里面空空如也。在穿堂风里,空无一物的衣架轻轻摇晃,相互碰撞,奏出忧郁的曲调。我关上衣柜,拉开了房间另一边的斗柜抽屉。
空空如也。如出一辙。
浴室里,洗脸池一侧没有躺着残留着牙膏的牙刷。
浴缸边上也没有搭着湿漉漉的毛巾。盆栽植物不见了,曾经它们就在氤氲的水蒸气里装点浴室。
我听到了响亮的汽车喇叭声,转身便冲去客房,艾瑞丝把它当作家庭办公室。我一把拉开窗帘,去看楼下的车道。车还在原地,爸爸也在。我看得到他跟着CD唱歌时嘴巴一张一合的。我拍了拍窗户,可他没抬头。转过身去,我注意到一排黑色垃圾袋,袋口全都整整齐齐地被扎起来,靠在房间对面的墙上,袋子上印着本地慈善商店的名字。
此时此刻,恐慌从我的嘴巴滑进喉咙,再落入胸腔,在胸腔里扩散开来,直至无法呼吸。我试着按照马丁医生的建议想象自己的呼吸,试着去观察它的形状。当我对着一个棕色纸口袋呼吸时,那个口袋的形状就是呼吸的形状。
我把艾瑞丝的椅子从桌子下面拉出来,坐了上去。就连回形针都被整整齐齐地收进了一个老旧的首饰盒里。我拿起两个回形针,把它们扣在一起。手上有事可做,会让我好受不少。我又伸手去拿第三个回形针,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丁零丁零的清脆声响,吓得我差点儿从椅子上蹦起来。我觉得声源是艾瑞丝的笔记本电脑,它被合起来放在桌子上。可能是邮件、报时或者什么别的提醒。我得关掉电脑才行,否则一台插着电的电脑会有火灾隐患。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似乎是个预约表格——一张爱尔兰轮渡的预约表。键盘上放着两只白色信封,摸起来还有温热。艾瑞丝又大又浮夸的笔迹我绝对不会认错。
一封信上面写着“维拉?阿姆斯特朗”,那是她妈妈的名字。
另一封信是给我的。
第2条时刻注意车速,并判断出最合适的行驶速度“区域道路的限速是每小时80千米。”爸爸说。
“抱歉,我......我很着急。”我瞄了一眼后视镜,以为听见了警笛声,结果并没有看见警车在后面追。
我用眼角的余光还能看到艾瑞丝的信,它被揉成了皱巴巴的纸团,就放在我的手提包上。
我最最亲爱的特里,你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你什么也做不了。我已经下定决心。
恐慌感在我的脑海里一圈圈盘旋,越转越快,直到我根本分辨不出自己究竟都在害怕什么。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开车载过法兰克?辛纳屈的事?”爸爸说。“没有。”我和爸爸的绝大多数对话里都掺杂着谎言。“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沿着哈考特大街开车,堵得要死,因为......那个什么事......水......”“下雨?”“没错,下雨,还有......”你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是你什么也做不了。我已经下定决心。
红灯,我紧急停车,刹车时发出刺耳的声音。下个月这车就该去送检了,我得在那之前修好车才行。布兰登说我应该买辆新车,小一点儿、好停放的那种。可我偏偏喜欢沃尔沃的重量感。没错,这车真的快要寿终正寝了,很可能会失灵,但是坐在车里我很安心。更何况,它从未让我失望。
“......我对法兰克说,我知道你所有歌曲的歌词,我......”......但是,希望你知道,这件事我已经思索良久,我是深思熟虑过才做的决定,我不会后悔,永远不会。
此前我从未去过都柏林港。我把车停在了一个残疾人车位。其实我不应该停在这里。
“爸爸,你能留在车里吗?我必须......办点儿事情。”“当然了,亲爱的,没问题。”“你要保证不从车里出去。”“你是要去接你妈妈吗?”“发誓你会待在车里,直到我回来。”......或许,我这样要求有点儿强人所难,想让你理解我的选择,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理解,因为你的看法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且......我的父亲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仿佛是在努力辨认出我是谁,可能他真的是在认。很难说他到底知道什么,可能记住什么。
我朝他弯下腰去,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很快就回来,好吗?”他咧开嘴笑了,这意味着他又把假牙取出来了。上一次,我在后备箱里一只安娜的旧运动鞋中找到了他的假牙。
“你很快就会回来?”他问。我说“是的”,然后关上门,把他锁在了车里。
......实际安排已经由瑞士的诊所负责,那里是完全封闭的......要是车着火了,他就出不来了。他会被活活烧死,或者因吸入烟雾而窒息。但是这车从来就没起过火,那么为什么今天就要着火呢?哪天都不着偏偏今天着?我游移不定。布兰登管这叫踌躇不决。
......这一切终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必须是现在,要赶在前头,在我不能......我跑过停车场,冲向码头大楼。我试着不去想任何事情,将注意力集中在鞋底撞击地面的声响上,集中在自己灼热而急促的呼吸上,集中在如拳头在胸腔里不断击打的心跳上。
我最最亲爱的特里,你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我一眼就认出了艾瑞丝。虽然她并不是大高个儿,但还是很容易马上看见她,她很显高。
我登时松了一口气,然后便如墙壁一般杵在原地。她正在排队,得体地等待着。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是打算在瑞士诊所里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和平常也没什么两样。青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没有化妆,没戴首饰,也不同人说话。只有当队伍慢慢往前挪时,你才能注意到她的拐杖,虽然已经用了这么久,它在她大而有力的手里还是显得那么怪异,那么多余。
我原地驻足,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艾瑞丝错了,我还是可以做些什么的,虽然我还不知道究竟能做什么。事实是,我人就在这里,而她也还在这里。我没有错过她。这是个好兆头,对吧?
我瞬间如释重负,已经无暇再有其他感觉。长舒一口气的感觉已然占满心脏,堵满喉咙。当我喊出她的名字时,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奇怪。
“艾瑞丝。”隔着重重人群,她没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又走近了一点儿:“艾瑞丝?”“艾瑞丝!”一堆脑袋转向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滚烫。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艾瑞丝脸上,她扭过脸来看我,大大的绿色眼睛牢牢地盯在我脸上。
“特里!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吗?”
媒体评论
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振奋,这是一部挖掘出友谊真正力量的小说,这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堪称“爱尔兰的乔乔•莫伊斯”。——《爱尔兰观察报》
很好好笑,很好感人,特里发现了生命中最值得的东西……她将幽默与悲伤结合起来,巧妙地维持了两者的平衡。——《爱尔兰时报》
真是一个精彩的好故事……格拉蒂笔下环环相扣的奇遇情节,又感人又有趣。——《独立报》
充满了温暖、幽默和人性。这本书是对生活和伟大友谊的致敬,它将温暖你的内心。——《星期日独立报》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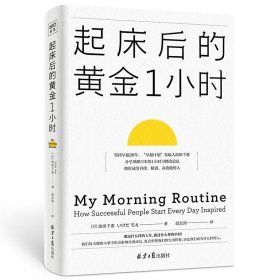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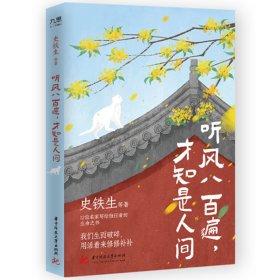

![【全新正版,假一罚四】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加] 马修·派瑞9787544798501译林](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19363336/ec517fa93239f8f3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