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我的逃生之路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37.7 6.4折 ¥ 59 全新
库存45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约翰娜·西尼萨洛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8558
出版时间2024-10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9元
货号32186709
上书时间2024-11-0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芬兰索丹居拉,曾担任广告专业设计师,之后开始从事编剧和写作。她的小说《日落前》(NotBeforeSundown)获得了芬兰文学奖。此后,西尼萨洛还获得了小詹姆斯·提普垂奖和普罗米修斯奖等奖项。2008年她的作品《娃娃》(BabyDoll)获得星云奖提名。
托芙·扬松、阿特伍德、雷·布拉德伯里、纳博科夫等作家都对她影响深刻。之后,她发现了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
目录
无
内容摘要
我顺从、讨好,只为在这世界不被抹去在禁忌的世界里,辣椒成了反抗的火种为了全民健康与繁育,卫生部对温顺的女性贴上“爱洛伊”的标签,她们的存在仅限于满足性和繁殖,任何拒绝丈夫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而聪明、独立的女性则被称为“莫洛克”,她们被分配到社会最底层,并接受绝育手术,以防止“有缺陷”的血脉继续延续。
万娜自幼聪明,但她懂得伪装愚笨。她的爱洛伊妹妹莫名失踪,为了寻找其下落,万娜卷入被政府严令禁止的辣椒交易中。原来,辣椒除了带来味觉上的快感,它还可能赋予人某种超能力。
主编推荐
一、思想性回应当下,当国家变成机器,当女性沦为容器,世界的法则被重新定义。在这个架空的世界中,人类的意义被拉回最原始的繁衍。当社会不再顾及公正与平等,首当其冲的便是生理上弱势的女性。作者敏锐的洞察与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不谋而合。这是反乌托邦的寓言,也是对现实的反抗。
人们发现芬兰已经从19世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吸取了教训。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生活拮据的年轻人感到沮丧,二是把多余的谷物蒸馏成酒精。(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期,是这个另类历史的分支点)在书中的另类现实中,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未婚男性获得妻子,即惩罚拒绝结婚的女性,从而提高未婚男性的社会地位。后来,权威人士利用从哺乳动物驯化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发现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防止顽固、霸道的女性生育,积极地将女性培育成温顺、温顺、有用的配偶。
在这本书的现代背景中,大多数芬兰女性都是艾洛伊,像洋娃娃一样的美女,她们性早熟,智力有限,幼稚,争夺男人,没有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少数妇女是莫洛克,她们相貌平平,智力正常,她们不是用来生育,而是作为报酬微薄的劳动力。
二、设定精巧有想象力,当社会失去自由,吃辣也成了一种抵抗。现实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竟成为高压之下人们反抗的最佳表达,崇拜辣椒、走私辣椒、感恩辣椒,还有辣椒所赋予的超能力……天马行空的创意把荒诞结构殆尽。
文摘:
我的头在旋转,脑袋里嗡嗡作响,当我无助地看着他们时,只有泰瑞的脸显示出某种理解,我得到了一丝顿悟的感觉。她兴奋地低声说话。我只听懂“联觉”这个词。我透过汗水的面纱看着她。我很少听到别人用一个我不知道意思的词。
“快,范娜——不加思索,字母A是什么颜色?”
“红色。”
“数字5是什么颜色?”
“浅绿色,带有一点黄色。”
“辣椒在你的口中是什么声音?”
“高音对位,像小提琴在音阶的最高点。但也有低音,像闷音的小号……当味道到达我舌头的后部时,会有更低的声音,特别是如果我在嘴里移动舌头,灼烧感重新开始。”
……
卖家一直把货攥在手里,这时递给了我。大约有一百克,要是我刚才塞进体内的就是这玩意,那劲儿也太大了。我转动手中的透明塑料袋,查看这些干燥的薄片,确保其中没有夹杂塑料、皱纹纸或红色花瓣的碎片。看起来没掺假。
他说这批货是娜迦毒蛇,但也可能是我没听说过的品种。从效果判断,大概一百万斯科维尔。这是有史以来劲儿最大的品种之一。
我从胸罩里掏出商量好的金额。当我这样做时,卖家盯着我,眼睛瞪得像茶碟那么大。
三、叙述方式多样丰富 结合信件、现代词典词条、图书节选、杂志摘录、国歌、法律条规、报纸报道、电影、证词报告等多种形式,打破沉闷的平铺直叙,里面既有现实真实存在的书目,也有虚构的法律条规,在真真假假中将迷幻的世界缓缓呈现。
文摘:
芬兰法律中的性别欺诈:
任何人通过手术或其他美容手段,故意误导国家有关部门对性别的官方定义,将天生的中性妇女的外表改变为女性的样子,将以严重的性别欺诈罪和嘲弄国家罪起诉。如果中性妇女本人有上述行为,则主体和行为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对这种罪行的惩罚是在国家改造设施劳动,并可能没收家庭财产。对实施这种罪行的行为人的处罚见适用的《社会破坏刑法》第6款220美元。
现代词典词条
莫洛克——一个流行的非官方方言词汇,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进入英语,现在被恰当地称为中性女人。指由于身体上的限制(不孕等)而被排除在交配市场之外的女性群体。这个词源于H.G.威尔斯的作品,他预言人类将在进化过程中被划分为不同的分支,一些致力于为社会结构服务,另一些则打算享受这些服务。摩洛克是社会中可随意使用的一部分,其用途主要限于作为日常工作的后备劳动力。
四、作者曾斩获芬兰文学奖 芬兰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作者出道即斩获芬兰最高文学奖,可谓奖项收割机。
精彩内容
万娜/薇拉2016年10月我在墓园边的小店里买了一束菊花。十月的晨光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在墓碑前,我慢慢地取下花束的包装纸。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着。薄薄的油纸像是脚下的碎冰一般,吱吱呀呀地响着。我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将碎纸放在一只半掩在土里的石制花瓶旁边,再将菊花的根深深地插进瓶中,我的指尖触到了花瓶底。
一股寒意涌进我的胃里。
我努力让自己的动作显得自然,又从花束里取出几朵花,假装在插花一样,把它们放入瓶中。但是不管我的手指如何在花瓶冰凉、粗糙的内壁上摸索,都无法找到那只小塑料包。花瓶里什么都没有。
空的。
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仅仅是想到我可能会回到密室里,我的脉搏就开始狂跳不止。
几小时之前我还拥有着一包娜迦毒蛇椒。我的那一份0I0足够我享受好几个星期。特别带劲的好东西。 令人崩溃。
我把剩下的菊花仔细地插在花瓶里,有紫色的,也有黄色的。都是曼娜喜欢的颜色。
我将包花的纸捡了起来,攥在手里,站了起身。我本打算把昨晚藏在花瓶里的东西裹在纸片中,当作要扔的垃圾带走。
我倚在亚雷身上,亚雷伸出右手搂住我。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摆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就是悲痛欲绝,装都不用装。我张了张嘴:“不见了。”亚雷的身子僵住了。他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他妈的。”“肯定是那个贩子。”“那个狡猾的浑蛋找到了你那巧妙的藏货之处。”“我本来以为没人敢在夜里搜墓。只要警报一响,他们都会仔细检查夜晚的监控录像,甚至恨不得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检查。”“但是货还是悄无声息地被拿走了。那家伙若是落在了他们手里,那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外面逍遥自在。”确实。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双手交叉护在胸口。我静静地看着那墓碑,还有花瓶里的菊花。昨晚藏包裹的时候,我假装在整理花瓶里干掉的紫罗兰花。在那场小插曲之后,它们就散落在墓碑上。现在,花瓶周围只剩下几片小小的、零落的0II紫色花瓣。
“墓园清洁工,”亚雷低声说道,“有人跟在我们后面,打扫了墓地,带走了原本瓶中的花,还顺手带走了一些别的东西。”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走吧。”我轻轻地挣脱了亚雷的怀抱。手里紧紧攥着包花的纸片,攥得手指生疼。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墓碑上的铭文。
曼娜·尼西莱(原姓内乌拉帕)2001—2016我的膝盖微微发颤。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心里的疼痛还是对辣椒的渴求。它们混合为一体,都让人烦乱。黑水从密室涌了上来,在门槛处窥探着,伸出漆黑的、湿答答的手指,触及我的思绪。我本以为把曼娜的墓用作中转站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别人会理解我为什么常常来这里,甚至是在最奇怪的时间来。当局对人的情感经历并不感兴趣。
每次去过墓地之后,我都会觉得十分沮丧。每次回来后我需要的剂量都比平常大很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转过身来,眼睛已经湿润了。我从裙子的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记起可能会有摄像头盯着我,于是便小心翼翼
0I2地用纸巾抹了抹眼角,以免弄花脸上的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样的小动作。
在墓园门口,我把纸片扔进了垃圾箱里。坐上了亚雷的公司车后,我蜷起身子,浑身发抖,脑中已经涌起黑色的浪潮。密室之门业已敞开。
“你能坚持到回家吗?”亚雷听起来很担心。 我必须坚持。
0I3亲爱的妹妹:有些事很难向旁人开口。奥利基已经不在了。我是有一些朋友,但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她们听。除了你以外,只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敞开心扉,可以认认真真 地听我说的每一个字,但是他同我的记忆没有太多的共鸣。 向“马斯科”倾诉困扰的时候,他们总是倾向于寻找解决方法,哪怕我的倾诉无非是希望分享自己的忧虑罢了。再说,我的问题也并不是这么轻轻松松地就可以找到方法解决。
于是我决定给你写信。
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看到这封信。但我还是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你听。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记忆已经被扭曲了。也有很多事或许你并不知道,或者不明白。
我很担心你。我愿意接收任何糟糕的消息,只要能知道你究竟在哪里。毕竟,你所坠入的深渊,也是一个出发点。也许在很久之后,我能战胜这悲伤与痛苦,甚至可以忘却这一切。但现在不可能。在确切地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一切都不可能好转。
0I4你曾失踪过一次。
我记得十分真切,虽然那时我只有六岁。那时奥利基在菜地里忙活,我们在秋千那儿玩耍。奥利基找了一块板子,挂在一棵大桦树的树干上给我们当秋千——你可喜欢荡秋千了。我在你背后推着,小心翼翼地加速。你浅金色的长发在空中飘扬着。秋千荡至最高处时,你总会乐得咯咯直笑。我记得当初自己多少有点懊恼,因为你还不会在后边推我,只会在我的帮助下自顾自地玩秋千。但这没什么关系,你是我的妹妹,奥利基奶奶把你交给我,让我来照顾你。
屋内传来电话铃声。奥利基拔萝卜拔到一半,停了下来,把萝卜放在一旁,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匆匆地走进屋子里去了。菜地后边矗立着一棵云杉,一只鸟从空中掠过,停在了云杉树杈间,它身上鲜艳的羽毛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很久之后,我在书上查到,那是一只松鸦。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于是我轻手轻脚地朝着菜地边缘走去,想要看得更清楚些。
我走得很近,甚至看得清它翅膀上绿松石色的细条纹,灰红色的羽毛,还有鸟喙两侧小胡子似的黑斑。我站在原 地观察了一分钟,看松鸦如何用鸟喙摆弄它放在枝丫间的橡子。我本想走到一个更适合观察的位置,但没留神脚下,脚底的树枝咔嗒一响,松鸦噙着橡子,扑棱一声飞走了。
我叹了一口气,转身往回走。
在桦树枝杈投映下的点点光影中,空荡荡的秋千慢慢悠悠地摇晃着。
0I5你不见了。
屋子里依稀传来了说话声,奥利基应该还在打电话。 我以为你偷偷溜进了房子。奥利基可不喜欢别人在她通电话的时候打搅她。我跑到门口,朝屋内望了几眼。你没有去打扰奥利基,她正跟人热火朝天地聊着土豆的收成。我又去看了一眼我们的房间。你也不在那里。
我回到了院子里,心怦怦直跳。你能去哪儿了呢?我不想让奥利基知道我是何等粗心大意。
内乌拉帕家的院子没有围栏,但两侧都长着茂密的云杉林,我想你多半不会去那林子里晃悠。如果你沿着院子前的砂石路离开的话,我一定还能看得到。唯一可能的是那条从桑拿屋后通往森林和泉水的小路。
你很喜欢那泉水。清亮的水流从两块石头的缝隙间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形成一个小潭,潭底沉积着细细的沙砾。 无论天气多么炎热,那泉水也总是冰凉的,你总是会把小手伸进其中,惊讶于那泉水形成的淙淙作响的狭窄小溪是如何流向远方……里希沼泽。
我冲了出去转过几个弯之后,我听到了你的声音。那是一声尖叫。 这意味着我没有工夫耽搁了。
我冲下小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已被地上的松果和树根磨出了血。跑了很远之后,里希沼泽终于出现在了树丛间。黄绿色的苔藓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洁白的0I6羊胡子草在风中摇曳着。里希沼泽是一个大水塘。漂在水面的苔藓是它美丽的伪装,苔藓下是乌黑、浑浊且深不见底的泥沼。
一抹红色闪过,是你的裙子上做装饰的红色条带,然后我看到了你。只有脑袋和肩膀还露在苔藓之上,肩膀以下的部分都已经被吞进了沼泽里。你两只手紧紧拽着草梗,扯着嗓子尖叫。你的身体在体重的作用下裹着泥潭藓不断地向沼泽深处滑去。
我比你更重但我在电视上看过冬天如何应付薄冰。 我没有尝试在这危险的沼泽地上行走,而是整个人趴下来,肚子贴着浮浮沉沉的苔藓,朝着你爬去。我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可靠,来给予你安慰,但当我靠近你时,你开始奋力挣扎,使劲想接近我,接近获救的希望。你的手松开了本紧紧拽在手里的苔藓,很快你整个身体都陷入了暗棕色的泥水中。
那时我已经离你很近了。我把手伸进泥水里,用力地向下探,指尖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于是我一边紧紧抓着,不敢松手,一边向后爬,竭尽全身的力气往外拉。我意识到——继而看到,自己抓着的是你的头发。接着,你的脑袋再次从水面上冒了出来,嘴巴张开,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我使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将你拉到了近旁,手伸到你的腋下,就这样拖着你,连滚带爬地回到沼泽的边缘。 那里的苔藓已经很厚了,能够支撑得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
我们两个都湿漉漉的,身上沾满了泥巴。我拉着你沿0I7着小路走回家去,一路上你仍然像只受了惊的小兽一般吱吱呀呀地哭喊个不停。奥利基从小路的一个弯角冲了出来,脸上满是惊吓,浑身上下散发着极度忧虑的味道。
奥利基给我们洗了澡,把沾满泥巴的衣服泡到了洗衣盆里,检查你身上有没有伤口,又给我擦破的脚底上了药。 她嘴上没有停,一直在唠叨着,不只是向你,也没有放过我。我现在知道,她这样只是因为受到了惊吓,但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保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会永远保护你。
你跑到沼泽那里去,我一点都不惊讶。你只是想到那个泉水边去。你本来不喜欢森林,但是你会愿意为了这个泉水在林间穿行。当你看到里希沼泽沐浴在阳光下,闪烁着 童话般的色彩,宛如暗绿色森林中一处圆圆的草坪,你定是以为那便是童话故事里的金色草地,是精灵和公主的神秘舞池。
在你天真的世界里藏着巨大的秘密:藏在美丽外表下的,是欺骗,是邪恶,是毁灭。
所以,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后来奥利基在房子和小路间搭了一道栅栏,但没有任何意义。你再也不愿意到那泉水边去了。
我再也不会让你孤身一人。
你的姐姐,万娜(薇拉)0I8万娜/薇拉2016年10月我关上了身后的公寓门,踢掉脚上的高跟鞋,然后跑——不,是冲到了睡觉的凹间边,然后像松鼠一样顺着衣橱的格子爬了上去——因为要把折叠梯翻出来还得好一会儿。我用拳头敲了敲顶层衣橱后面的墙壁,墙面滑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暗格和我的应急储备。我取出一只玻璃罐,纵身一跳,落在了地上,小腿骨震得生疼。我用力拧了拧玻璃罐的金属盖。
盖子如死了一般,纹丝不动。 “干!”我猛地栽在床上。哭声直接从密室里传了出去,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我的身上没有闸门也没有开关,哭声就像呕吐一样,向外涌着。
亚雷走到我身边,从我麻木的手指间拿走了玻璃罐,用他那饱经磨炼的马斯科手指,拧了一圈。玻璃罐发出了一 声微弱的“咔嗒”声。
我一把夺下他手里的玻璃罐,手指伸进盐水里,开始0I9把瓶子里绿色的小切片往嘴里倒。瓶口很小,我的手伸不进去,所以只能把墨西哥辣椒直接倒进嘴里,让那汁液将悲伤流淌在脸颊上,胸膛上,粉红色的床罩上。我只管狼吞虎咽。我知道墨西哥辣椒的斯科维尔指数低得可怜,尝起来应该和腌黄瓜没什么两样。但仅是知道那些清脆的小切片里含有辣椒素,就足以让我颤抖的双手平静下来。两分钟后,密室里的黑水稍稍退去,将将落在大脑的洪线之下。墨西哥辣椒的微弱冲击是暗淡的,呈灰蓝色,它在我的听觉皮层边缘微弱地震动着,仿佛它的声音来自那点点繁星之间。
我将罐子扔在地上。罐子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碎。它是外国制造的,质量很好。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打开了水龙头。我懒得去找玻璃杯,于是把脸凑到流淌的水柱边,半个脑袋埋进水池里,脖子别扭地歪着,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我抬起了头,用手背擦了擦嘴。口红在脸颊上留下两道血一般的痕迹。
“我的上帝啊,这东西也太咸了。”我对亚雷说。亚雷看着我,我看到他的嘴唇扭了一下,接着开始大笑,几乎腰都直不起来。
“哈哈哈哈哈……不……不好意思,这没什么好笑的,但……要是现在有个外人在这儿……如果他不笑出声,那可真是奇了怪了。”现在的我“久旱逢甘霖”,哪怕遇见这种无聊又幼稚的行为,我也能在嘴边挤出一丝笑意。我刻意慵懒地走到了前厅的全身镜前。亚雷是对的,我看着像一个从纸里蹦出来的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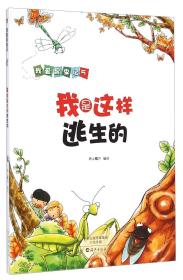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