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面的世界I 普通图书/文学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中信出版社 9787521750539
新华书店全新正版书籍图书 保证_可开发票_极速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
¥ 37.5 5.4折 ¥ 69 全新
库存21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21750539
出版时间2023-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1635549
上书时间2023-06-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1914—1996)充满野性、出乎意料的作家、剧作家、导演,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作品、十九部电影等。《情人》获1984年龚古尔奖,畅销全球。她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成就卓著,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杜拉斯生于印度支那,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九岁,这段生活影响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写作的源泉:作为她生命底色的童年的匮乏,永远与命运抗争却永远失败的母亲,偏爱大哥的母亲,总是和他要钱的大哥,亲近却早逝的小哥哥,死去的孩子……“活着让我不堪重负,这让我有写作的欲望。”她无时无刻不在写作,用写作解剖自己的一生,在写作中趋近自身的真相。
目录
目 录
译序 1
再版序 9
前言 17
关于文章排列的顺序 23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 3
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 6
“LILAS”这个词的高和宽差不多 15
巴塔耶、费多和上帝 21
关于乔治·巴塔耶 33
啊,不再有绞刑了吗? 38
下等人的巴黎 43
巴黎的旅游业 46
维耶特的贵族血统 55
莫尔尼公爵的沼泽地 67
巴黎的拥挤 73
百分之一的小说可见天日 78
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 89
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 96
公交公司的这些先生们 102
巴黎的种族主义 108
走开! 112
皮埃尔·A.,七岁零五个月 116
为《七月十四日》辩 124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 128
巴黎,8月6日 135
引人发笑的绘画 141
塞纳—瓦兹,我的故土 147
奥朗什的纳迪娜 159
“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 173
施瓦西—勒洛瓦的恐慌 181
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 194
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235
与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 256
快乐的绝望之路 272
这个黑色的大家伙 289
恐怖的知识 294
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人:萨特 302
萨洛尼克的猛兽 307
载着一千具尸体的火车从巴基斯坦开来 317
让—玛丽·斯特罗布的《奥通》 322
塞里格—里斯 328
德菲因·塞里格,不为我们所知的名人 331
让娜·莫罗 342
玛尔戈·冯泰恩 361
蕾奥蒂娜·普里斯 373
玛德莱娜·勒诺是个天才 381
美丽娜 391
西尔维亚和她的灵魂 403
芭铎皇后 414
卡拉斯 421
让娜·索盖 425
大海深处 434
阿基·库罗达的《种种黑暗》 437
卡洛斯·达莱西奥 442
让—皮埃尔·瑟通的《城市喧嚣》 444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448
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 458
韭葱汤 465
面黄肌瘦的孩子 468
源于同一份爱的恐惧 474
罪恶的幸福梦想 478
没有死在集中营里 487
泰奥朵拉 496
内容摘要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我会为外面而写,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这些文字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为身外世界所写。所谓的“外”,是与“内”相对而言的。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媒介——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政治——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介入”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
精彩内容
译 序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远离杜拉斯的年龄,她的激情,她的绝望,她时时刻刻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歇斯底里。我不再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她酗酒、唠叨和写作,我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深深地为她所震撼。
十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杜拉斯作品,是她的《情人》,王道乾先生的译本。后来看到了电影,再后来读到了法文本,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地读下去,《琴声如诉》《广岛之恋》《长别离》《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等等,等等。再后来我做了关于杜拉斯的论文。她的情人,她的湄公河,她的黑暗,她的空茫,她的暴力。
这时节,杜拉斯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国,她也算得上是作品卖得好的少数几位法国女作家之一。“伟大”这样的字眼不合适她,可恐怕谁都无法否认她是法国20世纪后半叶最奇特的女作家。她的传奇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一个殖民地孩子的故事,长大了,离经叛道,不可一世。她欣赏这个传奇,等待这个传奇,从孩提时代起。她觉得自己是在承担一种命运,迫不及待地冲进一切机会里争取主角的地位。
1996年,她死了,从此停止了她自己一手炮制的生命传奇。她的年轻同伴,扬·安德烈亚也不见了踪影。1996年的时候,听到她谢世而去,我第一个念头竟是:她的读者是否也会像扬·安德烈亚那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呢?也是这样猝不及防的,为了中断的中断。
可她毕竟上了百科词典,拉鲁斯,或者阿歇特,有明确的生年和卒月。不管她是否受人爱戴、受人尊敬,她在这个世界始终是留下了点什么。给她的词条不会长,但往往有这样简明扼要、尽量不加主观判断的几行字:法国作家、电影人,作品的主题通常是绝对然而失败的爱情以及死亡,语言极富音乐性1。词条的下方,会是她最常见的一张照片,戴着宽边眼镜,围着白色围脖。她自己也说过,不止一遍地说过(甚至在这本随笔里也可以读到),她不像法国人。
她写了很多书,很多文章,也拍了不少电影,虽然观众不多。她的第一本书名为《厚颜无耻的人》,五十五年前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面的世界》算不上是她最重要的作品,就像她自己在前言里说的那样,她写了很多文章,却忘得也很快。然而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从来不会。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她同意把三十几年间陆陆续续给报纸杂志写的文章辑成集子,出了第一本,接着又出了第二本,毕竟有了她不会忘却的书的形式。
其实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时下流行的“私人语言”的写作。杜拉斯不相信有自身之外的故事,虚构从来不存在,她说。或者可以这样说,她本身就是虚构的,有开头、结尾,有命定的快乐、悲伤和动荡。在文学史上抹去她会像抹去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不留痕迹—她知道这一点,如此才有生命与成名的局促感。她害怕“卡车”那样的旅程,永远望不到头似的。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作品。所谓的“外”,原来就是与“内”相对而言。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媒介—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政治—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介入”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
她热衷于破坏一切标准,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莫不以此为出发点。正如她在前言里所交代的那样,她为所有的运动浪潮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抵抗运动(和很多作家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她热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主义,毋宁说是运动本身,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动荡和摧毁的意味。她崇尚“快乐的绝望之路”,她想以自己来证明人类是可以活在绝望里的。绝望—生存,这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
但是她并不热衷于建立新的标准。有一段时间,巴黎滚动式地上映她的《卡车》,差不多是一成不变的画面:卡车不断地向前开着,开着。她或许只是不喜欢封闭,不喜欢封闭的文本,不喜欢封闭的电影画面,她把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她的观众和读者。如果她也有理论,一定会像罗兰·巴特那样大叫一声:作者死了!她做得出来。
她没有流派,有人把她归为新小说—据说罗伯—格里耶一年里给她打了二十个电话,要她写点什么,于是才有了《琴声如诉》—因为她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时间和地点,淡化古典文学的三一律。《情人》呼唤的不是种族平等,《广岛之恋》也只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艳情故事。如果说人类到处都在书写绝望,爱、情爱或性爱都只能使人类愈加绝望。虽然《外面的世界》是新闻性的写作,仍然写满了人类的绝望之情,写满了杜拉斯的绝望之情,它的语言仍然是贴有明显杜拉斯标签的语言:断裂、破碎、局促。
我一度离这一类的语言也远了。所以在接受它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我也和杜拉斯一样,喜欢承担“臆想”中的命运,可尽管这样,尽管真真实实地喜欢过杜拉斯,我从来没有“命定”自己和杜拉斯发生某种联系—我花了一段时间考虑。最后我想,我愿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了结十八岁的震撼和喜欢。《外面的世界Ⅱ》由黄荭承译。但愿我们可以做不同时期的杜拉斯的代言人,先前的那个更激烈一些,后来的一个要唯美一些。(注意,美也可能是个陷阱!)于是我又堕入了杜拉斯的圈套,在四十天的时间里,一打开电脑,我就会变得非常焦灼,以至于需要用电脑里那个愚蠢而机械的游戏平复内心的惶惑,平复这份断裂、破碎与局促。
事有凑巧,就在这本书行将翻译完成之际,法国《读书》杂志花了很大的版面纪念杜拉斯。看来爱也罢,恨也罢,忘却终究是需假以时日的了,虽然一切终将如冰雪消融。
袁筱一
再版序今年的春节,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买过一本《电影花粉》。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作者在写芭铎的时候,引用了这样的话:“她美得如同任何一个女人,但却像个孩子一般灵活柔软。她的目光是那么简单、直接,她首先唤醒了男人的自恋情结。”小小的引号,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终究没有耐心在书店里纠缠下去,看个究竟。以为莫名的熟悉感只是因为杜拉斯。杜拉斯真的是这样读的,不经意间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经上,生生的有些疼。可是年龄越大,越知道这些疼是该忍着的。
撇开自己做了这些年法国文学不说,站在一个纯粹的读者立场,她是因为这个才在中国流行的吧。就像《花粉》的作者,是因为撞到了“男人的自恋情结”这几个字。
书买下来,回到家泡上茶,在烟花爆竹声中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的文字,是经过自己手的,杜拉斯的文字。是自己在若干年以前译的《外面的世界》里的文字。这份确认让自己觉出一丝的欣喜来。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自恋,又何止是男人呢。
而在那个时候,我还在译序里写:一切终将冰雪消融。
我希望消融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最终一定会消融的,是什么呢?
这次不期而遇,却仅仅是个开始。没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纠缠竟然要到令冰雪也无法消融的地步。这才相信,如果相遇是命定的,如果相遇被视为命定,自己是不甘心让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
于是创造相遇,先是《杜拉斯传》在台湾付印,然后是在全校的法国当代文学公选课上再度讲到杜拉斯,再然后是没有轰轰烈烈,但多少有些声音的“杜拉斯辞世十周年”的活动,最后,在这年就要过去的时候,我重读了这本《外面的世界》。
几年前的回忆于是一点点地回来,当年读杜拉斯、写杜拉斯、译杜拉斯,当年的喜欢、震惊,还有当年那一点点因为疼痛到麻木的厌烦。
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经被译滥、写滥的今天,《外面的世界》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话题。因为它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被奉为中国小资必读作家的杜拉斯其实有大量的文字是关于“外面”的世界的。然后,再一点点地深入进去看,看她写的政治事件,看她写的社会问题,看她写的明星,看她写的艺术,会理所当然地发现,她的“外面”并没有那么外。她自始至终没有站在旁观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当她需要——如果我们相信她在随笔集开始所写的那段序言,当她结束一本书,需要挣脱自己,或者需要钱的时候——走到外面的时候,她仍然毫无保留地任自己冲入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裹挟。她观照这个世界的目光,从来不曾冷静、客观,她仍然是激烈地爱着的,激烈地爱着,所以恨,恨所有的不公平,恨所有的不可沟通;同时,也羡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性:宽容和独立。
《外面的世界》因而还给了我们一个连带的命题:她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所谓“自我虚构性”的小说——真的是如此内在吗?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因为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物质最终一定会走向结束。这其中,包括爱,包括文字。绝望来自这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抵抗这种绝望有两种途径:无知或是超乎寻常的,西西弗斯的勇气——那种走向灭亡,却充满幸福感的勇气。和大多数人一样,杜拉斯没有这份勇气,然而走进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无知里。
在《美丽娜》那篇文章里,提到自己的《夏夜十点半》,杜拉斯说,于是,必须喝酒,对于爱情的结束,可以怀着同样的激情和乐趣去经历。
或者更甚于此,在杜拉斯看来,我们还可以成为爱情的作者,这是抵抗结束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办法。就像《夏夜十点半》里的玛丽亚,她说,你们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
杜拉斯说,所有走向结束,以新的介入开始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这才是写作的缘由。写作所包含的,是失去、绝望、孤独和激情。是面对存在的种种悖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高贵的选择之一。远远超过了“自我虚构”的意义,超过了一个十五岁半的法国小女孩和中国情人的故事背后的“真相”的意义。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的,是爱,以及因为爱而产生的文字。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玩味绝望的方式抵抗绝望,只是,时至今日,杜拉斯的绝望已经成为绝望的酵母,弥漫在太多人的文字里。其中的原因,杜拉斯也在《外面的世界》里做出了回答。她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问她,如果没有人感到温暖,那么温暖又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感到绝望,那么绝望又是什么呢?
绝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绝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毁灭的必然;绝望是这冬天的雨,而在这冬天的雨中,去年为你撑伞的人已经离去;绝望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虚构世界的人物混作一团,却无能为力的心情——固然有成为一切爱情始作俑者的奋争,可是对于个体来说,绝望在何时、何地成为过一件好事呢?
出乎意料,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是个很慢的过程。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包括错误和我自己以为不再合适的文字。但是一定也留下了另一些错误和别人以为不合适的文字。这是译者的绝望,永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有时有进不了门的尴尬,有对自身身份和存在的怀疑。只是但愿有人知道,没有第三者的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爱情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更不能够继续。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在我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时,我得知这本书里的《面黄肌瘦的孩子》被选进了某个版本的《大学语文》里。爱情发生了,这是作为第三者的译者所得到的最好的心理补偿。而作为作者,杜拉斯也该得到安慰,辞世十年之后,对于她在法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的肯定也没有更多的争论。是的,作为个人,我们可以爱,也可以不爱,但是,文字早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袁筱一
前 言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为报纸写作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时的确会这样。
因此,我为报纸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如果我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说在1980年,我为《解放报》写专栏。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是什么范围内的不公正;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允许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想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十八岁就掉了脑袋的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上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吕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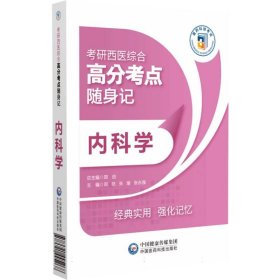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