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女同游美利坚
¥ 8 1.2折 ¥ 68 九品
仅1件
北京昌平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茹志鹃、王安忆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12
版次1
装帧平装
货号11-6
上书时间2025-01-0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茹志鹃、王安忆 著
-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 出版时间 2018-12
- 版次 1
- ISBN 9787508693606
- 定价 68.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400页
- 字数 290千字
- 【内容简介】
- 茹志鹃、王安忆母女访美,路程虽然一样,但由于彼此阅历迥异,所生发的感想不尽相同。于今视昔,很少有一本书可以同时照见中国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的心路,且是通过记录芝加哥的霓虹、沃尔玛超市的速冻牛肉、橱窗里的针织衫、德州的牛仔裤等琐碎却贴肤贴肉的文字得来。这样的文字无意间,也映射出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历史的后见之明,使得书中母女两人视角的反差颇具深意。
- 【作者简介】
-
茹志鹃(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浙江杭州人。中国当代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代表作有:静静的产院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关大妈三走严家庄等。王安忆,一九五四年三月生于江苏,原籍福建同安,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上海市作家协会,复旦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遍地枭雄匿名等。
精彩内容:
9月15 阴,时有雨
“写作计划”召开了关于非洲文学的讨论会,发言的有尼利亚、加纳、南非等五个的作家。这几位作家中,以加纳和南非的两位作家给我印象很深。加纳的作家,年纪较轻,循规蹈矩,很谦和,很听话,像一个很乖的大孩子。南非的女作家,从肤上看,不太像是一个黑人,有五十以上的年纪,鼻翼两边的纹路特长,特深,是一副愁苦的面容。他们谈了语言、文字问题,写“外在和内在的结合”、写“人类的本源”等等文学上的问题,同时毫无例外地都谈了本国的社会,争取独立,尊严等等,成为他们的文学题材。
不能硬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但是作家生于斯、活于斯的社会,不可地反映在作家的思想、心理之中,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发言完以后,有人提问,亦有争辩、补充,南非的女作家哭了。可惜话不懂,靠翻译只听得一鳞半爪。
会后有酒会,我们没兴趣。回来捧着自己准备下的菜,去华苓家会餐。许世旭俨然已是里的一员,他也去了。诗人叶维廉和他夫人也在,大家毫无拘束地吃了起来。我们包的馄饨生意尚好:c从昨天经营起来的红烧脚圈,一扫而光。酒足饭饱之后,许世旭套着中国的腰鼓,跳起了朝鲜舞,七等生和兰兰对着跳踢踏舞。虽然跳得不怎么样,可是情绪饱满,像是那么回事。“手而舞之,足而蹈之”虽然颇能表达情绪,但是需要十分的勇气和三分的技巧,能者不多。舞不能尽兴,于是歌。时与歌少见交往的萧乾,竟也唱了起来。不但唱,唱开了头而不可收拾,一首接一首地唱。大家一起以残缺的歌词,不全的五音,高不成低不的嗓子,唱童年时的歌、抗时的歌、大家都会的歌、我们这一代的歌。唱得十分醉人,十分开心。许许多多逝去的岁月,竟然又流回了头。华苓会哼的歌,我也会哼,什么“小麻雀呀”、“怒发冲冠”、“苏武牧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黄河奔流向东方”等等,等等。我们同庚,会唱一些同样的歌,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c唱了“一条大河波浪宽……”
歌,离开我已好久了。十年?二十年?我是唱过歌的。那时,是作为一种需要,一种希望,一种力量来唱的。在那些饥寒、困倦、疲惫、黑魆魆的夜晚。炮火烧红的村落,直立在破墙边的牛,雨落下来了,落在生死无界的战场上。那时倒有歌,轻轻地哼过许多歌。后来,后来歌从我生活里轻轻地、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也许,是歌的力量不够了,也许是生活的担子更重了。需要的是腰脊的力,肩腿的劲,需要的是迈步,是行动。歌,在我看来,变成一种轻飘飘的,可有可无的,属于青年人抒发剩余感情的东西。
歌,发现我老了。
9月15雨
下午三点钟,有一个报告会——非洲当代文学。这是“写作计划”活动的个报告会。共有五位作家演讲,一位加纳的,一位尼利亚的,两位埃及的,一位南非的女作家,她是剧作家、诗人,也是短篇小说家,她的作品是反映种族问题的,而她自己却并不是黑人。陈映真向她提问:“一般来说,黑人作家希望得到白人的认同,而你,是一位白人,却期待得到黑人的认同,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呢?”她回答说:“我是个黑人。”陈映真诧异了,我们也都诧异了。原来她是黑白混血的,在南非,有人种一律受歧视。然后,有人朗诵了她的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写的是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酒吧玩,过了宵时间,黑人是不允许宵时间在外活动的,于是一位黑人姑娘对白人说:“你带我回家吧。”念诗时,南非女作家一直在流泪。一位埃及作家谈到阿拉伯的民族:吝啬、受压抑之后的变态、没有创造等等。巴勒斯坦女作家,漂亮的撒哈站起来大声地反驳,她的声音很粗,很哑,态度很凶。她说:“我现在搞不懂我究竟是什么人了。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为什么要作这种区别。而事实上,埃及人幽默,我也幽默……”她的意思大约是,劣根并不能单纯以、民族来区别决定。另一位埃及作家阿里的话又引起一位听众的反感:关于小说要不要政治。争论的也很激烈。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而我以为这样主义对主义,思想对思想,是永远争不出结果来的。应该小说对小说,那么会发现,主张不要政治的小说中,很好者实际上有着政治,主张政治的小说中,很好者实际上并不接近是政治。政治究竟是什么?我也给他们吵糊涂了。
晚上,在聂家聚餐,我们每人带一个菜,我们做的是龙虾片和馄饨,潘耀明是汤,七等生是炸鸡,陈映真的——我揭开他的锅盖,他大声唱:“0333|1—|1—”是肥肥的猪脚!今晚来了很多人,叶维廉夫妇,萧乾夫妇,吕嘉行夫妇,以及来帮忙的小叶,alex,esther。
楼上闹哄哄的,我们几个跑到楼下聂华苓的工作室里看电视。是卓别林的电影《淘金者》。暗暗的屋子里,卓别林在作着一连串的笑而辛酸的表演,身后,谭嘉和兰兰的表弟小球在聊天。小球是为了安格尔先生的病特地赶来的。
“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做,还是美国人?”小球问。
“我不管他,我随便他们。”谭嘉说,她的声音很柔和。
“你有个希望。”
“要说希望,我希望将来能有,没有中国,也没有美国。”
“这有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是怎么培养孩子呢?”
“我教他们中文。不管他们干什么,我都要叫他们记住,他们是。”
“可是,我认识一些,决定让他们的孩子以为自己是美国人,这样兴许能少些苦恼。”
“可是,我也认识一些,他们从小说英语,自以为是美国人。当他们长大以后,忽然感到自己是,于是进学校学中文,然而,晚了。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机会,多一种选择,当他们想当的时候,他们会说中文,他们能够当。”
“我现在看了台湾地区地区的电视,我都感到回去是不可能的。”
“我无所谓。我看透了富贵和贫穷。我亲眼看见过,钱多得不晓得怎么花,而明天,成了乞丐……”
楼上在唱歌,是兰兰的生。
晚上,大家都好像发疯了。许世旭跳朝鲜舞,萧乾伯伯唱了很多他们青年时代的歌曲,这些歌,妈妈和华苓女士她们都会唱。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歌,那是很久以前的歌。而我们年轻人没有,没有可以一起唱的歌。哦,想起了,有一个,《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遥远的东方有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
9月16晴
随大家一起去密西西比河。来爱荷华讲演的叶维廉夫妇也去了。他是来讲中国古诗的,安忆去听过。他也写评论,曾两次去过北京、上海,都未见到。
汽车所经之处都是原,地里长着一些玉米。据说今年天旱,玉米长得不好。所谓的农村,实际无村,只是相距二三十里,有一幢别墅似的房子,房子附近必有附属设备,高的仓房、矮的车房、花圃、秋千,这便是农家了。四周是原,是树林。按我的观念看,这是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冷清寂寞得无异于中国的和尚庙、尼姑庵。可是带我们来的艾理斯(他住在附近的镇上)告诉我们,住在这里的人,相距虽远,实际他们天天在一起喝酒,他又向左后方一指说:“有钱的人家都在那里,家里什么都有,包括直升飞机。”哦!当然,有汽车、直升飞机,距离小得多,二三十里不算什么;打个比方,像上海住隔壁弄堂一样的近邻了。
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密西西比河。河水清澈,河里似有一个个树木茂盛的小屿,也许,只是曲折的对岸。据说河面很宽处有十里。过了河上一道大桥后,车子并不沿河行驶,而是开上了一条沙石公路。据说,这条路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为了运输而开辟的。现在为了行驶大型农机,没有铺设水泥,每个星期整一次。
路上,每人花五元,集资在一个小镇的店里买了肉排、茄汁黄豆。小店靠近一个加油站,生意不坏,在这里用餐的大部分是蓝领阶级、卡车司机等人。一份肉排,有长长的大骨头六七根(像中国的牛肋骨粗,但他们说是猪肋骨),还有大堆的炸土豆条。餐盘是丰富实惠的。我们买了食物装上汽车,说是带到河边去吃。可是还没看到河,车子在一个树林边停下来了。林里有桌凳,我们把几张桌子拉到一起,把食物搬下车来,大家开始向肉排进攻,几乎同时,树下的蚊子便向我们猛攻。于是人吃肉,蚊子吃人。肉排上的肉不多,而且很硬,倒是那茄汁黄豆味道不错。用完餐重新上车时,叶维廉夫人的腿上被咬起了十来个红包。艾理斯的脖子上也鼓起了好几块。而且蚊子兴尤未足,竟然有不少跟上车来了。在车上赶了一阵蚊子,我们才算真正到了密西西比河边。
水清,河宽。实际上望不见彼岸,只见这里那里,一丛丛浓浓的林,绿绿的树,组成了密西西比河宽阔的而不浩渺、静谧而不单调、迂回曲折、优美的河岸。我们穿过树林,踏着陈年的腐叶走向河边。河湾老树下,一位爷爷带着他的小孙子在钓鱼,远处停着他们的汽车。哦!谢谢啦,老人和小男孩,你们为我凑成了一幅画。
9月16晴
这是密西西比河。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这是条黑人的血和泪汇成的河。
密西西比河很静,河岸是苍绿的树丛。当然,有一些岸边,已开辟了区,而在它另一些岸边却悄无一人,静悄悄的。据说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林间,那是不能捕猎的,除了野和鹿。鹿在这里是太多了,因此很贱。而野,本是这里很早的居民——印地安人的神,可是,印地安人现在已没有一点权利,因此也顾不上他们的神了,只好随它去了。河岸边,只遇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在钓鱼,密密的树丛遮掩着他们,树丛里还有一条翻倒的小木船。这里很幽静,这幽静被人用心保护着。
回爱荷华城的路上,在一个农庄的小店前停了车,大家纷纷下去买瓜。这里的瓜很便宜,比城里的不错市场便宜一半。女主人很高兴,说:“这些作家们好像很喜欢这些东西,不知道他们明天还来吗?”
回到“五月花”,又跟上海尔的车去购买食品。妈妈很累,不去了,我一个人,很忙乱了一阵。首先是找白糖,偌大个市场,怎么也找不到。向爱荷兰诗人打听,他把我交到服务员手里,服务员指点我在一个走廊,来回走了两遭,都没看见白糖。而这时候,我的车子却不见了,前前后后地找,找也找不见。忽听几个中国学生在讨论:“这个车子好像不太像我们的。”“那恐怕是我的了!”我插进嘴去,他们领我去看。果然是我的,我把我的车推走了,他们便开始找他们的了。走来走去,又碰见了他们,于是向他们打听白糖,他们四个人便分头帮我找去了,人多力量大,终于找到了。在结账处,他们帮助我搬东西,借钢笔写支票,这么熟悉了起来。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可一问,却都是来自台湾地区地区,刚来一个月,念机械。其中一位说:“我的父母是从大陆来的。”我们便互相写地址姓名,其中一位用英语报地址,被其他几位喝住了:“说中文,这里都能听懂中文。”他们四个人买了一大堆东西,也没汽车,不晓得他们怎么将东西运回去。
晚上,潘耀明、七等生和esther一起去酒吧。潘耀明又试。他终有要发疯的,大家都这么说。为了不发疯,他决定今晚要“疯狂一下”。于是我们找了个很很疯狂的酒吧。没进去,头轰然胀大了,音乐声、人声,像潮水一般涌上来。门站着两个人,一个检查学生证、身份证,这个州允许喝酒的年龄是十九岁,凡不到十九岁者均不许入内;另一个人则收费,一人交一元钱,这个酒吧很大,名叫“fieldhouse”。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有一个舞池,男女学生跳着迪斯科,开心得不得了。坐着喝酒的大声谈笑,偶尔高兴了,大嚷一声。那音乐越来越强烈,没有一歇空隙,让人的神经休息一会儿。永远是高潮。esther说:“吵死了,怎么挑这么个地方。”潘耀明则很高兴:“难得嘛,洗洗脑筋。”esther告诉我,这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爱来的地方,大三大四的学生喜欢安静一些的。她和七等生先走了,我和潘耀明坐到十一点多,走出酒吧,门还排着长队接受检查,付钱,然后进来。
爱荷华城,好像在过节。街上满满的人,走来走去。一个男生走到我跟前,摊开胳膊拦住我,说:“excuse me!”潘耀明很紧张,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没什么,他很有礼貌。”我说。“到了,都发疯了。”“他们挺能疯的。”“美国人爱引人注意。我看见一个男人,穿了一条裙子。一回头,把我吓了一跳,我笑了起来。他得意得要命。”
我们一同沿着爱荷华河走回去,一边聊着天。我们开始讨论“写作计划”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我说:“我很喜欢爱德文。”
“这个人很奇怪,他的太太比他大得多,也不好看,倒是个德文教授。他也搞德文翻译。她很近和另一所大学订了个十年合同,已经走了。爱德文也要走。”
“什么时候走?”我问。我挺舍不得他走的。
“大概要等这一期‘写作计划’结束以后吧。”
“他很好。”
“不过也很莫名其妙。我到这里时,他和他太太来接我,他说:‘明天请你吃饭,’可是到现在也没请。”
“也许他忘了,他很忙。”
“不会忘的。我每天中午,都在他们的办公室吃午饭,每天都有一个提醒他的机会。”
“美国人很忙。”
“我想请他谈谈,他答应,却永远没有空。他们把自己封闭得很紧,不让人家进来。”
到“五月花”,已经十二点了。在电梯上,碰到那位爱尔兰诗人和西德女作家,两人搂抱着,喝得醉醺醺的。尤其是那女作家,一脸油汗,眼神恍惚,脸上带着惘然的微笑,诗人则还算清醒,记得对我说一声:“再见,安忆。”
9月17晴
不想出去了。一个人在“家”看了一些台湾地区地区作家的作品。
原来许南村是陈映真写评论时用的笔名。我喜欢陈映真的小说,恰恰也喜欢许南村的评论。他的评论是用他的观点,以对台湾地区地区社会的分析来统率被评论的文章。所以即使没看过被评的文章,光读他的评论,也是会有启发的。他的许多作品,是我早读过的,现在又读了他的系列小说《华盛顿大楼》部《云》。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子,各篇的得失暂且不论(我也论不了),且从他的序言里,可见他的意图,他的思想、计划。
“企业为了有效地达成它专享的目的,即利润的增大与成长,展开精心组织过、计划过的行为。这些行为,以甜美、诱人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和他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分析和批判这种影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文学不应也不能负起这个工作任务。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与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
“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和技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靠前企业的手中。除了从企业提供给我们的大众传播中去获得部份的、片面的、包装过的、常常是不正确的咨询,人们对人和他所居住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如果的作家还像过去一样,仅仅凭着对自己的‘天才’的迷信;仅仅凭着一时的‘才思’和灵感去写作,那么,他很快地便要成为那自以为一身锦绣的的国王。正如同觉醒的消费者要争取对于如山如海的商品的和实情的理解,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与思想,穿透层层欺罔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并不是‘反企业’的小说。不,它们简直与反不反企业是无关的。这些已经做成和将要做出来的小说,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自然产物。……”
这是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作家。他的眼光,不谓不远,不谓不深,不谓不透。这是他对台湾地区地区那个社会制度下,各国跨国公司纷纷挤进台湾地区地区这个消费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看。他对台湾地区地区农村的看,可通过他对农村诗人吴晟的评论来看。“从七七年到七九年间,吴晟对于城市消费文明强力地向农村浸透,表示了极大的关怀,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台湾地区地区传统农村中俭约、谦抑、勤劳、朴实、正直、诚恳的风气和价值迅速地在农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享乐、消费、对商品的贪欲、虚荣和损人利己这些消费社会所形成的意识和价值之变革……”
是的,我在这书案上向陈映真表示同感,同时作一点补充。我们希望农村里保持古老的纯朴、耿直,但同时也要改变那种每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的劳作。牧童横笛牛背的风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也是时代的趋势,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看了他的《夜车》,真好。如果《将军族》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那么《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首篇《夜车》,则是他后期作品的代表作。亲爱的同胞、同行,我在这里祝你顺利、如意。
9月17阴雨转晴
是极高兴的,我们去野餐!
说好十一点出发,可是等这等那,等到十一点半才开车。来到一块草坪上。这里有两个大木棚子,几个烤肉架子——我现在知道了,这种随处可见的铁架子是供野餐烤东西吃的,还有秋千,滑梯。天忽然下起雨来,雨点不很大,来的很急,但走的也很急,天又晴了。太阳很暖。
大家一起动手,把冰块和饮料倒在桶里;扎排球网;包玉米——把玉米剥好,抹上黄油,撒上盐和胡椒,包上锡纸;在铁架上放好煤球,再在煤球上倒上汽油,点起火来烤肉了。我只要了一个肉饼和一个半生不熟的玉米。吃完饭,大家一起唱歌,彼得吹琴,爱德文弹吉它,唱得好快活。那西德女作家则坐在一边,泪汪汪的。“她是怎么啦?”我说。“她有很多不顺心。”潘耀明说,“她到这儿来过不惯,想家。而且她来这里,她在德国的工作也许要保不住。”“那她不要来好了。”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神经兮兮的。
彼得放下琴,叫我一起去打排球。我说我不会,他还是拉我去。起先,爱德文、潘耀明、我、芬兰女作家几个人在一边,打了两局,输了两局。后来,爱德文提出调整阵容,把alex要过来,把我则推过去。而我一过那边,那边便开始输,输了一局。彼得把菲律宾诗人、印尼诗人几个年轻人叫过去,布置了一通,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第二局开始了,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战术好像有一个变化,那是——当我要接球时,他们都从四面扑过来,从我这里救走这个球。我很惭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发了几个漂亮的球,为我们这边挣得了一两分。当然,我发球是站在界内网前,并且有两次机会,失了一球还可再补一球,这是两方都同意的,当我发过网一个球,那一片叫好声,也是双方都参加的。
玩得很开心。却也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
潘耀明对alex说:“你帮安忆联系一些年轻的作家,交流交流吧。”alex说:“好的。不过,我要去问问,人家有没有兴趣。”我听了这话,心里句想回答他的便是:“你还应该问问我有没有兴趣。”可我忍住了没说,因为我并不期待来这里向人家证明我自己,我只想多了解人家。我很好奇。然而终究有点不高兴。潘耀明沉思了一会儿说:“在美国,在,你会明白文凭、学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些,我都没有,我只有小说。然而我的小说,他们看不懂,他们似乎只承认用英文写的。好在,说中文的有的是,占世界人四分之一呢——似乎有点阿q的味道了。然而我们是阿q的子孙。
晚上,兰兰接我们去看她的录像带,是八一年中国的一个晚会。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是兰兰一手搞起来的。有舞校的教员许淑瑛的表演,她是兰兰请来进行中美舞蹈交流的。在靠前从没听说过,因为她从不参加演出,只教学和编舞。然而她在美国却轰动得很。大家都迷上了她,她跳的朝鲜舞比朝鲜还朝鲜——这是南朝鲜女画家朱今嬉女士说的。今年,兰兰去中国,看到了许淑瑛,兰兰说:“她变了,她身体很不好,衰老了,我忍不住哭了,我对她说:‘你要去看病!’后来,我看了舞校学生的一台民族舞,我又哭了,我说:‘你可以放心了,后继有人。’现在许淑瑛带了几个学生去西藏采风,那是她很后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她是个很好的舞蹈家。”晚会上,还有一个笛子独奏,演奏者是“”中从广州游泳到的,后来到了美国。他开了一个出租汽车行维持生计,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乐团搞演出。他有三个孩子,生活得不容易,好几次,有人偷他的汽车;他出去和人打,打得头破血流。他很想家,据说,那年,毕朔望他们遇到他,问他想不想回去,他没开哭了。……演出很成功,结束时,全场起立,长久地鼓掌。哦,啊!
外面下了一阵小雨,地,湿漉漉的。
(未完待续) - 【目录】
-
无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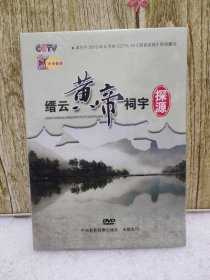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