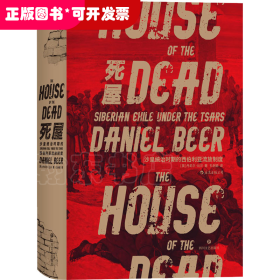
死屋 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电子发票
¥ 44.62 5.1折 ¥ 88 全新
库存19件
四川成都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英)丹尼尔·比尔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53624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8元
货号1202814514
上书时间2024-12-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序言乌格利奇的铜钟1
1流放制度的起源9
2界标31
3折断的剑57
4涅尔琴斯克的矿山91
5民主共和国115
6西伯利亚人150
7刑罚堡181
8“以自由的名义!”214
9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244
10萨哈林岛271
11鞭打304
12“失败者要倒霉了!”330
13收缩的大陆366
14严峻的考验393
尾声红色西伯利亚427
致谢432
注释434
出版后记509
内容摘要
《死屋》是一部原创历史研究著作,全面考察了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本书生动刻画了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以及逃犯和赏金猎人的历史。
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本书荣获2017年坎迪尔历史奖大奖,入围2017年沃尔夫森历史奖、2017年普希金俄语图书奖和2017年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被评为《泰晤士报》《旁观者》《BBC历史》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精彩内容
3折断的剑1826年7月13日凌晨3点,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罗要塞,警卫开启了位于要塞深处的狭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门缓缓打开,三十多名年轻的军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只会极其短暂地笼罩着俄国北方首都的天空,这些囚犯被带到院子里时,天已破晓。排在他们前面的,是来自圣彼得堡团的士兵以及数十名官员和显要人物。远处,在要塞的北门外面,囚犯们可以看到绞刑架,那是为了处决他们的领导者而专门竖立起来的。俄罗斯帝国最高法院已认定这些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人意图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起义于1825年12月14日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开始,两周后,随着切尔尼戈夫团暴动在基辅城外被镇压,起义失败。彼得保罗要塞是俄国专制政权的象征,它耸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国的权力中心冬宫与它隔河相望。这个要塞将成为国家复仇的中心。
十二月党人按要求排列成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一个噼啪作响的火盆前。他们的判决依次被宣读出来:被褫夺公民权,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他们的肩章被人从肩膀上扯了下来,连同他们的军大衣一起被抛至火中。每个军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后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剑刃中部被特意锉薄的剑,在军官的头上将剑折断。随后,这些囚犯换上发放给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权死亡”。这个仪式标志着他们被逐出了俄国社会,并且重申被他们触犯的法律的神圣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们“丧失了其地位带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是一种死缓。这场仪式结束后,书生气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甚至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怯懦地感谢沙皇“赐予我生命”1!
十二月党人将自己的判决理解为一种彻底毁灭的宣告。在这场仪式后,26岁的尼古拉·巴萨尔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时他“确信,我和这个世界的所有关联现在都消失了,我将在一个遥远又黯淡的地方度过余生……我将饱受折磨,穷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成员”2。这些被定罪的人将失去他们的财富、威望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贫穷和被忘却;他们将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光辉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亚银矿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维护了沙皇不可撼动的权力,保证他的敌人会被消灭。这就是在那个7月的早晨于彼得保罗要塞院子中大声宣读裁决背后的意图,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获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们因为领导了一场被镇压的起义而被流放,因此他们赢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当作自由和改革事业的牺牲者。西伯利亚后来从一个政治荒漠转化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舞台,如果要讲述这个转变历程,那么十二月党人的经历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成形。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沙皇王朝的忠诚。3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战场回来时头脑中也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军官称:“如果说我们用武力占领了法国,那么法国则用习俗征服了我们。”很多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比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伊万·亚库什金和米哈伊尔·方维津)在1815年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却发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军队生活中沉闷的纪律让人恼怒。他们曾和欧洲的“拿破仑专制主义”作战,如今他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基本是沙皇的个人封地的俄国。4被捕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写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释他参加起义的原因:我们让我们的祖国摆脱了暴政,但却再一次被我们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为什么我们解放了欧洲,自己却被困于枷锁当中?难道我们为法国带来了宪法,却不敢为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宪法?难道我们用热血换取了在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却在国内饱受压迫? 5其他军官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时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参战,比如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名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但他们却被伏尔泰、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所影响。在俄国战胜拿破仑后,他们从其他国家的自由派军官领导的要求立宪和独立的起义中获得了启发。61816年以后,这些爱国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开始在非正式团体和“秘密协会”中讨论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的集会越来越带有密谋意味,并逐渐产生了两大组织: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总部的“北方协会”,由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上校、卫队队长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列耶夫领导;另一个是以乌克兰为总部的“南方协会”,由帕维尔·佩斯捷利上校和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中校领导。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和波兰爱国协会之间有着广泛联系,波兰爱国协会中的很多波兰人后来也成为西伯利亚流放者。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在1825年的突然死亡促使十二月党人起义仓促举行,而此时十二月党人还未与波兰人结成牢固的同盟。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波兰人的观点较为保守,他们主要关心争取自身的独立、收回失去的省份。他们不想接触十二月党人更激进的共和主义计划。7当局知道了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以及由密谋者撰写和讨论的各种小册子。然而在开始时,当局对他们比较宽容,并没有采取行动来解散这些集会,更不用说逮捕参加者了。亚历山大一世在1823年视察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军队时,曾对他提出警告:“你最好继续你在[军队里]的工作,而不要关注我的帝国的政府,我恐怕那不关你的事。”8沃尔孔斯基没有理会这条警告。
1825年秋,十二月党人一直在筹划于来年夏天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然而,无嗣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出行俄国南部时突然于1825年11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康斯坦丁拒绝继承皇位,于是这些密谋者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到了。在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继承皇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十二月党人匆忙地拼凑起了武装起义的计划。12月14日,当卫戍部队按期齐集首都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时,十二月党人计划让忠于自己的部队开赴参政院广场。他们将在那里拒绝宣誓,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且要求颁布宪法。十二月党人依靠的部队并不了解起义目标,且十二月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清晰的战略规划。他们指挥的军队或许是支持他们个人,但几乎并不清楚他们的政治雄心。结果与其说是一场严肃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演出笨拙、很多演员忘记台词的政治戏剧。
12月14日早上,起义的军官率领大约三千名士兵进入白雪覆盖的参政院广场。士兵们围在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绘的是彼得大帝骑在腾跃的马上,而这匹马正踩着一条瑞典毒蛇。这个雕像标志着无情的彼得大帝驱逐其敌人的场景,现在它似乎在俯视着在其面前上演的戏剧。这次起义准备不足、组织混乱,因而在开始前就注定要失败。十二月党人委任的领导者和新共和国的临时“执政官”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在广场上;他已舍弃他的战友,在避难奥地利大使馆前已经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义者敲响战鼓,扬起他们的军旗,并呼吁制定宪法,但他们最终只展现了自己的孤立和无能。
忠于沙皇的军队迅速包围了他们,随着这一天的时间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尽,起义者人数不敌敌方且群龙无首。起义者试图通过协商来推翻专制制度,这种尝试自然是失败了,于是小规模冲突开始了。政府军用炮火和霰弹驱散起义者。起义军官逃跑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遭到了包围并最终被逮捕。即使是特鲁别茨科伊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的军官也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9南方的起义者在12月23日才听说圣彼得堡起义失败的消息,切尔尼戈夫团于12月31日在基辅城外发动了短暂而血腥的起义,但失败了。起义领导者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无法召集足够多的士兵参与他的事业,由他指挥的起义部队被轻易打败了。10这些革命者未能夺取政权,甚至连一天也没有。11十二月党人发动政变的尝试非常不专业、紧张且时机不当,这些问题有时掩盖了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主义。伟大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是几位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在他于1833年创作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表现出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密谋的轻视:他们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间进行的这些秘密议论,最初只是朋友间的争辩,还没让这种反叛的学问深深扎进他们的心坎,还都只是烦闷时的消遣,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12普希金居高临下地否认了十二月党人的观念,然而这种否认并没有公平地评价起义者的雄心的范围和意义。十二月党人从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国自己的共和主义传统里汲取了灵感。他们计划以共和式爱国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都很常见)为基础,彻底革新俄国的国家结构。他们设想着“诛杀暴君”尼古拉一世,谋杀皇室成员。专制制度将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在这两种制度下,主权都将从统治者手中转到人民手中。他们打算废除农奴制、贵族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团体和行会组成的混杂物。他们将引进现代国家的机制来代替上述机制。无论是作为一个单一制政府还是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政府,这些机制都将在平等和共同权利的基础上凝聚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从而锻造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再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相反,只有公民共同的权利和责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党人坚持欧洲的共和主义传统,在19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帝国,这类观念非常激进,因而是极富争议的。13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后续影响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为起义的暴力程度(大约三千人丧生)和刺杀皇室成员的计划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许多人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改革愿望,尤其同情他们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的主张。此外,对此次起义的镇压触及了沙皇俄国精英阶层的核心。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两三个兄弟都参与了起义。别斯图热夫家族和别斯图热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中都是重要人物;穆拉维约夫家族(还包括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三人于12月14日前往了参政院广场。十三名十二月党人是参政员之子,七名是省长之子,两名是大臣之子,还有一人是国务会议成员之子。但没有人比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族与皇室更亲近,谢尔盖所属的家族是俄国最古老、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儿时的玩伴。沙皇把他参加起义的行为当成对他个人的背叛。14即使法院的规章严苛,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家人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和兄弟逃脱沙皇的怒火。他们不断请求尼古拉一世宽大处理,指出这些军官年幼无知,而且惩罚他们就是惩罚对沙皇忠心耿耿的整个家族。面对这些请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专制权力的本质带来的一个障碍。在审理十二月党人这样重要的案件时,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会把所有关于审判和判决的事都交由年轻的沙皇做决定。所有人都明白,决定十二月党人命运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尼古拉一世个人的仇恨或宽仁。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发现:“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处决坏人,对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梦……俄国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我们的规则是父权制的、家长式的。”15在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尼古拉一世确实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权力和权威的顶端,这种情势又使得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家长式机制合法化:地主和农奴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父亲和家庭成员之间等类家长式关系。像许多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父权式统治体现着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协定:沙皇的臣民献出服务、服从和尊重,以换取沙皇的保护和照管。然而,在处理起义者家人的请求时,这种处于专制君主权力的核心的父权制构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16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