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穹之下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22.9 4.6折 ¥ 49.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玛蒂尔德?阿森西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90408
出版时间2019-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8元
货号28512704
上书时间2024-10-2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20世纪20年代,住在巴黎的西班牙画家艾尔维拉•德•普兰收到消息说,在中国经营家庭纺织企业的已分居的丈夫雷米离奇地死在上海家中,而她必须前去安排葬礼。
在费尔南达的陪同下,她乘船离开马赛,去上海取回雷米的遗体,并且要求分得他的遗产。可是,她没有意识到,这场旅程开启了一场穿越中国、不可抗拒的远征,只为探寻秦始皇陵的巨大宝藏。在历经艰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埃尔韦拉和费尔南达很快就发觉自己陷入了匪徒黑帮、鸦片烟馆和政治阴谋的罪恶陷阱……
作者简介玛蒂尔德•阿森西
1962年出生于西班牙阿里坎特,西班牙记者、超级畅销作家,主要擅长创作历史冒险及悬疑小说。
她在全球拥有两千多万小说粉丝,其作品在全球已畅销数,被译成16种语言,《阅读》杂志称她为“冒险小说女王”。她的作品都是苦心孤诣的成果,历史记述皆有据可依,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她曾荣获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其中:
2007年《后的加图》英语译本获得了国际拉美著作悬疑小说奖,以及冒险小说荣誉奖;
2008年《苍穹之下》获得国际拉美著作奖二等奖;
2011年因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萨拉戈萨历史小说荣誉奖。
目录
《苍穹之下》无目录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住在巴黎的西班牙画家艾尔维拉•德•普兰收到消息说,在中国经营家庭纺织企业的已分居的丈夫雷米离奇地死在上海家中,而她必须前去安排葬礼。
在费尔南达的陪同下,她乘船离开马赛,去上海取回雷米的遗体,并且要求分得他的遗产。可是,她没有意识到,这场旅程开启了一场穿越中国、不可抗拒的远征,只为探寻秦始皇陵的巨大宝藏。在历经艰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埃尔韦拉和费尔南达很快就发觉自己陷入了匪徒黑帮、鸦片烟馆和政治阴谋的罪恶陷阱……
主编推荐玛蒂尔德•阿森西
1962年出生于西班牙阿里坎特,西班牙记者、超级畅销作家,主要擅长创作历史冒险及悬疑小说。
她在全球拥有两千多万小说粉丝,其作品在全球已畅销数,被译成16种语言,《阅读》杂志称她为“冒险小说女王”。她的作品都是苦心孤诣的成果,历史记述皆有据可依,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她曾荣获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其中:
2007年《后的加图》英语译本获得了国际拉美著作悬疑小说奖,以及冒险小说荣誉奖;
2008年《苍穹之下》获得国际拉美著作奖二等奖;
2011年因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萨拉戈萨历史小说荣誉奖。
精彩内容乘坐安德乐朋号航行,我经历了无尽的头晕与痛苦。在某日中午,船竟意想不到地平静下来,我不情愿地用力睁开双眼,似乎那样就可以知道客轮在六个星期里次停止航行的原因。六个星期啊!四十个糟糕透了的日子,我只记得在甲板上待过一两天,而那还得非常勇敢才行。我没看见塞得港、吉布提、新加坡……甚至我们穿过苏伊士运河,停靠斯里兰卡和香港时,我都没能从船舱的窗口探出头去。从7月22日星期天早上离开马赛起,消沉和恶心就让我一直躺在那二等舱的小床上,喝姜茶和吸食令我发蒙的鸦片酊都无法减轻我的痛苦。
我与海无缘。我出生在马德里,一个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内陆城市,距离近的海滩很远,所以我觉得登上一条船,漂浮、摇晃着穿过半个世界,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更喜欢乘火车出行,但雷米总说那更危险。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起,横穿西伯利亚确实意味着真正的疯狂,因此我只好购买海运公司豪华蒸汽客轮的船票,希望海洋之神大发慈悲,不要萌生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的古怪想法,否则,我们的肉身将被鱼啃光,烂泥也将永远覆盖我们的骨头。有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来,当然,我也没有带着海员的天赋来到这个世界。
当船的平静和令人不知所措的安宁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我端详起悬挂在舱顶天花板上的风扇那熟悉的旋转扇翼。在航行的某个时刻,我曾发誓,如果我的脚能再次踏上陆地,就会按照在鸦片酊模糊的作用下看到的样子画出那台风扇,也许可以将画卖给酷爱我的同乡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立体派作品的商人康威莱尔。可是,扇翼朦胧的幻觉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船停了?为什么没有听见到达港口特有的嘈杂声和旅客们拥向甲板急促的脚步声?我马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毕竟我们位于不幸的中国海,在那里,在1923年,危险的东方海盗依然拦截客船,抢劫和杀人。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我的手开始出汗,恰好那一刻,我的客舱轻轻响起倒霉的敲门声:
“小姨,可以进来吗?”那位新晋外甥女用低沉的声音问道,她是我免费摸彩摸到的。
“进来吧。”我忍住轻微的恶心应道。费尔南达来看我只是为了把晕船茶拿给我,当她每次出现在我的客舱时,我的胃都会感到不舒服。
姑娘有点肥胖的身子艰难地跨过门楣。她一手拿着瓷杯,一手拿着总不离身的黑扇子。她从不放下那把扇子,从不松开在后脑勺盘成髻的头发。她那风华正茂的十七岁与从不脱下的丧服形成强烈对比,十分引人注目,那件丧服甚至对于一位马德里的小姐来说也显得很过时,完全不适合我们在那个纬度所遭受的炎热。我想给她一些衣服,一些更轻便、更漂亮的衬衫,还有一条更短,按照巴黎时尚,短到膝盖的裙子,然而,粗鲁且不会感恩的她断然拒绝了我的好意,画着十字,目光移向她的双手,俨然一副明确表示不再讨论此事的神情。
“船为什么停了?”我想知道,同时,闻着厨师为几位旅客例行煎制的汤药的香气,缓慢地直起身。
“我们离开大海了。”她坐在我的床沿,将茶杯送到我的嘴边,“我们在一个叫作吴淞的地方,距离上海十四海里。安德乐朋号行驶缓慢,是因为我们正在逆流而上,也许会触及河底,几个小时后就能到岸。”
“终于要到了!”我发现临近上海比姜茶对我更有疗效。可是,我无法感到舒服,直到离开那个令人讨厌的弥漫着硝石味的客舱。
无论我怎么躲避,费尔南达不但不把杯子从我的嘴唇移开,相反,还做了个想笑的鬼脸。那个可怜虫长得酷似她的母亲,也就是我难以忍受的姐姐卡门。五年前,她在1918年的那场可怕的流感中离世了。除了性格,她拥有和她母亲一样又大又圆的眼睛,一样突出的下巴,以及一个令人生厌的小肉球为终点的鼻子。那个肉球使两人都拥有滑稽的外表,她们的脸总是显露甚至让勇敢的人都感到害怕的酸酸的表情。肥胖,则来自她的父亲,我的姐夫佩德罗,一个大腹便便、下巴肉多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大胡子遮丑的男人,一个也不和善的男人。由那对讨厌的夫妻生出那样一个严肃、穿丧服、像蓖麻油一样甜的小姑娘就不足为奇了。
“小姨,该收拾您的东西了。您希望我帮您准备行李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嘀咕道,带着痛苦的表情让自己倒在床上。我在夸大痛苦,实际上相当真实,但却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不过,既然她自告奋勇,为什么不让她做呢?
她在我的箱子里翻动着,收拾我在那痛苦的旅行中使用过的少许物品,我开始聆听走道上快乐的喧哗声和说话声,二等舱的其他旅客无疑和我一样急着上岸,返回陆地,跟余下的人在一起。这个想法使我那么兴奋,乐意做出努力,在呻吟和抱怨中直起身,双脚着地,坐在床上。我十分虚弱,这不容置疑,但比疲劳还糟糕的是恢复悲伤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被鸦片酊带来的昏睡驱走,不幸又被昏睡后的清醒送了回来。
我不知道办理雷米的事会让我们在上海待多久。尽管那个时候想起回程会令我毛骨悚然,可我却希望在这座城市逗留的时间尽可能短些。事实上,为了加速办理手续和尽早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已经通过电报和律师约好第二天早上见面。雷米之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残酷、可怕的打击,一个依然令我难以接受的困境。雷米死了?多荒谬啊!这是一个完全可笑的想法,但是,我对接到消息的那天记忆犹新。就在同一天,费尔南达带着她的小旅行皮箱,裹着黑色外衣和小资的西班牙姑娘俗气的小短斗篷,出现在我巴黎的住所中。当时,一位外国事务部的先生站在门前,摘下帽子,在向我表示他深切的哀悼后,交给我一份官方公文,上面粘着一份海底电报,告知我雷米死于几个潜入他上海的住所进行偷窃的毛贼之手,而她则还在试图让我接受那个我一点儿也不认识的黄毛丫头是我姐姐和她刚去世的鳏夫的女儿。
我能做什么?根据公文,我应该长途跋涉到中国领走尸体及处理法律上的事务,可是也必须作为遗嘱执行人对费尔南达负起责任。她喜欢费尔南蒂娜的名字,但我无法这么叫她。她出生的时候,我已在几年前与我的家庭彻底断绝关系,并于1901年动身前往法国大茅舍画院学习绘画,那是巴黎一所免费注册的学校。我没有时间垮下来,也没有时间可怜自己:我贱卖了工作室里所有的油画,买了两张周日早从马赛起航前往上海的贵极了的船票。总之,不管怎样,雷米·德·普兰是我好的朋友。当我想到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欢笑、说话、行走、呼吸,就觉得心中一阵锐利的刺痛。
“小姨,您想戴哪顶帽子下船?”
费尔南达的声音让我回到现实。
“那顶蓝色花的。”我嘀咕道。
我外甥女待着没动,用我们小时候她母亲同样不确定的专注望着我。她继承的、隐藏自己想法的习惯是我不喜欢她的地方,尽管她不愿意,但无论怎么隐藏,都猜得出她在想什么。我已经跟她的外祖母和母亲进行了很长时间那种训练,所以那位姑娘拿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您不是更喜欢贝雷黑帽吗?搭上某件相配的连衣裙,挺适合您的。”
“我打算戴花帽,配上蓝色的衬衫和裙子。”
中立的眼神继续着。
“您还记得总领馆的人要来码头接我们吗?”
“就因为这我才打算穿戴跟你说过的衣帽,那是适合我的衣服。对了,还有白色的手提包和鞋子,拜托了!”
当所有的箱子都被关上,需要的衣物都摆在床边的时候,我外甥女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客舱。那个时候,幸好客船形同静止一般,我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从小窗口我可以注意到,我们的船在大船及一群有方形帆的小快船拥挤的交通中缓慢前行,在方形帆遮光的影子下躲着孤独的渔民,或者难以想象地躲着包括老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中国家庭。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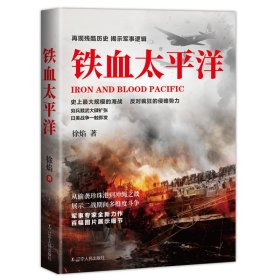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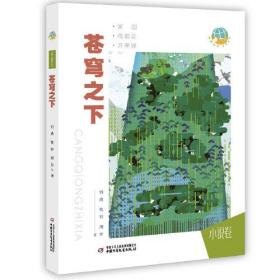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