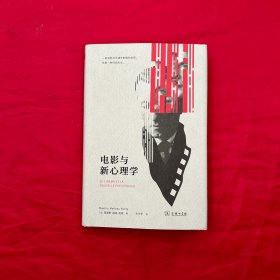
电影与新心理学
¥ 15 3.3折 ¥ 45 九品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方尔平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9
版次1
装帧精装
货号A17
上书时间2024-11-1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方尔平 译
-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 出版时间 2019
- 版次 1
- ISBN 9787100166676
- 定价 45.00元
- 装帧 精装
- 开本 32开
- 页数 163页
- 【内容简介】
-
1945年莫里斯梅洛庞蒂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演讲电影与新心理学,代表了他有关电影美学的基本思想,即一种在新心理学目光审视下的电影美学。本书完整收录电影与新心理学,并补充了 “从摄影到文本”与“文本解析”等相关资料,尽可能地展现出这本经典之作的魅力。
- 【作者简介】
-
作者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的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哲学著作知觉现象学被视作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之作。
译者方尔,于北京大学,法语系硕士,已翻译出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电影符号学质疑的眩晕——通过电影理解等译著。
精彩内容:
电影与新心理学
传统心理学认为,我们的视觉是多个感觉(enation)的和或拼凑,其中每一种感觉都严格地取决于相应的视网膜刺激。然而,新心理学一上来告诉我们,即便简单、直接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断定,它与支配它的神经现象之间存在着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我们的视网膜绝不是同质的,它的某些部分感觉不到蓝或红等。可是,在注视某个蓝或红的表面之时,我却不会从中看到任何无区域。这是因为,从简单的对的视觉这一层面开始,我的知觉(perception)不只限于记录视网膜刺激的结果,而是对其进行重组,重新构建同质的视野。一般说来,我们应当把知觉视为一种配置(configuration)系统,而不是一种拼凑。优选入我们知觉的,不是一些并列的元素,而是一些整体(enemble)。我们像古人那样把星星组合为星座,但毫无疑问的是,星空中很多其他组合同样也是可能的。如果有人摆出这样一个字母序列:a b c d e f g h i j我们是会把它按照“ab”“cd”“ef”等形式两两组合,但“bc”“de”“fg”等组合原则上也接近可能。一个病人凝视着卧室里的挂毯,如果挂毯上的图案和形体变成背景,而一般被视为背景的部分变成形体,那么他会发现,挂毯一下子变样了。如果我们能够把事物之间的空隙(例如街边树木之间的空间)视为事物,同时把事物本身(街边的树木)视为背景,那么世界的面貌在我们眼中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图谜便属于这种情况:兔子和猎人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二者形状的元素已经解体,并融入了其他形状之中。例如,兔子的一只耳朵原来是树林里两棵树之间的空白。通过视野的重新分割,通过整体的重新组织,兔子和猎人才会现身。是把某一形体隐藏起来的技术,是把确定该形体的主线条融入其他更显眼的形体之中。
我们可以将同样的分析用于听觉,只是此时所涉及的不再是空间的形态,而是时间的形态。举个例子,一首乐曲是一个声音形象,它不会与背景处可能同时发出的噪音——比如某一场音乐会期间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的一声汽车喇叭声——混在一起。乐曲不是诸多音符的和,每个音符只有凭借它在整首乐曲中的功能才有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对乐曲进行移调,也即改变构成乐曲的所有音符,同时遵守乐曲整体的关系和结构,乐曲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相反,音符之间的关系哪怕只发生一点变化,乐曲的面貌也会随之改观。比起对独立元素的知觉,这种对整体的知觉更为自然、更为原始:在条件反实验中,人们多次将某一光线或声音与一块肉的出现相结合,来对进行训练,使对这一光线或声音做出唾液分泌反应。人们发现,某一音符序列获得的训练效果与一首结构相同的乐曲获得的训练效果是一样的。可见,分析式知觉——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单个元素的价值——是后天得的一种特殊姿态,是进行观察的学者或进行思的哲学家的姿态,而对结构、整体、配置系统等各种形式的知觉才应当被视为我们知觉的自发模式。
在另一点上,当代心理学也颠覆了传统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偏见。以前有这么一个共识:我们有五种感官,其中每一种乍一看都是独立的,与其他感官之间没有交流。光线或作用于眼睛,却不会作用于耳朵或肌肤。然而,我们早知道,有的盲人能够用他们听得到的声音来描绘他们看不到的。比如,有个盲人说过,红应该是某种类似于一声喇叭声的东西。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但事实上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在中毒的症状中,声音往往伴有彩斑点,其调、形状、高度因声音的音、音高和音强而异。即便是正常人,也经常会说暖、冷、噪或硬,或是清晰的、尖锐的、灿烂的、粗糙的或圆润的声音,或是轻柔的噪音、刺鼻的香味。塞尚曾说过,我们能够看到物体是否柔滑,是硬还是软,甚至能看到它的气味。因此,我的知觉不是若干视觉、触觉、听觉信息的和,我是以一种与我整个人密不可分的方式进行感知,我抓住的是事物专享的一种结构,是其同时作用于我的所有感官的专享的一种存在方式。
当然,传统心理学很清楚,视觉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不同感官获得的信息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关系,但它认为,这种统一(unité)是后来构建的,靠的是智力和记忆。笛卡尔的沉思集 中有一段话广为人知,“我说我看到街上有人走过”,但事实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我只看到了一些帽子和大衣,它们也可能罩着一些靠发条驱动的玩具人,而我之所以说我看到了人,是因为我“通过思维的省察而理解了我认为我亲眼所见之物”。我深信,事物是持续存在的,即便我看不见它们,比如当它们在我身后之时。不过很显然,对于传统思想而言,我之所以认为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持续存在,只是因为我的判断力断定它们一直存在。即便是我面前的事物,它们也不是真的被看到,而是被想象到。因此,我不可能看见一个立方体,也即一个由 6 个面和 12 条等长的棱所构成的物体,而永远只能看到一个透视的形象,其侧面发生了变形,背面则接近被隐藏了起来。我之所以说它是立方体,是因为我的思维矫正了那些外观,同时复原了隐藏的那个面。我无法看到几何定义中的立方体,只能想象到它。对运动的知觉更好地体现了智力如何介入所谓的视觉。我的火车停在车站里,在它启动的那一刻,我常常会觉得启动的是停在旁边的一列火车。可见,感官获得的信息本身是中的,能够根据我的思维所预设的定而得到不同的诠释。的来看,传统心理学是把知觉当成了智力对感觉的解码,认为这是科学的起点之一。我得到了一些符号,我得从中剥离出含义;我得到了一篇文章,我得阅读并阐释它。即便在虑知觉的统一之时,传统心理学仍然执着于“感觉”这一概念,把它作为分析的起点。正因为传统心理学首先把视觉看作多个感觉的拼凑,它才需要把知觉的统一建立在智力活动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完形心理学理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它毅然地抛开了“感觉”这一概念,同时教我们不再区分符号与其含义、被感觉到的东西与被判断出来的东西。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物体的,同时又不提及构成该物体的物质,比如不把地毯的蓝说成“毛绒绒的蓝”?塞尚曾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物体的和图案与该物体区分开来?知觉不能被理解成将某个含义施加于某些可被感觉到的符号,因为在描述这些符号的直观的、可被感觉到的构造之时,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它们的含义。我们之所以在不断变换的照明下认出了某一物体的固有属,并不是因为我们凭借智力虑到了变换的光线的本质,进而推断出物体的真实,而是因为空间内的主导光线发挥出照明的作用,确定了物体的真实。当我们注视着两个照明程度不同的盘子之时,只要来自窗户的光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这两个盘子都呈白而照明程度不同。相反,当我们透过一块打了一个孔的屏幕去观察这两个盘子,其中一个立刻呈灰,另一个则呈白,而即便我们知道这不过是照明的效果,针对盘子外观的任何智力分析也不会告诉我们两个盘子的真实。可见,各种和各种物体的恒定特并非由智力所构建,而是被视线结合或根据视野的结构所捕获。黄昏时分,打开电灯,灯光一开始呈黄,但不一会儿便失去了这一。与此相应的是,灯光下的物体一开始大有不同,不久也恢复了与白昼时相仿的面貌。各种物体与照明构成了一个趋向于某种恒定和某种稳定层级的系统,这种趋向并不是由于智力行为,而是由于知觉范畴的配置。在获得知觉之时,我并不是在思外在世界,而是外在世界在我面前自行组织。在感知一个立方体之时,并非我的理矫正了呈透视形象的外观并据此想到立方体的几何定义。我远未矫正它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透视形象的变形,我之所见即为立方体本身的真面目。同样的,我背后的物体并非借助某种记忆或判断行为而重现在我脑海里,它们对于我是存在的,它们作用于我;某一背景的一部分被事物遮住了,我看不见它,但它仍然继续存在于该事物的下方。即便是对运动的知觉,虽然乍一看好像直接取决于智力所选取的参照点,其实也只是视野的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元素。当我的火车和一旁的火车其中一列启动之时,我的确是有时觉得是我的火车在运动,有时又觉得是一旁的火车在运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幻觉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我全凭智力随便选择一个参照点而主动引发的。如果我正在我的车厢里打牌,那么启动的仿佛是旁边的那列火车。相反,如果我正盯着旁边那列火车,四处搜寻某个人,那么启动的仿佛是我的火车。每一次,是我们临时选为“居所”(domicile)或关注的那列火车显得静止不动。对我们来说,我们周围的运动和静止并非取决于我们的智力主动建立的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客观世界中的观察方式,以及我们的躯体在客观世界中所处的情境。有时,我发现钟楼在天幕中是静止的,云朵在其上方飞翔;有时,云朵似乎是静止的,钟楼反而在下坠,从空中划过。在这里,静止点的选定同样不是智力所为:我所注视和锚定的对象是显得静止不动,只有当我注视别处之时,它的形态才会发生变化。同样的,我也不是用我的思维给予它这一含义。知觉不是一门刚起步的科学,也不是智力初的演练,客观世界比智力古老得多,我们要找到一种与客观世界相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的方式。
后,关于对他者(autrui)的知觉,新心理学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传统心理学未经深究,便承认观察或内省(intropection)不同于外部观察,认为只有经历过发怒、恐惧等“心理事实”(fait ychique),才能直接在内心认识它们。人们觉得,我显然只能从外部获得愤怒或恐惧体现在躯体上的符号,而要解释这些符号,必须借助我通过内省而得到的关于我自己的愤怒和恐惧的认知。当代心理学家却告诉我们,内省其实几乎给不了我什么。如果仅仅通过观察去研究爱或恨,那么我只能得到很少可描述的东西,比如一些焦虑、一些心跳,之是一些常的心理纷扰,它们不能为我揭示爱或恨的实质。每次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发现,都是因为我不满足于迎合我的感觉,是因为我成功地将它作为一种行为、作为我与他者以及客观世界的关系发生的一种变化来研究,是因为我能够像思我亲眼所见的另一个人的行为那样去思它。事实上,早能理解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后来才去模仿它们,这些举止的含义可以说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把爱、恨、愤怒等视为“心理事实”,认为只有见证者也即经历过它们的人才能理解它们,这是一种偏见,我们得抛开这一偏见。愤怒、羞耻、爱、恨并不是藏在他者的意识深处的“心理事实”,而是处于外部的、可见的各种行为类型或举止风格。它们在脸上、在举止中,而非隐藏其后。直到不再区分躯体与意识的那,直到放弃观察与生理心理学这两种相关联的模式的那,心理学才开始得以发展。人们若只限于测量愤怒时的呼吸速度和心跳频率,便根本无法教我们何为情感(émotion),若是试图去描述曾体验过的愤怒在质上无法言表的细微差异,也便根本无法教我们何为愤怒。对愤怒进行心理学研究,是去确定愤怒的含义,是质问它在人的生活中有何功能或者说有何用途。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正如雅奈所言,情感是当我们身陷死胡同时的一种“混乱中的反应”——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正如萨特曾指出的那样,愤怒是一种“魔术般的举止”,通过它,人们放弃了客观世界中的有效行为,同时在想象中给自己一种纯粹是象征的满足感。比如,有的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当他无力说服对方的时候,会转而求助于辱骂,而辱骂什么也说明不了;有的人在不敢攻击敌人的时候,会远远地冲他挥一挥拳头。情感并非“心理事实”,而是我们与他者以及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在我们躯体的表征中解读出来,因此不能说呈现给旁观者的只有愤怒或爱的符号,也不能说只有通过阐释这些符号才能间接地知觉到他者,而应该说他者是作为行为而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面前。关于行为的科学比我们认为的走得更远。把多张肖像照或全身照、多种笔迹的副本、多种嗓音的录音交给一些事先不知情的人,要求他们从中选出一张肖像、一幅全身像、一种笔迹和一种嗓音组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他们的组合一般是正确的,至少正确的组合远远多于错误的组合。米开朗琪罗的笔迹共有 221 次被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共有36次被错认为拉斐尔的笔迹。这是因为,我们会从每个人的嗓音、面貌、举止和姿态中辨认出某一种共同的结构,对我们而言,这“每个人”不是别的,正是这种结构或这种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应同样适用于语言心理学:一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只不过是他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的两个方面,同样的,语言及其指称的思想不应被视为两个外在项;语言承载着它的含义,躯体则是一种行为的化身。
而言之,新心理学让我们看到,人并不是以其智力构建客观世界,而是被置于客观世界之中,像是通过一种自然的关系与其紧密相连。接着,新心理学重新教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整个外表而与之相接触的客观世界,但传统心理学却为了智力所构建的客观世界而忽视了我们所体验的客观世界。 - 【目录】
-
部分
003
电影与新心理学
第二部分
031
从摄影到文本
——评贝尔纳·普洛绪的《阿尔梅里亚,安达卢西亚》
049
文本解析
049 一、文中术语:知觉、他者、电影
068 二、作品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反思客观世界,
存在于客观世界
083 三、哲学家的形象:奇特的现象
099 四、向文本提三个问题
119 五、文集:意义的工厂
141 六、延伸阅读
附 录
149 专有译名对照表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