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爱纳兰词/古韵流芳系列 中国古典小说、诗词 苏缨
正版书籍 支持7天无理由
¥ 9.4 1.6折 ¥ 59.8 九五品
库存5件
河北保定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苏缨
出版社武汉
ISBN9787543041905
出版时间2009-06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220页
定价59.8元
货号702_9787543041905
上书时间2024-06-2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32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正版特价书籍
- 商品描述
-
主编:
版本升级?与时俱进?纳兰迷的收藏
纳兰容若,清初词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一生富贵。行走于仕途,心却始终游离于喧嚣之外。他是血统纯正的八旗子弟,却因初入中原,未染纤毫汉人风气。一生喜结落拓之人,一生为情所困,一生几乎拥有了世间的,一生,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孤独。三百年来,纳兰容若,这样演绎着他的传奇,让后人欲罢不能——希望了解他的人,他的诗,他的朝代与情殇,点点滴滴。
读苏缨的一生很爱纳兰词,可以管中窥豹了解纳兰容若的人生,了解这位奇男子的一生是那样短暂却又那样如诗般璀璨。以为,除了清代女词人顾太清外,今人,唯有苏缨,很懂纳兰。
目录:
可耐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 / 1
剩月零风,人间无味 / 7
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著思量 / 21
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 / 28
是耶非耶 / 37
锦样年华水样流 / 43
人道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 / 49
若问生涯原是梦 / 55
看尽一帘红雨,为谁亲系花铃 / 61
莲子依然隐雾,菱花暗惜横波 / 65
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 69
谁是知音者 / 76
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 / 83
博山炉烬未全灰 / 86
伴我萧萧惟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 / 91
倚马客临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 / 95
逗雨疏花浓淡改,关心芳草浅深难 / 99
欲倩烟丝遮别路,垂杨那是相思树 / 105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 / 108
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 112
人生那不相思绝 / 116
鹤孤华表,人远罗浮 / 121
梦回疑在远山楼 / 125
人间何处问多情 / 131
谁道飘零不可怜 / 134
人生别易会常难 / 142
画眉闲了画芙蓉 / 149
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 / 156
鸳鸯拂破白萍去 / 159
至今青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 / 169
夜深千帐灯 / 176
寻常风月,等闲谈笑,称意即相宜 / 181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此身良苦 / 183
内容简介:
一生很爱纳兰词是清代词人纳兰德的词作典评集,收录了浣溪缕曲沁园春江城子台城路等经典作品。一生很爱纳兰词所选词作,在纳兰的作品中很具特,很具代表。词集由知名书作家苏缨执笔,可以说以很懂纳兰的心思写尽纳兰一生诗词之。此次出版,增加纳兰容若词精选一册随书,收录较为精简的纳兰词33首,供读者品读赏析。
精彩内容:
可耐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
——浣溪沙(欲问江梅瘦几分)
欲问江梅瘦几分,
只看愁损翠罗裙。
麝篝衾冷惜余熏。
可耐暮寒长倚竹,
便教春好不开门。
枇杷花底校书人。
这
首浣溪沙(欲问江梅瘦几分)是纳兰词研究中的一个迷案。很多人费尽心机地想要参详出这美丽文字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一位女子,藏着怎样的一个故事。搞历史和搞八卦大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只不过历史搞的是古代明星的八卦。
我们慢慢来看。“欲问江梅瘦几分”,像是咏物,吟咏的对象是江梅。什么是江梅呢,如果你把它简单理解成江边的梅花,那你不但在事实上错了,还严重违背了小资精神。范成大有个梅谱,详列各个梅花品种,但分类的眼光与其说是植物学的,不如说是诗人的。他说江梅也叫野梅,体现的是山野清绝之趣,花朵较小,清瘦有韵致,香气很清。
这种分类手法,充分体现着老百姓和小资的一大区别。比如喝咖啡,老百姓会说“来一杯咖啡”,小资会说“一杯蓝山”,虽然专家说中国从没进过真正的蓝山咖啡豆,但“蓝山式”足够了。细节决定小资,所以小资的眼里不存在作为泛称的咖啡,而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咖啡品种;小资的诗里也不存在作为泛称的梅花,而只有江梅、雪梅这样的细分。
江梅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是清瘦、孤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拟人了,于是有了下一句“只看愁损翠罗裙”。两句话连起来看,字面意思是说:要问江梅到底瘦成什么样了,只要看看那女子的裙子是不是又显肥了。这个修辞很好巧妙,用后半句来揭示前半句所谓的江梅其实是指一位江梅一样清瘦、孤傲的女子。而她的瘦,不是因为发育不良,而是因为“愁”。为什么愁,下一句交代得更加巧妙“麝篝衾冷惜余熏”。
“麝篝”是燃麝香的熏笼,“麝篝衾冷惜余熏”顺畅的语序应该是“衾冷麝篝惜余熏”,说那女子觉得被窝有点凉了,去看熏笼,麝香已经烧完了,那残留的香气和温度分外惹人怜惜。——文人能把龌龊的思想表达得很好优美、很好含蓄。在诗歌套语里,如果说一个女子嫌被窝冷,通常只暗示着一个原因:想男人了。这里还有第二层意思,因为在古代男权社会,话语权把握在男人手里,女人很少会写诗来想男人,而男人想女人的时候,常常会托女人的吻,或者想女人的生活情景,写那个女人在思念自己。——如果女方实在不具备对等的才华来作自己诗词唱和的红知己,那由男方亲手捉刀,玩左右手互搏好了。
下片开头两句对仗,是浣溪沙这个词牌的部分,容若这里写的是“可耐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这是描写女主角的生活:天晚了,冷了,倚着竹子,算春光好天气也不把房门打开。
“可耐”即无奈、可叹。“倚竹”是个诗歌套语,出处在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暮倚修竹”,写贵家女子生活的沦落和沦落之后保守的节。而春光明媚也不开门则说明了至少两种可能:一是她心里不痛快,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二是她心里想着某个遥远的情郎,因为得不到爱情的慰藉,便对撩动的春光也无动于衷了。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呢?末句给出了:“枇杷花底校书人”,这是用唐代才女薛涛的典故,王建有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不如”。“女校书”、“枇杷花”、“闭门居”都在王建这首诗里找到了出处。
“校书”本是“校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人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叔作过校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其中名句“弃我去者昨之不可留,乱我心者之多烦忧”尽人皆知。要作校书郎这个官,需要才学,也需要细心,薛涛二者兼备,名气又大,便被当地的长官戏称为“女校书”。逐渐地,这个雅号的使用范围被扩大了,变成了乐伎的代称,好像我们现在称为副处级干部一样。
这里有一点值得仔细区分,古代的乐伎、歌伎并不是,她们是艺不身的,对这一点,政策上有严格规定。比如在歌舞业很发达的宋代,如果按照现在的分类,歌伎属于合法的演艺人员。但另一方面,歌伎属于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官伎隶属于官府,属于乐籍;私伎隶属于主人,和牛马猪样一个地位,可以被主人自由买,也广为士大夫所蓄养,宋词名家如欧阳修、苏轼等等,概莫能外。
官伎又分几种,大家读宋词和宋史的时候会常见到“营伎”这个词,这不是随军慰安妇,而是特指隶属于地方的官伎,其管理机构叫乐营,负责人称乐营将,所以地方上的官伎便被称为营伎。
宋代对官伎是有管理制度的,们可以使官伎佐酒,但是被严令止的。史料里记载过一些因为越界受到惩处的例子,所以有的书里讲宋词多是嫖客写给的美丽情书,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这个官伎管理制度还延续到了后世,比如讲明史的书里提到靖难之变,常说明成祖朱棣把失败的政敌们的妻子、女儿没入乐籍,充任官伎,每天有很多男人兴致勃勃地来这些曾经的金枝玉叶。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其实这只是低俗小说的亢奋想像,不可当真的,官伎虽是贱民,但不是。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扬州瘦马”,因为投名状而尽人皆知,其实“养瘦马”其语其事早在宋代有了。这些“瘦马”养成之后被为歌伎。的时候还要签合同,要经过官方认可,合同有签终身的,也有只签几年的。
官伎不身,私伎当中有些则是市井,也有歌伎兼职的,李师师是其中的典范。
讲这么多背景知识,是因为这对理解女主角的身份很有帮助。有的注本把“枇杷花底校书人”简单理解为枇杷花底下的读书人,这大错特错了。文人写东西,对别人的身份经常使用代称,但这个代称要很好切合本人才行,不能有一点马虎。比如有人送阎锡山一副对联:“都督阎公雅望,晋国天下莫强”,上联抄自王勃滕王阁序里的“都督阎公之雅望”,很好切合阎锡山的身份;下联出自孟子,恰合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相反,如果身份不很切合,难受到别人的质疑和批评,比如吴梅村永和宫词“汉家伏后知同恨,止少当年一贵人”,这里的典故是:汉献帝的伏皇后被曹所杀,还有个董贵人也一起被杀,比喻的是崇祯皇帝的周皇后去世之前,田贵妃已经去世了。赵翼对这句的用典提出了批评:周皇后是奉旨自尽的,伏皇后是被曹所杀的,两者没有可比。
换一个角度来想,女校书已经变成了歌伎的代称,如果用这个词来称呼良家妇女,岂不是太过唐突了。像现在“小姐”变成了的代称,所以人们对年轻女一般不再轻易以“小姐”相称了。由此看来,容若这首词里的女主角无疑是一位歌伎,而且是像薛涛一样程度很高的歌伎。她会是谁呢?很合理的推测自然是沈宛。纵然不是沈宛,也只能是个歌伎。
但是,很流行的意见认为词中女主角是容若那位入宫的青梅竹马的表妹,这是苏雪林证出来的:“但不幸他恋人入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便死了。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入那深沉宫,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入宫以后的生活又像容若所写:欲问江梅瘦几分,只看愁损翠罗裙”
看看苏雪林的通篇证,倒也有鼻子有眼的,但至少对于这首词的含义接近领会错了。“女校书”这个称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冠在表妹的头上。“枇杷花”在写实的一面上又是南方的物产,如果表妹真收到这样一首词,恐怕非跟多情的容若表哥分手不可。
很后说说读音问题。这首词肯定很多人读起来感觉不流畅,原因很简单,这是字音的古今差异造成的。这问题其实古来有,明清时候要写诗填词已经得硬生生地背韵谱了,这也算是古典诗词的一个小小的技术壁垒。
“只看愁损翠罗裙”,“看”字可可仄,这里读声,现代汉语的一声。
“麝篝衾冷惜余熏”,“惜”是入声字,读诗词遇到入声字有一个很不规范但很方便的替代方法,那是把入声字读成四声,比如“惜”可以读成“戏”,但要尽可能读得短促一些。
“可耐暮寒长倚竹”,“竹”是入声,方法同上。
“便教春好不开门”,“教”字可可仄,这里是声,现代汉语的一声。
下面,把这些影响声音流畅的字换成括号里的字,大家再读一下,感觉不一样了。常常这样练一下逐渐能体会到古典诗词的音律之美了:
欲问江梅瘦几分,只看(刊)愁损翠罗裙。麝篝衾冷惜(戏)余熏。
可耐暮寒长倚竹(住),便教(交)春好不开门。枇杷花底校书人。
剩月零风,人间无味
——金缕曲亡妇忌有感(此恨何时已)
此恨何时已!
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
料也觉、人间无味。
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
钿钗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
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
待结个、他生知己。
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
清泪尽,纸灰起。
宋
词里边有很多缠绵悱恻的句子,隐藏着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词大多是写给歌女的,歌女作为宋代略具或颇具素养和艺术才华的群体,自然容易受到那些文人士大夫们的狂热追捧。但官方的三令五申止了他们“形而下”的结合,那千般幽怨、万种柔肠便只能付给鱼雁传书和浅斟低唱了。爱情在别处,唯独不在自己家里。
现代人对这些也许很难理解。古代社会里,妻子的任务是传宗接代、相夫教子,需要扮演的是贤内助的角,而不是丈夫的爱情对象,很理想的恩爱境界也不过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了。如果丈夫和妻子之间产生了爱情,反倒是大可怪异的事。
所以,我们看唐诗宋词,虽然很有一些丈夫写给妻子的佳作,但细心体会之下,会发现诗词中所表达的感情虽然深厚,但越看不像是爱情。屈指可数的那几篇悼亡的名作也是这样。
悼亡作品是古典诗词的一个特殊的门类。妻子去世了,丈夫借着诗词来表达哀思,表达对妻子的深情与怀恋,句句是泪水,句句是叹息,情真意切之处很能唤起读者的感动和同情。但是,那不是爱情。
历代很有名的悼亡诗要属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很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生未展眉。
有人把容若的悼亡词与元稹这三首诗相提并论,但是,它们虽然都是悼亡作品的典范,却貌似而神不相同。元稹所感怀的,更多的是一种感恩之情:回想妻子刚入门的时候,从显赫之家嫁入自己这个低矮的门庭,甘心陪自己过着清贫的子,好容易自己时来运转作了高官,本可以报答妻子的恩情,让妻子过上富贵的生活,谁知道人鬼殊途,再没有补偿妻子的机会。通观三篇,意尽于此。元稹的爱情到哪里去了呢?是:早随着“待月西厢”的往事化作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
悼亡诗首推元稹的遣悲怀,至于悼亡词,名篇则非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莫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也常被人与容若的悼亡词并论,但是,苏轼在这里所流露出来的感情,更多的是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情真意切虽然不,爱情的迹象却依旧难寻。
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和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分别属于悼亡诗与悼亡词的经典,但我们若把它们理解为之间的爱情宣言,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用现代的婚姻观念来解说古代的风土人情了。以前我在讲到宋代词人与歌伎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歌伎们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和文人士大夫很有共同语言,所以很容易摩擦出火花、产生出爱情。而嫁给文人士大夫的良家妇女却是严学这些东西的,之间只有义务和感情,而罕见会有爱情。这一点是我们现代人尤其值得注意的,否则的话,以现代价值观来衡量这些古人,把悼亡诗词理解为爱情的表现,那么我们在看到那些写出深沉悼亡诗的文人竟然又和歌伎缠绵起来,难会怒从中来,痛骂这些人面兽心的古人。”
理解诗词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很多诗词的注本、赏析本对婚姻爱情的观念问题不加辨别,所以解说的基础自然偏了。我们只有晓得了这些背景,再读纳兰词,才会明白为什么纳兰词会在词史当中别具一格,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悼亡诗词的典范之作里,容若这首金缕曲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因为词中所哀悼的之情既不是恩情,也不是共患难的人生沧桑,而是货真价实的、赤裸裸的爱情。现代读者很难理解的是:直接抒写婚姻生活中的爱情,这在古代士大夫的正统里是大逆不道的。
世说新语里有过一个有名的典故,是说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是降不下来,当时正是十冬腊月,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但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也被折磨得病重不起,很快也随妻子而去了。
这个故事,在世说新语里被当作一个反面教材,认为荀奉倩惑溺于儿女之情,不足为世人所取。尤其是,婚姻应当合乎礼法,而爱情正是礼法的破坏者。容若却喜欢这个荀奉倩的故事,因为世人虽然把荀奉倩斥为“惑溺”,容若却深深地理解他,只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是一样的不那么“理”的深情的人。容若的蝶恋花辛苦很怜天上月中,“不辞冰雪为卿热”一句用到的是这个典故。
只此一点,容若足以成为礼法社会中的异类。原因何在,大约是王国维所谓的容若一方面浸于博大精深的汉,一方面仍然保留着马背民族的淳朴天真。
现在要讲的这首金缕曲,写在容若的发妻卢氏去世后的第三年。卢氏在十八岁那年嫁给容若,,欢情无极,但三年之后便死于难产。卢氏的死,对容若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如果以编年的顺序来读容若的诗词,很容易会发现卢氏去世的那年是容若诗词风格的一个分水岭。苍凉取代了天真,取代了红烛,单是悼亡词,容若便写了几十首之多。
这首金缕曲是容若所有悼亡词中很感人的一首,也是整个诗词目前以爱情写进悼亡的典范。开篇“此恨何时已”,沉痛的一问,问自己,问苍天,背后的意思是在说:丧妻之痛从来不曾止歇,也永远不会止歇。
接下来描写忌当天的景:“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诗人写景,常常是借景抒情,写的既是实景,更是心情。“滴空阶、寒更雨歇”是说夜雨滴打在空荡荡的石阶上,雨渐停,声渐歇。“空阶滴雨”是一个诗人们相当爱用的意象,很为大家熟知的是宋代词人蒋捷虞美人中的“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名句的流传往往会使名句中特定的意象在后人的语言里也有了这一特定了的涵义,所以蒋捷之后的文人一看到空阶滴雨的意象,很自然的联想是年华老去、茕茕独立、漂泊无依和苍凉复杂的人生经历。容若这里多了一个“雨歇”的意象,使听雨所表达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多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渐渐熄灭、渐渐走入空旷与黑暗的感觉。
“葬花天气”也是虚实互现的写法。卢氏的忌是农历五月三十,正是落花时节。卢氏死时,不过二十一岁,一如盛开的花儿突然陨落。“葬花”这个意象别人也不是没有写过,比如彭孙遹“风雨年年葬落花”,但只有到了容若笔下,才有了黛玉的那种气质。红学研究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认为红楼梦取材自纳兰容若的家事,容若是贾宝玉的原型,证据也确实很多。我们大可以抛开那些繁琐的据问题不论,却也能够发现纳兰词与红楼梦的许多情节大有相合之处。读纳兰词会想到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会想到纳兰词,不必学索隐派去作什么牵强附会,神采上的暗合可以使人惊叹。
下句“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意思很常,无非是说妻子去世已经三年,自己对这个悲剧始终不能相信,但若说这只是一个悲伤的梦境,三年的时间也该醒来了。妻子一去,人间便再没有了快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意思虽然常,但正是这种直抒胸臆、不加雕琢的句子直接道出了众生共有的苦难,唯其实,故而感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某人的离去而伤心难过,所谓时间是很好的疗伤药,也意味着这种疗伤药从来不会马上见效。对于容若这种体质的人,时间这剂疗伤药必须用上很久才行。和卢氏的结合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如果去问容若:这三年的快乐是否值得用一生的伤心来换,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呢?既然人间无味,又该去哪里呢?
容若对后一个问题有过回答:“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无味的人间还不如冷清的坟墓,因为坟墓好歹有尘土与世间相隔,把所有的愁怨都埋在了地下。“夜台”是说坟墓,坟墓因为把死者长埋地下,不见光明,所以被称作夜台。“埋愁地”字面上很好理解,尤其联系起上下文,是说人间不如阴间好,因为坟墓虽然冷清清,却可以把愁绪埋葬。这样理解并没有错,但“埋愁地”实则是个典故,出自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生倜傥,不拘小节,是个有名的狂生,征召他做官,他却称病推辞,过着一般的生活,乃至以仙道自期。仲长统作过一首四言诗: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容若所谓“埋愁地”出自这首诗里的“寄愁天上,埋忧地下”,表达的是一种悠然的出世之志。人间已无可留恋,或者隐居为山民,或者游心于海左。容若用到这个典故,是词句蕴涵有两层意思,一是直接断章取义,说坟墓是埋愁之地,二是引起对仲长统诗句的联想,表达了一种在人间而离人间的生活态度。容若后来果然潜心佛典,无情正因为无法忘情。
上片的结尾,“钿钗约,竟抛弃”,呼应开篇的“此恨何时已”,长恨歌的意象便呼之欲出了。钿和钗都是女子的饰物,唐玄宗和杨贵妃以钿钗寄情,即是白居易笔下的“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只是物是人非,钿钗虽在,山盟海誓虽在,深情虽在,人却阴阳悬隔,再深沉的誓言便也幻作烟云字了。人力终究无法回天,这样的伤痛,无可奈何。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下片转折,重泉即九泉,双鱼即书信,这是设想幽冥之中能否互通音讯。通了音讯,也好知道妻子在那里是否孤单,可否有人陪伴、有人依靠。
这一句问得很是深情。有人以为这样的句子只有容若才能写出,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唐代诗人张说有一个组诗伤妓人董氏,四首如下:
(其一)董氏娇娆,多为窈窕名。人随秋月落,韵入捣衣声。
(其二)粉蕊粘妆簏,金花竭翠条。夜台无戏伴,魂影向谁娇。
(其三)旧亭阁,宿处白云关。春双飞去,秋风独不还。
(其四)舞席沾残粉,歌梁委旧尘。独伤窗里月,不见帐中人。
这个组诗是怀念一位姓董的歌伎的,如果把标准放宽一些,这也能算是一组悼亡诗。(悼亡诗所谓悼亡,对象有且只有于自家妻子。)多才多艺、温柔可人的董姑娘去世了,张说忧心她“夜台无戏伴,魂影向谁娇”,幽冥之地孑然一身,自然无人欣赏她那妖娆的魂影。此时此地,人间寥落,死者已矣,生者独自神伤。张说开篇的语句虽然略嫌轻浮,越写下去却越是深挚。但这一组诗并不出名,在现在的唐诗爱好者当中更少有人知。而这样的修辞,这样的表达方式,被容若用来,“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语言更实,艺术的力量却与张诗不可同而语。个中缘由,除了才情的差异之外,张诗写给歌伎,纳兰词怀念发妻,情绪的来路便是两样的。
怀念而无望,于是“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所谓湘弦,也是含有虚实两重意思。楚辞远游有“使湘灵鼓瑟兮,命海若舞冯夷”之句,此后诗词多以湘弦代指琴弦或弹琴。容若和卢氏的闺房之乐,音乐唱和便是其中的一项。如同张敞画眉一样,容若也天地为妻子调琴;而“湘弦重理”又暗示着当时有让容若续弦的提议,虽然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但这样的提议仍然让容若无法接受。词中之“忍”即是“不忍”,这在古文语法中一般被称为反训(这问题细讲起来还有些复杂,怕大家不爱看,还是略过好了)。
辗转相思,不忍续弦,还想和妻子再结来生缘,是谓“待结个、他生知己”。这句话虽常却不简单,不把妻子当作家中的女主人或贤内助看待,而是视她为知己。我们要知道,这对古人来说是个难能可贵的观念,浸在儒家礼教中的知识分子很难说出这样的话来。容若的词之所以成为一代高峰,不仅因为艺术上的成,也因为思想上的见地。这一点,又与红楼梦大有暗合,后者把本属于从属地位的女子抬高到与男子并列、甚至还高出男子一筹的程度,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纳兰容若和曹雪芹都不是思想家,对思想领域也都缺乏探索的热情,却不约而同地在这个领域里踏出了超前的一大步,原因只在一个情字——他们都是把情置于传统礼教与社会俗之上,也是说,把情作为了优选的判断标准,而俗只是一时一地的观念,情却是普世的、永恒的,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是普世的、永恒的。
至此,在一般人看来,容若对亡妻的感情到达“待结个、他生知己”这一步应该算是到达极限了,而对容若来说却不是这样。他心中存了这个期盼,虽然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盼,只是一个仅仅可以慰藉自己情绪的期盼,他却对此无比执着着、认真着,因为太执着、太认真,自然关心则乱,生出了种种“不必要”的担忧,这便是“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这两句化自晏几道的“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但深情大有过之。容若在此担忧的是,纵然自己和亡妻当真结了来生之缘,来生若再如今生一般,短暂的快乐之后便成永诀,脆弱的身心又怎能承受那凄凄凉凉的剩月零风呢!想到这里,思路一转,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说赢赢:虚诉讼案例指导 法律实务 王朝勇[等]主编](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dccfecba/1a6383987683e851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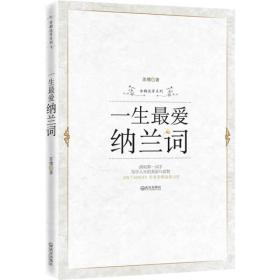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