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影响中文书写的100位文学大家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62.01 6.3折 ¥ 98 全新
库存35件
作者傅小平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9469793
出版时间2024-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98元
货号15351440
上书时间2024-06-2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傅小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评论部主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目录自 序/ 1
海外篇
辑 一
列夫·托尔斯泰:他竭力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寻求绝对的真理/ 4
安德烈·别雷:融合多种艺术技巧,使小说如复杂的交响乐/ 12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俄罗斯是他眷顾的心灵之乡,更是故事的源泉/ 18
伊利亚·爱伦堡:在任何时代,作家的重要使命都在于发现人的心灵/ 23
辑 二
若泽·萨拉马戈:重新学会“看见”,并让世界尽可能变得好些/ 30
塞尔玛·拉格洛夫:她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教科书”成了文学经典/ 40
克努特·汉姆生:文学选择了我,却让我如此纠结/ 43
约恩·福瑟:我探入未知,并带回了某种曾经未知的东西/ 48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应该相信碎片,因为碎片“创造”了星群/ 60
彼得·汉德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 68
安妮·埃尔诺:找到最合适的词和句子,让来自回忆的感受都被看见/ 77
吕西安·博达尔: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唯一方式/ 88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好吧,让我们来谈谈怎样构建自己的避难所/ 92
伊夫林·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系统/ 101
D.M.托马斯:以元小说叙述,揭示人生失落和孤寂的本质/ 106
哈尼夫·库雷西:看到我作品深处,才能看清反讽背后无言的悲伤/ 109
阿娜伊斯·宁:她用写延续性日记的形式来创作“小说”/ 113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我只是用小说来描绘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 116
马克斯·弗里施:我通过写作展示在写作之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121
伊塔诺·斯维沃:带着打开的“头颅”,写时代的复杂诗篇
/ 126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以写作一网打尽社会污浊底层的暗流/ 131
辑 三
约翰·厄普代克:赋予庸常生活以其应有之美/ 138
阿瑟·米勒:悲剧让观众对人类前景抱有最光明的看法/ 144
露易丝·格丽克:“诗人”命名的是渴望,而非一种职业/ 153
史景迁: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或多个人物的传记/ 160
彼得·海斯勒:通过对普通人的观察和描写,透视深远的中国背景/ 164
辑 四
肖洛姆·阿莱汉姆:他在伤心故事里,把悲剧描画成了喜剧/ 172
伊斯梅尔·卡达莱:在知道自由时,我对文学已经很熟悉了/ 178
约瑟夫·罗特:他从不写诗,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极富于诗意/ 186
卡勒德·胡赛尼:小说有一种将人们团结起来的特殊能力/ 195
辑 五
胡安·鲁尔福:写作是他与孤独对抗的唯一方式/ 200
托·萨瓦托:艺术可以挽救社会不发疯/ 209
辑 六
纳丁·戈迪默:写作时不要考虑后果,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218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新的眼光回望故乡/ 226
辑 七
三岛由纪夫:超越道德界限,展示纯美的存在/ 234
远藤周作:我写小说、讲故事,是为了传达神学思考/ 248
新井一二三:旅行在她笔下,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 259
渡海篇
辑 八
傅雷: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 266
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271
许渊冲:文学翻译,让一个国家的美成为全世界的美/ 279
草婴:我所做的只是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 288
钱春绮:多读多写是提高翻译水平的唯一途径/ 295
高莽:他把翻译当成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299
傅惟慈:生活好比一场牌戏,就看你怎么打好这手牌/ 303
李文俊: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还原出完美的原图/ 307
叶廷芳:文学翻译有着太多的艰辛和奥秘/ 311
周克希:在翻译里,追寻逝去的时光/ 315
蓝英年:只有永恒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 320
江枫:只要汉语不变,译诗自然流传/ 325
任溶溶: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 330
郭宏安:传达原作风格,才是最高境界/ 338
马振骋:生活是独一无二的“原著”,有阅历才能如哲人般思考/ 342
余中先:等待贝克特的路上,遇见萨冈的“忧愁”/ 346
袁筱一:翻译是全心的交付与投入,对原作,也是对自己/ 350
万之:高难度的翻译,是挑战,是诱惑,也是探险/ 353
辑 九
哈金:难就难在写作“成功”之后仍能不断地写下去/ 358
张翎:理性的审美距离,让我完成“文学救赎”/ 365
陈河:能远离喧嚣,只按自己的冲动写作,感觉真好!/ 370
张北海:“侠”是个快意恩仇的美梦/ 374
黎紫书:我不愿意让读者看出我在书写过程中的挣扎/ 380
张彤禾:只有从个人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的真实面貌/ 391
张惠雯:原地起飞,呈现丰富宽阔的生活/ 398
海内篇
辑 十
汪曾祺:我必须用笔写,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406
黄永玉:世界因为有了我,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 421
王蒙:他不曾告别的“青春”写作,始终有着温暖的色调/ 429
冯骥才:当下知识分子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觉/ 437
张贤亮:自言“最有争议的作家”,不落俗套,也不曾落伍/ 450
陈忠实: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454
辑 十 一
莫言:作家即使写的别处,实际上也是在写故乡/ 462
贾平凹:所谓现代意识,也是从真实的生活中长出来的/ 471
王安忆:写作就是给那些无可命名的事物一个准确的表现/ 479
阿来:文学写作理当对语言有追求,对现实世界有超越/ 484
余华:不要想着超越自己,需要做的是不重复自己/ 494
张炜:唯有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深处/ 511
韩少功:思想能力怎么会是个贬义词?/ 517
迟子建:写下文字,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523
毕飞宇:任何时候,离开世态人情,小说必死无疑/ 531
辑 十 二
马原:不是“小说已死”,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死了/ 536
王朔:我从来不认为这世上存在高级知识分子/ 545
刘震云:文学界的阿基米德?这也不在话下/ 555
刘庆邦:的技巧是真诚/ 562
欧阳江河:写作不仅仅是修辞,还要包含更深的呈现,更深的聆听/ 572
雪漠:“我”只是一个出口,流出了比现实更巨大的世界/ 579
辑 十 三
徐则臣:在海拔以下写作,眼光就没法高过地平线/ 584
李修文:我写散文的本意,是想促使自己更加贴近周边人事/ 591
冯唐:我所求不过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自在境界/ 596
赵本夫:写作有时就像在一片大雾里行走,走到哪算哪/ 599
阎真:“与真实零距离”中,追问人的生存困境/ 606
辑 十 四
吴兴华:游荡在中西文学之间,指示给他人奇异的梦/ 612
陈平原:文学教育切忌太功利,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619
戴锦华:向下看,向下流,向下走,我会比较踏实/ 628
余秋雨:要建立起对文化的信念/ 639
夏坚勇:坚守,行走,抒写“湮没的辉煌”/ 650
王尧: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感性与知性的融合/ 663
徐风:他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的源头和流向/ 676
辑 十 五
曹文轩:我宁要“浅显”的审美,也不要做作的“深刻”/ 690
赵丽宏:我还可以非常真实地,用少年的眼光观察世界/ 695
黄蓓佳:以孩子的视角,表达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 701
毛尖:你说,他说,看看“我”会怎么说/ 705
周云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带我去远方流浪/ 711
内容摘要余华
不要想着超越自己,需要做的是不重复自己
1
1993年底,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活着》,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不到12万字的小长篇,会被看成是他创作水准的标杆,以致他于2021年初出版《文城》,不少读者也是惊呼,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
言下之意,这次“回来”的不是写《兄弟》和《第七天》的那个余华。《文城》也确实如家潘凯雄所说,与余华早年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风格上更具一致性,但这样的类比或许还因为两者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刚读到这部小说节选文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问题:余华为何写这样一部小说?说来这不算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作家会无缘无故写一部长篇小说,像余华这样暌违八年才捧出一部,就更得找到非写不可的理由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晃而过了。等到要写推荐语,到豆瓣上看了看,却看到有网友也有类似的疑惑:第二个十年结束了,中国城镇化突破50%都已经过去十年了,再去写民国时期的村镇和乡贤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回来了。
像余华这样的作家,似乎更应该把有限的笔力用在写当代上,或者说他更正确的路是在《兄弟》《第七天》没完结处继续往前,而不是像这本新作从《活着》故事开始的时候回退。退一步说,即便他要写民国时期的故事,也得如《白鹿原》一般从十九世纪末写起,一直延伸到当代,那样漫长的叙述,才会给人以史诗般的震撼。
无奈余华并没有出来做任何说明,《文城》也是简洁到除正文外,不见前言、后记,扉页上也不见引语,我也就只能推想,我就想到他曾在《兄弟》后记里写,在到来前,他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我当时并不确定这部小说是《文城》,只是觉得有了这部,单从小说序列看,他已经完成,或接近于完成了自己的叙述抱负。好在这个推想,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余华和他的《文城》”新书分享会上,余华谈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他确实是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他们这一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所以在1998年或者1999年,眼看着20世纪快要过去了,他就想着从《活着》故事开始的年代往回写,因为《活着》是从1940年始,结果他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了下来。他在《兄弟》出版以后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疫情期间,他才把这部小说最后写完,所以确实是写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余华为何前前后后写了21年,其中原因在于他自己说的,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没能把握人物最终的走向,他对他们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要理解这个说法,我们就得看看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余华简言之写了两段旅程,小说主体部分主要写了林祥福南下寻找纪小美的旅程,后半部《文城:补》写了沈阿强携纪小美北上逃亡或冒险的旅程。
话说——,我们用“话说”这两个字切入来转述小说故事是合适的。第一节写主人公林祥福背着个大包袱经过溪镇,碰到镇上人就问:“这里是文城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又走出了溪镇。说白了这是个引子,是引我们进入故事情境的。从第二节开始,小说才算是步入了正题,而余华在某种意义上用的就是说书人的口吻,只是这个说书人实在是无比有耐心,从来不耍“说时迟那时快”的把戏。也就是说,余华叙述的速度,和小说故事发生的速度,是完全相匹配,甚至是前者还要略慢于后者的,但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慢,这实在很考验叙事功力。
有网友称,林祥福是那个时代朴素的理想主义者。照我看,林祥福确实是够朴素的,也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出生在北方一户富裕人家。但正因为他朴素,有理想,到了二十四岁都还没能成亲。话说那一年那一天的黄昏时刻,他听到宅院外有一对年轻——也就是读后我们知道的,自称来自文城的阿强和小美,用他从来没听过的,“仿佛每个字都在飞”的语速说话。他打开门把他们迎了进来,同时也是把小说真正要讲的故事迎了进来。说来也是投缘,林祥福因为刚死了母亲,渴望和人交谈,而小美在留宿一宿后又偏偏病倒了,如此谎称急于赶去京城的阿强,只能留下她独自“北上”。于是我们看到林祥福在照顾小美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她,两人在一个冰雹之夜发生了关系。但没过多久,小美拿着林祥福家从祖上开始积攒下来的七根大金条和一根小金条离开,这使得林祥福伤心欲绝,只是时间一长就慢慢平复了,但小美后来居然又回来了,她回来是因为她怀了林祥福的孩子,也因为她知道林祥福为人朴素,会善待她。问题是小美生下孩子后又走了。林祥福就此开启了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南下寻找纪小美的漫漫长路。
2
老实说转述故事是没什么意思的,越是好的小说越是不适合转述。毕竟一经转述,小说就被缩略成了故事。有网友说,《文城》前半部的前面部分,讲的是“一个媒婆引发的惨案”,虽有戏谑成分,却不无道理。林祥福在相亲过程中看上一个叫刘凤美的千金小姐,偏偏见面时这个姑娘一声不吭,让媒婆误以为是个哑巴,使得林祥福按惯例留下一块彩缎就走了,一段本来可能有的美好姻缘,由此烟消云散。等到很多年后,已经长大的女儿林百家问他她妈妈是谁时,他没法说小美,就假托那个已经故去的刘凤美是她妈妈。反正按这个逻辑推理,要不是因为那个媒婆搅和,林祥福娶了刘凤美,就用不着他这么凄惨地南下寻找了。
讲到这里,即使不知道小说后面写了什么,读者也能猜到,林祥福多半是找不到小美的,他根据那么一点线索,能找到才怪呢。实际上,余华是想过让林祥福到南方,也就是到溪镇后就找到小美的,但这样写的话,那个时代就没法展开,所以他就放弃了。也正是因为要写那个时代,他干脆让林祥福融入溪镇,亦即进入到那个时代里生活。他这么处理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即使林祥福还在北方,他也可能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时代已经乱了,“那是一个乱世,乱世不止是在溪镇乱,在北方也一样乱。所以田家四个兄弟拉着死去的大哥和林祥福回家的路上还在说钱庄的老爷也被绑票了,所以那时候全中国都是这样的”。
不过,小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余华虽然没让林祥福找到小美,但实际上已经无限接近于找到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不管怎样,能不能找到纪小美,对于林祥福生死攸关,对于我们来说,却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看的是他寻找的过程,这个过程套用余华一篇随笔的题目,即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两个人直到纪小美长眠十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交集”,更是让这个旅程百感交集。
而这个旅程实在是不好转述的。我只能说,余华写得饶有意思,很是精彩。尤其是他写林祥福一次次背着孩子敲开一家家门讨奶水喝的过程,是能让人读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史诗感的。而写他初次抵达溪镇时在万亩荡遭遇的那场离奇的龙卷风,和他回到溪镇后经历的那场长达十五天的大雪,要我看也是直追施耐庵在《水浒传》里写林冲夜奔的神韵和劲道了。余华写这个过程的篇幅,也大抵是施耐庵写林冲夜奔前前后后的那些篇幅。那接下来林祥福怎么样?他在当地商会会长顾益民的关照下,在溪镇这个有缘之地住下来了,并且和同样是外来户的陈永良合作成立了木器社,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以至于把万亩荡都买了下来。
再后来就如网友说的那样,发生了一场“一群引发的惨案”。余华写这个“惨案”真是写得巨细无遗、惨烈无比,在篇幅上大约都超过了林祥福寻找的过程,而且在这部分里,与其说余华主要写的林祥福,倒不如说写了那个荒蛮年代里溪镇人的群像。我看到有说,《文城》是一部更加丰富立体的群像小说,放在这部分——亦即小说前半部的后半部分里讲是成立的。而余华这么写,往好处讲是突破,是对围绕一个主要人物或家庭展开的叙事模式的突破,往不好处讲就是离题,而且离题离得那么远,是会落入凑戏份或不善于驾驭长篇的口实的。
但我想余华这么写,应该有他的道理。从写历史的角度,如果单看林祥福寻找的前半部分,除龙卷风和雪灾以外,甚至让人觉出祥和、温暖,也只是后半部分写到的匪乱才写出了真正的荒蛮、残酷,或者说正因为前半部分的祥和,更让我们觉得后半部分荒蛮的无以复加。再则,这部小说虽然我们能辨认出余华写的是清末民初,但我们很难找到具体的历史时间,也就这段匪乱最是能让我们明显联想到军阀混战的背景了。但余华应该无意于写历史,他是把历史当布景,写那个极端年代里人的生存经验。而他把历史背景写得扎实,说到底是为了把人写得真切。事实上,就文学而言,真正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往往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那种不为时间、地域拘囿的,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经验,这里面包含了文学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腰封上引了余华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显然是有所指的。
3
说回到小说写匪乱的部分,家杨庆祥在他的《余华〈文城〉: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一文里,可谓做了精到的分析。他谈及的“信”,与“信”相关的是“义”,也正是在小说这部分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如杨庆祥所说,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有情有义的最后得到了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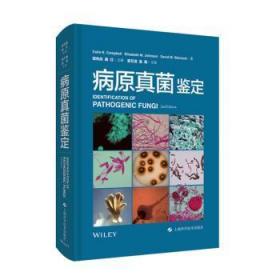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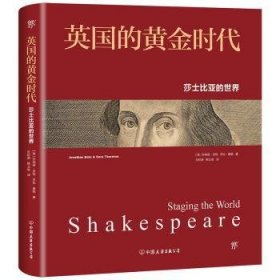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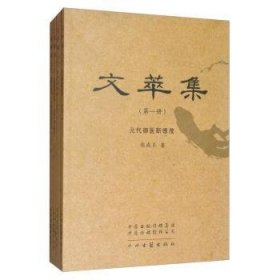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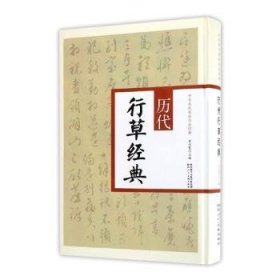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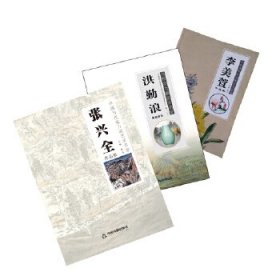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