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爱民国:民国文人的婚恋微纪录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18.98 6.3折 ¥ 30 全新
库存5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陆阳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ISBN9787512615670
出版时间2013-1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0元
货号8177096
上书时间2024-06-20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民国是一个中西交流、风云激荡的时期,更是一个思想开放、自由浪漫的时代,梁启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这些文人在民国舞台上次弟登场,他们不仅用强悍的精神引领时代,还有缱绻的柔情蜜意。
情感的缩命,人生的无奈,精神的求索交织而出的民国婚恋,或典雅从容,或惊世骇俗,或坦然率真。
《情爱民国(民国文人的婚恋微纪录)》由陆阳著,辑录了150位民国文人的爱情、婚姻轶事,既有写意式的记述,又有工笔式的描绘,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通过婚恋这一课题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它是札记,是文论,是历史的碎片,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饱览民国悲欢爱,缱绻世间不了情。
作者简介
陆阳 1970年生人,江苏省作协会员。生性慵散,年轻时好胜,然随着年岁增长,对世事之争纷,渐觉了无意趣,唯对读书、写书尚有几分痴迷。著有《中国企业的成功与失败》、《穷人也可以富》、《苏南的变革与发展》、《长三角批判》、《品城:对中国城市的批判》、《无锡国专》。
目录
第一章 从“上一站”走来的人
民国的上一站,是晚清。
从晚清走过来的文人,不得不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无论守旧,还是革新,无论伟大,还是尴尬,他们的婚姻无一不流淌着千年的制度之血,没有自由,缺少浪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之基;妻妾成群、儿女双全,是婚姻之相;人伦纲常、大义存焉,是婚姻之本。
如今,婚姻选择的空气自由、民主,但婚姻竟又变得如此脆弱,难经一场风雨。
似乎,婚姻的幸福,无关乎制度。
第二章 “双轨”的爱情
民国初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时代:旧思想与新文化,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小脚女人与新派女性……新旧交替,相互激荡。色彩缤纷的背后孕育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蜕变。
那个时代,“旧式婚姻”仍在,但自由恋爱之风已经浸漫开去。旧婚姻和新情感中的夹缝人,面临着多么尴尬的人生选择。从这些文人不同的选择方式,就看出他们不同的“主义”。有的“双轨制”,如鲁迅;有的偶尔从旧婚姻中“开小差”,如胡适;有的坚守旧式婚姻,如俞平伯……
与那个时代一样,这些文人的身上同样充满了矛盾:高贵而平凡,脱俗而市井,风流而坚守,孤傲而谦卑。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三章 那些“鸳鸯”那些“蝶”
民国有一群文人,曾经风采一时,如今却已经被人淡忘。
他们或开书局,或办报馆,舞文弄墨,吟诗填词,以卖文为生。
在他们的笔下,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他们的小说,广受普通民众的欢迎,又饱受新文学界的批评。
如同他们笔下的故事,他们的婚姻情爱同样千回百折,爱恨情仇,演绎出一幕幕温婉悱恻、缠绵动人的悲喜剧,让人唏嘘不已。他们的情、爱、欲,正是最普通人性的典范样本。
他们的流派,叫“鸳鸯蝴蝶派”。
第四章 婚姻的大学
婚姻是一所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有着许多的课程:责任、感恩、包容、互助……而且,这些都是必修课。
在这所大学里,只有日复一日地学习,爱情才能进步,婚姻才能美满。
从婚姻这所大学毕业,需要一分天资,两分勤奋,七分智慧。
然而,总有人学不精,学不透,于是,婚姻成了沉重的负担、窒息的枷锁、爱情的坟墓。
十全十美的婚姻,并不存在,当然,理想的婚姻大学也不完全是乌托邦。
于是,民国大学里的爱情、婚姻,更值得去探究、体味和思索。
第五章 革命的爱情
民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充满着青春的朝气。
革命,以反抗现有秩序为目的,于是,当爱情与革命碰撞时,爱情就更显浪漫。
青春,以满腔热血沸腾为特性,于是,当爱情与青春相遇时,爱情就更为躁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这样一帮青年,活跃在革命的前沿,青春、激情、理想,再加上流浪和窘困,“力比多”(性力)借助爱情释放开去。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要么沉在海水里,要么燃在火焰里。
于是,他们的情爱显得那么精彩多元,又那么惊世骇俗。
第六章 才女的花样人生
她们,或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或卓尔不凡,秀外慧中;或美艳优雅,仪态万千。
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掩然百媚,如一树静美的桃花绚丽开放。
身为女子,她们渴望爱情的滋润,正如苏青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身为女子,她们经受婚姻的冷暖,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红颜如花,开时极尽妖娆芳华,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花样人生,无怨,无悔。
读民国女人,总能品味一种淡淡的哀愁,饮尽凉薄的爱之味。
第七章 诗人之爱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这是诗人徐志摩倾尽全部生命喊出的“爱情宣言”。
诗人风流,风流便不免多情。
诗人,极尽优美的言语和句子,歌颂爱情,赞美爱情。
诗人,用尽一生追求梦幻爱情,纯碎、青春,还带有几丝哀伤。
因为诗歌,爱情绚丽多彩。因为爱情,诗歌从来黯然。
斯人不在,谁来歌颂爱情?
第八章 当爱情遇上婚姻
爱情是行而上的、精神的,而家庭是形而下的、物质的。
相爱的人走进了婚姻,组成了家庭,爱情的神秘光环褪色不少。当不再包容,少了责任,再甜美的爱情,也会生出一摊尴尬的琐碎和避之不及的隐晦。
人在情海,身不由己,爱仇难却,恩怨无尽。
幸福的婚恋是相似的,不幸的婚恋各有各的不幸。
或许,爱情的世界,没有是非;又或许,婚姻的鞋子,冷暖自知。
此时,爱,或被爱,都成了伤害。
其实,在爱情里,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只为喜欢的人付出,让他(她)幸福,而不索取呢?所有的苦痛,都因为索取而生。
爱情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对方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第九章 爱上最好年龄的人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
民国有这样一批文人,也许沉浸研究,也许埋头著述,但他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始终为一个“最好年龄的人”保留。
侠骨柔情的男人是最男人的男人,为爱而生的女人是最女人的女人。
这样的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才会抛开乱世的纷扰,纵心随性,风轻云淡。他们点燃的爱情之火,比烟花还要绚烂。
爱是人性的美的力量,爱是爱你年少时的桃之夭夭,更爱你年老时的白发苍苍。
最美的爱情在民国。
而如今,物欲横流,爱情已成奢侈品,试问:世上还剩多少真心人?
内容摘要
民国初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时代:旧思想与新文化,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小脚女人与新派女性……新旧交替,相互激荡。色彩缤纷的背后孕育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蜕变。
那个时代,“旧式婚姻”仍在,但自由恋爱之风已经浸漫开去。旧婚姻和新情感中的夹缝人,面临着多么尴尬的人生选择。从这些文人不同的选择方式,就看出他们不同的“主义”。有的“双轨制”,如鲁迅;有的偶尔从旧婚姻中“开小差”,如胡适;有的坚守旧式婚姻,如俞平伯……
与那个时代一样,这些文人的身上同样充满了矛盾:高贵而平凡,脱俗而市井,风流而坚守,孤傲而谦卑。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胡适的好人缘以及人格魅力在民国时期是尽人皆知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那个年代许多精英人物借以提高身价的时尚用语。但少年时的胡适,生活一度放浪颓废,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据现存59天的胡适《藏晖室日记》统计:1910年二三月间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遇巡捕盘问,胡博士乘着酒劲,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后被罚款5元。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跻身社会名流,但仍未摈弃喜好风月的旧习,外出济南或武昌时也不忘到妓院“看看”。就是这位胡适,1914年6月还发出了禁嫖的言论:“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舆论,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在13岁时就由寡母作主订了婚。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去毗邻的旌德县旺川村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不知怎的就把胡适看上了,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长胡适一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硬生生地把胡母说动了心。按照当地的习俗,胡母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冬秀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胡母还不放心,又将几个女孩子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隔了好几天,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个“八字”,打开一看,仍是江冬秀,真乃“天赐良缘”。当时只有13岁的胡适,与14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便由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掐算、灶神老爷的“赐缘”而确定了。
●婚虽订了,但胡适与江冬秀没有见上面。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继而留学美国,一直到13年后结婚的时候才与未婚妻第一次谋面。那一年夏,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探望老母,商订于本年寒假结婚。他很想先与江冬秀见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28岁的老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13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
●1917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举行文明结婚。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结婚之日是阳历卅日,阴历十一月十七),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他身旁一个绰号叫“疯子”的本家哥哥,虽无功名,却有捷才。他脱口而出:“廿七岁老新郎”,巧妙而风趣地对了那幅上联。胡适认为很好,照着写了。在结婚仪式上,他们破除了旧式礼节,只是新郎新娘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致谢,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都是以鞠躬代替叩头。婚礼上,江冬秀的4位伴娘中,有一位正是胡适的三嫂的胞妹,名叫曹诚英,因此胡适与曹诚英是姻亲表兄妹。岂料,这一会面,今后竟生发出一场胡适一生最销魂的“烟霞之恋”。
●胡适与江冬秀虽然相伴一生、风雨兼程,但心灵上却从来没有真正契合过。胡适不到30岁就名满天下,在学术、教育和政治活动中都取得了赫赫的成就,而江冬秀却是一个缠过脚、识字不多的乡村女子,两人在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或者相近之处。1916年 1月,远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胡适为此曾写了一首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这首诗几乎代表了胡适终生对江冬秀的感情,只是“欢喜”而已。婚后的江冬秀沉迷于麻将,将家中的客厅变成麻将战场,在“三缺一”的情况下,还多次将在书房中写作的胡适拖出来凑数。
●1923年4月,胡适到了杭州,见到了在此求学的表妹曹诚英,曹诚英刚刚离婚。2个月后胡适再次来到杭州。这一次,胡适和侄儿思聪租了烟霞洞和尚庙的三个房间,疗养他的痔瘘顽疾。曹诚英正值放假,赶来帮他叔侄俩料理生活。远在北京的江冬秀也来信,表示感谢:“珮声照应你们,我狠(很)放心,不过他的身体不狠(很)好,长(常)到炉子上去做菜,天气大(太)热了,怕他身子受不了……”胡适住最东头一间,曹诚英住中间一间,只好贴隔壁。此壁开了一扇门,因为胡适住的东间朝走廊无门,于是 表哥就从此门经过表妹房间出入走廊。3个月间,两人过起了神仙般的眷属生活。好友对这对“洞府神仙”的甜蜜,更是心知肚明。9月28日,一众好友到海宁观钱塘江大潮,那张著名的“到此一游”合影里,有胡适、徐志摩、曹诚英、陶行知、汪精卫等。
●回京之后,胡适原想与江冬秀解除婚约,和心上人从此共结连理。谁知江冬秀一听此言,她不号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一手搂住只有二岁的小儿子思杜(1921年生),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1918年生),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谁想到,这位柔弱的不识字的小脚女子,在那一刻彻底爆发,其刚烈不屈震住了大名鼎鼎的胡博士。
●已经怀有身孕的曹诚英,就这样得了婚外情人原本该有的命运。她只能拉住他的心,却永远得不到他的人。后来,曹诚英打掉了胎儿,选择了留学,几年后,她回国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1973年初,曹诚英去世,她把自己的坟墓选择在去胡适故乡上庄的路边,她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胡适在回老家的时候能够彼此相望。临终前,她曾经委托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的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
●当时,大城市里追求婚姻自主已渐成风气,身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胡适依然携着个小脚太太到处跑,不少青年人都感到奇怪,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据说,反对者如陈独秀曾竭力规劝胡适离婚,甚至拍着桌子指责他太窝囊,但胡适依然不为所动。还有,高梦旦则对他为婚姻作出的牺牲表示敬重佩服,他却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 “我对于我的旧婚约,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
●胡适是个热心人,喜欢成人之美,乐于当“媒婆”。他先后为四对名人做媒与证婚,他们分别是赵元任和杨步伟、千家驹与杨梨音、沈从文与张兆和、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四对“鸳鸯”的名气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可见胡适的“媒婆”层次之高。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点“鸳鸯谱”,让胡适尴尬不已:“情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据传最初是胡适与陆小曼交往,因其无法跟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极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
●在同时代的文人中,胡适很有“惧内”的名声。江冬秀发脾气时也不避外人。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及此事,想起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和忍受,身边种种的流言蜚语,越想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还有,江冬秀对当时学界流行的“弃旧妇,娶新人”孟浪习气颇为看不惯。蒋梦麟与好友遗孀陶曾谷结婚,请胡适作证婚人,江冬秀因为蒋梦麟遗弃原配,不准胡适前去,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北大教授梁实秋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梁妻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最后闹到法医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实秋败诉,一时间传闻沸沸扬扬。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向胡适 “河东狮吼”,唬得大博士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胡适是乐意接受太太管束的,正如他所言“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胡适手指上有枚“止酉”戒,那是在他40岁生日时,江冬秀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搬到米粮库四号新宅,设宴招待同人、朋友,大家正觥筹交错,不料江冬秀给他戴上了“止酉”的戒指,不免煞了风景。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1931年春,胡适赴青岛,青岛大学“酒中八仙”(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纯、方令儒、闻一多、梁实秋)邀他斗酒,他扬起戴着“止酉”戒指的右手,要求免战,并说“得意尚呈金戒指,自羞感谢吾夫人”。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和证据。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朋友,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在台湾时,他与人谈笑时讲到现代男人的“三从四德”,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1961年5月,台湾报刊上发表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指出:“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他还说,所谓“胡闹”是指有些引证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至于“伪装惧内”,他还是默认了。
●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很清楚:“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一位福星。”胡适1938年就任中国驻美大使,江冬秀在信里提醒他:“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参加国民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如此明智的观点,真比胡适还要高超。
……
主编推荐
民国是一个中西交流、风云激荡的朝代,更是一个思想开放、自由浪漫的时代。梁启超、鲁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这些文人在民国舞台上次弟登场,他们不仅用强悍的精神引领时代,还有缱绻的柔情蜜意。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遗风尚在,但“自由恋爱”的琼浆玉液,已经充满蛊惑地摆在眼前。旧婚姻与新情感中的“夹缝人”,面临着多么尴尬的人生抉择,或是接受自小的定亲,平静而又平淡地度过一生,或是选择为爱而不婚不娶,孑然一身,或是一如飞蛾,积蓄一生的力量扑向爱情的火焰,很后落个身心俱疲、苦乐参半……
或许,正因为有了如此的矛盾,又有了那些才子佳人们的动情演绎,民国的情爱才会显得这般典雅从容,或者这般惊世骇俗,始终充满坦然率真之气。
精彩内容
本书辑录了近150位民国文人的爱情、婚姻轶事,既有“写意”式的记述,又有“工笔式”的描绘,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通过婚恋这一课题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它是札记,是文论,是历史的碎片,是一个时代的吉光片羽……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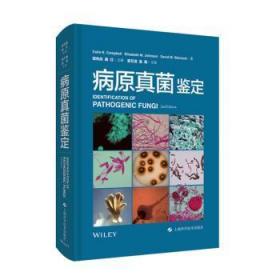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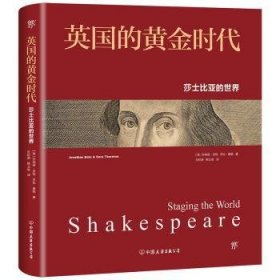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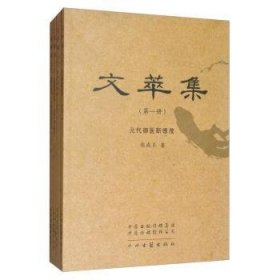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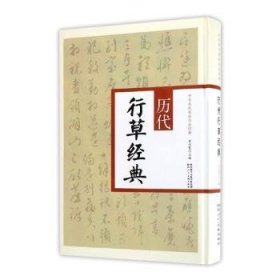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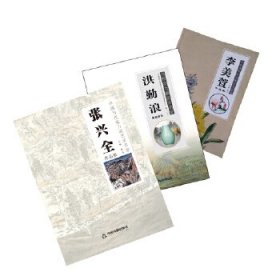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