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尔沁旗草原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56.17 6.6折 ¥ 85 全新
库存40件
作者端木蕻良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87521224634
出版时间2023-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5元
货号14226749
上书时间2024-05-2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端木蕻良(1912—2012),原名曹京平,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红学家。21岁完成长篇小说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一生笔耕不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新都花絮》《曹雪芹》,中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早春》,散文集《火鸟之羽》《友情的丝》,红学文论集《说不完的红楼梦》《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病逝后出版有8卷本的《端木蕻良文集》和4卷本的读书笔记《日知日录》等。
目录
一 一个古远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开始的……
二 四太爷、大爷、三爷
——丁府财源无限的膨胀期
三 另外一只魔手
四 这是真正的故事的起头,
万里的草原上一只孤寂的影
五 一个清晨
六 小爷的哀伤
——和他的堇色的罗曼斯
七 三奶家——
科尔沁旗大财主腐败的阴影
八 猪的喜剧
九 水水
十 !
十一 钱
……
内容摘要
这是每个鴜鹭湖畔的子孙们,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这是记忆里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最惨痛的记忆。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这长蛇的征旅,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猥琐的,狼狈的,在那灼人的毒风里,把脚底板艰难地放在那焦砂的干道上,企望着,震恐着,向那“颟肘子”的国度进行。那曾经禁闭过的王国。大队里,一切都是破旧的、颓败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单调的。忽然,一道银光一闪,似乎是白马尾的蝇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亮,但随即就有一个丑恶的人影,遮没了这白色的一道。就像一尾褪了鳞的鲮鱼似的,吃力而迅速地向前顶着水游移。一个被饥饿损害了的老丑妇,把三升炒米放在水罐里,外边用一条油干的猪水泡包了,放在臃肿的背上。两只带红丝的眼睛,偷偷地向左右不住地贼视,似乎是她曾偷了谁的东西,又好像怕谁去偷了她自己的东西,非常地不安,一会儿用手小心翼翼地揩了揩鼻尖头上渗出来的黏汁,一会儿又疑心地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后的水罐。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妇,把已经被长久的饥饿折磨了的小小的乳头,塞满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嘴,睁开了惺忪的眼睑,困顿无告地向四边一望,正碰见那灰色的可怜的人影。老丑妇像是被她窥见了秘密似的,连忙就向焦老爹的驴车那边去躲。一转眼,便鬼魅似的不见了。她看见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实的水罐,把一种同情的怜悯和自己身世的哀愁混合在一起,哀婉地也矜持地楚楚一笑,便低下了头,眼睛里闪耀出失望的光。火炙的风,从四面里吹过来,她困顿地一动也不动地在痛苦地冥想。那是两个月以前,一道吃人的黄流,带着不可抵抗的威力,忽地从不知是什么地方冲出来。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惨烈地号叫,绿铅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向人们直灌。茅屋冲走了,三个月的小驴驹冲走了,大贞的针钱包也不见了。一切的东西,都变了次序,变了颜色。水,水在这儿统治了两个月,一点没有打回头的意思。天气转到三伏,水面的蚊虻蒸腾起来了。蝇子轰轰的,大的像盖盖虫,啪的一下,用什么东西一打,里面便钻出三四条小白虫来,打转盘地蠕蠕地动。水里的蛆虫,都是浓灰色的,长的有半寸长,拖着比自己的身子还长的半截尾巴,在水面上钻聚。水面上,不知是什么东西酿成羊脂油的结晶块,花红脑子似的到处漂着。自己的丈夫,便在一个清早里,被大水裹去了,许多少妇的丈夫,也被大水裹去了,不见了。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想自己的丈夫,也许没死,将来跑关东,也许能碰见他,那时候,他们……她昏乱地想着,她昏乱地想着,她好像突然从半天空里降下来,落到一片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野里,她和她的丈夫,勤劳着,经营着,谷堆像小山似的长起来,他们都愉快地用着红花碗吃饭……忽地,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奶汁太稀薄了,稀薄得直到没有一点奶汁,她无力地揩了一揩额头上的虚汗,把目光无神地向一片火烧云呆望着,寄托在半天空一片火烧云的辽远里……那火热的云海,也正像她所想忘记而不能忘记的那道吃人的洪水,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只纤弱的指头,插在蓬松的鬓发里。那好像就是昨天,也好像就是方才,水面上,远远摇来两只画着红卍字的粥船。刚一摇到,人们都一窝蜂抢上去了。都想第一个把嘴伸到缸里去,人们都想第一个来攫取这一点可以维持生命的渣沥呀,于是便拼命抢了,抢,抢……缸抢翻了,人,趴在甲板上舐,舐着抢,上船的人更多了,两只船,一起沉,从此不见了放赈的船……就这样,他们转过了一重山,又转过了一道水,从早晨到夜晚在炎阳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运赶去……每个人都带着那不可描画的愁惨,每个人都刻着一脸的悲苦,在饥馑里,在瘟疫里,在高山的峻险里,在河水的迂回里,爬向那关外的荒原去。这样,他们便给赶出去了,从人类的世界给摈弃了。他们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命运去稳定他们自己生命的彷徨了。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走,悄悄地向命运的那一端走。石子弄痛了脚背,瘟疫夺去了最亲爱的亲人,于是万千的脚步都无端地疲惫了。把头凄迷地向后扭转,那门前可纪念的杨柳不见了,那长满了青苔的柳罐,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里汲水了……长天里,只是一片红云,在半空里下火,越走越是焦热。啊,你回过头来瞧,那走过来的故乡的方向啊……那苍白色的女人把头低到不可再低……她已是寸步难行了。
主编推荐
暂无
精彩内容
这是每个鴜鹭湖畔的子孙们,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这是记忆里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最惨痛的记忆。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这长蛇的征旅,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猥琐的,狼狈的,在那灼人的毒风里,把脚底板艰难地放在那焦砂的干道上,企望着,震恐着,向那“颟肘子”的国度进行。那曾经禁闭过的王国。大队里,一切都是破旧的、颓败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单调的。忽然,一道银光一闪,似乎是白马尾的蝇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亮,但随即就有一个丑恶的人影,遮没了这白色的一道。就像一尾褪了鳞的鲮鱼似的,吃力而迅速地向前顶着水游移。一个被饥饿损害了的老丑妇,把三升炒米放在水罐里,外边用一条油干的猪水泡包了,放在臃肿的背上。两只带红丝的眼睛,偷偷地向左右不住地贼视,似乎是她曾偷了谁的东西,又好像怕谁去偷了她自己的东西,非常地不安,一会儿用手小心翼翼地揩了揩鼻尖头上渗出来的黏汁,一会儿又疑心地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后的水罐。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妇,把已经被长久的饥饿折磨了的小小的乳头,塞满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嘴,睁开了惺忪的眼睑,困顿无告地向四边一望,正碰见那灰色的可怜的人影。老丑妇像是被她窥见了秘密似的,连忙就向焦老爹的驴车那边去躲。一转眼,便鬼魅似的不见了。她看见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实的水罐,把一种同情的怜悯和自己身世的哀愁混合在一起,哀婉地也矜持地楚楚一笑,便低下了头,眼睛里闪耀出失望的光。火炙的风,从四面里吹过来,她困顿地一动也不动地在痛苦地冥想。那是两个月以前,一道吃人的黄流,带着不可抵抗的威力,忽地从不知是什么地方冲出来。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惨烈地号叫,绿铅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向人们直灌。茅屋冲走了,三个月的小驴驹冲走了,大贞的针钱包也不见了。一切的东西,都变了次序,变了颜色。水,水在这儿统治了两个月,一点没有打回头的意思。天气转到三伏,水面的蚊虻蒸腾起来了。蝇子轰轰的,大的像盖盖虫,啪的一下,用什么东西一打,里面便钻出三四条小白虫来,打转盘地蠕蠕地动。水里的蛆虫,都是浓灰色的,长的有半寸长,拖着比自己的身子还长的半截尾巴,在水面上钻聚。水面上,不知是什么东西酿成羊脂油的结晶块,花红脑子似的到处漂着。自己的丈夫,便在一个清早里,被大水裹去了,许多少妇的丈夫,也被大水裹去了,不见了。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想自己的丈夫,也许没死,将来跑关东,也许能碰见他,那时候,他们……她昏乱地想着,她昏乱地想着,她好像突然从半天空里降下来,落到一片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野里,她和她的丈夫,勤劳着,经营着,谷堆像小山似的长起来,他们都愉快地用着红花碗吃饭……忽地,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奶汁太稀薄了,稀薄得直到没有一点奶汁,她无力地揩了一揩额头上的虚汗,把目光无神地向一片火烧云呆望着,寄托在半天空一片火烧云的辽远里……那火热的云海,也正像她所想忘记而不能忘记的那道吃人的洪水,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只纤弱的指头,插在蓬松的鬓发里。那好像就是昨天,也好像就是方才,水面上,远远摇来两只画着红卍字的粥船。刚一摇到,人们都一窝蜂抢上去了。都想第一个把嘴伸到缸里去,人们都想第一个来攫取这一点可以维持生命的渣沥呀,于是便拼命抢了,抢,抢……缸抢翻了,人,趴在甲板上舐,舐着抢,上船的人更多了,两只船,一起沉,从此不见了放赈的船……就这样,他们转过了一重山,又转过了一道水,从早晨到夜晚在炎阳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运赶去……每个人都带着那不可描画的愁惨,每个人都刻着一脸的悲苦,在饥馑里,在瘟疫里,在高山的峻险里,在河水的迂回里,爬向那关外的荒原去。这样,他们便给赶出去了,从人类的世界给摈弃了。他们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命运去稳定他们自己生命的彷徨了。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走,悄悄地向命运的那一端走。石子弄痛了脚背,瘟疫夺去了最亲爱的亲人,于是万千的脚步都无端地疲惫了。把头凄迷地向后扭转,那门前可纪念的杨柳不见了,那长满了青苔的柳罐,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里汲水了……长天里,只是一片红云,在半空里下火,越走越是焦热。啊,你回过头来瞧,那走过来的故乡的方向啊……那苍白色的女人把头低到不可再低……她已是寸步难行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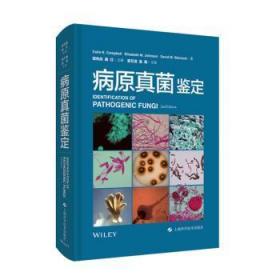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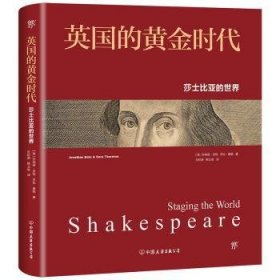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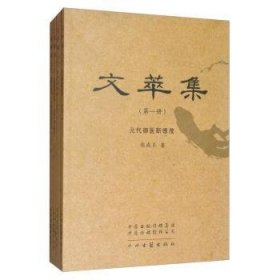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