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讲析
正版全新
¥ 46.76 5.3折 ¥ 88 全新
库存6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周志文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47858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88元
货号1011941
上书时间2024-05-22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0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书 名】 论语讲析
【书 号】 9787200147858
【出 版 社】 北京出版社
【作 者】 周志文
【出版日期】 2019-10-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定 价】 88.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专业性:作者虽非专门研究《论语》,但其学术主业是古代文化、思想史研究,长期浸染其中,对古典著作十分熟谙,于《论语》等书更是经常思索讨论;另外,作者少时开始接触《论语》,此后读、讲此书凡几十年,若就思索上言,已近一生,可谓用力甚深,足以保证此书的专业水准。
2.可读性:作者对西方历史、哲学亦广博涉猎,又深谙美学与音乐,故对《论语》,博采众长,多有新解。又发挥了他擅长糅合理性思考与生命经验的随笔的写作优势,注释翻译,文字均流畅精准,使这部经典解读著作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3.切身性:作者以为孔子所言之道德其实为一种生活美学,故认为《论语》一书充满灵动美感,绝不僵化。此书以新知与故训结合,有统整之效。引证多取材现代人易懂者,又融中外文史哲之学为一炉,使人阅读古籍,思索生命,感悟更切。
【内容简介】
作者以自身数十年阅读《论语》的工夫为根基,以多年讲学积累为基础,完成这部文质兼美的《论语》读本。本书每章包括四部分:《论语》原文、注释、语译和讲析。原文部分,采用权威底本,准确无误;注释部分,注重会通,以简驭繁,解释清晰而明确;语译部分,尽量切合古人语言特点,十分注意气氛与语言力度,力争兼顾达意与传神;讲析部分,作者用力*深也*有特色,作者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阅历,多有新见。作者试图融汇文史,打通古今,使人阅读古籍,思索生命。本书语言朴素生动,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目录】
《论语》这本书(代前言)
卷一
学而第*
为政第二
卷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三
公治长第五
雍也第六
卷四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五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卷六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卷七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卷九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卷十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孔子年表
后记
【文摘】
【前言】
《论语》这本书 (代前言)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论语》这本书。
一、《论语》的地位
《论语》被认为是儒家或整个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书,古时很重要的书都被称为“经”,经原义是指直线,引申有一切标准、法式的含义。中国为经书所下的定义很早,大约在汉代初年就有了,到武帝董仲舒时大致确立,西汉时,往往把经书也叫作“艺”。但《论语》这本书在唐代之前并不被看成经,尤其在汉代,因为汉代人认为《论语》并不是圣人所作,所以不能称之为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文中的“六艺”指的便是“六经”。又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在汉儒的观念中,经必须是与圣人的“作”(创作,如《春秋》)或是圣人的“述”(叙述、引用或整理,如其余的五经),否则绝不能算作经。《论语》由于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弟子所记录的,既不是孔子的“作”,也没有经过孔子的“述”,所以不能算是经。清末今文派的学者皮锡瑞在他的《经学历史》中说:
“……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皮锡瑞对经的看法,比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更加坚决与极端,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作品,都是孔子为万世所定的“教科书”,所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论语》由于不是孔子所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当然从传统的经学观念看,不能算是经书。
从严格的定义上看,《论语》虽不能算是传统儒家所认定的经书,但这本书在汉代就十分重要,在汉武帝之前,政府除了立“五经博士”外,还立过“《论语》博士”,不过有别于五经博士,《论语》的博士叫作“传记博士”,在汉儒的语言习惯中,“传记”是孔子弟子叙述圣人之意的著作,地位是低于经的。
《论语》当然重要,它记载孔子一生的言行,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一本书比它更翔实、更可信的。汉以后的人,有人把孔子看成“素王”,有人看成“至圣先师”,都视之为*崇高的圣人,孔子一言一行,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论语》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了。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上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錧辖是古代车辆前锁车辆的金属器具,而咽喉(喉)对人,衣领(衿)对衣服都是*重要的部分,可见《论语》虽然在汉代人的眼中不是经,但却具有甚至比六经更为积极的含义。
唐宋之后,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十三经”的时代,就干脆把《论语》立于经部了,到此《论语》的地位当然就更加重要。《宋史·赵普传》说:“普尝谓太宗曰: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成语的来源,尽管这种说法稍嫌功利,语意所涉也有不明确处,但可见传统社会对《论语》的重视。
到南宋朱子,他将《礼记》里的两篇《大学》《中庸》拿出来,再加上《论语》与《孟子》合成为《四书》,集合前人注疏与自己的解释成为《四书章句集注》。自《四书章句集注》一出,此书的地位俨然有取代“十三经”之势。而《四书》表面上有四部“书”,其实《大学》《中庸》的分量比起《论语》《孟子》显然不足,《孟子》的字数虽多过《论语》,但孟子与孔子较,他在儒家的地位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四书》中,当以《论语》为核心,殆无可疑。
假如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找一本与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同样地位的书,《论语》可当之无愧,所以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说,《论语》绝对是一本极重要的书。
二、《论语》的编纂
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上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班固的这一段话,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由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下来,也有是弟子在言谈中转述孔子的话语(接闻),由弟子间接地记录下来;其二是孔子死后,由孔子门人与弟子门人论纂、编辑而成。
班固的说法*具权威,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论语》可以说绝大多数是记载言语的“语录体”,但其中也有只记行而不记言的,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7.4)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7.9)
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7.12)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7.17)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7.26)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9.1)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9.4)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子罕》9.9)
此外还有许多。以上所举,都是只记行而未记言的,更有趣的是《乡党》一篇,几乎全记孔子之行,可见《论语》虽为语录体,但也有一部分是只记行不记言的。因此《论语》的“语”字应作广义解,不只专指记载语言,尚包含记载孔子的行为。
还有《论语》虽然以记录孔子的言行为主,其中也记载了弟子及时人的言行,如: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5.13)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雍也》6.7)
上面两章只记弟子言行,与孔子不见得有关,甚至《子张》一全篇,记录的全是弟子的言语,证明班固之说:“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虽可信,但不可拘泥。
班固的解释,又涉及“论”字的读音问题,如依照班固的说法,《论语》是孔子死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书,则《论语》的“论”字就该念成去声。但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则采“伦次”“伦理”“经纶”等义。邢昺《论语注疏》又加疏解说:
“郑玄云:‘……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合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
邢昺的解释,更为折衷综合,是故,《论语》的“论”字如解作“纶、轮、理”的话应读为阳平,如解作“次、撰”的话则应读为去声,两种解释与读法都有理由。但在习惯上,都将论字读成阳平。
班固所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这句话也有点问题,如果把“门人”指的是“及门”的弟子而言,照班固字面的说法是《论语》是孔子生前门弟子各记所见闻,孔子死后即由弟子编辑而成,其实《论语》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孔子死后的事情,像《泰伯》篇两段记录曾子临死的故事: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8.3)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到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8.4)
这两章所记是曾子临终前的事。曾子是孔门年纪*小的重要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其实孔门弟子与曾子同年的有颜幸,比曾子更少的还有冉孺、曹恤、伯虔、公孙龙等人,只是他们不如曾子重要。)曾子死时当然距离孔子死后已经很久,《论语》有曾子死的详细记录,可证《论语》不是孔子死后即由弟子相与论纂而成,而是孔子死了很多年,由他的再传或三传弟子编辑整理而成的,所以也不必拘泥于班固的说法。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门人记孔子的言行,有的记于孔子生前,有的记在孔子死后,这些材料留下来,由*后的人编辑而成书。那么*后完成《论语》的人到底是谁呢?前面引用了《论语》里记录曾子临死时的故事内容,而曾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徒”里面*为年幼者之一,曾子死时,孔门的“大”弟子应该一个不剩了,所以说《论语》完成于曾子弟子之手应该是*为可信。
为什么说是完成在曾子弟子手上呢?因为我们看上面所引《论语》的两段的文字,并不是曾子的自记,而是他人所记,而记录像死亡过程这么隐秘的事,只有亲人或随侍在旁的学生才有可能,这两段文字,当然只有是曾子弟子才能记,所以《论语》这本书应该可以确定完成在曾子死后。
另一个证明是《论语》里面称孔子固以“子”或“夫子”相称,称孔子的弟子却大多只称其字,孔子呼叫他们则直呼其名。要知道古人使用称呼是很严格的事,名是给人自称或辈分高的人用的,而字是给同辈或晚辈的人使用的,孔门的“大弟子”如颜回(字渊或子渊)、仲由(字子路或季路)、端木赐(字子贡),在《论语》里头,孔子称他们必称其名,如:“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3.17)“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6.6)“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6.9) ,如果不是孔子的语气,《论语》记他们则必以字,譬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八佾》3.17)“颜渊、季路侍。”(《公治长》5.25)等。然而《论语》里面记曾参与有若从不用字,而直接称他们为“曾子”或“有子”(夫子、老师),这两人在年龄辈分上比颜渊、子路要小要低不说,在孔门的地位也远不如“前贤”远甚,何以称重要的人却用一般的字,而称比较次要者反而使用“夫子”或“老师”这种尊称呢?可见说《论语》完成在有子或曾子学生的手上是有道理的。唐代柳宗元在他的《论语辩》一文中曾说:
…………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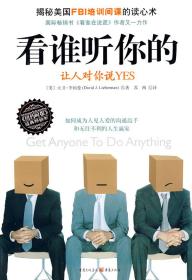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