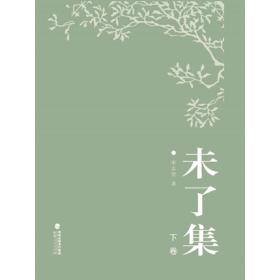
未了集(上下卷)
正版全新
¥ 35.75 5.3折 ¥ 68 全新
库存2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宋志坚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1080571
出版时间2019-01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700页
定价68元
货号1023053
上书时间2023-10-09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书 名】 未了集(上下卷)
【书 号】 9787211080571
【出 版 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 者】 宋志坚
【出版日期】 2019-01-01
【开 本】 32开
【页 码】 700
【定 价】 68.00元
【内容简介】
《未了集》所收录的200余篇文章,均为杂文家宋志坚近年新作。该书分为上下卷,上卷重在论今、重在时政,下卷重在说古、重在文史。作者以严谨、犀利的文笔,开放多元的思路,读古籍、看时政,见解独到,不偏激、不避讳,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和长远的历史眼光。
【目录】
上卷
不干预就是*大的支持
作秀离“上德”有多远
官民关系的互动
车有病还是人有病(外一篇)
大年三十的大欢喜
群众的眼睛归根结蒂是雪亮的
十年之后看“非典”
涉“官”三题
段爱平的“贴补”与“贴近”
村官贿选不可等闲视之
举报嫌疑人“自证清白”之诡异
“小庙容不下大菩萨”论
我不赞赏“工作狂”
特权是如何固化的
贵在“扎根”
难在“限己”
我曾见过禹作敏
我很想对父亲说
送别世庆
同学会纪事
柯中情缘
《柯中缘同学情》序言
“碰珠”与“门吸”之间
礼义之“礼”岂在大礼厚礼
媒体义士与官场生态
“亡羊”之后做点啥
群众路线教育实效很具体
“第*书记”的利与弊
马向阳的“领导艺术”
令人忍俊不禁的“倒逼”
周一波请辞不配“高调”
新陈代谢亦有谱
育人与育才
城镇化的“空间”有多宽
莫将“乱写”作“才气”
老家的古樟与春兰
“任性得起”也不能任性
说说“村官”之“气”
再说“村官”之“气”
“无所不烧”的专家解读
大言“提拔”当真不愧?
一篇杂文的脚注
法制意识的跑冒滴漏
“严禁”怎能滥用
“争名”辨析
基层是篇大文章
有些亮点是污点
讲好“小道理”
“集体研究”之研究
学会“忍让”
党纪严于国法
腐败高发区与腐败规律
文化名人是评出来的吗
实大于名项星耀
比什么与怎么比
贪官与什么有关
富豪的“能量”
“官场孤例”发微
什么叫“守土有责”
官本位的资历
评审者亦受评审
愧祭
级别恰似“硬通货”
琉璃瓦下的“友情提醒”
两种“断崖式”
孝例点评与“孝顺艺术”
“极极少数”并无衍字
注释«古文观止»的晶如先生
“拆墙透绿”的喜与忧
城市的记忆
山西“拍蝇”议
媒体“风暴”何其多
现代民主的“古代元素”
盛夏说扇
三分之一的“真话”
雷锋三题
从海昏侯墓说到后人与后事
目连嗐头
管好管官的官
“廉政尴尬”刍议
扶贫缘何不够精准
守护“学习”真谛
“雁过”为何被“拔毛”
“吹牛”论
“政治资源”是什么
从“真话”说到“泡沫”
“苍蝇”的边界
从“小官巨贪”说到“老虎”“苍蝇”
龙舌兰不是芦荟
城市文明的细节
闲人闲书闲文
尊孔批孔识孔
恍若时空错位
“攻坚战”二题
防人与防火
五味杂陈的“悦读”
下卷
孙叔敖“其俭逼下”议
“门第”问题
典衣、典冠及其他
朱熹“遏人欲而存天理”解
朱熹不是状元
蔡京的党与派
朱熹“纳其尼女”议
权大法大
殷浩的名与实
娄师德怎样推荐狄仁杰
挑剔《韩诗》:“默默”者何“谀”
朱买臣的“报复”不够男人
庄周化丘还是丘化庄周
寇准的“好刚使气”
苏轼要不要叩谢皇恩
王安石为何怨恨“福建子”
引经据典的“年龄”问题
荐贤而不市恩
修身齐家与治国理政
大度宽容的极致与边界
遗恨终天之“默”
王安石的两个学生
苏轼可“废”的四条理由
马援诫侄怕的是什么
曾参“出”妻
王素谏奢
蔡襄为犯颜直谏者辩
公私不分之“*”
墨子“尚贤”
论葫芦僧
孟子*不值得称道的是什么
元载的“白头信”也有威
《茶花女》触动林纾哪条神经
李世民的用人原则
齐威王突出重围识真伪
嵇康眼中的管蔡旧案
孔子“乘桴浮于海”欲去何处
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
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
儒墨恩怨
唐德宗之“局”
“斜封官”之“斜”
郑振铎的“持中之论”
骊山的“鬼”惹不起
李唐蝗变
端妃误议朱熹
鲁迅给川岛的书信
文景异同
两面邹忌
陈独秀“反孔”
司马光论汉武帝
劝君少为子孙谋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
新莽时期的“行为杂文”
贾宝玉不宜做官论
刘秀的“仁明之累”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人算不如天算
孔僖自辩
李大钊的“反孔”视角
敢言“吾之过”
“父母唯其疾之忧”例解
官不扰民也是功德
«鲁迅“反孔”论»序跋
鲁迅的“礼教吃人”辩
鲁迅的“天才泥土”论
高允的“矫矫风节”
言路与才路
被谏阻的封禅
拓跋珪之“爱”
鲁迅的“父道”
赵绰的选择
徇私枉法者鉴
舍身求法
宋真宗“敬畏天命”说
宋真宗的“天书”续说
宋朝皇帝“快意事”
南宋中期的“伪学”与“逆党”
朱熹之死
庆元党禁之“驰”
朱熹与朱子理学的命运
“台谏”之鉴
韩侂胄的“头颅”问题
南宋中后期的三大权臣
济王赵竑案的专制底色
“权归人主,政出中书”考辨
宋朝真有那么好吗
后记
附录
丁酉之春的“绝地体验”
天使依旧
亲情友情
人生如豆荚
【文摘】
实大于名项星耀
宋志坚
海峡书局推出一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学创作丛书,该校副校长汪文项教授为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有关于该校文学学科的两句话:“历史上,叶圣陶、董作宾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译家项星耀也曾任教于师大中文系。”我在《文化名人是评出来的吗》一文中说到这件事,并且因此议论说:“汪文项教授引他为福建师大文学学科之荣,只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令人瞩目。……他的名气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人为的色彩。岁月的流逝,没有使他的身影远去,只把他的名字淘洗得更加亮丽。”
我曾与老项有过交往,不妨接着上面这个话题,说说他的“名气”。
说不清老项到底懂得几种语言,他是从来不同人说这些的。我只是听项夫人邢桂芬说过,老项精通六国文字。那一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老项的短文中我说了这句话,他就来信批评“内容失实”了,说就像在中文中也会出现俄文、英文一样,在俄文、英文读物中,也会出现别国的文字。懂得一点这些国家的文字,是翻译工作所必须的,谈不上精通。
也说不清老项到底翻译过多少作品。照例,他也从来不同人说这些,连邢桂芬也未能帮我弄到他的全部译著的书名。但仅据我所知,经他之手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就有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上下)、萨克雷的《潘登尼斯》(上下)、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谢甫琴科的《音乐家》、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谢德林寓言选集》和《狄更斯文集·中短篇小说选》。其中《米德尔马契》和《一位女士的画像》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米德尔马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库”。
和科学没有国界一样,文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优秀的文学作品要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必须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翻译,就是沟通中外文学,连接中外文明的桥梁与纽带。项星耀译著等身,堪称中国翻译界的大家。然而,当今中国,又有多少人熟悉这位翻译园地中默默无声的耕耘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向著名散文家郭风说起老项,郭风老人连声感叹:“有的人是名过其实,他却是实过其名,难得,难得!”
我与老项相识,是在1970年早春。
1969年,我与项夫人邢桂芬一起下放到闽东沿海的霞浦县溪南公社。当时老项还在受审查,几个月后才获得下放农村的资格。他到霞浦的那一天,正在县城的我前去他下榻的民族招待所看望他。
我已听邢桂芬多次说过老项其人,知道他学识渊博,很有些肃然起敬。老项也听邢桂芬说过我,但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他的精神尚未从接受审查的阴影中解脱,他在与我握手之后,只说了几句话就沉默了。
我打量起老项。他年近五十,瘦高的个子,高耸的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镜。胡须刮得精光,却未能刮去留在皮肉中的胡碴,下颌泛出一层青黑色。这青黑色使我十分离奇地联想到小时候在连环画中看到过的美军飞行员戴维斯上校,甚至感到他的受审查,或许正是由于这些连剃刀也未能刮去的戴维斯上校式的胡碴。
短暂的寂静使邢桂芬感到很窘,她带着几分歉意说:“小宋,老项就是这个样子,见人没有几句话,以后熟悉了,话就多了。”
毕竟是同命相怜,我和老项很快就熟悉了。
老项他们住在台江村,离公社所在地有十里路,还要翻一道岭。但他们还是常来公社,有时开会,有时买米,有时领工资,有时寄邮件。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的落脚点。我也间或去台江走走,就住在他们家。邢桂芬做得一手好菜,我们又是同乡,我去了,她总要煮上几个合口味的,有时饭菜尚未就绪,她就让老项带我去外面走走。我和老项于是就去浪花飞溅的海边漫步散心。
他的知识面很宽,也很健谈。他和我谈法兰西的几次共和及几次帝制复辟,谈梅林的«马克思传»,谈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谈唐弢的杂文……只要一打开话匣子,就再也见不到留在我印象中的那一份矜持。但我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忧郁和苦闷:头上顶着怎样的华盖,心中就有怎样的阴影。
老项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老邢是芳华越剧团的。20世纪50年代末,因为芳华越剧团“支援前线”,老项也随老邢调到了福建,如今又从福州来到溪南。生活适应需要过程,业务专长不能发挥,农村工作自然也没有本地干部来得熟悉,且在一些人眼里,下放干部都是犯了错误的。尽管他们白天下田,晚上下队,不敢有半点懈怠,但还是不断传来闲言碎语。例如,老项和老邢工资都在一百元以上,在当时当地,无疑属于高薪阶层,这竟然也成了一个话柄,有人甚至在背后用“双百夫妻”作为绰号称呼他们。病了,邻居帮他们挑几担水,他们过意不去,给了一点钱,于是又传出“双百夫妻雇人挑水”的话头。这些闲言碎语,都隐含着“不劳而获”“剥削劳动”之类的意思,对于正在“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下放干部,犹如风刀霜剑。
而且,就像雾茫茫的大海,谁也说不准,这种华盖运何时才能有一个了结。
就在这被不少人称之为“流放”和“发配”的下放期间,把忧郁和苦闷埋在心里的项星耀,开始了一项介绍和传播域外文明的巨大工程。我曾目睹,在闽东沿海的那个村落,在没有窗户只靠嵌在屋顶的一块玻璃采光的农家小阁楼上,老项汗流浃背地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情形。
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第*个亮出旗帜反对沙皇君主制度的人,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诚然,赫尔岑也有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他与巴枯宁关系密切,但他逝世前已同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决裂;他与马克思曾有过嫌隙,但他同巴枯宁决裂时,已把视线转向了马克思领导的共产国际。«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劳动写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罗斯与西欧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艺术纪录。这部作品充分显示了赫尔岑的艺术造诣。屠格涅夫在读完«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叙述家庭悲剧的那一部分的手稿后,激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
项星耀开始翻译的就是这样一位作家的这样一部作品。
老项对我说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要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著是不可能的,尽管列宁在«纪念赫尔岑》这篇文章中对赫尔岑做过全面、客观的评价,但那是一个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年头,仅凭马克思曾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过赫尔岑这一点,只要出版了《往事与随想》的译著,出版者就会和翻译者一起倒霉。但老项又说,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著,因为中国文化界不会一直这样沉寂下去,中国翻译界不会永远留下这样的空白,中国不会永远没有《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凭着这种信念,他一句一句、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翻译着,寒暑易节,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但老项没有想到,就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还有一个人和他一样,正在默默无声地从事着这项巨大的工程。这个人就是一代文学大师巴金。
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巴金的夙愿。早在1928年2月5日,当青年时代的巴金刚刚买到《往事与随想》的英文译本时,他就感到了燃烧在这部巨著中的那一团火正在和自己心中燃烧着的火熔为一体。巴金称《往事与随想》是自己的老师。他当时正在写他的第*部小说《灭亡》,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此后,他曾陆续翻译过《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然而,巴金始终没有整块的时间将《往事与随想》全书译出。直到1974年,巴金才开始偿还这笔拖欠了几十年的旧账。比起项星耀,巴金的处境无疑更为恶劣:四人帮要让这位文坛耆宿“自行消亡”。他翻译这部巨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只是感到自己在做这一生中的*后一件工作,只是一边翻译一边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巴金的一封信,当时已经调回福建师范大学翻译联合国文字资料的项星耀,正是从这封信中得到了巴金正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信息。他“撞车”了,而且撞在巴金的车上,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白费了心血。重要的是把这一份人类文明的成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至于用不用自己的译本也可以在所不计。能有巴金的译本,更是值得庆幸的事。老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字一句翻译出来誊写得工工整整的前四卷译稿寄给了巴金。1978年9月17日,巴金在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册(包括一、二两卷)“后记”中说到几位新老朋友对他的无私帮助,其中第*位就是项星耀。巴金是这样说的:“福建师范大学的项星耀同志把他翻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供我参考……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
巴金也希望项星耀的译本能得以问世。他亲自为老项联系了一家出版社,要老项把译稿寄去。但老项推辞了。巴金或许猜出了老项的意思,写信对老项说,他在整理茅盾遗稿时发现茅盾说过,有些世界名著,能有几部译本没有什么不好。但老项还是没有接受巴金的这番美意。直到1986年,得知巴金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不允许他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但他又一再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书的全译本时,项星耀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了翻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合同。老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译这本书也是接受他(巴金)的委托。”
年过花甲,已经离休在上海定居的项星耀于是孜孜不倦地进行了后四卷的翻译工作。1988年初春,我到上海出差时曾去看望老项他们。性格外向的项夫人邢桂芬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说:“这个老项呀,从来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连大年三十都守着这张写字台。你老远地从福建来,他才难得坐下来与你聊聊天。”我理解邢桂芬,她这是嗔怪,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其中有自豪,也有心疼。我于是再次仔细地打量老项,就像刚与老项相识时打量他一样。高耸的鼻梁上仍然架着那副近视镜,但两鬓和胡须均已变得花白。我这才意识到老项已经老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岁月的流逝,更是艰辛跋涉留下的印记。
送我出门时,老项告诉我,后四卷的《往事与随想》译著初稿已经脱手。项星耀的《往事与随想》译本,原定书名是《往事与沉思》。或许为了与《俄国文学史》《俄罗斯经典作家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著述保持一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项星耀采用《往事与随想》这一书名。但这个书名是巴金首先采用的。为此,1992年3月26日,项星耀写信向巴金征求意见。巴金收到老项的信后,于3月31日回信说:“全译本仍用《往事与随想》译名,我当然同意(‘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了一位读者的建议),而且我应当感谢你替我偿还了一笔拖欠了几十年的大债……”
《往事与随想》只印了1380套,几乎创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印数的*低纪录。老项给巴金老人送去了这部译著,巴老自然也为中国图书市场的这种现状感到忧虑,他神色黯然地说:“能有1380册已经算是不错了。”然而,能在垂暮之年看到«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巴老依然感到欣慰。
事业和名利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事业心强的,会被人说是名利观念重;名利观念重的,又会被人说是事业心强。然而,事业心与名利心毕竟是有区别的。项星耀事业心很强,但他淡泊名利。下面说的几件事,一般人或许都会感到难以置信。
项星耀不知道自己能享受离休待遇。离休之前,他曾长期住在老邢的工作单位,不会骑自行车,只好挤公共汽车来回奔波于福建师范大学与芳华越剧团之间。老项舍不得这些虚掷在路途之中的时间,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翻译工作。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向组织上提出了退休到上海的请求。福建师大人事处的同志是善解人意的,他们查阅了老项的档案,发现他早在1945年就投奔新四军,于是说:“项老师,您该办的不是退休手续,您是可以离休的。”此后,老项在上海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待遇却是别人为他挖掘出来的。
项星耀没有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凭他的成就,在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挂个常务理事之类的头衔并不过分,但他从来不图这些虚名。他也不喜欢把时光虚掷在交际、应酬和各种会议之中,一位与他分别数年的教授写信给他,预期在次年召开的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理事会上与老项相见,但他哪里想得到,老项连翻译工作者协会都没有参加呢!
项星耀未曾有教授的职称。他一直是副教授,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次评职称时评的。他是带着这一职称离休的。在他离休之后,福建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范公荣同志曾去上海看望他,说凭老项的成果,完全可以申报评教授职称,要他填表。但他谢绝了。他的夫人与女儿要替他填,也被他阻止了。邢桂芬说:“这个老项呀,别人争都来不及,他到了手边的东西都懒得伸手,不知道他到底图个啥?”老项图个啥?他图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为后人留下点东西。在他看来,职称、待遇、名利、地位全都是身外之物,他舍不得去花那个工夫。那一次,当我笑着向邢桂芬说出这个意思时,坐在一旁的老项,唯有颔首不已。
我于是再次感受到事业与名利的区别。事业与名利作为人们奋斗的源泉,有丰富和贫乏之分。前者像江河取之不尽,后者如溪水极易枯竭;事业与名利作为人们奋斗的目标,有伟大与渺小之别:“虚荣的人总是注视着自己的名字”,极易为一时的成功津津乐道、忘乎所以,止步不前,而“光荣的人永远注视着革命的事业”,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于是也不会受身边的掌声和鲜花的牵制,只是不断地跨越自己,开拓前进。事业心与名利心作为一定的情操和格调又有高尚与低下的不同,名利属于个人,事业属于人类。为名利的人往往妒忌别人的名利,甚至为获取名利而不择手段;为事业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力量促成别人的成功,又从别人的成功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老项就是这样的人。
老项是1997年10月28日去世的,得的是肠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得这种病,身体不适只当是伤风感冒漠然置之,直到挺不下去才去检查,但病情已经无法挽回。把他送入医院时,因为需要排队办手续,他躺的担架在医院水泥地板上搁了好一阵。病房自然也是不理想的,以后由邢桂芬几经周折才稍有改善。看病需要花钱,他让邢桂芬去上海译文出版社预支了一万元钱的稿费。以老项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他应有相当的待遇,但老项始终都很平静,因为他过的一直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老项患病住院后,邢桂芬曾与老项离休前所在的单位福建师大联系过。有关人士一直都说比较忙,一时走不开。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与老项隔了好几代的他们并不了解老项,他们从档案材料中知道的项星耀只是一个副教授,一个享受副厅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直到老项去世前的几天,福建师大才派人去上海看望老项。回福州后马上得到噩耗再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一起操办老项的丧事。他们这才发现,老项翻译出版的作品已有上千万字,而且大多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只要属于知识阶层的人士,谁都能掂得出这分量,这样的翻译家,在当今中国翻译界也屈指可数。于是,福建师大的悼词中称老项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福建师大副教授、副厅级离休干部”。虽说老项生前从来不在乎什么头衔,他认为这只是虚名,但将这三个并不相称的头衔一起放在已经作古的老项头
上,仍不免使人感到一种悲哀。
没有更多的悼念文章,没有与他的贡献相称的悼念仪式,一个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翻译界的大家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老项临终前几天,躺在病床上拉着邢桂芬的手说:“桂芬,你要坚强些,再坚强些,只要挺过前面的八个月,你能挺得过去。”老项去世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志兴冲冲地打来电话想告诉老项,他的又一部译作已经问世。然而,老项已经不在了,出版社的同志唏嘘不已。
邢桂芬给我寄来了老项去世后出版的译作,这是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昆丁·达沃德»。这部小说使司各特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各国也享有了广泛的声誉,从此被公认为真正的历史小说的创始人。邢桂芬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小宋,你已收不到老项亲自赠送的书了,现在由我代他赠送新**,请永远保藏留念。”下面署的日期是1998年6月6日。
老项悄悄离去,至今已过十八个春秋。
朱熹“纳其尼女”议
宋志坚
朱熹与尼姑的话题,乃是“庆元党禁”的遗留问题,“伪学逆党”案已在宋理宗时平反昭雪,朱熹与尼姑的关系,却总有疑团未释,这个话题也就绵延不绝。
事情的缘起,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充当韩侂胄之打手的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的弹劾。沈继祖为朱熹列举的罪状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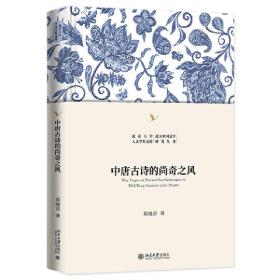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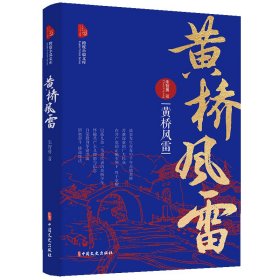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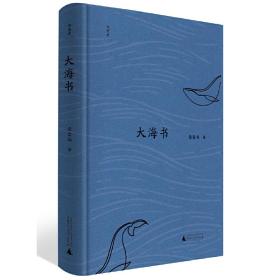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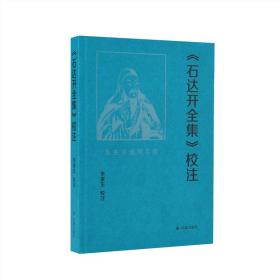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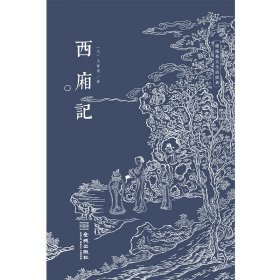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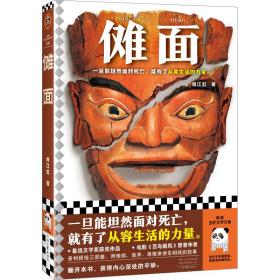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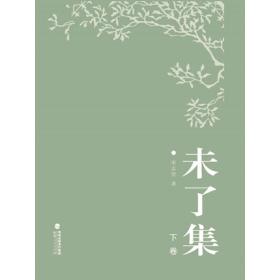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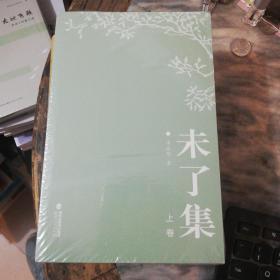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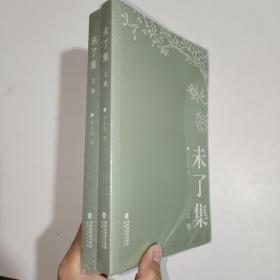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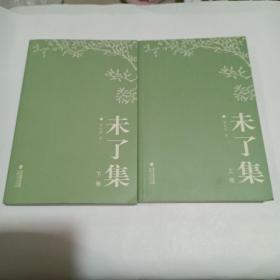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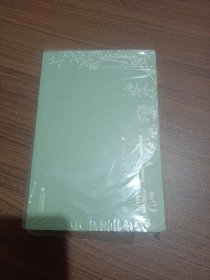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