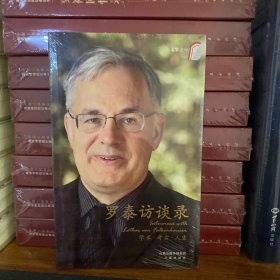
罗泰先生访谈录
正版,未拆封,无划线笔记,可以发京东顺丰➕费用就行,
¥ 25 8.9折 ¥ 28 九五品
仅1件
重庆沙坪坝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孟繁之 编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
版次1
装帧平装
货号内1上2
上书时间2024-02-2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孟繁之 编
- 出版社 三晋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4-08
- 版次 1
- ISBN 9787545710021
- 定价 28.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开
- 页数 314页
- 字数 200千字
- 【内容简介】
- 本书稿是对国际知名东亚考古学家罗泰教授的访谈,就罗泰教授对中国考古学的见解展开,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的缺失、考古学方法论、海外中国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西方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变迁等热点问题,是国外考古大家对中国考古学的独到认识,学术意义较大。
- 【作者简介】
-
孟繁之,现任职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从事古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编著有小字白劳:李零自序集曾祖周馥:从李鸿章幕府到国之干城等书。
精彩内容:
我们是别样的、美国的希望!
访谈人:helmut orge
罗泰教授成长的家庭塑造了他良好的礼仪惯,他从未曾想过仅仅因为周围那些穿着t恤配牛仔裤或鼓鼓囊囊的灯芯绒裤子配西部牛仔衬衣的美国师生的嘲笑而放弃这种生活方式。49岁的罗泰教授坚持穿着并不宽松的夹克、法兰绒裤子、皮鞋,系着领带去上课。这个生于埃森(een)的学者这种优雅的装扮无疑并不过时,他的背后拥有着令人惊异的职业历程。罗泰教授先后读于德国波恩大学、中国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本京都大学,并且熟练掌握了中国古典文言文、现代汉语以及语,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并从1993年起任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艺术史与古学教授——一位有地位的汉学家。至2006年,罗泰已出版了两本书:乐悬:中国青铜时代的编钟(upended muic: chimebell in the cultur of bronze age china)、宗子维城[原名孔子时代的会(公元前1000一前250年):古学的证据,chinee 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1 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以及集中国盐业古(卷)。罗泰是个极其少见的例子,避开了德国新兴学术力量所遇到的官僚主义——即使这些新兴力量已经具有了不容忽视的规模。在慕尼黑获得教席之后,“资助我的当局暗示,在德国大学得到教席已经是个不可思议的荣誉”,罗泰回忆道,“因此我不必再提其他要求了”。当局一向如此,罗泰教授宁愿留在加利福尼亚。在此期间,他成为美国公民。尽管如此,罗泰教授仍然熟悉德国的教育体制,对美国的体制也了然于胸。他认为德国的高校结构有所欠缺,比如当局的干涉,对他而言无法忍受,很多也缺乏学的意愿。此外是大西洋两岸的教育需要注意的短缺。他也担心,美国毫无保护地受到来自同龄人的压力的影响。如果人们不能及时批判地认识媒体的信息交互,来自电视和网络的大量消费则会“推动人们愈发呆滞”。
简单来说,是埃森(een)的一所学校促使我前往中国,又终来到了美国。
在上文理中学的时候,学校生活极其无聊。而实际上,这所学校并不差,只是他们对于开启心智实在有限(毕竟还有一个不错的校园管弦乐队)。在埃森,这个我于1959年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本可以找到一所更好的学校,但我读的文理中学“恰在街角”,而且这是我父亲曾经读的学校,我自然而然被送到了那里。于是我只好另选其他地方去寻求挑战了。
市里的青活动中心有中文培训课,为什么不参加呢?去学数以万计的文字(一般通常掌握4000到5000个即好),此外还有四个声调,这些声调决定了每一词汇的意思。一门语言,对我终生都是一项挑战。作为一名中,那么多职业需要的技能我都还不知道呢。像我父亲一样做一名律师?公证人?还是外交官?我曾经这么幻想过:事业的很好在多哥(republique togolaie,西非的一个)。一位部长突然造访洛美(lome,多哥的首都),在大使馆游泳池边享受鸡尾酒,部长的妻子希望寻找原始的艺术,部长自己则想看侏儒或者大猩猩(多哥所无)。他又不懂非洲基本的地理,对之所知甚少。所有这些都要我管。外交官的职务,那不是我的选择。
终,我在波恩大学注册读,主攻专业为汉学。我的家庭与中国没有特殊的联系,除了太祖父的一位远房亲戚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按: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人多的,她有老子、孔夫子、皇帝、阴阳、水墨画、义和团运动、汉字、战争、默剧、石窟寺、陶瓷、印刷术、长城、杂技演员、抒情诗、陶笛等等,还有直到依旧吸引我的铜钟。
我们几乎不了解时代的中国,于1949年建立起中华共和国。那时候接触西方是受限的,甚至学者交往也很麻烦。1972年,与美国统尼克松(rlichard m.nixon)次会面之后,开始有了慢慢增多的交流的希望,也促进了1979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1972年起,还在“”期间,德国交换留允许来中国学。不过在那时,他们觉得既站在门里,又站在门外。“门里”“门外”是形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常用词,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有一本书叫作门里门外话中国(china: within the outer gate)。越深入了解历代皇朝、近代、唐诗、周代编钟、明代绘画等,我对于这个世界越发好奇。
p14 - 【目录】
-
preface
序
我们是别样的、美国的希望!
古:匡正书本上的历史
谈中国古学的缺失
罗泰与中国古学
谈陕西与陕西古
谈古学方
谈中国古学
谈社会古学
北京大学古系六十周年系庆对罗泰教授的访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学著作都是当代的
中国公共古的新思路
罗泰教授学术访谈
附录:
文献古并重的《剑桥中国远古史》筹编述略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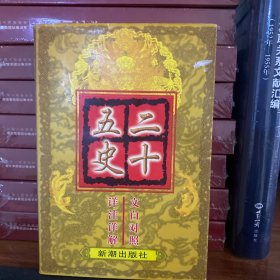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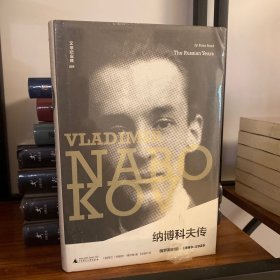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