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之三——书串汇编
曲艺花草集,曲艺赋赞,说书赋赞。
¥ 48 ¥ 48 全新
仅1件
河南焦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吕武成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4865428
出版时间2019-08
版次1
印刷时间2019-08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大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452页
字数250千字
定价48元
上书时间2023-08-1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0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没被翻阅过。如需作者签印,请备注。
- 商品描述
-
河南四大曲种之一河洛大鼓已到了涉临灭绝的边沿,老艺人不断故去,新艺人青黄不接,大量的经典曲目已流失,而河洛大鼓艺人曾赖以生存的长篇大书因演出市场的萎缩而首当其冲。留住优秀的传统长篇书目,以便于传承和振兴是编撰《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之宗旨。“书串儿”(赋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历代艺人长期演出实践的结晶,是独特性曲艺语言的精华,更是购成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的主要元素,随着长篇大书的淡出,“书串儿”也面临灭绝的厄运。出版此《书串汇编》,意在留住曲艺语言艺术的精髓,以便更好地研究、继承和发展。
《书串汇编》大32开本,488页,25万字,是《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的第三部。下面摘录书中的部分内容,以便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前 言
河洛大鼓是河南省四大曲种(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大调曲子、三弦书)之一,广泛流行于河洛流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俗称“说书”。2006年6月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入选“国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河洛大鼓的命运,老艺人陆续故去,把很多经典书(曲)目带进了坟墓,成为千古遗憾!在濒临失传的经典书(曲)目中,长篇大书则首当其冲。
大鼓类曲种也称鼓书、鼓词儿,鼓儿词,内容上除小段、中篇段子以外,说唱长篇大书是其主要功能。故说大书是衡量艺人是否学艺有成的标志。一个艺人在一个村子或一个固定场所,不动地方经年累月的演唱,吸引听众听罢这场听那场,显然单靠“段子活儿”是站不住脚的。而长篇大书场面恢宏,纵横交错,千头万绪,曲折迂回,一波未平,一波又生,险象环生,环环相扣。书味、书理、书情,处处扣人心弦,使人欲罢不能。而“段子活儿”一段一结或一场一结,不能给听众留下悬念,只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故长篇大书只所以成为河洛大鼓的“主角儿”,是河洛大鼓艺术生存的智慧,是说书艺人 “饭碗儿”的保障,如果没有长篇大书,说书人就不可能在一个场地经年累月地唱。
较“段子活”而言,唱一部长篇大书要复杂得多。同记叙文的六要素一样,长篇大书也是由有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的六要素构成。这六要素“交待不真,如钝刀杀人,听书的听不懂,说书的白搭功。”六要素固然重要,却仅是长篇大书的一个骨架,支撑起整部大书的纵横脉络,使其浑然一体,光有骨架远远不够,需要有血有肉,才能血肉丰满。骨架再完整,也只是一具“空架子”,只有充满了血肉,才能赋予鲜活的生命。这里的“血肉”就是长篇大书极具特色的,经典性的语言——赋赞。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至西汉司马迁之后,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曹植的《洛神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因赋和曲艺说唱类的曲词都具有诗词的韵律感,使赋走进说唱艺术,或说唱艺术引入、吸收赋成为顺理成章的一种可能。
“赞”:赞美、赞扬之意。早期的“赞”多为抒情文体,多用于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如颂扬人物的“像赞、小赞”等,也有叙事状物的《白杨礼赞》、《天安门赞》等。早期的赞只讲究文词华贵、典雅,不要求合辙押韵。引入到说唱艺术中受其感染,就分化为韵诵体和非韵诵体。韵诵体的就具备了诗的韵律感,说唱音乐的节奏感。不仅可以朗诵,吟咏,更宽泛地用于唱段之中。
和赋相比,韵诵体的赞语以上下句为主,讲究一韵到底,但平仄要求不像赋那样严格;非韵诵体的赞语是句法结构自由的散文,或“贯口”,或叠字垛句,语言铿锵有力,节奏性强。经常使用的有英雄赞、美人赞、山景赞、擂台赞、刀赞、枪赞、剑赞、马赞等。
“赋”和“赞”在文学史上原是两种独立的文体,引入说唱艺术后,大多数艺人习惯把赋和赞连在一起,称为“赋赞”,而赞与赋的特征和区别也逐渐淡化、融合,甚至赋赞不分,混为一谈。本书收录的大多数赋或赞就没有严格的区别和界限。
“赋赞”融入了说唱艺术,发生了质的改变。由原来华丽典雅演化为通俗朴实,由原来的书桌案头走向了书场,由原来文人雅士吟诵转变为艺人的舌中生花,由曲高和寡转向了大众化,由普通百姓欣赏不了演化为妇幼皆知。形成了源于文学而又区别于文学类特征的一种独特的曲艺语言。
曲艺中的赋赞发生的变革是历代文人学士介入曲艺的必然,是无数前辈老艺人智慧的结晶。赋赞最初也可能是文人创作,后经无数代艺人历经反复实践,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打磨而成,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形成了一个个的“串子”(或“条子”)。这些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串子”用错纵复杂的故事情节“串”起来,就形成了长篇大书。
赋赞除了在评书中迅速发扬光大以外,在大鼓书中更加盛行。评书受其自身条件(只说不唱)的局限,赋赞只能用于说表,吟诵,“贯口儿”等,而说唱类的大鼓书中的赋赞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不仅可以可以用于说表、“贯口儿”,更多地穿插于唱腔之中,成为构成长篇大书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或写人绘景、或叙事状物,或拟声寓情,或渲染气氛……无所不能。文学中的夸张、比喻、拟人、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在赋赞中发挥到了极致。使听众在享受韵律和节奏带来的快感的同时,陶醉在美的旋律里,沉浸在艺术的享受中。
在河洛大鼓的长篇大书中,赋赞因地域、师承及习惯不同,艺人们有不同的叫法。巩义一带河洛大鼓艺人把贯穿于整部大书,随处可见的赋赞称之为“串儿”、“书串儿”,意即一串一串地“串”起来“串”成大书之意。巩义河洛大鼓第四代名艺人尚继业老师在所著的《河洛大鼓初探》中,采用“串儿”的称谓。新安县一带的河洛大鼓艺人则把这些赋赞称之为“条子”、“书条儿”。“条子”一词在其它江湖行当也有运用,如算卦的卦歌通俗、生动、押韵,称为“卦条儿”,算卦有“透不透(准,应验),条子溜”的说法,算卦有“卦条儿”,抽签有“签条儿”,说书的就有“书条儿”,一条一条,编织成书。笔者拙著《河洛大鼓》则采信于“条子”之说。有的艺人还把类似于赋赞,描述某件事物的比较程式化的曲词叫做“歌儿”,如梳妆歌儿、十二月歌儿、卦歌儿等,有的则称为“词”,如开场词、拉马词、舞枪赋词等。有的则称为“套”或“套子”,如出兵套、拳套、算卦套等,有的则称为“条”,如五色条、卦条等。有的称为“图”,如小武士图、阵图等。
由于河洛大鼓自身独特的语言特点,严格来说,在河洛大鼓的长篇大书中,书串儿或书条儿并不是赋赞的代称,比赋赞包含的内容要丰富。赋赞只能是书串或条子的一部分。除了赋赞以外,还有很多如快板体的顺口溜儿、打油诗。虽不朗诵、吟唱,但却合辙押韵,流利通畅,一气呵成的“贯口”等都在书串或条子之列。
在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的演唱中,赋赞起着主要的作用,担任重要角色。在戏曲中,每一个角色出场,看穿戴,看化装,凭直观视觉,一目了然。但曲艺就不同了,一人多角,不可能变换角色就化一次妆,换一次衣裳。全凭演员以精练细微的语言,极富乐感、美感的韵律,生动传神的眼神、表情,虚拟化地、逼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使听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个过程曲艺中的行话称为“刻脸儿”(或为“开脸儿”)。戏曲中凭化妆师化妆,曲艺中凭说书艺人“刻脸儿”。怎么刻脸儿?就是凭借丰富的赋赞、条子来完成。如美人赋、公子赋、母子赋、将赞、五色条、小武士图等,美、丑、俊、傻,各色人等,千姿百态,远比戏曲中的“脸谱化”丰富、细腻得多。以此类推,各种动物、器物如刀枪棍棒,虎马牛羊,车船衣裳,纸砚文章等均可用赋赞来描述、刻画,以达到闻其声,如睹其物的效果。
在戏曲中,幕布徐徐开启,剧情中的场所、景致,山水四季,亭台楼阁通过舞台的摆设、布置,布景来展现在观众面前,而曲艺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了,全凭艺人舌生莲花,状物传神,通过一系列的赞赋、条子,虚拟地勾勒出一副风花雪月的山水画,把疆场之恢宏,雕梁画栋之瑰丽,幻觉地、逼真地在听众面前再现。让听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一部大书,情节是骨架,内容是血肉,赋赞是构成血肉的主要元素。赋赞丰富,血肉才能丰满,人物才能鲜活,有生命力。这就是长篇大书引人入胜,历演不衰的根本所在。
由此可见,熟练掌握和运用各色各样的赋赞是说唱长篇大书的必修课、基本功。一部大书,故事情节叙述得再准、再完整,内容再精彩,没有赋赞的画龙点睛,同样显得干巴巴无味,吸引不了听众听罢这场听那场。一个资深的,经验丰富的大书艺人,只要知道故事梗概,就可以用各色各样的赋赞、条子来迅速“串”成一部大书,搬到书场去唱。
前面说过,赋赞是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只所以说相对固定,是因为赋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深的艺人掌握一条赋赞,并不是熟练、流利地背会就可以了,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喜好,根据书情临场发挥而加以改变、增删,使其更适合,更贴切。把赋赞融入书情,才能真正的“活”起来。才算真正地掌握、吸收并消化了赋赞。所以赋赞同大书一样,也是“十唱九不同”,每个艺人都会根据自身喜好、需要,进行多次的再加工,再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赋赞是丰富多彩的。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赋赞,才能避免多个场景,多个人物使用单一的赋赞而出现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脸谱化”的缺陷。美人赋中,所有的小姐、佳人不可能相貌、穿戴、性格完全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用一个美人赋生搬更套地来给所有的姑娘、小姐来“刻脸儿”,那就把人物“木偶化”了,失去了真实,甚至闹出笑话。赋赞不是教条的、死板化的程式,只有活学活用,才能传真、入神,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为了力求达到赋赞的多样化,本书中收录的赋赞来源于各渠道、各曲种的各种风格,尽可能地涵盖全面。有最早的赋赞专集《花草集》。有鼓曲体裁的长篇大书,如《小将呼延庆》、《双枪将下山》、《海青天》等。有评书体裁的长篇说部,如《杨家将》、《封神演义》等。有评弹体裁的长篇说唱,如《西厢记》、《九龙口》等。有最原始的早期清末民初的长篇大书的木刻本、石印本,有最现代的如郑永昌、蒋敬生等曲艺作家创作的长篇大书。有的赋赞来源于网络,如新浪博客、百度贴吧等。有的则是来源于艺人口头演唱的记录,是经艺人实践出来的,最接地气的经典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赋赞大部分都不可能是原生态的,大都经过艺人的多次、反复锤炼,书的作者又经过进一步的再创作和二次加工的。这些加工过的赋赞大多又是为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书情而专设,故在学习运用赋赞时,只能做参考、取舍,不能生搬硬套,张冠李戴。
笔者是河洛大鼓艺人,受自身偏好的影响,收集的赋赞大多偏重于鼓曲类。受地域、方言的影响,弹词类的赋赞无论是句式,走笔行文都不太适合大鼓类曲种的演唱习惯。但弹词的词藻雍容华贵、优美典雅,极富文采,值得鼓曲类曲种借鉴。故本书酌情收录了一些弹词类的赋赞,供比对和参考。
在赋赞收集整理过程中,虽然想尽最大的努力,力求搜集得全面一些,完善一些,但局限于自身水平不高,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些比较生僻、冷门的赋赞难以收集齐全,尤其描述现代人物、场景的赋赞仍然非常欠缺,尽管收录一些,也难免不尽人意,不能说不是遗憾。另外资料在抄写、敲字、扫描、录入电子版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诸多差错、纰漏。敬请诸位有识之士、同仁及爱好、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们多提宝贵意见。
后记部分
编纂这部《书串汇编》是很久的心愿。只所以久久没有成书,是因为一直很纠结,很矛盾。整理成书有多大的价值,能派上什么用场?在这个效益至上的金钱时代,究竟值不值得为此付出这么多的心血,花这样的代价,能产生什么效益?
曾几何时,曲艺行业,具体到河洛大鼓行当,早已风光不再,一直在走下坡路,已到了频危的边沿。河洛大鼓再没有原来在一个村子就能唱上几个月的辉煌,仅剩下政府偶尔象征性的举办些公益活动外,剩下的就是隔三差五的,断断续续的三两场还愿书来支撑这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残局。河洛大鼓原本是以长篇大书为主的,但现在说唱长篇大书越来越没有机会和市场了。长篇大书没法生存,主要用于长篇大书的赋赞、书串儿还有何用?正如河洛大鼓艺人高红军老师所言,以前学会赋赞,都“卖”出去了,现在学会也“卖”不出去了。正因为此,所以迟迟不想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现在书稿草就,就想与各位同仁、朋友汇报、分享一些成书的曲折历程,以期倾诉其中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吧。
三十多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步入河洛大鼓之门,初次涉足长篇大书。当时我的从艺老师郭汉有一本用32开本的塑料日记本抄写本《花草集》(当时没有见到原印刷本),上面有许多说大书用的赋赞、条子(当时老师是这样说的:说段子书不能用赋赞、条子的,只有说大书才能用),如获至宝,用记工用的工帐本抄写下来,熟练地背会了大部分赋赞。赋赞背会得差不多了,抄写的本子也不记得丢到哪里去了。
以后在河洛大鼓艺人王管子老师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李进银处见到了《花草集》的正式印刷本,32开本,很薄,大概一百页多些。就又用塑料皮日记本重新抄写,做为留存。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曲艺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不断有曲艺作家改编或创作的新编传统体裁或现代体裁的长篇大书问世,如蒋敬生的《海青天》、《南包公》,郑永昌的《黑虎闹东京》、《秦琼打擂》、《双枪将下山》,王润生的《呼延庆打擂、上坟、挂帅》系列,李全林的《太原府》,李书春的《劫囚车》等。还有非鼓书体裁的如评书的《杨家将》、《封神演义》、《薜刚反唐》等,评弹的《西厢记》、《九龙口》等,西河大鼓的《小将呼延庆》等。这些曲艺大书作品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争艳斗奇。这些曲艺大书里有大量的赋赞经作家的加工润色,更加精辟、经典,给大书的演唱增加了丰富的营养。出于行业需要和爱好,每遇此类曲艺书籍,必想方设法搜集,珍藏。许多精彩的赋赞被背会,消化,吸收。把一些认为比较好的赋赞抄录在《花草集》的后面,做为《花草集》的后续和补充,后来一本记满了,就有了第二本,第三本。我把这抄录赋赞的三本日记本命名为《艺海拾贝》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再后来,伴随着曲艺行业的逐渐衰退,曲艺方面的大书淡出了市场,曲艺行业难以为继,也就没有再后续第四本,第五本了。
上面所说的十几部大书购买收藏不易,非常珍惜。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正紧,抄家,拉家具,抢粮食,人人自危。躲计划生育时,把这些书籍装进一个袋子,藏在草窑里,埋在草堆里,试图躲过一劫。但仍被计生办的人翻出来了,这些被视做比家俱、粮食还重要的“资产”仍难逃厄运,洗劫一空,再没有追回。
遗憾的是,这三本被视为命根子一样珍贵的手抄本《艺海拾贝》,在1999年移民搬迁时失落了第三本,感觉非常可惜,但无可奈何。随着弃行河洛大鼓,仅剩余的两本也被束之高阁,与冷落、寂寞为伴了。
2006年,我的同行——孟津县的河洛大鼓艺人杜子京的委托我,希望将他手中珍藏的一本手抄本《花草集》通过电脑打印出来,以得到更多的保存和传阅。既是同行,又是朋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提供的这个手抄本《花草集》虽然抄写得也非常认真,但错误之处仍然不少,漏洞较多,前半部分每个“条子”都标明了出处,如“某某某口述”之类的,后半部分却略去了,造成不完整之憾。敲入电脑时,我参考自己的手抄本做比对,取长补短。除个别地方因转抄之故明显的错误予以纠正外,基本尊重原著,保持原貌,不做任何的更改和增删,包括原书的前言部分(写在前边)也完整保留,后面加了我增写的后记(写在后边的话),与前言遥相呼应。
原《花草集》前言部分内容如下:
写在前面
曲艺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绚丽多姿,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其广泛流行,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广大曲艺艺人和曲艺工作者创造、总结、积累了大量的演唱程式。这处程式形象生动,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娓娓动听,是非常宝贵的艺术珍品。
近十余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致使整个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曲艺事业倍受摧残。如今,十恶不赦的林彪、“四人帮”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双百”方针重返艺坛,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春天已经到来。为了继承并发扬曲艺程式的优良传统,给青年曲艺艺人和青年曲艺工作者提供一些学习、借鉴、参考的资料,我们组织了以邢相云、马现瑞、梅春海、常秀君、叶正品、张鑫风、邵玉玲、王玉兰、李彩云老艺人和曲艺工作者共同编写了这本传统曲艺小资料——《花草集》,值此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之际呈献于大家面前。
鉴于时间仓促,编者缺乏经验,水平低劣,谬误之处定将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我补加的后记内容如下:
写在后面的话
近年来,河南省四大曲种之一——独具洛阳地方特色的民间曲艺河洛大鼓艺术,几乎面临失传的绝境。许多珍贵的曲艺资料不断的流失,依本人拙见,将是河洛文化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对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挽留,受我的同行——孟津县的河洛大鼓艺人杜子京的委托,将他手中珍藏的一本手抄本《花草集》通过电脑打印出来,以得到更多的保存和传阅,也算是作为一个河洛大鼓艺人尽了一份自己的职责,为传承和保护民间曲艺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若能为读者所理解,也算心安理得了。
原手抄本《花草集》虽然抄写得非常认真,但错误之处仍然不少,漏洞较多,前半部分每个“条子”都标明了出处,后半部分却略去了,造成不完整之憾。在打印时,我参考其它本子做了一定的校正,但仍然不太理想,又没有其它资料可参考,就只好如此了。如果以后能找到原书,一定要重新校正。
搁下笔来,松了一小口气,总算是了却了一点小小的心愿,但我知道还远远不够,挽救河洛大鼓艺术,任重而道远!盼望着振兴河洛大鼓艺术那一天。
吕武成
2006年11月2日星期四完成于孟州寺上
这个《花草集》的电子版完成后打印了两份,一份送于杜志京,一份自己留存。说是留存,不如说是尘封。因为后来的空闲时间里一直忙于河洛大鼓网站的制作、维护和运营,河洛大鼓资料的挖掘、搜集和整理,编辑出版《河洛大鼓》、《河洛大鼓志》,这个打印出来的《花草集》也一直没功夫,没兴趣,也懒得去翻看一眼了。
前些日子,我的《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破镜记》出版之际,同行艺人,嵩县的高红军老师鼓励我把《花草集》整理重新出版。他认为虽然这些赋赞眼下没用武之地,但整理出版是对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瑰宝的一种挽留。至少可做纪念,可留给后人来延续。高老师还有其它同行艺人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在大家热情的 鼓动下,重新把压在书柜底下的《花草集》和载着《艺海拾贝》的日记本翻了出来。
原《花草集》内容太单薄,如果照搬原著成书,一是有盗版、侵权之嫌,意义不大,二是内容不丰富,远不能包括长篇大书赋赞的方方面面。在大家的建议下,计划在《花草集》的基础上,把《艺海拾贝》中的内容补充、添加进去。二者合二为一,这样内容就丰富、充实了许多。于是就戴上老花镜,把《艺海拾贝》手抄本中的文字一个一个地敲入电脑,融入了《花草集》中。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时想起了丢失的第三本《艺海拾贝》来,不禁顿足叹惜。因为第三本上摘录的抗日体裁的《双枪将下山》,海关体裁的《九龙口》中的赋赞都是现代的,而原《花草集》和《艺海拾贝》前两本都是传统大书的赋赞,而现代赋赞是空白。没有现代赋赞,这本书就不完美,是残缺不全的。怎么补上去呢?只有找到原书,重新摘录。但时过境迁,到哪里去找原书呢?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搜了下,感谢万能的网络,感谢孔夫子旧书网!竟然搜到了《双枪将下山》和《九龙口》!惊喜之余,立马拍下。既如此,何不再搜搜我曾经拥有,又而失去了那些大书?竟也找到了!经过比价,下单,邮寄,焦虑的等待,这十几部大书陆续到手。看着淘来的这一堆破烂,既熟悉,又陌生,有一种久违的,失而复得的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终天把所有大书中认为有价值的赋赞全部录入电脑,经过重新归类、排列组合,总算大功告成。怎样给这部书命名?颇费斟酌。原打算命名为《花草集续编》或《花草集增补》。由于增加的内容远远多于原作数倍,且与原作内容打乱重新归类,续编或增补都感觉不妥。又想用手抄本的《艺海拾贝》来命名,但一查,已经被作家秦牧,曲艺作家张守振捷足先登了。又想命名《曲艺赋赞选荟》或《曲艺赋赞汇编》之类的。网上查了查,有好几部已经出版的赋赞的书,如《说书赋赞选》、《评书赋赞赏析》、《河南曲艺赋赞》等,不想再走别人走过的路了。本书内容包括赋赞,但有的内容归属到赋赞有些牵强。如第十三章“片段”之类的,不能称其为赋赞。只能是书串儿,或条子。所以经深思熟虑,暂定为《书串汇编》。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除前言和后记外,绝大部分内容不是个人原创,或摘自长篇大书,或艺人口述,或来源于网络。为尊重原作,保持原生态,除查错和补漏外,极少改动。很多作品年代比较久远,岁月沧桑,物是人非,没有机会当面致谢。仅在此表示真诚的歉意和发自肺腑的感激!
即将付印,啰嗦了这么多,权做后记。
吕武成
2019年8月13日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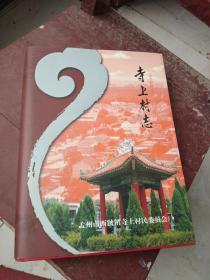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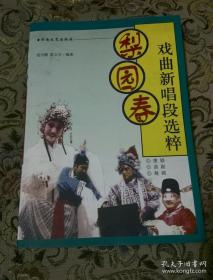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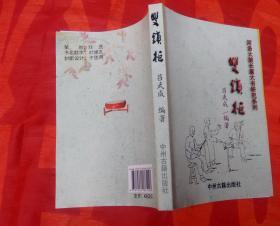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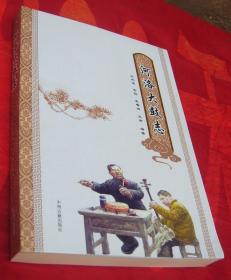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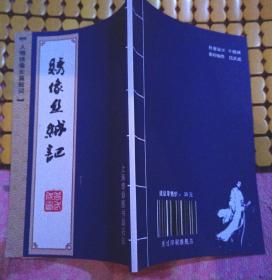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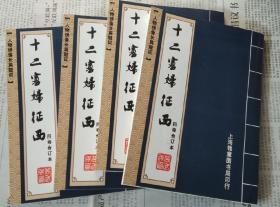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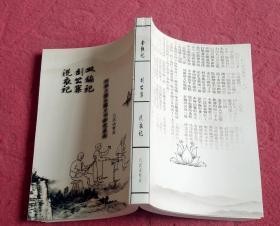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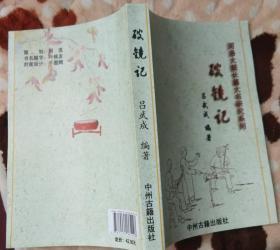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