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现货!《忧郁的解剖》(增译本)唯一中译本,增订再版,比原版增加十余万字。
兰姆、博尔赫斯、钱钟书、梁实秋等推崇之作。
¥ 40 6.7折 ¥ 59.8 全新
仅1件
作者罗伯特•伯顿著;冯环译注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ISBN9787515516882
出版时间2018-08
版次1
印刷时间2018-08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纯质纸
页数376页
字数300千字
定价59.8元
货号HB-0026
上书时间2024-03-1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是一个学问渊博而性情古怪的人。他于1593年进入牛津,至1602年方得到学位,历时9年,因为自从他进入学校到1599年一直重病缠身,深深体会了忧郁的滋味。他终身留在牛津大学,做导师、做图书馆管理,他一生埋首在图书里。他从不旅行,从未结婚,只是博览群籍乐此不疲,以至于死。他死于1640年1月25日,正好和他根据星象学推算出的死期非常接近,有人说他是自杀而死以证明其预言之不虚。
内容简介:
《忧郁的解剖》一书部头大、范围广,可谓搜罗古今、穷极八荒,潜于过往、浸入未来,并以嘲讽之态扫视当下。伯顿坦言他写《忧郁的解剖》是为了排遣自身的忧郁。我们虽无法确知伯顿关于忧郁的成因、治疗的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否灵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百多年来他的作品已然成了忧郁的“预防剂”。
目录:
1932 年版导言 001
第一部分 德谟克利特二世致读者 001
第二部分 忧郁的成因与症状 057
一、何谓忧郁 058
二、忧郁的成因 061
1. 过度锻炼,孤独、懒散 061
2. 谈幻想之力 068
3. 悲伤 074
4. 恐惧 078
5. 羞愧与耻辱 080
6. 好胜、仇恨、敌对、报复 082
7. 愤怒 086
8. 不满、忧虑、苦恼 092
9. 迷恋狩猎、娱乐无度 102
10. 自恋、自负、爱虚名、好吹捧 107
三、好学或过度研习,附论学者之苦 117
四、忧郁的偶然成因 131
1. 乳母 131
2. 教育 133
3. 恐惧与惊吓 136
4. 讥讽、诽谤、挖苦 140
5. 自由之失、奴役、监禁 145
6. 穷困与贫乏 148
7. 其他导致忧郁的偶然成因,如友人之死、财物之失 159
五、 忧郁之症状 178
1. 身体中的忧郁之症状 178
2. 大脑中的忧郁之症状 181
第三部分 忧郁之疗法 197
一、闲话空气 198
二、锻炼 207
三、对治各种不满之良方 229
1. 身体的缺陷、疾病、出身卑微 234
2. 贫穷与困窘 243
3. 奴役、自由之失、监禁、放逐 250
4. 嫌弃、辱骂、中伤、蔑视、羞辱、谩骂、诽谤、嘲笑等等 253
四、对治忧郁本身 263
第四部分 爱之忧郁 265
一、前言 266
二、爱的定义及爱之忧郁的成因 277
三、爱之忧郁的症状 295
《忧郁的解剖》原著目录 317
中译名索引 323
增译本后记 345
内容选读:
1932 年版 导言
一部论述忧郁症的专著,竟成了英文作品里的一大消遣读物,这真是出人意料。然而此一反讽却得自于机缘巧合。因为即便写《忧郁的解剖》的人不完全属于马可• 塔普雷一脉,他也称不上是忧郁症患者,亦未有过编写一部感伤之作的念头。罗伯特• 伯顿可谓乐观的悲观者,若非他亲口道来,我们怎也不会猜到他竟忧郁成性。忧郁,之于他是大不幸,之于我们却是万幸——须知此乃促成他写下这部闲书的首要原因。而倘要一证伯顿那骨子里的好性情,我们就得援引肯内特主教所讲的故事了。据其言,伯顿在不堪忧郁之重负的时候,便会离开他在牛津基督堂的书房,漫步至佛里桥,去听船夫们卖劲儿地打嘴仗,好借此来给自己找点乐子。不过,伯顿又坦言他写《忧郁的解剖》是为了排遣自身的忧郁。我们虽无法确知这法子是否灵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百多年来他的作品已然成了忧郁的“预防剂”。他那虽怒气冲冲却又悲悯仁慈的灵魂依旧在其大作的后续版本中行进着,为无缘受惠于其生前风采的后代开辟了一条条快乐的新路径。
有关伯顿生平的细节是极少的,然而,过多的细节也无甚必要。不是有“书如其人,人如其书”的说法吗?罗伯特• 伯顿就是这样的作者,《忧郁的解剖》也正是这样的书A。伯顿仅有的生平资料如下:1577 年2 月8 日,生于莱斯特郡林德利府,在全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先是就读于萨顿科尔德菲尔德的私立学校,而后转入纳尼顿文法学校;1593 年进铜鼻学院,1599 年又进基督堂学院,1614 年获神学士,两年后任牛津圣托玛斯教堂牧师;1630 年受恩主伯克利爵士乔治之助,得享莱斯特郡西格雷夫教区圣职。他擅作拉丁文和英文诗,参写过数部学术选集,并在31 岁那年,还创作了名为《冒牌哲学家》的拉丁韵文讽刺喜剧。这是他流传下来的第一部作品,于1615 年经他改写一遍,并于1617 年在基督堂由学生搬上舞台。《忧郁的解剖》(以下简称《解剖》)则出版于1621 年,在作者生前共刊行过五版。伯顿亲见印行的最后一版是1638 年那版,也就是在这之后的一年,他去世了,享年63 岁,被葬在了大学的主教堂里。其兄威廉,即《莱斯特郡纪》(1622 年)的作者,在此为他立了座半身纪念像,并涂以颜色使之栩栩如生,这遵循的是当时的旧俗。
伯顿一生无甚波澜。“在大学里,”他说,“我过着一种安谧沉寂、一成不变、退隐遁世的生活,独自一人仅有诸位缪斯做伴,其时日之长久恐与雅典的色诺克拉底相差无几,竟至垂垂老矣。如他那样为了求知求识,我亦是夜以继日地枯坐在我的书斋里面。”这话我们信,因为职务可托人代理,也可撇下不管,无论怎样他都匀得出时间来——尽管他身为牧师,而且有几年还供职数地,担任了不少职务。然而,若因此就断定创作《解剖》这类庞杂的大作必然会成了其全部的事业,则又属推演过当。须知勤奋加上以苦为乐是足以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暇中创造出奇迹的。伯顿说来虽已离群索居了,但也绝不是什么隐士。除了担任教堂神职外,他还做了些别的工作,比如自己学院的图书馆长、牛津市场的检察官(至少供职了一年)。不过通体来看,伯顿本质上还是学者、书痴。他总是惬意地幽居在自家堆满书籍的屋里,或待在所谓“欧洲最辉煌的学院”那宏伟的图书馆(即博德利图书馆)中,研究忧郁的成因与疗法,力求不当“寄生虫”或“如此高贵的学术团体中无用又不相称的一员”,亦不写“任何有损于这般恢弘的皇家学院之荣誉的文字”。
通常而言,像伯顿这样的人往往会流于学究气。然实际上,伯顿写书的风格虽属学究式,其观点却远非如此,他的身上也鲜有学者的坏毛病。此外,他的牧师身份亦未见诸其文风,因为《解剖》一书实在不大像是牧师所写的:他连训诫也显得彬彬有礼,说话也说得活活泼泼,饶有趣味,尽管按托马斯•赫恩A的说法有那么几分“不谙世故”——不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我们却知之甚少。因为说来也怪,尽管伯顿当初在学院里无人不晓,其作品也颇受欢迎,可他竟落得跟莎士比亚一个下场——在当年的街谈巷议中几乎没有听人提到过。除了关于他任职情况的文档资料和零星散见于其书中的生平片段外,在与他同代的文献中还未曾出现任何涉及他的有用信息。而要待伯顿长眠五十余年后,才会有安东尼• 阿• 乌德B在《牛津名人传》中为其写下一篇性格特写。然而,乌德本身并没有见过伯顿,他只是同见过伯顿的人谈过话而已,所以这位牛津史家的文字也仅为老调重弹。其实,乌德所写的那些,我们只消看看伯顿自己书里相关的只言片语,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安东尼• 阿• 乌德写道:“他是个严谨的数学家、精准的算命师、博览群书的学者、研究古典的专家,且还对地理勘测颇为精通。有不少人将他称作了严肃的学人、噬书的饕餮,性情上忧郁而不失幽默;另有一些相熟的人还说他为人老实、坦诚又敦厚。我自己亦常常听一些基督堂的前辈说,有他在就会有乐子——他诙谐幽默,童心未泯。虽按当时学院里流行的做法,他也爱在寻常对话中夹带诗人的诗句或古典作家的话语,不过他于此的敏捷和机巧却是无人能及的,这也就使得他越发地受人喜爱了。”
至于伯顿的样貌,我们则能据其肖像推知。他的肖像共有三种,即藏于铜鼻学院里的油画,《解剖》一书卷首由拉• 伯隆刻制的雕版小画像,以及牛津主教堂中的彩绘半身像。借此我们便可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来——我们这位英国的德谟克利特正置身于书本堆中,其所在之地恰是彼时那座著名的、业已显赫的学院。他身形壮实,且略有点发胖,深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是规整,大大的眼睛里还闪着一缕讥讽的光,而硕大的额头则显出了睿智和好记性。他的鼻子神采奕奕,那嘴就如同所有见识不凡的人一样,也是又利又尖(但还好下嘴唇是较为宽厚的)。这看起来是一张才华横溢、若有所思、怡然自得的脸,略微地带着点儿羞涩,仿佛是在暗示此人爱幽居胜过了冒险——当然,于群书中探胜又该另论。其实,这种面相在当时的英格兰可谓比比皆是,即便到了现在也仍未绝迹。而靠了上述拼合而成的形象,我们还可进一步做出如此的推断——伯顿其人虽亲切却孤僻,虽谦虚却固执,为人友善但不至热心过头,宽厚而又易怒,不笑人傻,只悲悯傻人。
至此,关于伯顿我们已谈了这么多,也细细地听了安东尼. 阿. 乌德的说法,但我们还远未触及伯顿的灵魂,亦未摸到伯顿之为伯顿的本质。这位解剖大师真是个矛盾体。他同其他怪人一样,也断不会始终如一。他宣讲中庸之道却不践行。他写书总是连篇累牍,笔下的每句话都词富义繁。他这书虽说是世上引语用得最多的,但读来却又如小说一般轻快。他往书里面塞的文字,也是至理名言与胡言乱语相杂糅。在书中,他总不忘抱歉自己啰里吧嗦,可刚道完歉转身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他生怕会把爱之忧郁讲过头,但之后他还真讲过了头。他没有结婚,然婚姻之于他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嘲笑世人,但同时也悲叹世人的不幸和愚蠢。他既信科学,也崇迷信。他有时粗言糙语就像个写淫书的,有时又扭扭捏捏,活脱脱一个假正经。他把插科打诨与神学宗教相提并论了起来。他虽不故作幽默,但却远要比专业的小丑还好笑。
他最郑重的时候显得最轻浮,而他随口说说的时候又最为意味深长。与惠特曼一样,他也是浩瀚无垠、包罗万象的。他把自己连同整个古代的学问都倾注进了他的书里,然后又巧妙地将这团大杂烩变成了一部条理分明的专著。这本大部头的书,读起来可能会把读者累到,但写起来他却是不厌其烦。
罗伯特•伯顿实乃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痴,他成天活在书堆里,嗜书如命,并且还用大半辈子写了本将古往今来的所有书籍都熔于一炉的精粹之作。这部论著出自嗜书者的手笔也属情理之中,它即便只是各类著作的集萃,然仍不失为一部原创作品。——诚然,《解剖》看上去颇似一册东鳞西爪的引语集,也的确大幅地征引了他人之观点和看法,但浮现于每页书上的并非被征引的人而是伯顿那个“劫掠者”,躲在每句引语后面不时窥探两眼的也唯有伯顿罢了。这个中的缘由显而易见,即伯顿堪称精通文字马赛克的艺术家,善于把从他人著作中扯下的碎屑纸片拼接成一幅个性鲜明的画作。所以书本也就成了他的原材料。其他的艺术家拿泥来塑像,取石头来做花样和造型,将文字、声韵或颜色调配和谐,而伯顿则是在用引语塑造“宇宙”。他劫掠古时的著作(大多早已湮没或毁损),并将搜刮到的东西都囊括到了自己的构架内,这就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取法古罗马遗迹,将个中所获运用到了文明新纪元的教堂和宫殿里。
对于该书的奇谲构架,伯顿会经常地为之而辩解不休,这让人感到颇有点多此一举。不过,他的辩解却既非源自假谦虚,亦非出于他的自卑。伯顿可是从来都不缺那份自负的。他深信自己能写完这部大作,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睿智。通常而言,肯去创作近五十万言大部头的作者,哪会不坚信其书是值得一写的呢?所以,伯顿的辩解也只是遵从旧俗罢了——17 世纪作品的正文前都得要有一篇作者的辩白。伯顿曾为他的主题辩解,为他呈现主题的方式辩解,甚至还为书名辩解。从这些辩解来看,伯顿的去写忧郁,实非仅仅如其在某处所坚称的,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忧郁。他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即忧郁诚为“一门必要、合宜的科目,且还不似神学那般司空见惯,争议纷纷——虽然我也承认神学是众学科之女王”。而该书的书名,如今看来则是再明晰不过的了,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援引先例,因为那时候解剖类的书和现今的各种文选一样也是随处可见的。至于书名的略微古怪,伯顿却放任之,因为“如今给待售的书籍加上个新异的书名已成了一种策略,正如云雀飞落捕鸟网,不少喜欢猎奇的读者也会受书名吸引而留步——好似痴愚的过客驻足凝视着画店里某幅哗众取宠之作,而那真正高明的画,他是连瞧也不会去瞧一眼的。”此外,伯顿也用相似的理由来辩解他为何主要用英文来写此书,他说“我本无意用英文写书来把自己的思想糟践”,但若用拉丁文来写呢,则在当时又没人肯承印。“我们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只对英文的论战小册子来者不拒,统统付梓,但凡是拉丁文的,他们便不肯接手。”我们还是不要跟着伯顿一道去痛斥那些贪财的出版商了,若是他们不以自身利益为计的话,我们哪能得见伯顿的英文大作,恐怕伯顿早就如许多饱学之士那样淹没于无闻了吧。
伯顿文风之独特多得自于其写法上引经据典之铺张。他实可谓此类技法的大师,他那引语的庞杂、奇崛和机巧总能令读者的心为之一振,眼为之一亮。所以在那个不乏精于此道者的时代里,伯顿才能够轻易地脱颖而出,达到在警句箴言之编排上无人能及的地步。而如果把这些独特、有趣的赘词冗言都统统剔除掉的话,或许伯顿的散文就要反倒流于直白和寡淡了。伯顿的文字,正是多亏了有一种轻快、如断奏般的风格,才能使得他那漫漫长卷总是流畅可读。我又常听人言伯顿为文古怪,然他距我们年代已远,觉其古怪也在所难免,故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伯顿虽则自觉地征引并创制了一组组的绝妙好辞,但他却并不仅仅着眼于文辞的创造。伯顿从不循文辞至上的做法,不似布朗和多恩那样会让人觉得他们在写就一句之后还要往后退几步欣赏一番。伯顿的文风太过口语化了,不适合那样去雕琢,其文读来真仿佛是闲谈一般。你能听得到他声音的抑扬顿挫,那声音好辩而又亲切,总在不厌其烦地给建议,作说明。——然即便是这样,他也总能以一个巧妙的转折或突如其来的翻转令你不致落入到单调乏味中,而就算这法子失了效,他还能拿出窖藏的奇闻异事,引人入胜地向你一一道来。
《解剖》一书部头大,范围广,可谓搜罗古今,穷极八荒,潜于过往,浸入未来,并以嘲讽之态扫视当下。尽管伯顿所选的主题乃忧郁,但他却靠了插话和题外话,近乎谈遍了人类的每一种趣味或活动。因此,这部著作实可算作对人类之生活与习好的一篇评述。而且,它还是横跨在中古思想与当代思想之间的桥梁—— 一方面唱响了专制的经院哲学的挽歌(全是格兰维尔A在其《教条之虚妄》里所谴责的),另一方面又预示了观测实验法的到来。在书的结构上,伯顿取的是当时传统的纲要构架。《解剖》一书共分三大“部”,往下又细分出许多的“章”“节”和“小节”,而书中大、小标题则以纲要形式分置于各部卷首。全书内容,除三大部和相应的章节外,还收录了伯顿自认的种种“离题话”——篇幅大多堪比论文,以及那“便于引入正题的讽刺性前言”——在对开本的定版中足足填满了78 页纸。
威廉• 奥斯勒爵士曾将《解剖》誉为“外行人写得最好的医学专著”。不过,书之主题虽属医学一类,但书里也有貌合神离,实可单独成篇的章节——其中有些甚至还具有开创性。例如,题为“闲话空气”的一章,娓娓不休,趣味盎然,乃第一篇谈论气候学的专文;而“宗教忧郁症”一节,则可说是对该题的首次探讨。伯顿对性心理学的研究实要早于霭理士,他对罗曼蒂克爱情的拒斥又要先于萧伯纳C。他的论“妒忌”数章涵盖了所有战后问题小说的要素,而藏在那篇有名的前言中的“乌托邦”则还能让人想到威尔斯。在书中,伯顿向我们展现出了多种面孔,他既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此外,他还是垄断的抵制者、战争的抗议者,而对于改善公路、拓展内陆航道、开垦沼泽地、兴建花园式村庄和发放养老金,他则予以了赞同。
《解剖》仿佛就是那种具有人性和人格的书,这类书似乎是生长发育而成的。像《解剖》这样能与作者如此显明而又如此精微地融为一体的书,真是世间少有。《解剖》就是伯顿,伯顿也就是《解剖》。读《解剖》即在读伯顿,所谓读伯顿便是与之相谈,他读来就像是小说中的主角一般。换句话说,伯顿是那类少有的作者,他们能将自己完全投射到作品中去,从而跟小说和剧作巨匠创造其故事和戏剧中人物一样,以相类的才能塑造出了自己的鲜明形象。伯顿与蒙田、皮普斯E、兰姆F相仿,已将自己小说化了,变得与真人相异,但却又更加有趣。
《解剖》一书于1621 年面世,那一年伯顿整45 岁。当时的版本采用的是小四开本,全书近900 页,已然部头过大。不过在接下来的17 年中,它的内容还将继续增加和受到修订。——于此期间,《解剖》共计再推出了四版,分别印行于1624 年、1628 年、1632 年和1638 年,各版均用的是小对开本。
然而,待到作者去世后,也就是在1639 至1640 年间,《解剖》一书的出版便始现颓势了。比如1651 年版,其印刷和纸张就皆堪称低劣——此版乃《解剖》在作者身后的第一次重印,收录了作者生前所作的修订,往后当再无修订一说。而在1660 年,《解剖》又有新版面世,但那质量却是更加地不堪。
经过诸多版本后,该书在17 世纪的最后一版,竟成了1676 年那册细长的对开本,原书的精彩和风貌早已荡然无存。此后的124 年间,《解剖》就再没有新版本问世了。若仅就出版于17 世纪的书而言,实在还未曾见到有哪一本能比此书更清楚地展现作者对印刷商所施加的个人影响。
相关推荐
-

【正版全新现货】巴黎的忧郁
全新北京
¥ 15.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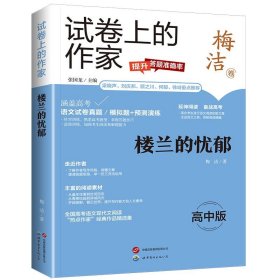
全新正版现货 楼兰的忧郁 9787523202388
全新北京
¥ 18.7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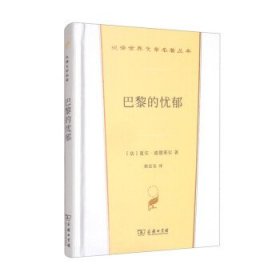
全新正版现货 巴黎的忧郁 9787100206648
全新北京
¥ 35.56
-

全新正版现货 忧郁的色彩 9787510459023
全新北京
¥ 17.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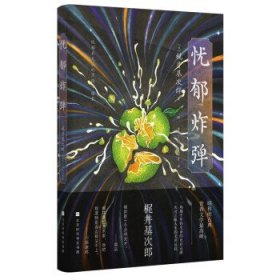
全新正版现货 忧郁炸弹 9787569944532
全新北京
¥ 21.15
-

全新正版现货 忧郁城 9787540489137
全新北京
¥ 26.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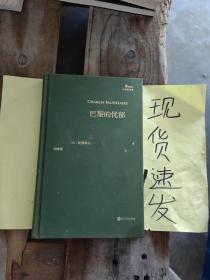
【现货】巴黎的忧郁
九品杭州
¥ 3.00
-

【现货】巴黎的忧郁
九品杭州
¥ 6.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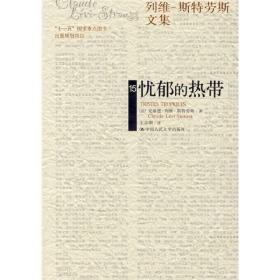
忧郁的热带(全新)
全新广州
¥ 57.00
-

忧郁的热带(全新)
全新北京
¥ 25.00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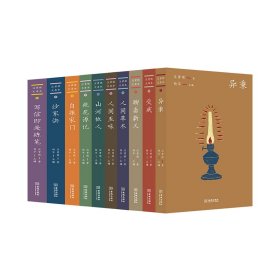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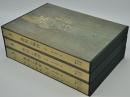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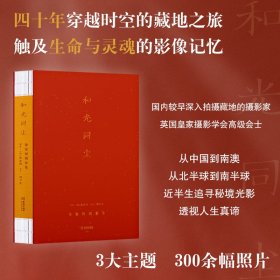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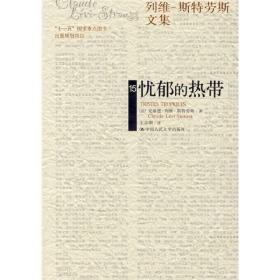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