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16开精装 全三十六册 原箱装)
¥ 22464 7.8折 ¥ 28800 全新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范铁权 主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9787501375219
出版时间2022-08
装帧精装
定价28800元
上书时间2024-06-2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8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16开精装 全三十六册 原箱装)
作者: 范铁权 主编
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 9787501375219
出版时间: 2022-08
定价¥28800.00
“科学救国”是近代以来的重大主题。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学”的大旗,各类科学团体相继产生。本书是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214)”阶段性成果之一。收录中国近代科学团体文献收录图书一百三十九种,期刊十六种。涉及中国科学社、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二十余团体的工作报告、机构概况、会务、会员名录、机关刊物、专刊等。资料以学科分类,图书在前,刊物在后,按时间顺序编排。这些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科学体制化形成过程、科学团体的组织体系建设、近代科学的职业化过程,深化近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均有所裨益。
近代以来,作为舶来品的“科学”(science)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构成巨大的冲击。随着各类“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科学”观念渐入人心,相应的新式科学团体也逐渐建立并得到发展。
科学团体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科学发展的积极推动者。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怀着不同的动机来到中国,创办了一些科学团体,如益智会、上海文理学会等。这些团体的主要宗旨,虽“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但它们发行报刊、翻译西方书籍、设立学校和图书馆,客观上为国人创建科学团体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受此影响,国人也开始自发创建科学团体。戊戌维新时期,先进士人意识到兴办学会、集合同人以研习各种学问的重要性,创办了一些科学团体,如算学社、化学公会等,在科学知识启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不断传播,国人对科学团体的认知不断加深,一些学术性强的专业学术团体涌现并得到发展。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科学学会性质的团体是一九〇九年由张相文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之后影响较大的有一九一〇年丁福保等发起组织的中西医学研究会、一九一二年詹天佑等在广州创建的中华工程师会等。
进入民国后,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已经基本定型,加之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归国,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团体的建立与发展。一九一四年夏,有感于中国科学意识的缺乏,留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了科学社,任鸿隽、秉志、赵元任等九人为发起人。随着毕业生的大举归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改名为中国科学社,规模不断壮大,各项事业的开展可谓如火如荼,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成就最为突出的群众性、综合性民间团体之一。一九一六年,留日学生社团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在日本东京创建,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之后,一大批专门性的科学团体陆续成立,如中国林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化工学会等。除了自然科学团体外,社会科学团体也相继创建起来,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会学社、中国经济学社、中国政治学会等。这些科学团体中,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门性的;既有民间自发形成的,也有官方支持组建的。他们大多保持纯粹的学术立场,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社团模式组建并展开活动。与西方科学团体相比,近代中国的科学团体无论是创建的社会环境、还是与政府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组织等,都有其自身的特征。
近代诞生的科学团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绩,是书写中国科学史、学术史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科学团体,大都以昌明学术、传播知识为宗旨,通过发行刊物、编着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科学演讲等多种途径宣传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致力于科学体制化的探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诸方面。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综合性团体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认可,一度代表民国政府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发挥了“领头羊”的角色。而很多专门性科学团体的兴起、发展,大都受综合性团体的影响和示范,成员间也互有交叉,有的专门性团体就是从综合性团体分化出来的,其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效法综合性团体。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呼吁“德先生”与“赛先生”,提倡民主与科学,矛头直指民初以来甚嚣尘上的复古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开宗明义:“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它族者,科学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在新文化运动那里,科学被冠以“赛先生”的称号,其地位一度上升到与民主(“德先生”)并立,并被无限扩展至价值观领域。一九二三年,胡适颇为形象地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着《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十页)对科学的尊崇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中国当时的诸多思想家、学者都参与其中,为之推波助澜,使之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为一股势力巨大的思潮。五四以来,正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和科学家们的呼吁促成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的尊崇。但科学家们尊崇科学并非停留在口号,而是身体力行,扎实开展科学研究,大力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兼顾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
科学团体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确有一些成功经验可寻,依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组织机构的民主色彩。科学团体大都仿效欧美学会组织,尝试引进民主选举、决策和监督机制,保证领导层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克服个人独裁专制的出现;其二,保持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性是科学发展的前提,是学会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著名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指出,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与法国科学院的发展代表着近代学会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是科学家的自主团体,自由决定活动内容,学术交流;后者则与此相反,因为一直受国家的资助,要承担行政与管理的使命,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组织,更像一个国家管理机构。近代中国诞生的科学团体大多是群众性社团组织,相对独立,避免了政府过多的控制;其三,社员的倾力参与。科学社团取得的成功是社员长期辛勤耕耘的结果,许多社员为学社的发展不遗余力。此外,科学团体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襄助,蔡元培、张謇等众多民国教育家、实业家为科学社团寄予厚望,提供赞助或其他支持。
当然,科学团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民国年间,时局动荡,科学团体在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磨难下,或发展迟滞,或不久销声匿迹,即使维持下来其发展亦举步维艰,往往是在挫折中求生存,因缺乏稳定的资金援助,经常处于徘徊不前的低迷状态。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三十五周年纪念时指出,“虽靠了社会人士的扶持策励与社中同仁的艰苦支持,得以维持不坠。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甚难以言语形容。揆厥原因,就是大家以为科学研究是少数人的兴趣事业。他们赞助科学,等于慈善布施,至多只能维持到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这样,欲求科学事业的继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科学社挫折中求生存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多数科学团体发展的共同经历,也是民国科学团体发展的缩影。
笔者介入科学团体的研究,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记得,起初导师建议我以留美生团体——中国科学社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多少有些迷茫,毕竟当时对科学团体非常陌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翻阅资料后,对科学团体在中国的发展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渐渐喜欢上了中国科学社,对发生在它身上的人和事充满了兴趣。为查阅资料,我曾往返天津、北京、保定等多地,摘抄资料的卡片积攒了两大箱。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对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科学团体及其骨干人物越来越关注,成果不断增加,这也从另一方面增强了自己持续开展科学团体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在研究中我注意到,在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科学团体还有许许多多,一些团体直至今日还依然活跃着。但许多科学团体并未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是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于无闻。于是,博士毕业后至今,我一直坚守着这个研究领域,奋力耕耘着,一转眼二十来年了。
近代中国活跃着大量的科学团体,留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却一直没能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整理,颇让人遗憾。以往有关科学团体史的资料,除《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以及中国科学社的相关部分档案资料得到整理外,其他大量资料依然散落在海内外,有的因年代久远正在破损,亟待得到保护利用。近几年来,“大成老旧刊全文资料库”“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资料库”收入部分科学团体的报刊资料,但仅是报刊中的一部分,仍有大量的资料依然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中,未得到系统整理、发掘。这与科学团体在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二〇一九年,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资料库建设”成功立项。课题组以搜集、整理资料作为课题前几年的核心任务。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制定了搜集资料的时间表,并在二〇二一年基本完成了资料索引目录。二〇二〇年以来,课题组成员先后参与编纂了《中国医界指南》(八册)、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刊《工程》(二十七册)、《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二十三册)等资料,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反响。
今年年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锦锦编辑联系到我,表示愿意和课题组一起精选一批科学团体资料出版,令我欣喜万分。如今,看到这么多散落在各个图书馆的科学团体资料汇编在一起出版,作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我的内心无比兴奋和自豪,也要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王锦锦编辑。我相信,这一资料汇编的出版,对于中国科学团体史的史料建设是一个有益尝试,对于中国近代科学团体史研究的推进必将产生积极影响。当然,中国近代科学团体资料极为丰富,此次编选的资料只是选择“典型性”的科学团体资料,可以说是一次抽样性的尝试。下一步,我们还将商定出版续编、三编,乃至多编,力求将更多的中国近代科学团体资料呈现给读者诸君。为此,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同仁能够与我们一道,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全,并进一步为推动中国科学团体史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奋力前行。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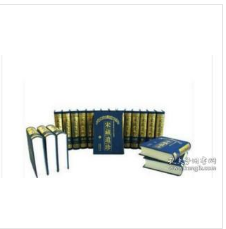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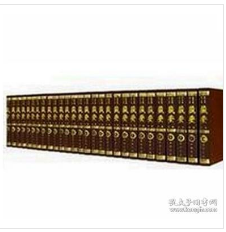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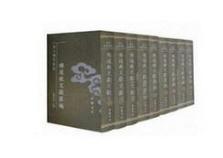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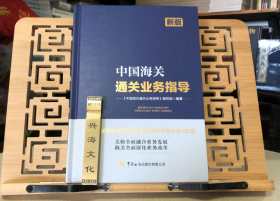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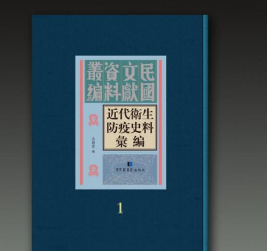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