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如德译文集(共15册)(精)9787532781249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1407.72 7.1折 ¥ 198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责编:冯涛//刘晨|译者:荣如德
出版社上海译文
ISBN9787532781249
出版时间2020-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1988元
货号30877630
上书时间2025-01-08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荣如德,上海文史馆官员,中国著名俄语、英语翻译家,主要翻译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狄更斯《雾都孤儿》、斯蒂文森《金银岛》、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萨克雷《名利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目录
\\\\\\\\\\\\\\\"【目录】:
《荣如德译文集》总目
第一卷
萨克雷《名利场》(上)
第二卷
萨克雷《名利场》(下)
第三卷
狄更斯《雾都孤儿》
奥威尔《动物农场》
第四卷
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坎特维尔的幽灵》《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斯蒂文森《金银岛》《化身博士》
切斯特顿《“十二真渔夫”》
西格尔《爱情故事》
第五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第六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
第七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
第八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普罗哈尔钦先生》《女房东》《涅朵琦卡》《小英雄》《庄园风波》
第九卷
西蒙诺夫《军人不是天生的》
第十卷
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
第十一卷
田德里亚科夫《死结》《路上的坑洼》《3、7、A》《审判》《六十支蜡烛》
第十二卷
阿塔洛夫《初恋》
李别进斯基 布洛克《党的儿子》
克诺莱《护士勒妮》
第十三卷
布尔加科夫《屠尔宾一家的日子》
奥青纳雪克《公民布里赫》
连奇《训斥》
第十四卷
斯捷尔马赫《真理与歪理》
雅科勃逊《生活在城堡里》
第十五卷
伊萨克扬等《希望的旗帜》
普列木·昌德《变心的人》
卡尔娜乌霍娃《好朋友的故事》
安东诺夫《绿山谷集体农庄》
罗森菲尔德《阿尔玛斯山谷探险记》
马夫尔《小游击队员》
马丽尔若娃等《魔针》
依腊谢克《不屈的好汉们》
\\\\\\\\\\\\\\\"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荣如德译文集》共十五卷,几乎囊括了荣如德先生一生翻译的所有译著作品,横跨俄语、英语两大世界文学大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奥威尔、王尔德等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家,同时还有苏联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涉及小说、戏剧、童话故事等多种体裁。
第一二卷:萨克雷《名利场》(上、下);第三卷:狄更斯《雾都孤儿》,奥威尔《动物农场》第四卷: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坎特维尔的幽灵》《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斯蒂文森《金银岛》《化身博士》,切斯特顿《“十二真渔夫”》,西格尔《爱情故事》;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六七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第八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普罗哈尔钦先生》《女房东》《涅朵琦卡》《小英雄》《庄园风波》;第九卷:西蒙诺夫《军人不是天生的》;第十卷: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十一卷:田德里亚科夫《死结》《路上的坑洼》《3、7、A》《审判》《六十支蜡烛》;第十二卷:阿塔洛夫《初恋》,李别进斯基、布洛克《党的儿子》,克诺莱《护士勒妮》:第十三卷布尔加科夫《屠尔宾一家的日子》,奥青纳雪克《公民布里赫》,连奇《训斥》;第十四卷:斯捷尔马赫《真理与歪理》,雅科勃逊《生活在城堡里》;第十五卷:伊萨克扬等《希望的旗帜》,普列木·昌德《变心的人》,卡尔娜乌霍娃《好朋友的故事》,安东诺夫《绿山谷集体农庄》,罗森菲尔德《阿尔玛斯山谷探险记》,马夫尔《小游击队员》,马丽尔若娃等《魔针》,依腊谢克《不屈的好汉们》。\\\\\\\\\\\\\\\"
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第二天,道连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因为怕死而时时刻刻感到芒刺在背,但对生命本身又漠然无动于衷。一种遭到尾随、追逐、行将落入陷阱的意识在他身上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只要挂毯被风稍一吹动,他就发抖。枯叶打在镶铅条的窗框上,也会使他联想起自己的种种打算已成画饼而懊丧万分。他一闭上眼睛,立刻看到蒙着雾气的玻璃窗外那个水手虎视眈眈的面孔,于是恐怖又一次攫住了他的心。
不过,也许仅仅是他的幻觉使复仇神的幽灵从黑夜中现身,使森严可怖的报应景象呈现在他的面前。现实生活是一片混乱,但想象的思路却有条不紊得可怕。正是想象驱使着悔恨在罪孽后面尾随不舍。正是想象使每一颗罪恶的种子结出了丑陋畸形的果实。现实世界里恶人并不遭恶报,好人也没有好报。成功的照例是强者,弱者总是倒霉,历来如此。何况,如果有陌生人在庄园宅子周遭徘徊不去,定会被用人或猎场看守发觉。花圃上如果发现足印,花匠也会来报告。可见,这纯粹是他的幻觉。西碧儿·韦恩的弟弟并没有回来索命。他随船出航,也许已经葬身冰冷的大海。无论怎样,詹姆士·韦恩对他并不构成威胁。那水手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不可能知道。青春的面具救了他的命。
虽然这仅仅是幻象,但良心竟会生发出如此恐怖的怪影,而且赋以清晰可见的形状,令其在你面前出没活动,想起来真叫人胆寒!倘若他的罪恶的魅影一天到晚从冷僻的角落里瞅着他,嘲笑他,在宴席上向他耳语,用冰凉的手指把他从睡梦中触醒,这样的日子叫他怎么过?随着这个念头潜入他的脑髓,恐惧使他的脸色愈变愈惨白,空气对他又骤然变冷了。天哪!他在陷入狂乱的时刻竟把自己的朋友杀了!一想起那幅景象,他就毛骨悚然!可怕的细节在想象中一一重演时更加触目惊心。他的罪行的幽灵阴惨惨、血淋淋地从漆黑的时间洞穴里冉冉升起。当亨利勋爵六点钟走进来的时候,他发现道连正哭得心都快碎了。
直到第三天,道连方始敢出门。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洋溢着松树清香的新鲜空气似乎使他恢复了兴致和生趣。然而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完全在于自然环境。过多的苦痛企图彻底摧垮他内心的安宁,结果他自己的天性起来反抗了。禀性敏感、气质高雅的人往往会这样。他们强烈的欲念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不是把人毁灭,就是本身死亡。渺小的忧伤和渺小的爱寿命很长。伟大的爱和伟大的忧伤却毁于自身的过于丰富强烈。此外,他已使自己确信:是疑心生了暗鬼。现在回顾几天来心惊胆战的情状,对自己既有些怜悯,也颇为鄙夷。
早餐已毕,道连同公爵夫人一起在花园里散了一小时步,然后他坐车穿过林苑去加入打猎的一伙。干脆的霜花像撒在草上的盐巴。天空犹如一杯倾覆的蓝色金属溶液。湖面平静如镜,芦苇丛生的岸边结着一层薄冰。
到了松林边缘,他看见公爵夫人的弟弟杰弗里·克罗斯登爵士正从猎枪里拔出两颗空弹壳。道连纵身下车,吩咐车夫把马牵回去,自己穿过枯蕨蔓草和乱丛窠子向这位客人走去。
“手气好吧,杰弗里?”他问道。
“不太理想,道连。看来鸟儿大多飞到旷野里去了。下午我们换一个地方,估计情况会好些。”道连在他旁边走着。空气中的芳香沁人心脾,棕色和红色的光斑在树林里时隐时现,助猎的人们不时发出嘶嘎的吆喝惊起鸟兽,接着就响起扳动枪栓的咔哒声;这一切吸引着道连,使他充满了愉快的自由感。他沉浸在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情绪中。
忽然,从他们前面大约二十码处一个留着残草的土墩子那边,窜出一只野兔。它支楞起尖端长着黑毛的耳朵,蹬着细长的后腿向一片赤杨丛中逃去。杰弗里爵士把枪托到肩上;但是,说也奇怪,那只野兔优美矫捷的动作竟使道连·葛雷为之心动。他急忙喊道:“别开枪,杰弗里。饶它一条命吧。”“你真傻,道连!”杰弗里爵士笑道。就在野兔刚刚溜进树丛的一刹那,他开了枪。紧接着,同时传来两声号叫:其一是野兔痛苦的哀号;其二是一个人临死前的惨叫。后者比前者更加惨不忍闻。
“天哪!一个助猎夫给我打中了!”杰弗里爵士惊呼起来,“这头蠢驴怎么会跑到枪口前面去的?喂,你们那儿别开枪!”他扯开嗓子大叫。“有人受伤啦!”猎场看守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闻声赶来。
“在哪儿,先生?他在哪儿?”他气急败坏地问。这时,整个一条线上的枪声都停了下来。
“在那边,”杰弗里爵士生气地回答说,自己急忙向树丛中跑,“你怎么不叫你手下的人离远些?把我今天打猎的兴致全败坏了。”道连看着他们拨开富有弹性的枝条钻进赤杨丛去。隔不多久,他们从那里出来,把一具尸体拖到阳光下。道连惊骇地掉过脸去。看来,他走到哪里,厄运就跟到哪里。他听杰弗里在问:那人是否确实死了。猎场看守作了肯定的回答。道连觉得树林一下子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面孔。他仿佛听见亿万人跺脚和嗡嗡地说话的声音。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古铜色胸脯的大山鸡,在头顶上的树枝间扑打着翅膀。
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内,心乱如麻的道连好像熬过了无数小时的苦痛,——他感到有一只手搁在他肩上。他吓了一跳,急忙回过头来。
“道连,”亨利勋爵说,“我看还是叫大家今天停止打猎吧。这样继续下去也怪没趣的。”“我愿意永远停止打猎,亨利,”他沉痛地回答,“这件事太糟了,也太惨了。那个人难道……”他无法把这句话完全说出口。
“是的,很遗憾,”亨利勋爵应道,“他的胸膛把整整一发枪弹的火药照单全收了,想来几乎是当场毙命的。走,我们回去吧。”他们朝着林阴道的方向并排而行,默默地走了有五十码左右。然后道连看看亨利勋爵,长叹一声,说:“这是一个凶兆,亨利,一个很坏的兆头。”“你说什么?”亨利勋爵问,“哦!你是指这件意外事故吗?老弟,这是没有办法的。是那个人自己不好。谁叫他跑到枪口前面去啦?何况,这也不关我们的事。当然,杰弗里非常懊恼。请助猎夫吃开花弹太不像话。人家还以为他是个乱开枪的射手。其实不然,杰弗里的枪法很准。可是说这话又有什么用呢?”道连摇摇头。“这是个凶兆,亨利。我觉得将有可怕的事情临到我们中某一个人头上。八成会临到我自己头上。”末了他添上这么一句,同时深感痛苦地抹了一下眼睛。
亨利勋爵笑了起来。“世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无聊,道连。这是不可宽恕的罪过。不过我们大概不会遭到这种厄运,除非那些家伙在吃晚饭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谈这件事。我得告诉他们不准涉及这个话题。至于兆头,那是根本没有的。命运女神从来不事先向我们报信。凭她的聪明和残忍都不会这样做。再说,你还怕什么事情会临到自己头上,道连?凡是一个人可能需要的一切,你都有了。没有人不乐于同你交换位置。”“没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不愿意同他交换,亨利。你不要笑,我说的是实话。刚才死去的那个不幸的乡下人比我现在的处境好得多。我对死亡本身并不恐惧。使我恐惧的是死神的即将来临。它好像已经在我周围铅一样沉重的空气里舞动巨大的翅膀。天哪!你看,那边的几棵树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人影在移动,在监视我,在等待着我?”亨利勋爵朝着道连戴手套的手瑟瑟发抖地所指的方向望去。“是的,”他微笑着说,“那是花匠在等你。他大概要向你请示,今晚餐桌上该插什么花。老弟,你的神经太脆弱了!回伦敦以后,你得找你的大夫看看去。”道连看见花匠走近来,才松下一口气。花匠举手触帽行了个礼,犹豫地向亨利勋爵看了一眼,然后掏出一封信交给他的东家。“公爵夫人叫我等候答复。”他嗫嚅着说。
道连把信放进衣袋。“告诉公爵夫人,说我就来。”他冷淡地说,花匠转身向宅院那边很快地走去。
“女人尽爱做危险的事!”亨利勋爵笑着,“这是她们身上最为我所赏识的一种品质。女人会跟任何人调情,只要旁人注意她们。”“你尽爱说危险的话,亨利!这一次你大错特错了。我非常喜欢公爵夫人,但是我并不爱她。”“公爵夫人非常爱你,但是并不怎么喜欢你,所以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不要无中生有,亨利,这里头没有任何制造丑闻的根据。”“制造丑闻无须深信不疑,反正有闻必丑。”亨利勋爵说着点了一支烟。
“你为了说一句俏皮话,不惜用任何人作牺牲。”“世人是自愿走向祭坛的。”这是亨利勋爵的回答。
“我真想能够爱上什么人!”道连·葛雷以凄怆的语调叹道,“可是看来我已经心如止水,万念俱灰。我的心思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我本人已经成了我的累赘。我想逃脱、避开、忘却。这次我到乡下来实在愚蠢。我打算给哈维打个电报去,叫他把游艇准备好。在游艇上才能摆脱威胁。”“你要摆脱什么威胁,道连?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我会帮助你的。”“我不能告诉你,亨利,”他忧郁地回答,“很可能这完全出于我的胡思乱想。这次不幸的意外把我闹得心里烦透了。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类似的事情将要临到我头上。”“简直是梦话!”“但愿如此,可是我确有这样的感觉。啊!公爵夫人来了,就像一位穿紧身长袍的狩猎女神。你瞧,我们不是回来了吗,公爵夫人?”“那件事我全都听说了,葛雷先生,”她说,“可怜的杰弗里懊丧得不得了。据说你还劝过他不要开枪打那只野兔。真是件怪事!”“是啊,真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话。大概是心血来潮吧。那只野兔确实是一只极可爱的小动物。但是,我很抱歉,他们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你。这件事惨极了。”“只不过是件不愉快的意外,”亨利勋爵插嘴说,“根本没有心理研究的价值。要是杰弗里故意干了那件事,他这个人倒有意思了!我很想结识一位真正的杀人者。”“亨利,你简直全无心肝,”公爵夫人大声说,“葛雷先生,你说是不是?亨利,葛雷先生又犯病了。他恐怕马上就要昏倒。”道连好不容易把身子站稳,强作笑容。“不要紧,公爵夫人,”他费力地说,“我的神经系统严重紊乱。别的没有什么。大概上午路走得太远了。刚才亨利说什么来着?我没听见。又是什么可恶的怪话,是不是?以后你再告诉我。很抱歉,我要去躺一会儿。失陪了。”他们走到花房通凉台的宽阔的台阶前。等道连进去把玻璃门带上,亨利勋爵转过脸来倦眼惺忪地望着公爵夫人,问道:“你真的爱上他了吗?”公爵夫人半晌没有作声,只是站着眺望风景。“我自己也想知道。”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
亨利勋爵摇摇头。“知道了就会味同嚼蜡。妙就妙在迷离恍惚。雾里看花分外有趣。”“雾里也会迷路的。”“条条道路都通往同一个终点,亲爱的格蕾狄丝。”“通往哪里?”“幻灭。”“我的生活正是从幻灭开始的。”她不胜感慨。
“你感到幻灭时已经戴上了爵冕。”“我对草莓叶公爵冠冕上的装饰。厌倦了。”“你戴着正相宜。”“那只是在人前。”“你少不了它。”亨利勋爵说。
“我不打算舍弃任何一片叶子。”“蒙茂斯是有耳朵的。”“上了年纪的人听觉不灵。”“他难道从来不吃醋?”“我真希望他能生一点醋意。”亨利勋爵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什么。
“你找什么?”公爵夫人问。
“你花剑上的小球击剑运动中戴面罩和在剑尖上套一小球都是安全措施。有一句成语thebottonscameoffthefoils(剑尖上的小球掉下来了)意即“把游戏当了真”。,”他回答说,“你把它掉了。”公爵夫人放声大笑。“我还戴着面罩呢。”“这会使你的眼睛格外动人。”亨利勋爵说。
她又笑了起来。她的皓齿像鲜红的果实中间的白籽。
道连·葛雷躺在楼上自己卧室里的沙发上,恐怖渗透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生命一下子变成他无法承受的负担。那个倒霉的助猎人像一只野兽在树丛中饮弹惨死一事,在道连看来预示着他自己的死亡。刚才亨利勋爵脱口而出的一句俏皮怪话差点儿使他晕厥。
五点钟,他打铃吩咐侍从整理行装,让马车八点半等在门口,准备赶夜班快车回伦敦去。他决意不在塞尔比庄园上再睡一夜。这个地方处处是凶兆。死神在光天化日下出没无常,林中草地已经染上斑斑血迹。
他给亨利勋爵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要回伦敦去就医,并要求亨利勋爵代他款待宾客。他正要把便笺装入信封,他的侍从敲门进来,说猎场看守求见。道连皱起眉头,咬住嘴唇。“叫他进来。”迟疑片刻后,他相当勉强地说。
猎场看守一进来,道连就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支票簿,把它翻开了放在自己面前。
“你来大概是为上午那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吧,桑顿?”他一面说,一面拿起笔来。
“是的,先生。”猎场看守回答。
“那个可怜的人有没有成家?有没有人靠他养活?”道连露出不耐烦的神色问,“如有的话,我愿赡养他们。你认为该付多少钱,我就拿出多少钱来。”“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先生。我冒昧求见正是为了这一点。”“不知道他是谁?”道连心不在焉地问,“你说什么?难道他不是你手下的人?”“不是,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他像是个水手,先生。”笔从道连手中跌落,他觉得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水手?”他失声惊呼,“你说他是个水手?”“是的,先生。看样子他当过水手,两条胳臂都刺着花。”“他身边有些什么东西?”道连上身前倾,瞪着猎场看守问,“从中能不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身上有一点钱,先生,可是不多。还有一支六响手枪。没有姓名标记。那个人长相还可以。就是眉目粗些。我们猜想他是个水手。”道连霍地立起身来。一个可怕的希望在心头闪起。他发疯似的抓住这点希望不放。“尸首现在什么地方?”他急忙问,“快!我得立刻去看一下。”“在家用农场的空马棚里,先生。大伙都不愿把死人搁在家里,那样总是会带来坏运气的。”“在家用农场里?你马上到那里去等我。你叫一个马夫把我的马带来。不,不必了。我自己去吧。这样快些。”没过一刻钟,道连·葛雷已经以最快的速度骑马奔驰在很长的林阴道上。树木像鬼怪列队从他旁边刷刷地飞掠过去,在他经过的路上投下骇人的魅影。有一次,道连的坐骑看到一根白漆门柱,突然向那里一拐,险些把他摔下马背。道连在马脖子上抽了一鞭。那匹马像一支箭划破飞扬的尘土向前直奔。石子从马蹄下被踢起来纷纷溅开。
他终于赶到农场。两个雇工在院子里闲荡。道连翻身下了马鞍,把缰绳扔给其中一个雇工。在最远的一座马棚里有灯光露出来。他下意识地感到尸体就在那边,便三脚两步跑到门前,准备拔闩开门。
这时他立停片刻,觉得自己正站在打开闷葫芦的门坎上:他的余生究竟可以优哉游哉呢,还是永沉苦海,立即就要见分晓。于是他猝然把门打开,走进马棚。
在马棚深处角落里的一堆麻袋布上,停着一具穿粗布衬衫和蓝裤子的男尸。一方血迹斑斑的手帕覆盖着他的面孔。插在瓶子里的一支劣质蜡烛,在它身旁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
道连打了个寒战。他感到自己没有勇气伸手揭去那方手帕,只得叫一个雇工进来。
“把脸上那东西拿掉。我要看一看。”他说时扶住门柱支撑自己的身子。
雇工照他的吩咐做了。道连跨前几步,一声惊喜的叫喊从他口中迸发出来。在树丛中饮弹身亡的那个人正是詹姆士·韦恩。
道连站在那里,对尸体看了好几分钟。在回家的路上,他两眼噙满了泪水。他知道自己的安全已不再受到威胁。第十九章“你何必向我宣布要重新做人呢?”亨利勋爵大声说,他的白净的手指正浸在一只盛玫瑰香露的紫铜钵子里。“你本来就十全十美。还是不要变吧。”道连·葛雷摇摇头。“不,亨利,我一生作的孽太多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我昨天已开始做了些好事。”“你昨天在什么地方?”“在乡下,亨利。我一个人借宿在小客栈里。”“我的老弟,”亨利勋爵面带笑容说,“在乡下任何人都可以做好人。那里没有诱惑。这就是远离都市的人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原因。文明决不是唾手可得的。只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文明:一条是修身养性;另一条是腐化堕落。这两种机会乡下人一种都没有,因此他们停滞不前。”“修身和腐化,”道连像回声般沉吟道,“我都体验过。现在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两者怎能并行不悖。由于我有了新的理想,亨利,我决定重新做人。我觉得自己已经换了一个人。”“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你好像说做了不止一桩?”亨利勋爵一面说,一面把去籽的草莓倒在自己盘子里堆成一座鲜红的小金字塔,再用有孔的贝壳形匙子把白糖撒在草莓上。
“我可以告诉你,亨利。这不是一个我可以随便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我放过了一个叫海蒂的少女。这话听来有些浮夸,不过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她长得极美,同西碧儿·韦恩像得出奇。这大概是我被她吸引的首要原因。你还记得西碧儿吗?那是多么遥远的往事啊!当然,海蒂不是你我这个阶级的人,她不过是个乡下姑娘。但是我真心爱她。我确信这是爱情。在今年整个美妙的五月里,我一星期要去看她两三回。昨天她在一座小果园里和我相会。苹果花不断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笑得挺欢。我们本来打算今天黎明时分一起私奔。但我突然决定让这朵花保持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原样。”“道连,我想这种新奇的感觉一定使你得到某种真正快意的刺激,”亨利勋爵把他的话打断,“但是我可以代你叙述你们这首田园诗的结尾。你给了她忠告,也撕碎了她的心。这就是你脱胎换骨的起点。”“亨利,你真可恶!你不应该说这样刻薄的话。海蒂的心没有碎。当然,她哭了,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她的名节保全了。她可以像珀狄塔一样生活在薄荷飘香、金盏花开的乐园里。”“并且为负心的弗罗利泽弗罗利泽和珀狄塔是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一对情侣。流泪。”亨利勋爵接口说着仰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亲爱的道连,你哪来这许多孩子气的傻念头?难道你以为那个姑娘今后会看得上哪一个跟她出身差不多的人?将来她多半会嫁给一个赶大车的粗汉或傻乎乎的农夫。既然她遇见过你,跟你相爱过,今后她必定瞧不起她的丈夫,觉得自己命苦。从道德观点看,我不敢恭维你这种急流勇退的壮举。即使作为一个起点,也不值得鼓励。何况,目下海蒂也许像奥菲莉娅那样,周身围着睡莲,正漂浮在某一座磨坊池塘映着星光的水面上呢?”“我受不了,亨利。你总是把任何事情变成嘲笑的资料,然后又凭空描绘最悲惨的情景。我后悔告诉了你。不管你对我说什么,反正我知道自己做得对。可怜的海蒂!今天早晨我骑马经过那个农家时,看见她雪白的脸蛋像一枝茉莉花紧贴在窗上。这件事再也别提了,你也不必说服我相信:多少年来我做的第一桩好事,我有生以来作出的第一次自我牺牲,实际上又迹近罪恶。我要革面洗心。我正打算革面洗心。谈谈你自己的事情吧。近来伦敦有些什么新闻?我好多天没上俱乐部了。”“人们还在谈可怜的贝泽尔失踪这件事。”“我还以为这一阵子人们已经谈腻了呢。”道连说着给自己倒了点葡萄酒,同时略微皱起眉头。
“老弟,这件事才谈了六个星期,而英国人至少要三个月才换话题,否则他们的头脑适应不了。不过近来新闻层出不穷,够他们谈的。其中包括我的离婚和艾伦·坎贝尔的自杀,现在又是一个画家神秘地失踪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是一条很短的街名,1890年前为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现已迁往泰晤士河畔的新苏格兰场)。但一百多年来,“苏格兰场”一直是伦敦警方、尤其是伦敦警察厅刑侦处的代名词。坚持说,十一月九号坐午夜一班火车前往巴黎的那个穿灰大衣的人就是可怜的贝泽尔;可是法国警方声称,贝泽尔根本没有到达巴黎。没准儿两星期以后我们会听说:有人看见他在旧金山。说也奇怪,谁要是失踪了,总会有人在旧金山看见他。那一定是个挺可爱的城市,想必具备身后世界的一切妙处。”“依你看,贝泽尔出了什么事?”道连问,他举起一杯红葡萄酒放在灯光下细看,对于自己竟能如此从容自若地议论这件事,心里也很纳罕。
“我一点也想象不出。倘若贝泽尔愿意躲起来,这不关我的事。倘若他死了,我不愿想起他。唯一使我心惊肉跳的就是死亡。我恨死亡。”“为什么?”道连有气无力地问。
“因为,”亨利勋爵说时把一只嗅盐盒的镀金箅子放到鼻子底下闻了一下,“如今的人什么都熬得过,唯独这一桩例外。死亡和庸俗是十九世纪至今得不到圆满解释的现象。我们到琴室里去喝咖啡,道连。你得给我弹肖邦的作品给我听。跟我妻子一起私奔的那个人弹肖邦的作品非常出色。可怜的维多利亚!我倒是挺喜欢她。她走后家里怪冷清的。家庭生活固然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坏习惯,但即使坏习惯也舍不得丢掉。也许恰恰是坏习惯最叫人难以割舍,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道连没有说什么,只是从桌旁站起来,走到隔壁的琴室里,在钢琴前坐下,手指按在黑白分明的象牙琴键上弹了起来。咖啡端上来后,他停止了弹奏,望着亨利勋爵,问道:“亨利,你是否想到过贝泽尔可能被人谋杀?”亨利勋爵打了一个呵欠。“贝泽尔人缘挺好,又老是带着一块不值钱的表。为什么人家要杀害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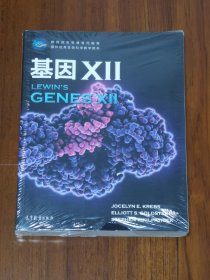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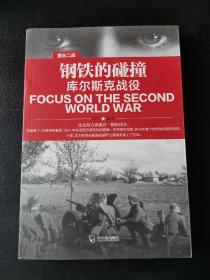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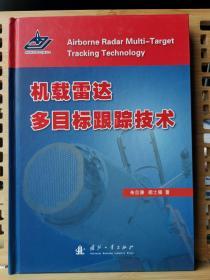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