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人的事9787549639786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0.52 3.0折 ¥ 69 全新
仅1件
作者梅根?斯塔克|译者:詹涓
出版社文汇
ISBN9787549639786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1827383
上书时间2024-12-2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梅根·斯塔克(MeganK.Stack)
美国作家、记者。曾任职于《洛杉矶时报》,先后担任耶路撒冷、开罗、莫斯科、北京等地驻外记者,并任莫斯科分社社长。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曾获美国海外俱乐部哈尔·博伊尔奖,并入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2010年出版非虚构长篇《这个村里每个男人都是骗子》(EveryManinThisVillageisaLiar),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目录作者手记
序幕
第一部分 如何消失
第二部分 去印度
第三部分 女人们
中文版后记
致谢
内容摘要·当战地记者成为母亲,家是新的战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私人战事,也是所有女性面对的现实
·辛辣吐槽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公,细腻坦陈生育带来的身心洗刷,一部在尿布和失眠中寻回自我的回忆录
在你们家,谁做饭,谁照顾孩子,谁刷马桶?
你如何走向外面的世界?如果你在外工作,谁在家里呢?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女性,总会有那么一刻,你仍然只是一个女人。
女性的日常生活被怀孕、流产、婚礼、家庭暴力、葬礼、生病的孩子和学费打碎。我的,你的,全世界女人的那些事情。
家务就是一切。这种无处不在的生理需求,一直阻碍着女性的发展,让女性保持缄默。
这个故事关于每个在为人母后依然想要自食其力的女人。同样的故事在全世界重复发生。
我听得到你。我看得到你。我理解你。
精彩内容我在中国和印度生了两个孩子。他们是移民的后代,一出生就是侨民——在亚洲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他们成为在亚洲大城市长大的美国人。在海外生孩子并非我的本意,事情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在能怀孕的时候怀了孕,在当时所在的国家生了孩子。我是记者兼作家。我不想为了生儿育女放弃工作,而我也确实没有这么做。生了老大以后,我已经写了两本书。这是其中一本。
我想继续工作,同时也想要孩子。在没生育之前,这似乎是件很简单的事。
但后来孩子们出生了。我的丈夫来了又去,忙着工作,他走着我曾经走过的路,走着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穿越国家,走遍世界,带回我从未踏过的道路上的细沙,我能从他的皮肤里嗅见一缕香料、一抹细烟的遗味。而我呢,留在家里陪着孩子,继续写作,一些女人帮我照看孩子、打扫房间,这样我才能继续写作。这些女人和我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是贫穷的女性,棕色皮肤的女性,进城务工的女性。起初,我把她们塞到脑海边缘。她们对我很重要,主要因为她们能让我自由。我希望她们开心,但不想知道任何细节。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些女性来来去去,有时在这儿,有时在那儿。不变的是,我们都滞留在家庭里。对于这种安排的功能性目的,我再清楚不过,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有意义。
我发现我们家的混乱和琐碎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在任何媒介上。人们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方式描述家政工人:她们是毫无内疚感的家庭所做的必要性财务投资;她们既精力旺盛又天真纯朴,是无情、无知的富人残酷剥削的对象;或者——我得说,这是最阴险的说法——她们“亲如家人”。女性的基本经验永远被简化成最粗浅的漫画。生孩子就是一通尖叫。月经是血。家务劳动是一则童话:灰姑娘被无情的继母欺压,但终有一天梦想成真,她成为和善的公主,手下的仆人微笑有礼。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住宅是一个由职场妈妈构成的封闭景观。这是基本事实。为我工作的最重要的员工——那些改变我的思维、为我的工作扫清道路、将我的孩子当成心头肉来疼爱着的女性——是一群为了在城里工作、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最终在我家落脚的农民工。我们编织了一张由妥协、牺牲和金钱组成的网,而这一切都围绕我展开——我的工作、我的钱、我想象中一对一公平贸易的乌托邦,但这种想象从未真正实现。
在我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对于那些报道海外战争和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女性,曾存在一些陈词滥调。他们过去常说——有时我们自己也常说——我们是某种“第三性”。当然,我们不会梦想成为男人,但我们也被免除了一些束缚——而我们所报道的女性仍然要受到这些约束。我们可以在街上露出面容,也可以在男女分桌的晚餐上和男人们同桌吃饭。也许一个永远不会和本国女人直接说话的指挥官会给我们一个采访的机会。在默认属性为雄性的新闻机构,与受到新闻事件影响的那些悲痛的母亲和忧心忡忡的妻子之间,我们充当一座桥梁。我们既和这些女人不同,又和男人不同。
不管我在一个选题上花了多少时间,不管采访会变得多么亲密,我和我所写的人之间仍然相距甚远。他们过着一种生活,我过着另一种。报纸的具体性和新闻的抽象性束缚着我。女性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没有影响到我,我个人的挣扎也与我采访的女性无关。我只是从她们身边路过。
可是在生完孩子后,在和我雇来帮忙的女人同居一室一起抚养孩子后,这种必要的距离开始扭曲和消解。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我在继续前行,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情况似乎不太好。有时乱成一锅粥。
家庭生活的直接和小人物的绝望,令我们几乎没有机会随时质疑自己的选择。我们晕晕乎乎、跌跌撞撞地穿过一间既是家也是工作场所的房子,在内衣、浴室、喂奶和抱着孩子睡觉的亲密气氛中纠缠。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怀孕、堕胎、流产、婚礼、家庭暴力、葬礼、生病的孩子和学费打碎。我的,她们的。全世界女人的那些事情。我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个男人暂时离开的空间。殴打我们和我们爱着的男人,失望和消失的男人。男人的承诺,男人的威胁,男人行为的不确定性。
那些年,我们生活在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以及印度——一个新兴的经济引擎。从人口统计上看,这些地方有减少女性数量的倾向。这种做法并不是政府的主动行动,而是一场广受欢迎的、半地下性质的基层运动。当然,女性自身也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我们——我和那些住进我家的女人们——却被留下来忍受所能忍受的一切,让自己变得愈发古怪。我们的存在和互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在行为——在四壁之间,在彼此之间。
我们并非个例。毫无疑问,我们的私人问题在全球各地的家庭中不断重复着。然而,家务活很少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连讨论的空间都很有限。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家务就是一切。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理需求,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需求一直阻碍着女性的发展,让她们保持缄默。我相信,争取女性平等的斗争集中在办公室和生产厂房里,但我开始相信,第一场且最具决定意义的斗争发生在家里。
当我们在家中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劳作时——事实上,研究表明所有女性都是如此,养育孩子的那些年尤甚,我们羞于大声说出来。我们不想抱怨。我们不想给自己的婚恋关系再添上一重负担。到头来,承受各种指责留难的还是我们自己。这种不成比例的劳务安排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选对伴侣(我们太愚蠢),我们没有为自己挺身而出(我们太软弱),我们在自己的家里一败涂地(我们缺乏战术技巧)。这些统统证明,我们要么是对孩子不够投入,要么是对事业不够热心,这取决于谁在评判。这些也统统证明——而且证据还在积累——我们做得并不够。
雇用家政服务是权宜之计,也是一种逃避。整个模式对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帮助,只有足够富有、能够支付家政服务费用的女性,或者穷得从社会流动性或仅仅是从生存角度考虑这些工作的女性,才会受到影响。不过,对于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的人来说,请保姆可以减轻父母和婚姻的压力;减轻雇主和整个社会的压力。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文章,把雇人做家务当作婚姻生活的灵丹妙药,甚至是幸福生活的秘诀。然而,这些安排是否为家政工人提供了个人满足感和婚姻幸福——这个细节从未被提及。
我想起辞职在家工作后住过的所有房子。我记得那些场景和故事。我认为,应该有人探寻一下,应该有人把这些都写下来。
但这就是我的生活。如果我去探寻,我必须接受审视。如果我提出问题,我也必须是那个回答的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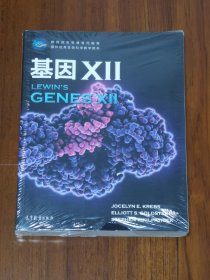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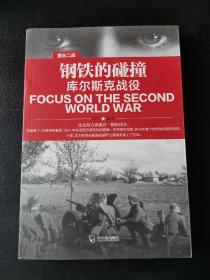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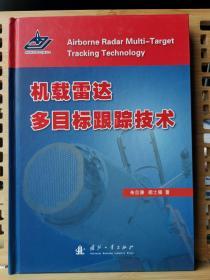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