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一位声名鹊起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考察9787547749159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52.8 6.0折 ¥ 88 全新
库存26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埃利兰·巴莱尔
出版社北京日报
ISBN9787547749159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2156134
上书时间2024-12-25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以]埃利兰·巴莱尔(EliranBar-El),约克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际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期刊的审稿人。他曾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并在那里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知识介入社会学。他翻译过特里·伊格尔顿、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等人的作品,著有《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等作品。
目录
引 论
从洞穴到数字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
定位齐泽克
第 1 章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斯洛文尼亚:叠加定位的源起
开篇:铁托(对抗苏联)
结构主义超越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立
公民社会与另类文化:从朋克到NSK
南斯拉夫的政治解体与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化
第 2 章 如果你首战失利,千万别泄气:拉黑体初试啼声
何以齐泽克在法国失利
为叠加定位做担保:拉克劳为齐泽克作序
表演型的全球介入
作为知识介入的叙事
第 3 章 走向全球:叙述(创伤性的)当下
对齐泽克的反应:介于接受和拒绝之间的再生产
全球性创伤的意义:“9·11”事件和反恐战争
推广齐泽克:在媒体与学术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介于风险与机遇之间的当下:金融危机与“阿拉伯之春”
第 4 章 齐泽克谢幕:扮演牺牲型知识分子
学术界之外的齐泽克:笑话、说笑话的人和教学法
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格雷、乔姆斯基和达巴什与齐泽克之争
对哲学和反哲学进行叠加定位
终末期的开始?齐泽克叠加定位之效果
结 语
知识社会中的知识生产
数字复制时代的知识劳动
鸣 谢
译后记
内容摘要
齐泽克是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成长,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壮大,使用了哪些策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从寂寂无名到赫赫有名的?为何他醉心于剑走偏锋,且能屡屡出奇制胜?为何他美名远扬,却又恶名昭彰,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文化巨星”“知识名人”,也有人说他是“宫廷小丑”“学术贱民”?他至少精通五种语言,对西方学术传统了如指掌,对全球政治现实洞若观火,为何放着严肃庄重的学者不做,偏要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讲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做些令人不以为然的糗事,像苏格拉底断送自家性命那样葬送自家的清誉?全球化使他如鱼得水,数字化使他如虎添翼,为何他又声称自己只欠一死,宣布要当众自杀?个中蹊跷,且听作者细说端详。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齐泽克学术传记。它扎根于生机勃勃的社会学理论,立足于方兴未艾的数字公共领域,借助对齐泽克及其同侪的深度访谈,参照学界内外褒贬不一的评议,对其学术轨迹做了精当的描述,对其职业生涯做了缜密的考察,对其思想观念做了透彻的剖析。
◎作者简介[以]埃利兰·巴莱尔(EliranBar-El),约克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际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期刊的审稿人。他曾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并在那里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知识介入社会学。他翻译过特里·伊格尔顿、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等人的作品,著有《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等作品。
精彩内容
无论这两种方式有多么诱人,它们都可能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正如吉尔·埃亚尔(GilEyal)所言:“添加限定词‘公共’到底有何作为?答案是边界作业。‘公共’一词的加入,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重新划定了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谁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边界,将学者特别是那些一门心思地追求技术进步的专家排除在外。”本书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边界作业,利用定位理论(positioningtheory),特别是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介入(intervention)的概念,来克服这种限制性的二分法,从而挑战知识分子要么站在(或应该站在?)权力一边,要么站在真理一边的观念。一边是权力,一边是真理,这种二分法与齐泽克独特的知识介入模式严重不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遵循的是下列观念:知识分子是“一种混合的存在,一脚站在沉思的世界,一脚站在政治的世界”。
此外,今天的数字公共领域(尽管它面临挑战)保留了齐泽克的介入的知识轨迹(interventionallocusintellectus)。最近的技术变革为知识活动创造了新条件。限制的减少使大众更容易获取知识,推动知识的普及,同时导致了信息的极度膨胀。这回过头来,又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变化或知识生活的转变:社会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大规模扩张,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宏大”哲学体系的影响力日益衰微,因此,“权威型知识分子”(authoritativeintellectual)随着知识权威的凋谢而衰落。总之,对于齐泽克在公共领域和全球的崛起而言,这些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最近的发展导致了知识的实体化现象(intellectualsubstantiation),而知识的实体化使得对我们目前的知识社会进行知识介入变得合法了。知识介入不仅需要在当今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他们工作的机构如大学以及他们表演的空间,即新兴的数字公共领域。在网络出现之前,传统上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基本政治经济大多由精英控制,这极大地限制了公众对知识的获取。正如迈克尔·凯伦(MichaelKeren)和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Hawkins)所言,在这种环境下,“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可能看起来像是观念的供应商和媒体的供应商进行浮士德式交易的产物”。
事实上,“媒体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诞生的。罗纳德·雅各布斯(RonaldN.Jacobs)和埃莉诺·汤斯利(EleanorTownsley)认为,媒体知识分子是由政客、记者、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充当“专业的传播者”或叙述者,将新闻媒体格式(newsmediasformats)用作“收集和讨论当前问题的集结地”。然而,在今天这个“后法典时代”(post-codexera),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完全由专家在纸上完成,它还由非专家在屏幕上完成。以技术为媒介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是丰富充足,而不是匮乏单一:“我们的时代是由开放的和互动的传播媒体的日益多样化来界定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现在都能接触到这些媒体。显而易见,与传统大众媒体的兴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大众媒体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令批判理论家着迷),更多的个人从未有过如此大的潜力,可以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更直接地与他人交流。至少表面看来,现在进入障碍更少,进入的门槛更低,限制和监管更少。”这是维基百科的时代,原声摘要、博客或推特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实体和风骨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何变化?如果说伴随着“知识权威”的式微,“权威型知识分子”也告衰落,那么知识分子还能有什么作为?随着数字传播和新社交媒体的兴起,今天的“技术知识分子进入了注意力经济。……如果他们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使人们注意到他们自身和他们要传播的信息,他们就能以此谋生,就会大功告成”。
这个被亨利·法雷尔(HenryFarrell)称为“技术知识主义”(technologyintellectualism)的崭新世界带来一些明显的益处:与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相比,它把观念世界与更广泛的公众联系融为一体。它还推动了某些思想者(thinkers)的地位的提升,而这些思想者在传统学术环境下只能永远甘拜下风。不过,亨利·法雷尔还指出,新的技术知识主义也有害处。他认为,这主要是忽视了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正是这些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平等影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成和形态。职是之故,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同时对于本书而言,眼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弄清楚喜爱与人作对、怪异有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种似乎旨在拉拢、腐蚀他们或将他们变成职业争议分子(professionalcontroversialists)的默会经济(taciteconomy)中养活自己的”。茱迪·迪恩(JodiDean)在其《博客理论》中指出了数字媒体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网络通信的动荡骚乱,即快速的创新、采纳、改编和淘汰”。这是她所说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的一部分,即通过网络化的传播和娱乐性的媒体将民主政体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正是在这里,正如乔纳森·贝勒(JonathanBeller)在研究注意力经济和景观社会时所言:“专注于注意力的电影组织(cinematicorganizationofattention)导致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注意力……就是为了后期资本的价值生产而与社会之整体结成的必不可少的控制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以知识认识论(intellectualepistemology)和合法性为基础的观念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定位过程的知识的实体化,是公共生活(当下的紧迫问题、日常公共事务和论争)与知识生活(涉及对观念、知识等的生产和传播)之间的交叉点。实体化“支撑着那些名义上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现身的人的可信度,以及他们陈述的效力和他们见解的品质”。但今天,“学术研究的成果必须在一个新的信息‘以太’中竞争,在这个信息‘以太’中,许多传统的知识等级秩序已被打乱,知识分子要想使自己的主张实体化,使他们的主张成为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的主张,已经相当困难”。
学者和公众在获取知识方面面临关键挑战,网络为应对这种挑战铺平了道路,这改变了我们寻常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公共领域。尽管传统上把公共定义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的机构和实践与置身于日常生活的普通民众相互作用”,但今天的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谁授予他人对媒体的访问权,而言论本身的内容和性质则由这种权力关系来塑造”。这种发展也派生了一个虚影(phantom)和一个幻影(phantasm)。基于现在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更加开放,有人声称“我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这句格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幻影。因为网络理应允许访问,于是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这种开放是民主社会力量的产物这是一个难以立足的历史假设;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公共事务将具有与之类似的开放特征这是一个不足以采信的技术假设和政治假设”。事实上,莉兹·皮尔尼(LizPirnie)声称,知识分子努力传递旨在刺激社会变革的信息,但其功效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采用的特定的传播技术。如此认知的一个早期范例来自索伦·克尔凯郭尔。他在1864年出版的专著《当今时代》中对“新闻界”及其在创造和维持“公众”这个幻影时发挥的构成性作用(constitutiverole)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公众”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整体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已。
知识(在数量上)的民主化和(在质量上)的大众化还是一项挑战,这种挑战还影响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数字公共领域中的表演性角色,因为他们与知识、真理和权力密切相关。在数字洞穴中,表象越来越无所不在,越来越错综复杂,这使知识分子和公众处于截然不同的状况之中。鉴于这些情形的发展,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决定了介入公共领域并试图以知识和观念来影响当代事务的知识分子的合法性,而不怎么关心知识分子的类型和定义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超越围绕着知识分子的本质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争。通过研究“齐泽克”的“如何”问题,本书还就“免费获取”的数字集市(digitalagora)对知识介入的影响进行详尽的反思。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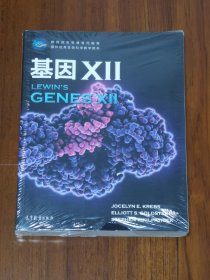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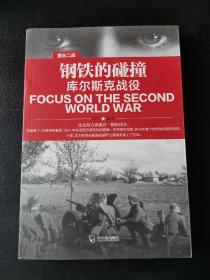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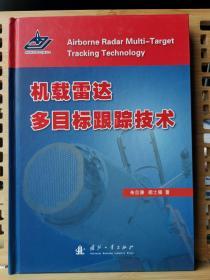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