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顶上的轻骑兵(插图珍藏版)9787559485106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41.13 5.3折 ¥ 7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著 者:[法] 让·吉奥诺 绘 者:太 贰 译 者:潘丽珍
出版社江苏文艺
ISBN9787559485106
出版时间2024-09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2216169
上书时间2024-12-18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让·吉奥诺(JeanGiono,1895—1970),法国著名作家,被列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列。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入反军国主义斗争,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1932年获得法国荣誉勋章,1953年获摩纳哥文学大奖,1954年当选为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士。他的作品多描绘普罗旺斯的乡村世界,代表作有“潘神三部曲”(《种树的人》《一个鲍米涅人》《再生草》)、《屋顶上的轻骑兵》、《山冈》等。
译者简介潘丽珍,1943年生,现居上海。原解放军外语学院法语教授,法语翻译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蒙田随笔全集》(合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屋顶上的轻骑兵》、《海底两万里》等。
绘者简介太贰,中国青年画师,毕业于于中国美术学院。基础功底深厚,风格多样,尤擅速写及写实造像。以对水墨元素的灵活驾驭而知名,深受当下青年群体喜爱。
目录
十九世纪中叶,在一场政治决斗后,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安杰洛·巴尔迪流亡到了法国,前往寻找儿时伙伴日于塞普。此时,霍乱席卷了法国南部,而安杰洛误入疫区,举步维艰。由于被污蔑在水源中下毒,他只能暂居于屋顶上以躲避追捕,期间偶遇了勇敢善良的女主人公波利娜。两人一路结伴而行,彼此扶持,惺惺相惜,在霍乱肆虐的阴影下,共同经历了追捕、隔离、感染等种种磨难,演绎了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
精彩内容
第一章黎明降临,安杰洛已醒来,他心情怡悦,默默无声。这地方夏天露水很少,加之有山冈保护,他身上没沾上露水。他抓了把欧石南擦了擦马,将鞍囊卷起来。
他走下小山谷。山谷里,鸟儿纷纷醒来。即使在夜色依然深浓的谷底,也并不凉爽。天空被急急冲出的朦胧晨光照亮。最后,一轮红日从森林中升起,但被高草般的乌云挤得扁扁的。
尽管安杰洛已感到异常闷热,但他仍想吃些热乎乎的东西。他走到一个大谷地,谷地这一边是他露宿的丘陵,另一边是一个更高更荒凉的山丘,向前伸展二三法里[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如无特别标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朝晖照在这山丘上,照得高大挺拔的橡树金光闪闪。他看见路边有一座小农庄,牧场上,一个穿红衬裙的妇人正在把沾了露水的衣服收起来。
他走过去。她胸衣外面穿一件粗布内衣,露着肩膀和胳膊,挺着晒成褐色的硕大乳房。“对不起,太太,”他说,“能不能给我喝点儿咖啡?我付钱。”她没立即回答,他意识到刚才说的话太过彬彬有礼。“说‘我付钱’也很蠢。”他心里想。“我能给您咖啡,”她说,“跟我来。”她块头很大,又那样密实,因此,转起身来慢得像条船。“门在那边。”她指着树篱的尽头说。
厨房里只有一个老头,还有许多苍蝇。有一个矮墩墩的炉子,炉火烧得旺旺的,旁边有一小锅麸皮猪食。但在炉子上,咖啡壶送出浓郁的香味,以至于尽管屋子黑得像炭,安杰洛仍觉得它非常可爱。昨晚,他啃了些干面包,现已饥肠辘辘,即使是麸皮猪食,也令他馋涎欲滴。
他喝了碗咖啡。那女人矗立在他面前,他清楚地看见她那肉乎乎的有着一个个小窝的肩膀,甚至看见了大得出奇的紫黑色的乳头。她问他是不是坐办公室的。“当心,”安杰洛寻思,“她后悔给我咖啡了。”“噢,不是!”他说(有意避免叫“太太”),“我是马赛的一个商人。我去德龙,那里有我的客户,乘机散散心。”那女人的脸色变得更加和蔼可亲,尤其当他问及去巴农如何走的时候。“您吃个鸡蛋吧。”她说。她已把猪食锅往一边推了推,将平底锅放到了火上。
他吃了一个鸡蛋和一块肥肉,另加四片雪白的面包,是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来的。他感到这些面包片轻如羽毛。此刻,那妇人慈母般地在他身边忙碌起来。她身上散发着汗臭味,她抬起胳膊,将发髻弄牢一些,于是露出了浓密的红棕色腋毛;他闻到了她的汗味,看到了她的腋毛,惊讶自己竟能忍受。她不让他付钱,见他坚持要付,甚至格格地笑出了声,并且毫不客气地把钱包推开。安杰洛为自己的笨拙和可笑而感到十分尴尬:他真的很想付钱,这样,他走的时候,就可摆出一副冷漠的神态,他习惯用冷漠来保护他的腼腆。他赶紧说了几句客气话,便把钱包塞进了口袋。
那妇人给他指了路。那条路穿过山谷,爬上高地,消失在橡树林中。安杰洛穿过绿油油的牧场,在这小平原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很久。他刚才吃的食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回味无穷。最后,他叹了口气,便策马飞奔起来。
太阳高挂,天气炎热,但阳光并不强烈。那阳光很白很白,完全碎成了粉末状,仿佛在用稠厚的空气涂抹大地。安杰洛早已上了山坡,走在橡树林中。他沿着一条小路前进,路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马儿每走一步,都会扬起无数尘埃,有如掀起滚滚浓烟,久久不落。在每一个拐弯处,透过干枯焦黄的林下灌木丛,可见他路过的痕迹依然停留在下面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树木没有带来丝毫凉意。相反,坚硬细小的橡树叶子反射着热和光。树林的阴影使人眼睛发花,喘不过气来。
在被太阳烧得露出骨头的山坡上,几株白色的矢车菊在他经过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马蹄踩得周围金属般的大地微微颤动。除了这微弱的椎骨颤动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这马蹄声尽管被厚厚的尘土减轻了,但听上去依然清脆响亮;周围一片寂静,那些默默无声的大树,仿佛成了幻景。马鞍滚烫滚烫。系马鞍的肚带一动一动,溅出汗水。那牲畜嗍着马嚼子,不时晃晃脑袋,轻咳一声。气温越来越高,仿佛是从无情地塞满了煤炭的炉子里升起来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橡树树干嘎吱作响。那光秃秃干枯枯的灌木丛,犹如教堂的地板,淹没在白色的阳光中;那阳光虽不强烈,但已变成粉末状,刺得人睁不开眼,马儿走在这灌木丛中,慢慢地转动着长长的黑影。道路蜿蜒曲折,拐弯越来越急,从覆盖着白色地衣的古老岩石中间向上攀登,有时迎着太阳前进。这时,在白垩般的天空中,会出现一条异乎寻常的磷光闪烁的深渊,一股火炉中和发烧时才有的黏黏糊糊的气息从里面冒出来,可以看到那黏糊而浓稠的物质在颤动。一棵棵大树在这炫目的光线下消失,一片片橡树林被阳光淹没,只露出一丛丛土色的树叶,朦朦胧胧,看不清轮廓,几乎是透明的,炎热的气温突然将一个慢慢晃动的黏乎乎亮晶晶的旋流覆盖在它们身上。接着,小路向西拐弯,突然变得更加狭窄,成了羊肠小道,路旁挤满了光灿灿的树木,树干成了金晃晃的柱子,弯弯扭扭的树枝成了金光闪闪噼啪作响的干茎,静止不动的树叶也镀上了一层金色,犹如一面面边缘镶嵌着纤纤金丝的小镜子。
安杰洛一路上只见阳光,不见其他生命,惊讶不已。至少也该有几只蜥蜴抑或乌鸦吧,它们喜欢这种白色的炎热天气,就像在下雪天那样,待在树枝上窥视。安杰洛想起了在加比亚山区的夏季军事演习;他从没见过那种清澈晶莹的风景,那种半球形的玻璃钟罩,那种矿物学的幻景(连树木也像大水晶,有了无数个面,无数个棱柱)。可眼前却似一个个渺无人迹的洞穴,他深以为异。他想:“我才离开那位给我喝咖啡的赤露双肩的女人!可现在,整个世界离那赤露的双肩多么遥远,连月亮或中国那些磷光闪闪的洞穴也不像这样遥远,而且,这个世界可以把我杀死。嘿!”他继续想道:“可这是我居住的世界呀!在加比亚,有我的小参谋部,还有军事演习,如果不想挨那位有着极其漂亮的胡须、说话极其粗野的圣乔治将军的咒骂,就得专心参加演习,这样,我就可以同这个世界分开,不去注意那些四面体的树林。这也许就是最崇高原则的根本所在:假如因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球形玻璃钟罩下,可能被一丁点儿荒唐的阳光杀死而感到恐惧不安的话,只需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参谋部和一个满口粗话的将军就够了。在阳光下,有阿里奥斯托[阿里奥斯托(1474—1553),意大利诗人。]的兵士。因此,大凡不是杂货商,都尽量严肃地对待一些崇高的原则。”然而,那些树木,就连最小的一棵,他估摸也有十万公斤,可看上去却轻如鸿毛,它们藏在或溜进阳光中,比鳟鱼钻进水中还要敏捷,这使他忧心忡忡。他快马加鞭,赶快奔向大山顶,指望至少那儿有点儿风。
山顶上也没有风。那里荆棘丛生,阳光和高温更加沉甸甸地压下来,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天空,白茫茫一片。天际蜿蜒着微微发青的群山。安杰洛所去的方向,被一座灰蒙蒙长绵绵的高山占据,尽管山头是圆的,但很高很高。从他所在的地方到大山之间,高耸着一块块大岩石,宛若一个个三角帆船,稍为带点儿绿色,在锋利的岩脊上,矗立着一些村落,犹如一个个马蜂窝。这些几乎一丝不挂的岩石从山坡上异军突起,山坡覆盖着褐色的橡树林和栗树林。山脚下有一个个峡谷,海角和海湾看得清清楚楚,山谷一片金黄,抑或比天空还要白。阳光强烈,暑气熏蒸,一切都在颤动,一切都变了形。在炎炎赤日下,大地散发出尘埃或烟雾,开始从这里那里袅袅升起,从禾茬地里,从火焰般颜色的小块牧场里,甚至从树林里。人们感到高温正在将树林里的最后几棵青草烤熟。
那条路不肯下决心往下走,依然在山脊上奔跑。山脊很宽很宽,像是个起伏不平的高原,左右两侧,是更高的山峦,那山脊的两侧牢牢扎根且,他们的先人说:‘喝吧,这是我的血。’我就做了一件事,把我的侄女打发走了。她在这里,他们不方便。当然是因为她穿裙子。穿裙子是出于自信,但是,看到有人穿裙子是迫不得已,那是很讨厌的事。现在,这小屋里就我一个人。当他们时不时想往肚子里灌一小杯酒时,我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有好处嘛。这不是最重要的吗?呵!再说,”他又说,“他们做这事很有绅士风度。他们不走大路,而是绕一大圈,从树林里来。他们很渴,但还这样做,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在苦行和其他方面都比我强。他们从后门进来,马厩的门总是开着的,这对于自尊心比较强的人,也是一种凌辱。这没什么:以前谁会对我说哪天我会开食堂呢!”安杰洛沉思片刻。他很理解,一个人住在这不会说话的树林里,是很需要有个伴儿说说话的。“我热爱人民,”他想道,“在这点上,我和这个住在只有狐狸出没的荒路旁的士官是一样的。爱是很可笑的。有人会对我说:‘让我们安静些吧!真实存在于给你喝咖啡的那个女人的肩膀上。它们很美,它们的小窝在向你微笑,尽管风吹日晒,皮肤黝黑。你还想要什么?刚才,你对水池,甚至对那棵山毛榉树的凉爽绿荫,对那些同样可爱地闪烁发光的柳树表示蔑视了吗?’可那是因为对山毛榉树、柳树和水池可以表现得自私一些。谁来教我自私自利呢?不容置疑,这人贴肉穿着红背心,显得心境恬然,他可以同任何人谈他想谈的事。”树林的岑寂给安杰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没有餐室,”这个心境恬然的人最后对他说,“您看,那里有张大理石桌,平时,我就在那张桌子上享用我的饭菜。我想,如果我们分两张桌子吃饭,未免有点儿愚蠢。尤其是我必须随时起身侍候您。我们的餐具放在一张桌子上,您看有没有不便?如果您同意,我会举止文雅的,不过,我孤身一人在这里(这句话促使安杰洛下了决心)……”他终于安排停当,他自己待会儿喝的酒,也会让安杰洛付款。
他果然举止文雅;他在军营中早已养成习惯,吃饭时不把胸毛领带弄脏。
“像您这样的客店,”安杰洛说,“一般都是血淋淋的。总有一个炉子用来煮尸体,一口井用来扔骨头。”“我有一个炉子,但没有井。”那人说,“不过请注意,”他接着又说,“我完全可以把骨头埋在树林里,有人能发现才怪呢。”“就我的精神状态而言,”安杰洛说,“有这样一次历险,我会感到比什么都愉快。人生来是很奇怪的,我想,同一个有幸在轻步兵第二十七团服过役的士官谈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但是,在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上,我要费极大的劲儿同自己辩论,所以当我遭到几个果断而残忍的人袭击时,看到他们看中我的钱包,以为只有不顾一切威胁我的生命才能避免苦役和断头刑,我会感到莫大的宽慰。我想,我会愉快地接受战斗,哪怕在我从这里看得见的那个小楼梯上,但在那里是很难做假动作的。甚至我喜欢在一个顶楼上,门开着,听得见凶手光着脚上楼来,我对自己说,我先开两枪,然后,就该用我从不离身的那把极其锋利的尖刀解决问题……”他做了一个非常伤感的宣战。他一本正经。“这是谈论爱又不致被人讥笑的唯一办法。”他想道。“话是这么说,”那人说,“可我认为,这样的时刻并不好玩。”然而,因为安杰洛阴沉而狂热地坚持,那人给他倒了一杯酒,旷达而明理地说,人人都从青年时代过来,这充分说明,危险的事并不因年轻而致命。“我将来要做隐士。”安杰洛想道。“嘿!干吗不呢!一小块果园,几株葡萄,也许还有一件修士服,这毕竟是一种舒服的衣服。脖子上还有几根细瘦细瘦的腱子,好把我的脑袋系在修士服上。不管怎样,这会给人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怕受嘲笑的人,穿修士服倒是个很好的保护。这也许是一种不受约束的办法。”结账时,那人就不再旷达明理了,直截了当地乞讨几个里亚[里亚,法国古铜币,相于四分之一苏。]。他不再谈轻步兵第二十七团,而是反复使用“孤独”一词。他意识到,他只要一说这个词,安杰洛就会同情他。他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戴上他的警察帽,以便在陪安杰洛到上马石那里去的时候,将它摘下来拿在手中。
大约是下午一点,天热得像磷那样苦涩。“不要走在太阳底下。”那人说(这在他看来不无讽刺意味,因为哪里都没有阴凉)。
安杰洛觉得,他随着马,慢步进入了他刚才谈到的火炉里。他沿着一个山谷前进,山谷很窄,长满了一丛丛矮橡树。直冲山谷的岩壁,被太阳烤成了白色。阳光变成了刺眼的粉末,犹如玻璃砂纸,在他和马的身上摩擦,他和马都昏昏欲睡;粉末状的阳光摩擦着小树,小树渐渐消失在污浊的空气中,那空气如粗粗的纬纱般颤动着,将黏稠的金色斑点同暗淡的赭石色和大片的白垩色混在一起,平时的东西已无法辨认了。被雀鹰抛弃的窝窠发出腐臭味,沿着高耸不平的巨岩往下流淌。山坡将四周远处苍白山丘中一切腐败的臭味注入这个山谷。树根和树皮,蚂蚁窝,拳头大小的胸廓,宛若一段段银链的死蛇骨,粘满了死苍蝇犹如一把把科林斯葡萄的豆科植物蝶形花冠的旗瓣,白如栗子浆的死刺猬骨,散布在大块气息奄奄平地上的怒目而视的一堆堆野猪尸骨,从头到脚被虫咬得千疮百孔连枝梢也充满了木屑被稠密的空气扶着站住的树木,倒在被烈日烧烤的橡树枝丛中的鵟鸟骸骨,还有在暑气熏蒸下从野生花楸树树干的缝隙中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浆液味。
出现所有这些野蛮的景象,并非只是因为安杰洛被太阳烤得昏昏欲睡满眼红光。在这山区,从未有过如此炎热的夏日。而且那一天,热浪势如潮涌,席卷南方各地:在僻静的瓦尔河流域,小橡树热得发出爆裂声,在高原偏僻的农庄里,蓄水池上立即飞来了无数鸽子,在马赛,阴沟洞里冒出了青烟。在埃克斯,中午,全城都在午睡,鸦雀无声,林荫道上,公共取水处响起的钟声像在夜里那样清晰。在里安镇,早晨九点就有两个人病倒:一个是车夫,他进镇子时,突然发病,被抬到一个酒吧里,躺在阴凉处,被放了血,但仍不能说话;另一个是二十岁的姑娘,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她刚到公共取水处喝了水,突然站着拉起肚来,她强撑着跑回家,她家离得很近,刚走到门口便栽倒在地。当安杰洛在马背上打瞌睡的时候,那姑娘好像已经死了。在德拉吉尼昂,山峦把酷热反射到城市所在的盆地上,让人无法午睡:平时,屋子的小窗户能给房间带来凉意,可这次天气闷热异常,人们恨不得用铁锹把窗子扩宽,以便能喘过气来。人们都跑到田野里;没有泉水,没有水池;人们吃甜瓜和杏子,可它们烫得像是煮过似的;大家都趴在草地上。
在瓦莱特,人们也吃甜瓜。正当安杰洛经过冒臭鸡蛋味的岩石时,年轻的泰于夫人顶着烈日,奔下城堡的楼梯,跑到村子里去,好像是一个厨娘刚才突然病倒了,那厨娘是一小时前去村子里的(正是那位客店老板,这个老恶棍对安杰洛说“不要走在太阳底下”的时候)。而现在(安杰洛正继续闭着眼,穿过炽热的山丘),那厨娘已死了,人们猜想,她死于中风,因为她的脸是黑的。燥热、死人的气味和黑脸,使那位年轻的夫人感到极其恶心。她只得跑到一个灌木丛后面去呕吐。
在罗讷河谷,大家拼命吃甜瓜。那河谷沿着灰绿色的土地向东延伸,这正是安杰洛现在穿越的地方。因为有罗讷河,那地区高耸着一丛丛树木:埃及无花果、高达三十米的梧桐、长着美丽凉爽的叶丛雍容华贵的山毛榉。今年没有冬天。毛毛虫已把所有的松树吃得片叶不留,甚至将各种柏树的叶子一扫而光,更有甚者,它们改变自己,吃起了无花果树、梧桐树和山毛榉树的叶子。在卡庞特拉高原,方圆数百法里,树木瘦骨嶙峋,树叶被咬出了锯齿,烤成了灰烬,被风吹走;站在高原上,透过那些残败的树木,依稀可见阿维尼翁的城墙,宛若一个爬满白蚁的牛胸廓。同一天,酷热降临阿维尼翁,一上来便让那些病得最重的树木一一崩折。
在奥兰治火车站,有一列从里昂开来的火车,旅客们拼命敲打所在包厢的小门,喊人来给他们开门。他们渴极了,许多人呕吐,肚子疼得缩成一团。司机带着钥匙,来到那些包厢门口,可是,刚开了两个门,就开不动第三个了,赶紧去把脑门靠在一个栏杆上,最后倒在了那里。他被抬走时憋足力气说,得赶快摘钩,机车会起火或爆炸。他说,无论如何得赶快把第二个操纵杆向左转到底。与此同时,第三包厢的旅客一直用拳头猛敲他们紧闭的包厢门。
在罗讷河谷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到处是甜瓜。高温有利于甜瓜生长。人们不想吃东西,对面包和肉想起来都觉得恶心。于是便吃甜瓜。吃完甜瓜便想喝水;公共水池的龙头上,生出长长的青苔。人们特别想漱漱口。有些树已崩折,从树枝堆里冒出尘埃。牧场像是覆盖着白雪,牧草被太阳烧焦,被滞重的空气压倒在地上,牧场上也升起了尘埃,这些尘埃和梧桐树的花粉一样,刺激着人的喉咙和鼻孔。犹太教堂周围的小巷子里,到处是瓜皮、瓜子和瓜汁。人们也吃生西红柿。这是第一个大热天,接着,这些垃圾很快腐烂。在这第一天的晚上,它们开始腐烂,夜里比白天更热。眼下,农民们已给卡庞特拉市运来了五十多车大甜瓜。下午一点,三十来辆空车返回瓜田,出了城便是瓜田。那时,安杰洛位于卡庞特拉以东三十法里处,半睡半醒,任马儿驮着他缓步前进。正当他行进在这热得让人想吐、充满了臭鸡蛋味的小山谷的时候,甜瓜皮已开始充斥卡庞特拉市的主要街道,连专区政府、图书馆、宪兵署和客人最多的狮子宾馆周围也到处是瓜皮,还有许多运瓜的车辆正在进入城里;一位医生服了几滴掺了点儿糖的复方樟脑酊;开往布洛瓦克的驿车两点钟要出发,到现在还没把马套在车辕上。
如同在原野上一样,无论在城市还是村庄,这炽热的阳光似迷雾般神秘莫测。它使街道两侧看不见房屋的墙壁。阳光照在正面墙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反光,致使对面的阴影刺得人睁不开眼。空气稠得像糖浆,万物都改变了形状。行人走起路来仿佛喝醉了酒。他们醉眼蒙眬,不是因为匆匆吃下去的绿瓜瓤和瓜汁在肚子里咕咕叫,而是物体的形状变得模模糊糊,使得大门、窗子、搭闩、门帘、酒椰叶纤维窗帘都移动了位置,人行道的高度和铺路石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加之人人走路都半闭着眼睛,和安杰洛一样,低垂的眼睑被太阳染成了丽春花的红色,所有的欲望都化成了沸水的形象,人们在沸水中踉跄而行。
因此,头几天便有许多人病倒了,但没引起人们注意。只有在那些病人无力走到家里而倒在大街上的时候,才有人照管他们。即使这样,也不是人人都得到照顾。如果他们是脸朝下摔倒的,人们可能以为他们在睡觉。只有当他们在地上滚了一下,最后以仰卧的姿势固定下来,人们才会看见他们发黑的脸孔而感到不安。即使这样,也有病人被忽视,因为这酷热、这喝水的欲望,使个人主义更加膨胀。因此,事实上,在这第一个大热天——恰恰是安杰洛在阳光染红的眼皮下梦见倒在大橡树枝丛中的鵟鸟骸骨的时候——不管怎样,这第一天的病人很少。一个犹太医生接到了一位犹太教士的报告后,考虑到教堂的圣洁,前来检查恰好倒在教堂小门口的三具尸体(人们猜想,他们是想到教堂里去凉快一下)。那天下午,在卡庞特拉只有两次警报,其中包括前往布洛瓦克的驿车车夫,况且,很难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使车夫得病的,究竟是苦艾酒,还是天气热(此人是个大胖子,嘴巴一渴,肚子一饿,就迫不及待地要吃要喝,他在客店里吃了中午饭——那天全城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中午用餐——吞下了一盘猪下水,又接连喝了七杯苦艾酒,用来代替咖啡和餐后烧酒)。
在奥兰治、阿维尼翁、阿普特、马诺斯克、阿尔勒、塔拉斯孔、尼姆、蒙彼利埃、埃克斯、瓦莱特(那里,那位年轻的厨娘率先死去,却丝毫未能引起震惊)、德拉吉尼昂,甚至直到海边,都有一两个人死去,几乎并没引起忧虑(但从下午开始,人们感到有些不安了,而那时安杰洛正在打瞌睡,马儿的脚步颠得他想吐),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有的轻一些,有的重一些,却被归咎于到处毫无节制地吃甜瓜和西红柿。人们给这些病人治疗,让他们服用掺有方糖的复方樟脑酊。
在土伦,才下午两点,海军的一位督察医生就登门求见海军上将兼要塞司令T公爵了。人家请他晚上七点再来。他表现得很不得体,甚至极不礼貌地在接待室里大嚷大叫。他终于被一个值勤的准尉逐出门外,准尉发现医生神色惊慌,好像很难抑制想讲话的欲望,只见他突然用手捂住嘴巴,不让自己讲话。准尉表示歉意。督察医生说了句“算了”便走了。
在马赛,除了阴沟发出恶臭外,还没什么问题。几小时内,这老港的海水变得似柏油般稠稠的,黑黑的,金褐金褐的。马赛人口太稠密,谁也没注意到,大夫们从下午起就坐着双轮马车在城里东奔西跑。有几位大夫神态极其严肃。此外,这粪便的恶臭使得大家神态忧愁和沉思。
安杰洛在骑马而行的小路上,迎头遇上了一块形同三角帆的大岩石,这条路紧贴岩石通往一个村庄,那村庄犹如一个马窝隐蔽在石头中。安杰洛感到马的步幅改变了,他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穿过一些小梯田往上爬,梯田由白石矮墙支撑,长着愁容满面的柏树,村子冷冷清清,小巷两旁的墙壁令人窒息,太阳的反光使人目眩。安杰洛下了地,把马牵到教堂旁的一个半塌的拱门下躲避太阳。拱门下,可闻到一股浓烈的鸟粪味,顶上燕子窝琳琅满目,鸟窝里渗出暗黄色的水。这阴凉处虽然灰尘扑鼻,但使安杰洛发烫的颈背舒服了些,他的后颈像是受了伤,他不停地用手去抚摸。他在那里站了足足一刻钟,蓦然,他看见小巷的另一边,就在他对面,有扇门敞开着,在黑乎乎的门里头,好像有个女人的裙上衣或衬衣什么的在微微晃动。他穿过小巷,去要水喝。那是个女人,看上去有点儿迟钝,汗流涔涔,喘着大气。她说已经没水了,鸽子已把蓄水池里的水弄脏,那水勉强可以试着用来喂马。可是,马在水桶里直打响鼻,它在里面洗鼻孔,在太阳下喷出水沫。
那女人有甜瓜。安杰洛吃了三个。他把瓜皮给马吃。那女人也有西红柿,但她说这蔬菜吃了会发烧,只能煮熟了吃。安杰洛在一只生西红柿上猛咬了一口,汁水溅到了他那件漂亮的紧腰中大衣上。他管不了这些了。口渴平息了一些。他也给马吃了两三个西红柿,那马急忙吞下肚里。她说,她丈夫就是因为这样逞勇,已病倒了,昨天开始发起烧来。安杰洛瞥见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张床,堆着一条花卉图案的大毯子和一条鸭绒压脚被,几乎看不见病人的脑袋。那女人说,她男人再也暖和不起来了。安杰洛心里感到纳闷,认为这肯定是不祥的预兆。况且,那男人脸色发紫。那女人说,她男人现在已不再痛苦了,可他一上午肚子疼得直打滚,肯定是吃了生西红柿的缘故,因为他也不愿听她的话,和安杰洛一样固执。
安杰洛在这间屋里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人家还把他的马也牵了进来,然后,他就继续赶路了。阳光和酷热一直滞留在门口。很难想象会有夜晚。
就在那个时候,那位海军督察医生说了句“算了”,就回土伦市里去了。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位犹太医生匆匆赶回家里,向妻子交待了几句,让她为她自己和他们十二岁的女儿准备一只小手提箱,那位牛眼睛鹰钩鼻的胖女人便乘坐去韦宗的驿车,离开了卡庞特拉,她丈夫让她坐驿车赶快往前走,直到迪厄勒菲,甚至到布尔多才停下来。她别过脑袋,不再看她丈夫留守的城市,她把一只指头放到嘴上,示意女儿不要说话,她女儿坐在她对面,睁圆了眼睛,浑身冒汗。就在那个时候,安杰洛看见,可怕的夏天在那些高高的群山上呈现出荒蛮而光彩夺目的景象:树变成了橙红色,栗树变成了焦黄色,牧场面黄肌瘦,泛着铜锈色,在柏树的叶丛中,仿佛有无数盏油灯在闪烁悲郁的光芒,在他周围,光雾铺开了阳光织成的旧地毯,犹如海市蜃楼,在光毯那透明的纬线上,飘浮和颤动着依然是灰色的图案:森林、村庄、丘陵、高山、天际、田野、树丛、牧场,那些牧场几乎完全消失在麻布色的天空下。就在他第一百次问自己夜不会降临的时候(他第一百次转向东方,那里依然是不变的赭红色),在瓦莱特,时光已然停止转动,那位厨娘腐烂得很快,她前面站着几个村里人和那位年轻的夫人,他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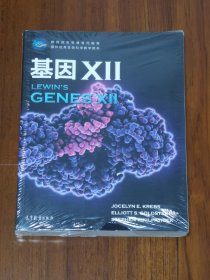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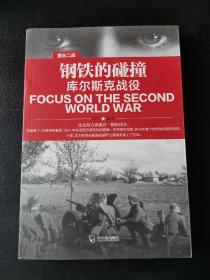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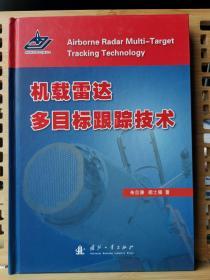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