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席地而坐(新版)9787544780216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33.57 4.9折 ¥ 6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胡迁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80216
出版时间2022-10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1581423
上书时间2024-12-0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小区(长篇小说)
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剧本)
内容摘要
拍电影时,他叫胡波;写小说时,他叫胡迁。这两个身份如同两条平行线,一直贯穿其创作生涯,构置了两条独具魅力的创作轨迹,直到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交叠重合。本书完整收录了这部非凡遗作的三万字电影拍摄剧本,从中可以看到胡迁对文学语言和影像语言敏锐的感知力和表现力。书中还收录了胡迁完成于2011年却从未发表过的长篇处女作《小区》:小区的下水道污水横流,住在三单元的女人赵湘被杀,车棚管理员黄枪被当成了替罪羊,他不得不开始关注小区的变化,并慢慢发现了藏在每个住户身上的秘密……正是这部小说开启了胡迁的文学创作之路,犀利的社会洞察、别具匠心的文本结构和叙事手法都呈现出高度浓缩的戏剧张力,而压抑的基调也铺垫出胡迁在其后小说写作中不断强化的主题:世界是一片荒原。
阅读本书犹如观看一场无声电影,他的才华他的锐利他的锋芒,字字句句都是绽爆在白纸上的生命能量。虽然距离胡迁离开已经两年过去,但他仍在以他的缺席,对我们和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为了向这部非凡杰作表达敬意,随书还特别制作了36页电影纪念别册,收集了百余幅《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幕后花絮照片,供喜爱这部电影的读者珍藏。
精彩内容
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剧本)1.朋友家卧室晨内——于城、于城朋友妻于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他前几天是这么说的,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头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儿,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好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于城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一个女人半裸着躺在床上。
女人:“他跟我提过。”于城:“怎么说的?”于城穿上裤子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抽烟。外面大雾弥漫。
女人:“踩着我裤子了!”于城:“他怎么说的呢?”女人:“跟你说的差不多。”于城:“给我倒杯水。”于城看向女人,女人在整理头发。
2.王金家晨内——王金、狗一只老狗趴在王金脚边,王金坐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他好像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是金属敲击玻璃的声音,哒,哒,哒,他头朝向屋外,静静地看着。
3.黄玲家晨内——黄玲、黄玲母亲抽水马桶继续不停往外涌水,水漫到黄玲屋里,黄玲躺在床上睡觉,她立即坐了起来,脚踏进了水里。
水漫到客厅里,黄玲母亲躺在沙发上,手垂在一旁。
4.韦布家卧室晨内(合并5)——韦布、韦布父母胶带被拉扯出来,缠绕在一个擀面杖上。房间幽暗,韦布一层层地缠着擀面杖。
他咬断胶带,往外吐着沾在嘴上的碎片。他尝试着狠狠挥舞了几下,又垂头丧气。
他把缠着透明胶带的擀面杖放进书包里。
韦布看起来有十七岁,寸头。
外面传来韦布父母的声音。
父亲:“怎么这么臭?谁他妈开的窗户?”母亲:“关了。”父亲:“怎么不早点关?现在屋里全是臭味儿!”父亲:“太臭了,一起床就这么臭,我操他妈的一天又开始了。”韦布一脸厌恶。他母亲敲门,韦布走了出来。
5.韦布家客厅晨内——韦布、韦布父母这是一间普通的三居室,屋子里看起来很满,各种杂乱的东西很多。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早饭。可以听到韦布母亲在房间里忙碌的声音。
韦布的父亲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他穿着宽松的睡衣,胡须凌乱,看起来身体很虚弱,他坐在韦布的另一边,一只打着石膏的腿放在一张矮板凳上。父亲在桌子上打开了三个药瓶,旁边摆着八九粒药丸,他开始倒酒。
韦布坐下来,说:“厨房的窗户。”父亲正在看一份报纸:“什么?”韦布:“厨房的窗户刚才开着。楼下的垃圾没人清。”父亲:“没你的房间臭,外面有什么都没你的房间臭。”韦布开始吃油条。他的父亲厌恶地看着他。
母亲在客厅的柜子上翻找着什么。她说:“购物卡呢?”韦布低着头:“不知道。”母亲:“你前天用了,放哪了?”韦布:“柜子上?”母亲:“没有。”韦布:“那不知道了。”父亲打了一个嗝,说:“他偷走了。”韦布摇摇头:“我没有。”父亲:“他拿着卡,站超市门口,给人打八折结账,收了钱就去网吧玩。”母亲看着韦布,说:“嗯?”韦布:“不是。”父亲看着报纸:“怎么不是?你除了去网吧还能干什么?狗东西。”韦布听着。
母亲在把两个大包往外拖,里面是叠整齐的衣服。
母亲:“每人每天早上都要听你说一遍。”父亲:“我说什么了?”韦布喝豆浆时洒出来一点。
父亲放下报纸,对韦布说:“赶紧去跟你奶奶住,看见你就烦。”韦布:“她屋里要是有暖气我就去了。”父亲:“这里也没暖气,你弄得满屋子都这么臭,满屋子都这么臭!”韦布站起来,去卧室背上书包,在校服外套上羽绒服。
母亲在外面喊:“拎下来。”6.朋友家阳台—卧室晨内——于城、于城朋友妻、烧垃圾的人、中年男人楼下是个垃圾堆,一个人在焚烧垃圾,黑色烟雾飘向天。一个中年男人举着一根棍子,晃悠着走过来,对着烧垃圾的人喊:“谁让你烧的?”烧垃圾的人:“那去哪烧?”中年男人:“爱去哪去哪,小区里不让烧。”烧垃圾的人:“这是小区的垃圾。”中年男人:“聋了?不能在这儿烧!”于城朝楼下喊:“就在这儿烧。”中年男人抬起头:“你谁啊?”于城:“就在这儿烧。”中年男人:“你下来!你谁啊?”于城:“我是你爹!”女人跑到阳台上,她衣服还没穿好,就一把扯过于城来,关上了阳台窗户。下面的人还在骂骂咧咧。
女人看着于城,伸出手指了指他,叹了口气,说:“你快滚吧。”于城躺到床上,说:“我晚上再走。”女人:“不行。”于城:“为什么?”女人:“我得去单位交报告,下午可能要开会。”于城还掐着那根烟。他举着烟蒂说:“你点烟,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然后烟蒂上会有血,看见了吗?”烟蒂上沾着薄薄一层血。
女人:“所以呢?”于城:“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女人:“我真得走了。”她穿上了裤子,但没穿上衣。
于城:“你就这么走吧。”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两个人警觉起来。女人站着,于城坐着,维持着固定的动作僵持不动。
小区(长篇小说)背乌龟的男人2004我对十二岁那年的记忆总是不可控地惶恐,不是因为这又过去了很久,发生过的一切可以成为封存的东西,这是个矫饰的说法。我花费了很多年探索向外的通道,但绳索一般的莫名事物总是将我拖拽回来。在这巨大的如黑洞般的世界里,我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拴绑在这洞窟的哪一部分,去探索那个源头便会远离洞口,而洞口微弱又时时刻刻都在消散的光令人恐惧。我仅有的一次接近那种真实的存在,是在深不见底的湖水中,下沉中我睁开眼睛,被冰冷包裹,数不清的细碎事物凝固于此,所有方向都朝着无尽的黑暗。
在母亲离开这个家庭以前,我有过一段正常的生活,住在我楼上的邻居——别人都叫他二狗,那时他四十几岁,还没有变成一摊肉饼,洪亮叔也没有一把火烧光他自己的家。后来母亲走了,一年后那个背乌龟的男人来到我父亲开的家庭旅馆里住了一周,然后有一天清晨,楼群像是被一种灰烬熔化了一般,并飘着一股煮肉的味道。二狗跟在那个背乌龟的男人身后,他的邻居洪亮看到了他,以为他要去湖边,那正是去往湖边的方向。那天二狗的头发打了蜡,那发蜡让他的头发像刚磨好的菜刀一样。洪亮说见到那发蜡他微微感到奇怪。二狗跟他打了招呼。
二狗跟在背乌龟的男人身后大约六七米的距离,沉重的包裹把中年男人的腰坠得像虾米一般,二狗跟他走得一样不快不慢,在清冷得快要融化的小区里,还有其他人也看到了二狗,他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阳台上日复一日地消磨着自己,开着半边窗户,看着楼底下走过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混混沌沌得像开始和结束一样,就差去死了。”洪亮叔告诉我。
二狗那天穿的条纹衬衫还带着霉味,他从床头柜里翻找了半天,后来桌上的茶缸子掉在地上,他也没有去管。他从床底下的纸盒里找到那个边沿带着锈迹的铁盒子,里面是发蜡,几乎在打开铁盒的瞬间就好像生出许多毛茸茸的东西。这些毛茸茸的东西在二狗枯萎的手指间一搓就不见了,只剩下油亮。二狗看着自己的手指,像街边吃剩的沾着油水的大梁骨。后来在他出门的时候,还蹭到了门边石灰墙上深绿色的霉斑。然后他走到家庭旅馆前,找了两块砖头立起来放在一起,坐在上面。这时我父亲在旅馆前台看到了他,我父亲厌恶这个邻居,以为他是来装可怜的。我父亲去厨房煮了碗面,靠在厨房的门框上吃了起来,他还不时地看看二狗,二狗仍然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也许他连根完整的烟都没得抽。这时我父亲还在怀疑二狗是不是来找他的,有一瞬间他觉得二狗的可怜真的触动了他,然后父亲扭头去洗碗,洗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想了。
背乌龟的男人把房间钥匙留在前台,他低着头,稳重地踏下一个台阶,出了大门。二狗站了起来,他眯着眼睛,眼角旁的肉干瘪得如同橘子,事实上他一点也不饿,但看起来却好像要虚脱的样子。二狗跟在背乌龟的男人身后,谁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清楚这件事,后来也无从知道。当我问起来的时候,二狗的女儿裘子怡说谁会想要关注那个卖乌龟的,他是否知道二狗跟在他身后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社会缺的是劳动力,不论那个背乌龟的男人还是二狗,都跟劳动力没有一丝关系。
等我的父亲从厨房里走出来,他在衣服口袋那里擦了擦沾水的手,四十几年来他一直这么做,洗完手之后在衣服口袋那里擦一下手背和手心。前台留着一把钥匙,父亲把钥匙穿进腰上的绳子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往门口看去,而那里只剩下两块立着的青砖头。与此同时,裘子怡端着粥和馒头,来到二狗同他妻子吵架后才住的棚子里,虽然那个棚子很快便被拆掉了。二狗的妻子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床头柜下歪倒的茶缸子,细碎的廉价茶叶从杯口一直铺到地面上。不论是我父亲还是裘子怡,在那恍惚的一瞬间,都有一股莫名的失落感,而那莫名的失落感将会从此缠绕他们,以至于当我父亲把青砖踢回墙根,裘子怡用报纸擦着腐烂的水泥地板时,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烦躁,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弥补什么。
洪亮叔在游乐场工作,他亲眼见过在这个挨着火车站的游乐场里,人贩子是如何给小孩下药的。
“也许他爸妈坐在摩天轮上就看到了,我在搬一个瘪了的垃圾桶,那个小男孩大概八九岁的样子,被一个女人拉着,走路晃晃荡荡,不快不慢。后来摩天轮停了,那个爸爸跟条野狗一样朝那个女人离开的方向跑,鞋子还掉了一只。但是没有找到,他朝我们大吼大叫,骂人,后来我也骂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儿子自己跟着走的。迷药太可怕了,梦游大概就是那个样子。”洪亮叔想起二狗走丢的那天,楼间的那条路也许就一百五十米的样子,但二狗好像走了很久。那个走丢的男孩,像只蝴蝶一样摇晃着,沿着碰碰车的铁栅栏,松软的胳膊被前方的女人拉着,拉向另一个噩梦。
“喝醉了之后,你就会变成一只蝴蝶,他妈的一飞就不在这里了。”洪亮叔酗酒,他住在二狗家隔壁,有一张宽大的红肿脸庞,喝酒之后就跟个红艳的灭火器一样。他短手短脚,又十分强壮,可手脚限制了他,感觉他有无穷的力量却无处使。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找了份游乐场的工作,又在游乐场附近的小区里买了套房子,主要是为了照顾他姐姐,一个疯了的女人。洪亮叔搬到小区时已经在游乐场工作了八九年,他在那里收门票,有时叫工人来修理坏了的器械。他来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叫了游乐场的工人来给他装修房子,房子只装修了一半,因为有一次洪亮叔喝了酒,回来后看到自己的家,大声咆哮:“你们把我的房子搞成什么样了!”一切都像是计划好的。二狗跟着一个陌生人不知道去了哪。我知道这件事时,二狗已经走失了一个星期,当我回到小区,楼群里还弥漫着那股煮肉的味道。母亲告诉了我,父亲站在一旁一言不发,他跟二狗有我们所不知的秘密。当母亲提起那个早上父亲吃面还看到过的二狗时,父亲就把头瞥向一边,好像对此漠不关心的样子。
后来,当洪亮叔在小区找的女人在怀孕时跟着另一个男人消失后,他烧了自己的家,然后不知所终,留下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姐姐。
我走到七号楼的后面,墙角还堆着潮湿溃烂的蜂窝煤,我来到那个棚子的门口。房顶上还飘着一个鱼形的破风筝,木门上挂着锁。我在记忆里搜寻着所有有关这里的印象,想起曾经在洪亮叔家中,他在一旁揉着太阳穴,肿胀的腿旁边有一根拐杖,他的女人脸色红润,腹部隆起,双手撑在椅子旁边像一个软体动物。那时我脑海里却响起母亲的话,她说:“这里已经坏得流了脓。”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所说的这里,不是一栋房子,而是即将有一个新生命,从另一个世界,从这丑陋的生活里破土而出。我重新打量着这里,水泥的墙面不太平整,雨水印在上面如同花花绿绿的肠子。我靠近窗户,里面昏暗无比,充斥着腐朽气息的浓重颜色。而二狗一个月后就回来了。
在我成年之后,仍旧无法忘记这一切,于是我开始寻找那个背乌龟的男人。
人头1996.10.13从楼顶看下去,整个小区如同一片混沌的沼泽,裹挟着雾的颜色,每栋建筑从五楼即开始有乌云般的暗淡色调。楼体覆一层碳色,连接着油烟机排烟管道的窗口下,结痂的油脂向下流淌,凝结出钟乳岩洞墙壁的形状。而傍晚,窗户里统一燃起四十瓦灯泡,在永远也望不到穹顶的天空中,油烟气带着浓郁的饥饿感向上贴到更灰暗的云层底面。
黄枪知道赵湘是通过街口搓麻将的两张桌子。只要天气不是冷得冰手,这些老太太和妇人便会来到街口,坐在两张腐朽的木桌旁。她们议论起赵湘的语气没有善意,这是一个大约十几年前因被丈夫抛弃而疯掉的女人。
赵湘生一对凤眼,皮肤白,白得像月亮。她终日藏匿于二楼的屋子里,深夜时,她带着剪好的报纸,贴满整个三单元楼道的墙壁。
那天晚上十点,有晚归的人叫黄枪开车棚存车,车棚里的灯泡亮了,等人走后,黄枪在门口抽烟。天黑了,棚里探出来的光能照亮一小片地面。车棚有窗,镂空的,水泥拼成个兰花形状嵌进去,光从里面漏出。人影大约在黄枪十米远处,窗光照亮一双鞋子,藏青小布鞋。黄枪不清楚是谁。严打期间,除了武警谁也不敢上街,因为武警身上贴着两个夜光的绿幽幽大字:严打。
女人走过来,窗光继而点着了她的上半身。她朝黄枪看,黄枪心里慌张了。女人定定地看了黄枪好一会儿。
你的脸怎么是黑的?
我长得吓人,用布遮了。黄枪紧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时屋里的小峰好像醒了。爸,跟谁说话呢?
女人又目光凝滞地看着黄枪的屋子。
黄枪抬眼观察她,这个女人清瘦得像张纸,皮肤姜黄,窗光下如同一根燃烧的蜡烛。他觉得这个住在三单元的女人晚上是真的疯,他慌张,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但女人看起来还算温和。
回家吧,晚上有严打。
女人小步走了,她悠悠然好像路过一条满是菊花石子的小路。她又从阴影里回头。黄枪一阵毛骨悚然。
没事,我跑得快。
黄枪似乎听到好多重叠在一起的脚步声,破碎的路面像是张鼓面。果然跑得很快,他想。
九十年代绝少死于非命的人,以前在街头巷尾时有发生,后来有了严打。严打的学名是,严厉打击各种违法乱纪。负责严打的是特种兵和武警,他们有良好的装备和强健的体格。严打期间,违法乱纪的人会有两个结果,被打死在街头,或者关进号子里,关的期限最少五年,只有加刑没有减刑。在街口打架要在号子里蹲个小学毕业的年限,这令所有人非常恐惧,因此就收敛了很多。严打催生了一种报复手段,许多心狠手辣的女人揭发自己恋爱的对象,这批男人因为一点小过失就带着对世界的仇恨进了牢房,在许多年的消耗里被磨灭了仇恨,心态平和的他们在出狱时,会看到这些心狠手辣的女人牵着已经读小学的小孩,携她幸福的家庭招摇过市,然后她们会非常愧疚地说,当初是我年幼无知。
严打期间,七号楼有个老爷子会功夫,使春秋大刀,他儿子就因为被一个女人揭发而有了牢狱之灾。老头心胸广,都怪罪在严打上,于是手腕捆了白绷带,提着春秋大刀上了街。他在街口挥舞着大刀,可是街上没有一个人。老人盘腿端坐十字路口,等待人生最后的械斗,但一天天过去了,既没有人跟他械斗,也没有武警和特种兵浩浩荡荡地赶来。老人端坐路中,在寒冷的秋风里,在他疲惫地再也举不动春秋大刀时,一个好心的警察安慰他,回家吧,我们不打老年人。老人在社会对他的关怀中独自回家,春秋大刀的刀锋插入水泥路面有二十公分。
老人从此再也没见过他的儿子。在所有有相同遭遇的男人从牢中释放回来的时候,那些心狠手辣的女人认为该去表达她们的歉意。这些她牵着已经读小学的小孩,携幸福的家庭来到老爷子面前,非常愧疚地说,当初是我年幼无知。
傍晚的天空渗出一丝潮晕般的红色,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从乌云满布的天空中看到颜色。再次下雨的时候,又全部灰茫茫了。黄枪和他的养子小峰站在车棚大门前朝三单元看着。二楼开了灯,人影攒动,是赵湘家。
一辆警用侉子(注:三轮摩托)开过来,在车棚大门前熄了火。高瘦的男人从车上跨下,朝父子俩的背影走来。
听到声音的黄枪转过身子,朝男人点了点头,打开车棚的门,男人把侉子推进去。黄枪顺手从门旁的一角拉了灯线,车棚里亮起一排昏暗的灯泡。
开侉子的叫嫚哥,高瘦,眉弓清晰,还带着几年前大学毕业时的稚气。毕业后分配到小区派出所当片警,做了几年,嫚哥自从能把侉子开回家就不再骑自行车,一个侉子占两个摩托车车位,他便跟黄枪比较熟络。
今天下班很早。
我是提前回来的。
嫚哥从警服里掏出大鸡烟,递一根给黄枪,黄枪接过来,烟嘴塞进面罩下的小孔里。嫚哥抽了两口,盯着二楼的窗户。
赵湘死了。嫚哥说。
在家里?黄枪问。面罩下面冒出他呼出的烟雾,向上飘动。
嫚哥只是看着那个阳台,赵湘住在二楼。
三楼的二狗家阳台上,一个倾斜的木质模特下垂着身子。黄枪走了几步,站在楼口,向楼后望去,拐角处露出苍白的救护车,几个小区的邻居静默地站立着。佝偻的李二士像只猴子。一种如积压灰尘般的压抑感弥散在周遭。
小峰显得很兴奋,溜到两人中间。爸,是谁杀的?
哥看向小峰,用手抚了把小峰的脑袋。他熄了烟,就走了。
他听了我的话,肯定会查你。小峰说。
黄枪看着安静的人群,车走后,人群渐渐散去,这时他的手被水滴砸到,面罩上也有了滴答声,他抬起头,下起了雨。他看到从楼房上的窗口处钻出许多脑袋。那是在街口打麻将的老太太们,她们捋着头发,面孔模糊。
黄枪走到街口。李二士尖削的颧骨向上拥簇,鱼尾纹铺张开一张略带委屈的脸。他靠近李二士。
怎么样了?
李二士只是看了他一眼。
夜晚,黄枪去了三单元,来到赵湘家门口。门上已经贴了封条。楼道里又潮又湿,混合着臭味。他站在楼道,透过门,好像看到一具躺在地上的女尸,藏青的小布鞋上已经没有光,胸口竖刀,刀柄上还有些许泥垢。墙壁上有大片水草般的血,又如同摔死在地上的老鼠遗留下来的污迹。旧房子都是水泥地板,上面有裂缝,血水就顺着这些细纹向四面八方缓缓地流淌,向更深的地方下渗,又干涸成一个巨大的伤口贴在地面上。
花小区里有七八座楼排成一列,楼有正面背面,正面的大道里通常是一排平房车棚,背面是楼宇的单元入口。我把有车棚的一面称为正面,是因为我家在一楼,一楼的院子会开一个大门,除了一楼的住户,其他楼层只能从背面的单元入口进入。
我的童年一直弥漫着一股股淤泥的味道,从紧贴小区东面的那条腌臜的护城河到所有楼宇的背面,下水道终年堵塞而污水横流的背面,那股淤泥的味道带着一种既青又绿的黑色从天上遮盖到地面,走在其中,好像浑身的毛孔都被其浸透。从家里后门出来,出了单元口,就是两个下水道井盖,这里的水泥井盖通常都盖不平,或碎裂一角,泡烂掉的卫生纸和其他秽物从里面流淌出来,漫延到整个街道。这层污水终年如同一个浅浅的湖,地面与其生为一体,在仅有的两次治理中,下水道系统通畅了一个月,在那一个月,没有污水覆盖的地面带着无数细小的褶皱和干裂的黏稠物痕迹,如同被烧灼的皮肤。
常年阴雨的小区穿过一条护城河,据说河底潜藏着一条巨龙,眼睛有自行车轮胎那么大,身上的鳞片结实,且通体发亮,它白天沉在淤泥里,夜晚出来活动。但这个据说很快就被推翻,理性的小区人民认为,这条河是人工开凿,没有天然的精气,河水浅,没有藏神兽的样貌。另外,河东人由于不通自来水,常在河水里洗衣服,于是河西人就往河里倾倒屎尿,后来河东人就不在河水中洗衣服,这是人性阴暗挤兑灵兽的证明。
理性的小区人民还认为,造这种谣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是要被执行绞刑的。可惜传说还在萌发阶段就被批斗,说自己看到巨龙的小孩,受到邻里的指责,被挂到树上供人瞻仰。撒谎者三次就基本毙命,不是因为撒谎,而是因为撒谎的人少。
在这个不具备美感的小区里,每座楼宇后面都有一排不通畅的下水道口,每个单元正对一口,源源不停地涌动着粪水,催生出了一片汪洋湿地。
在七号楼正面,是细长的瓦房车棚,居民代步工具基本是自行车或摩托车,共享集体车棚。车棚里分成两排,一排自行车,一排摩托车。车棚东段分割出一个小房子,供人居住。看自行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大家都叫他黄枪,而我每次想到要直呼其名都觉得极不合适,但同龄人又没有人称他黄叔。
这间破屋子像城市所有的破屋子一样,终日滚进一股小便的味道,人们成双结对地在各个墙角随地小便,每个人都可以用尿滋出一幅山水画。
我还记得那个神话覆灭的夜晚,想要给不具美感的小区缔造一个传说的黄枪儿子——小峰——高举着一个像龟壳的东西,大声嘶吼:龙鳞!
在一堆篝火的映照下,居民们各个脸红脖子粗,极力地要打压这个佝偻的少年。他们高声呐喊:龟壳!我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黄枪尴尬地立在那,又似乎听到小区里比我年纪稍大的愚蠢青少年喊着“龟头”的字眼。
先承认是龟壳,私下里你可以当作龙鳞。黄枪安抚自己的儿子说。
小峰愤怒地扫了一眼黄枪,黄枪脸上一阵惭愧。
小峰细弱的小胳膊乏力地颤抖着,龟壳仍高举头顶,换作我,龟壳也许早已摔到地上。他声嘶力竭:龙鳞!
伴随着居民整齐统一的讨伐声,我看到惭愧的黄枪把儿子捆上了树,他的眼睛在火光里闪烁了一下。也许连小峰也没看到黄枪面罩后面流下的眼泪。那是坚信不是龟壳的眼泪。
十几年前就丧失信仰的小区,不会允许一条浸泡在自己屎尿里的龙存在。
那天中午我穿着父亲的拖鞋,骑着一辆奇丑无比的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我每日都祈祷它被偷走,它看起来比废铁还要丑,只是有个形状,它一直到躯干即将断掉都硬朗地活在我的生活里。其实我完全可以不骑,然而在虚荣心和懒惰的斗争中,基本上都是懒惰控制了行为。
自行车从家中的院子里被推出来,在门框那咯噔一下,抖落些许红锈,这一个震动使得从院门到商铺的路上,都留下一条浅浅的淡红色痕迹,风一吹就变得更淡,斜斜地晕染开。
这条线是带着美感的,只是我在面条店遇到了裘子怡和她的好朋友,她们看我的第一眼,就注视着我那斑驳的大拖鞋还有那条长长的红色锈迹。之后的几年我每次回忆起那天中午都在想这件事。等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其实不会细致到那个层次时,也逃脱了伴随我整个童年的那份混合着大粪味道的羞耻感。
你干吗去?裘子怡的好朋友说。
原本打算在这个小卖铺购物的我愣了一下,掉转车头。
买面条。我说。
裘子怡和她的好朋友爽朗地笑了,尽管我知道裘子怡笑起来像个水果,我的脸还是嗖一下就红了,爆竹一样。我困扰的是,究竟是那双大拖鞋还是红色锈迹,让她们突然爆发出那么爽朗的笑声。
我骑着车绕过小卖铺的门,打算去另一家,但我的自行车并没有停止抖落锈迹。我想在她们的眼中,那必定是一个浑身围绕着微妙臭气的人还有自他的破车轮胎底下延伸出的一条线。
我一路都在想为什么要去买面条,因为何铁在我家。
七号楼距离学校很近,走路只有五分钟路程,家远的如果中午需要午睡,就去家近的同学家里。我不喜欢招待人,原因是母亲在六岁时就跟人跑了,这当然不是我父亲陈江告诉我的,是小区的嘴告诉我的。
小区的嘴长在街口。只要我想知道什么事情,便会来到小区的嘴附近,在心里默默念着想知道的事情,等待一会儿,就可以聆听到答案。这张从街口一棵柳树旁生出的嘴,夜色里包裹着一层雾气。小区的嘴是两个麻将桌,一桌中年女人,一桌老太太。夏天的时候,洗牌的声音咀嚼不停,老太太纷纷敞开衣襟。
小区的嘴告诉我,时间可以模糊掉性别。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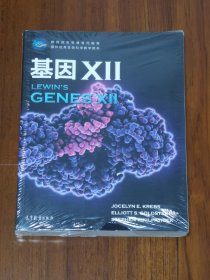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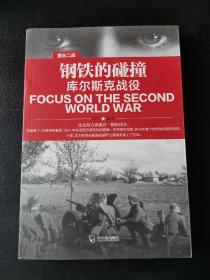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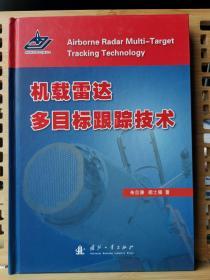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