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塔索尔9787540791025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2.35 4.7折 ¥ 48 全新
库存4件
作者[智利]比森特·维多夫罗著,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ISBN9787540791025
出版时间2021-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31218397
上书时间2024-11-06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比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1893-1948),生于智利圣地亚哥,诗人,创造主义诗歌流派创始人。他和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及巴勃罗• 德罗卡并称为20世纪智利的四位诗人。
译者李佳钟,生于1994年。于四川外国语成都学院。短暂停留过西班牙和拉美。现居成都。
目录
诗歌
阿尔塔索尔
序
第一歌
第二歌
第三歌
第四歌
第五歌
第六歌
第七歌
天空的震颤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由《阿尔塔索尔》和《天空的震颤》两部诗集组成。出版于1931年的《阿尔塔索尔》是维多夫罗最富盛名的作品。这部创造主义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先锋诗歌之一。全诗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似乎是天神的阿尔塔索尔带着降落伞从天顶跳下,坠入深渊,最后疯癫发狂的故事。在这包括序言和七歌的降落伞之旅中,有气势磅礴的寓言史诗,有无尽柔情的女性颂歌,有构思奇巧的文字游戏,有故意为之的漫长折磨,有破碎之时的声嘶力竭。
《天空的震颤》以更为灵活的散文诗形式,描述了主角在对“伊索尔德”的不断呼唤中,在不断的前行中,一步步走向末日的故事。在诗人自己看来,这部作品是对《阿尔塔索尔》的补充,“更成熟,更有力,更完整”。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人的创作理念,本书还收录了1921年维多夫罗在马德里文化协会的演讲选段。1931年《天空的震颤》首次在西班牙出版时,该选段收录作为序言。
精彩内容
天空的震颤首先必须知道,我们应该多少次抛弃我们的新娘,从无休止的性爱中逃离,直到世界的尽头。
在虚空越过地平线划过它小提琴的琴弓之处,那人变成一只鸟,和奇石中的天使。
永恒圣父在他的实验室中制造了黑暗,使盲者耳聋。他手握一只眼睛,不知赠与何人。在他的一个广口壶里,一只耳朵和另一只眼睛在交媾。
我们身在远方,在尽头的尽头,那儿有人的双脚倒挂在一颗星星上——他在宇宙中头部朝下,晃来晃去。折弯了树的风,在甜蜜地吹拂着他的头发。
飞扬的溪流休憩在崭新的丛林中——鸟群在那里咒骂黎明开出了多少无用的花。
它们准确地辱骂那些黑暗事物的悸动。
假如仅仅是把繁花的领袖斩首,并让那有着多余的情感,充满着秘密和宇宙碎片的心脏流血。
在一面鼓上一个被爱之人的嘴。
那令人难忘的女孩的双乳被钉在树上,夜莺将其啄食。
和极点上的英雄雕像。
毁灭一切,一切,用子弹,用刀。
偶像们在水下争斗。
“伊索尔德,伊索尔德,我们相隔到底多远,我们之间曾有过多少欢愉?”你知道上帝剜去了花的眼睛,它的躁狂症就是因为失明。
他还把精灵变成一堆羽毛,把坐在玫瑰上的新娘们变成了自动钢琴的蛇,变成了长笛的姐妹蛇——那根长笛会在雪夜里被亲吻,并在远方将其呼喊。
但你并不知道为何乌鸫要把那棵树撕碎在它流血的指间。
而这就是一个谜团。
四十天四十夜在洪荒的枝叶中攀爬。四十天四十夜在岩石和高峰间的谜团。
我会在一个又一个命运中坠落,但我会始终保留天空的记忆。
你可曾了解高处的景观,可曾见识过闪光的心灵?有时我会化作一片巨大的丛林,巡视整个世界,如同检阅军队。
看呐,那些河流的入口。
在某些午后,大海几乎就是我的舞台。
在梦境的街道没有树木,也没有被钉在花上的女人,也没有划过大海篇章的船。
在梦境的街道有个巨大的肚脐,那里隐约可见一个瓶子。在瓶子里有个死去的主教,瓶子一动,他就变色。
四根蜡烛不断地燃起,又熄灭。有时,借着闪电我们能看见空中有个破碎的女人,一百四十年前她从空中跌落。
天空藏着她的谜团。
每层楼梯都可能藏着一个杀手。那些有心脏病的歌手一想到这,就被吓死了。
如此,那些病态的蝴蝶将变回幼虫,它们甚至觉得自己从来不该破茧而出。听觉遗失在了童年,并被大海的回声和漂浮在某些飞鸟眼里的海藻填满。
只有伊索尔德知晓这个谜团。但她只是用她颤抖的手指检查彩虹,来寻找一种特别的声音。
如果一只乌鸫啄食她的眼睛,她也会带着那吸引水牛群的微笑,让乌鸫尽情吃喝。
在所有的海洋中,在每一朵浪花里,你能在怎样肿痛的心上漂流?
因为你应当知道,像浮标一样紧贴心脏是危险的,因为海里的岩洞将它们吸引,纠缠如蛇如象鼻的章鱼永远封闭着它们的出口。
你发现那是一座高举双手的山峰在祈求谅解,它觉得海洋没那么危险,比友谊更为可及。
然而,你的目标是爱上危险,你身内身外的危险,亲吻深渊的嘴唇来祈求黑暗的帮助,让你所有的事业凯旋,所有沾满晨露的梦想实现。
否则,你还是道谢,然后就退到人类记忆的深处吧。
“伊索尔德,伊索尔德,在冰河时代,熊曾经都是花。当冰雪化开,它们终于自由,奔向四面八方。”想想复活。
只有你了解奇迹。你见识过发生在一百个精美的竖琴和所有瞄准地平线的大炮前的奇迹。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一个国王带领着一队水手。海浪在不耐烦地等待他们的归来。与此同时,大海也在鼓掌欢迎。
温度计缓缓降低,因为乌鸫已经停止唱歌,并想着要从吊杆飞向世界的中央。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你从电灯或是某个花瓶里逃离,并跟我用雄辩的术语对话,如同午间的洋玉兰一样对话。房间里满是垂死的蜻蜓,我不得不坐下,以免失去意识跌倒在地。死亡将会是思考本身。眼睛归来的地方,到处都是反射。
在城堡上,将军的骨架将作为交通信号灯发出信号。我们将清点那些无人可认的头颅——那些被一根无止境的绳索绑在那无人认领的梦游的马尾上,拖拽于旷野之中的头颅。
那些黑奴会在和他们醉得差不多的女奴肚子上鼓掌,并没有注意到风是一个幽灵,而远方的树漂浮在一片墓地之上。
谁清点过所有的死者?
是否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是否所有的灯都开始歌唱,是否那片墓地开始燃烧?
每一只天空中的鸟都将会在大地上拥有一个猎人。
号角将会响起,旗帜会化为孟加拉烟火。信仰死去了,所有那些啃食你心脏的猛禽都死去了。
迁徙的雕像飞行而过。
在广阔的平原上,可以听到树木歌声中那些偶像遭受的折磨。
花惊恐地逃离。
一个未知的音乐之门打开了,那些年岁奔逃而出——它们属于一个垂死的巫师,他双手交叉于胸,颓然地坐着。
在我们内心,有多少东西已经消亡了。我们给自己带来了多少的死亡。为何我们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尸体?为何我们要固执地复活自己的尸体?他们会阻止我们看到新诞生的想法。我们害怕显现的新光芒,害怕我们还不习惯它,就像我们害怕自己静止不动又没有危险的意外的尸体。必须为了生者放弃死者。
“伊索尔德,埋葬你所有的死者吧。”思考吧,记住吧,遗忘吧。愿你的记忆忘记它的记忆,愿你的遗忘记住它的遗忘。在你的死亡到来之前,小心,别死了。
如何给这只现实的野兽增加一点点崇高——它只会在深夜时分屈下它疲惫的膝盖,那时月亮会飞翔而来,伫立于此。
然而,我们都在苟活中等待一个偶然,等待在远方的救赎中恒星符号的形成,那里我们无法抵达,甚至无法听到我们的钟声。
就这样,等待那巨大的偶然。
愿北极点分崩离析,如同致敬时脱下的帽子。
愿那片大陆升起——我们已经坐在地平线的铁栏后面等待多年。
愿杀手疾行而过,无所顾忌地射击那些追捕者。
愿人们能知晓为何是那个女孩出生,而不是那个被梦境许诺并多次宣告的男孩。
愿能看到那个在地下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的尸体。
愿能看到那个光荣的幽灵在天空的树丛间穿行而过。
愿所有的河流能被一声令下突然停下。
愿天空会随着地点而变换。
愿大海堆积在一个巨大的金字塔里——它比所有那些野心壮志所梦想的巴比伦塔都更高。
愿绝望的风吹灭那些星星。愿发光的手指在夜空中写下一个字。愿对面的房子轰然倒塌。
我们为此而活,相信我,我们是为此而活,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为此,我们发出声音,为此,我们的声音连结成网。
为此,我们的静脉里有着痛苦的奔逃,胸中有着受伤动物的飞驰。
为此,词语殉难的肉身变红,由地下河浇灌的思想生长起来。为此,那惊恐的嚎叫声是继承自最悲剧的祖父。
砍掉那在睡梦之门咆哮的怪物的头。这样,再没人能禁止任何事情。
有人在诉说,一株虞美人则盛开在声音的顶端,盛开在来自未来目光的鸦片闪耀之前。
“大地的平静献给夜晚的水手。”沉默的探索者们抬起了头,旅途则脱下了它华服。
这是日落的含义。
或许日落会倾听我们的声音,你们也终将明白夜晚的符号。你们终将明白沉默的创造。那梦境的目光。深渊的初始。山峰的迁徙。
那夜晚的穿越。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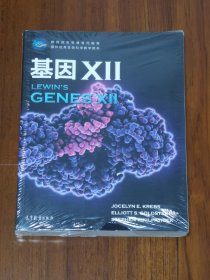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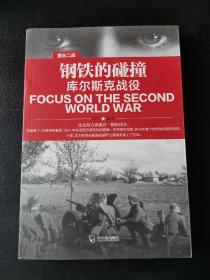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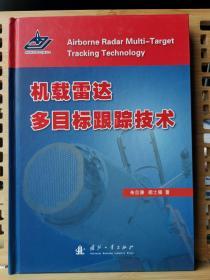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