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耳甫斯诗译丛~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9787544799249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34.8 6.0折 ¥ 5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奥地利]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99249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2067651
上书时间2024-11-06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新浪漫主义派及象征主义派诗人、剧作家、散文家。
出生于维也纳,是富商后裔、受封贵族,亦是文坛传奇。
16岁开始发表作品,其诗呈现出罕见的轻盈俊逸和宛如天成的精致完满,随即赢得了“神童”的雅称。后主要转入诗剧的创作,以《昨日》《提香之死》《愚人与死神》《白扇记》为代表,延续了与诗歌相同的主旨和风格。“生命,梦幻与死亡”这个主题,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晚期致力于革新古希腊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和巴洛克戏剧,改编了多部古希腊悲剧。后与马克斯·莱因哈特等人一起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并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写了多部歌剧,如《玫瑰骑士》《失去影子的女人》《埃及的海伦娜》等。
李双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教授。长年往来于欧亚两端,出入于汉德两语,受文学之魅惑,求审美之精微,研磨词句,探求奥义,不问春秋。尤其心仪于德语文学中的浪漫派、颓废美学、现代主义经典。译有《现代诗歌的结构》《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比利时的哀愁》《荒原狼》《所有的桥都孤独》,以及《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合译)等。著有《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目录
纪念霍夫曼斯塔尔(托马斯·曼)
诗
春尚早
有此一生
世之隐秘
三行体
外部生活之谣曲
强大魔力之梦
有的人自然……
两人
生命之歌
你的面容……
沉夜不祥
寄语
对话
旅歌
短歌三则
幸福之屋
天将晓
风景中的少年
交游之群
一个男孩
写给一幼童的诗行
少年与蜘蛛
中国皇帝说
祖母与孙儿
船上厨子,一位囚徒在唱:
年迈男子对夏日的渴慕
世界是什么?
有问
为我……
你可看到那城市?
思想幽灵
繁花满树
一个亡灵的阴影……
致一位匆匆而过者
我的花园
花园女工的一双女儿
云
晨昏朦胧雨
梅露西娜
当那夏日早晨清冽地……
生命,梦幻与死亡……
我熄了那灯……
孩子的祈祷
从船上走下
世界与我
因为我知道……
“作品”是死的岩石……
在我走近,在我落脚之处……
春日里的黄昏
南方的月夜
箴言诗
诗剧
昨日
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第五场
第六场
第七场
第八场
第九场
第十场
提香之死
愚人与死神
白扇记
散文
谈诗
内容摘要
“我们是用造梦的材料造成。梦如此睁开双眼,好似樱桃树下幼小的孩子。”作为新浪漫主义派及象征主义派诗人、剧作家、散文家,霍夫曼斯塔尔被视作才俊早成的“伟大奇迹”。16岁开始发表作品,其诗呈现出罕见的轻盈俊逸和宛如天成的精致完满,随即赢得了“神童”的雅称。他是19世纪末维也纳炙手可热的少年诗才,唯有彼时的济慈和兰波可比肩。
《风景中的少年》由诗歌、诗剧、散文构成,为国内首次全面译介霍夫曼斯塔尔。这个赫尔曼·布洛赫推崇的“现代那喀索斯”,一如希腊神话中那个化为水仙花的少年,他用美编织出光华与颓败,恋生与念死缠绕的绮丽之梦。“生命,梦幻与死亡”这一主题,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他执意写出唯美与枯萎和速朽之间的宿命般的关联,并呈现出罕见的梦之质地。
茨威格、里尔克尊他为时代的首领,他是那个时代☆精美也☆纤弱的文化符号,象征着逝去的“昨日的世界”,是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前☆后一缕瑰丽的余晖。
精彩内容
春尚早春风轻拂
穿过空寂无叶的林道,它的拂动含着一些事物异常奇妙。
它低回之处曾有过黯然哭泣,它曾掩入过揉得凌乱的发里。
它摇落过金合欢盛开的花群它沁凉过呼吸着的灼热躯体。
欢笑着的嘴唇它也曾轻轻触及,柔滑的廊道不眠,它从中穿梭而去。
它滑过了那管笛仿佛一声幽泣熹微的绯红霞光它倏然掠离。
它默然飞过絮絮私语着的屋室它俯首之时悬挂灯的微光尽熄。
春风轻拂
穿过空寂无叶的林道,它的拂动含着一些事物异常奇妙。
它拂过的林道光滑而空寂
它催驰着
苍白的影子。
还有它携带的香,从它所来之地从昨夜起开始拂临。
有此一生
薄暮时刻的山谷盈满银灰色的芬芳,仿佛云丛筛下的月色。夜却未深。
伴着这沉暗山谷银灰色的芬芳我暮色般的思绪渐趋朦胧,静默中我沉入那纵横交织的透明之海,离开了生活。
那里曾有多么美妙的花朵于花萼上幽然而炽烈!透过草木之丛,有绛黄色的光,仿佛自明玉而来以阵阵暖流奔涌闪动。这一切渐渐盈满波澜深垂的忧郁音乐。而这我当时已知晓,虽然我至今不曾解悟,可是我已知晓:这就是死亡。它化作了音乐,带着狂烈的欲求,甜蜜,幽然而炽烈,近似于最深沉的忧郁。
可是多么奇异!
有一种无名的乡愁怀想着那生活在我的灵魂中无声地哭泣,它哭泣好似某个人黯然泪下,在他黄昏时分乘着有黄色巨帆的庞大海船于幽蓝的水上驶过了那座城市的时刻,那是他的父亲城。这时他看到了条条小巷,听到了淙淙井泉,嗅到了簇簇丁香的芬芳,看到了他自己,那个立在岸边的孩子,有着孩子的眼睛怯然欲哭的眼睛,他从那敞开的窗子看到了他自己房间里的亮光——可是那庞大的海船却载他于幽蓝的水上无声地滑向了远方船上有形状陌生的黄色巨帆。
三行体一 关于消逝我还可以在我的脸颊上感觉到她的呼吸:怎么可能,那些切近的时光竟成遥远,永不可及,消失了踪迹?
这是无人能彻底解悟的一件事,它太过可怕,远甚于人们的那些哀怨:一切都会滑落,匆匆奔逝。
而我之自我,无从阻留,从一个幼童脱出滑落至此让我感觉正如只狗,沉默且陌生,令人悚惧以及:百年之前我已在而我的先辈,身着死亡之衣,与我相似,犹如我自己的头发,如此与我成为一体如我自己的头发。
二那些时辰!当我们朝那海水的淡蓝凝望,理解了死亡,如此轻松而庄重,毫无恐惧之感,如同面容格外苍白的小女孩有着大大的眼睛,总是觉着体寒在一个傍晚默然端视前方她们知道,生命现在正静静从她们沉酣的身体流向树木青草,她们带着浅淡的微笑将自己装扮如同一个圣女,献洒自己的鲜血。
三我们是由造梦的材料造成,梦如此睁开双眼
好似樱桃树下幼小的孩子,那树冠间满月正凌然启步开始穿行庞然之夜的淡金色旅程。
……我们的梦也如此浮现,如此存在,生动盎然如一欢笑的孩子,它们飞升它们飘落,气势不凡,毫不逊色于从树冠间苏醒的满月。
内心最深处敞开以待它们编织;好似幽灵之手栖居于锁闭的屋室它们栖居于我们而始终拥有生命。
于是三者合一:一人,一物,一梦。
你的面容……你的面容满载了梦。
我静默并在无声的颤抖中看你。
此情如何升起的呵!我曾经在早年深夜将全部身心付与明月和钟爱至甚的山谷,那里空旷的斜坡上四散着
瘦削的树木而其中穿行着
小团小团低垂的云雾透过静谧传来永远清新也永远陌生的银白色河水放出的潺潺之音—此情如何升起的呵!
它如何升起!那种种物类和它们的美——无所孕育的美——曾让我满心渴慕,纵身相与,正如现在一心只看你的头发和你眼皮眼睑间灿然的光华!
外部生活之谣曲而孩子们成长,双眼深邃,他们一无所知,成长然后死去。
而所有人走各自的路。
而甜果由涩果育化成而后于深夜坠落一如死去的鸟
而后横陈些许时日随后腐烂。
而风时时在吹拂,而我们一次次听闻着,说出许多话语而又感觉着躯体的欢欲与倦意。
而街道在草中穿行,而地点在此在彼,载满火把、树木、水塘,其势逼临,而又凋萎将死……为何将这些建起?而彼此迥然相异?而又如此繁多,难计其数?
什么在转换欢笑、哭泣与苍白的面容?
这一切以及这游戏于我们又有何益?
我们这些俨然不凡而又永远孤独者漫游逡巡而不问目标所在的人?
纵然洞察这许多,又有何益?
而那说“黄昏”的却已道明了许多,从这一个词中流淌出了哀伤与深意正如中空的蜂房里流淌出沉重的蜂蜜。
强大魔力之梦有王者的矜贵,远胜于一束珍珠之链有勇者的凛然,犹如晨芬中的年轻之海这便是一场宏伟的梦——让我有如斯体验。
从敞开的玻璃门中有风吹过。
我睡在平旷之原的凉亭中,而从四扇敞开的门中有风吹过——而之前已有众马披鞍越门而去,还有成群的狗结伴驰掠过我的床前。然而那魔术师的面容——那至先者,那强大者——却倏然降临于我与一面墙之间:他的颔首傲岸,他的头发有王者之相。
而他的身后不复有墙:尽现出一片壮阔宏丽,悬崖临谷,深海暗沉牧原青葱,都在他手后生成。
他俯身,将那深渊引来。
他俯身,他的手指伸入地面之下,仿佛地面是水。
从那细流的泉水中却有硕大乳石凝成于他手上随后又盘旋落下,铮然作响。
随后他轻甩腰肢,跃身而起——仿佛仅是凭了骄傲,朝下一处礁石而去;在他身上我看到重力的威效尽失。
在他双眼之中却是宝石所含的沉睡——而富于生机的宁静。
他坐下,说出这样的一个你向着那些时日,我们似乎已永失的时日,于是它们归来,满怀着哀伤,气势宏大;魔术师为此而乐,且欢笑且哭泣。
他梦幻般感觉着所有人类的命运,正如他感觉着自己的肢体。
对于他,无一物近无一物远,无一物大无一物小而其下那大地已凉却如许,那深渊的黑暗向上逼临如许,那夜将树冠上的温润气息拨弄如许,他享受着一切生命的宏大之行如此欢畅—便带着庞然酣醉如一头雄狮般,越过礁石。
*****天使与至尊的主是我们的灵——他并不栖居于我们,在上空群星中他放下了座椅,而任我们如弃儿孤苦伶仃。
然而他是我们最深的内核里的火—我有如此预感,当我将此梦寻获——并且与那远方的火群叙说而活在我之中,一如我活在我手中。
风景中的少年园工清空了他们的苗圃,许多乞丐散在四处眼前蒙黑,手撑拐杖——可也手持竖琴和新开的花,有柔弱的春花浓烈的香。
赤裸的树让万物尽览:往下看得到河流,看得到集市,和许多在池塘旁游戏的孩童。
他缓缓穿过这一片风景感到了风景的强力并知道——世界诸多命运与他相系。
他走向那些陌生的孩童准备着越过未知的门槛以仆役的姿态引入一个新的生命。
他不曾动过心念,不会看重他灵魂的财富,往昔的路与回忆交缠的手指和交换过的灵魂
那不过是份不足道的财物。
花香只向他讲述陌生的美——而新的空气他静静呼吸纳入,却无渴望:他可为人效力,唯此让他欢欣。
致一位匆匆而过者你曾让我恍然何物在我心中暗藏你曾是这心灵的琴弦上那夜风在低声呢喃仿佛是呼吸着的深夜那谜一般的呼唤当屋外流云飞散当梦中人醒这迫近的相临涨漫成一片辽远而柔软的蓝月前杨树林里涌过一阵轻微的战栗诗剧愚人与死神【片段】序幕:在塔楼林立的维也纳古城,那棱堡散布,侍童、信使穿梭的城,住着四位诗名高蹈、才华奇伟
却完全不为人知的诗人,其名为:巴尔达萨、斐兰特、
加里奥托与安德里亚。
巴尔达萨从医;此外他还会在一架小小的仿造的立式钢琴上演奏,就着曲谱弹起甜美的儿歌,矫情的小步舞曲或是严肃的赋格。
加里奥托倒是拥有一套傀儡剧:他会在朋友前演出傀儡戏,技巧精湛地牵起拉线,让木偶演绎宏丽而极为梦幻的哑剧,其中有皮耶罗和柯伦班有阿尔莱辛和斯美拉丁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儿连死神本人也亲自上场以及天堂里那条蛇。
第三位是斐兰特:这位有一只美丽的身材修长、毛色淡黄的猎犬,名叫米莱奥。最年轻那位是安德里亚:他的财宝是一本大而老且厚的书:《罗马人传奇》,书中满满都是最美的古老童话和奇幻的故事,满满的古典时代轶事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智慧。
谁若拥有这书,那么《圣经》也好,山鲁佐德的童话也好,神圣的传说也好都不用再读,不用读柏拉图不用读教会元老,不用读乔万尼·薄伽丘的寓言,因为这一切他书中都有,一切智言,一切蠢事交汇得缤纷斑斓,格外奇妙。
这四人如今结为好友,每逢星期日的午后,趁那春日午后温煦而光亮满眼,他们便相聚于一处闲聊。
在一个宁静而蔚蓝的星期日午后则有如此一事,在巴尔达萨的内室,他自己和唐·斐兰特卧在敞开的窗户旁
酣梦半醒,同时那良伴小狗米莱奥正将头儿枕在小爪儿上睡得呼吸低沉。必是一场噩梦惊扰了它,因为它正低低怯怯地呻吟,直到它的主人将它唤醒,而它便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感激地看向他。这只忧郁小兽的这些呻吟
就如同一种陌生强力吹拂而过。两个友人的灵魂中那幽暗的琴弦被触动,在朦胧的兴奋与惊惧中颤动不已,从他们灵魂的门槛升起了那些深邃的梦带着与生俱来的人生
恐惧。闷热而迷乱的春风里飞入了他们的幻想:“仿佛我们血管中奔涌着的沉暗的血
无意义,无可救药,无从把捉,在一次呼吸之际便可诞出死亡;仿佛它能将那最高也最神奇的狂热极乐赠予,是既往之生
莫大无垠的喜乐,一切生者都无从领受”……这幻想变得愈加黑暗,滋长着残酷,直到巴尔达萨满怀忧伤坐在了羽管键琴前用幽沉的小三和弦奏出饱满的渴慕与翻腾的痛感
将幻想的重压释放掉。
有沉沉而庄重的声波幽然炽烈地从窗口飘浮而出,又闪耀着消散于圣卡尔教堂穹顶上方的春日夕照中。
当此之际另两人正约好了在加里奥托的房中相晤,为的是从那里出发两人同行去巴尔达萨家。
这住宅坐落在沃尔采乐街,是座古旧而有岩石灰色的幽暗房子,窗前配着凸肚状铁栏;在大门门柱顶端狄安娜与恩底弥翁在左,英雄科里奥兰纳斯在右,(他脚边躺着他的母亲,那血统格外高贵的妇人),都是由灰色石头雕成。
这门柱的左右两侧是窗明几净的小店:左侧一个园艺匠,一个拿着
美丽古董讨价还价的犹太商人。在这两家店里那两个友人总会驻足:加里奥托站右边:那儿正有一只象牙制成的兽诱惑地露齿而笑,来自中国神佛家中犬;出自多纳泰罗一派之手的女子青铜雕像也有不小吸引力而最吸引人的是大座钟,因一流大师布勒添了装饰而增色,那表盘四周有了金属小人儿环绕移动,做报时的轮舞,领头的是扛镰刀的萨图恩带着意味深沉的神情。
此外还有堆积在一处的形态奇异的兵器,波斯人的马鞍,摩尔人的匕首,来自哈勒,满是铁锈的古老斧子,嵌着金线刺绣的丝绸布匹,迈斯纳出产的瓷器小人儿和旧得已泛黑的画。
安德里亚则最喜欢在另一边立定那里有带耳柄的高罐,装满红色玫瑰、
罂粟和颀长的火百合,还有那些碗,碗中上千朵暗色丝绒质地的紫罗兰托着熟葡萄,泛出金色暗红,也有浅浅轻轻的篮筐,填满丁香和金合欢。
因为星期日的缘故,谁都不愿禁止自己获得一份小乐趣。加里奥托买下一把玲珑小巧的锋利匕首;蓝色的刀刃是托莱多的钢材,装饰着
《古兰经》的箴言和阿拉贝斯克花纹。
安德里亚则买了玫瑰,一大捧松松束起、颜色明媚的粉色玫瑰。这一位将花儿插在自己腰带上,另一位则插入了他的武器,转身离开。
但是加里奥托说:“玫瑰和一把匕首,安德里亚,是一出戏剧的结局和开端。”但安德里亚还迟迟没有作答,因为他寻思着
某只甲虫的名字,它那金绿色的,闪耀着蓝光的鞘翅他可以用来与圣卡尔教堂的穹顶相比,后者的光辉此刻正投过来,因为他钟情于比喻。
他们便沉默不语地往前走走过宁静的星期日街巷,在这街边黑色的山墙和巴洛克式的石质阳台上方悬着春日蓝天,默默不语,那么明亮,俯首看向此间。
当他们走到离巴尔达萨家仅仅几步远的地方,那起起伏伏的幽暗声波从窗口涌来,这两位只觉得这声响仿佛是普遍之美中最后也最美的一个不知不觉思念起的音符。
安德里亚便将松散的玫瑰扔入了这声响的炽流与颤抖中,扔进了窗,作为他们到达的信号,好似一位阔绰的主人让小小的红色侍童跑到路上,传达他来临的讯息。
屋中两人还沉浸在不知起自何处的忧郁中而另两人的欢笑却已闯入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为何缘故如此开怀。
但是他们四人都明白,被轻轻打动的灵魂
正如琴弦上一次小小拨弄在生活的幽暗之手中……此时暮色已降下;在方才还明亮的天空里,在黑色的屋顶上浮起了银光灿烂的月亮,而好狗米莱奥却怀着敌意立起身来狺狺低鸣而向它凝望,仿佛一个黑暗妖魔怀着敌意凝望一朵圣洁
莲花的银色盛放。
红色蜡烛的金色火焰被这群友人点燃,于是安德里亚为他们轻声读起一则短小而别有格调的死神轮舞的喜剧。
出场人物:死神克劳迪奥,一个贵族他的随身仆人(以下皆为亡故者):克劳迪奥的母亲克劳迪奥的一个情人一个他年少时的友人克劳迪奥的府邸上个世纪20年代的服装克劳迪奥的书房,装饰是旧帝国的风格。在背景中左右都有大窗。中间是通往阳台的玻璃门。阳台一侧有外挂木梯伸向花园。左侧一扇白色的单页门,右侧同样一扇门,门内是卧室,被一张绿色的天鹅绒帘幕遮住。在左侧窗旁边放着一张书桌,桌前一把扶椅。靠着墙柱摆着装有古董的玻璃盒。右侧墙边是一个暗色雕花的哥特式大箱子;箱子上方挂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乐器。还有一位意大利名师所做的画像,暗得几乎发黑。壁纸的基本色调是明亮的,几乎呈白色;镶嵌着石膏和黄金装饰。
克劳迪奥:独自一人他坐在窗边。夕阳余晖满地。
最后一脉青山也披上了晚照,盈满霞光的空气如湿润的珐琅将它笼罩,一圈雪花石膏质地的云环悬挂
在高空,投下灰色的阴影,镶着黄金的边角:早些时代的大师正是这般描画云彩,让它们托举圣母马利亚。
山坡上洒落了蓝色的云影,广阔的山谷中充盈着山影又蒸腾成草地的浅绿与光辉;山顶在饱满的余晖中灿烂晶莹。
我的渴望如此移近了那群人,他们住在广阔山坡上远离众生,用手采摘的物产是他们肢体的有益疲乏换来的收成。
狂野的晨风奇妙非凡,赤脚奔跑过原野的芳香,唤醒了山民;围绕他们的是野蜂和神的空气,温热,光亮。
是自然让他们为之忙碌,他们所有的心愿里都有自然流露,清新与疲惫的力量交相轮替印记于他们每一份温暖的幸福。
现在黄金球缓缓移动,它沉落于最远的海那泛绿的水晶中;最后一点余光在远树间闪烁,现在红色烟雾正氤氲,热流涌过,填满沙滩,那诸多城市坐落的地方。
它们浮出水面,借水仙娜雅得的臂膀
在高大的船中轻晃自己的孩童,那一族民众,鲁莽,狡黠,出身不凡。
他们滑行于那遥远、奇迹般沉重、
沉默不语的水波,从没被龙骨劈开过的巨洪,狂野之海的愤怒激荡着他们的心胸,随即治愈了其中所有的疯癫与苦痛。
我便这么看着真义与福乐在远处铺展满怀着渴望不停地凝视彼岸,可当我的目光滑到了近物的近旁,一切变得单调,让人难堪,郁郁寡欢;看来我的整个被迟误了的人生,丧失了的情趣与从未落下的泪水,都交织在了这窄巷,这房屋的周围,还有永无意义的寻觅和纷杂的欲念相随。
散文【节选】谈诗除了自己在抒情诗歌中饶有成就的少数人之外,现在在德国找不到五个能对灵魂这最温柔的生娩有所判断的人。
—赫贝尔加布里尔:我为你在窗台这儿放了一本诗集。
克莱门斯:是济慈吗?
加布里尔:不是,是德语的诗歌。这些诗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正是这样编排的。这个整体名字叫作《灵魂之年岁》。这里写的是秋天。这本诗集从秋天开始。
马蜂们身披金绿色的羽鳞,飞离了紧闭着的花萼,我们乘轻舟以阔弧环绕披覆铜棕色叶子的岛群。
克莱门斯:这是秋天。可是你要么一次读完要么就别读。
加布里尔:你能静心细听吗?
来这诉说着死亡的公园看望:远方微笑着的海闪烁的微光,照亮了水池与斑斓小径的是无瑕的云朵那不期而见的蓝。
去那里摘取桦树与杨树的深黄摘取它们的淡灰:轻风熏暖,迟开的玫瑰尚未完全凋萎,将它们折采,亲吻,编成花环。
也别忘了最后的紫菀,那紫色在野生葡萄的藤须四周不论绿色生命有何遗留且在秋天的面容中轻轻忍受。
克莱门斯:真美。这首诗呼吸着秋天的气息。虽然“无瑕的云朵那不期而见的蓝”这样的说法挺大胆的,因为那激发欲求的夏日般的一湾蓝色本来是在云朵之间的。当然只会在无瑕的云朵的边缘。除此以外,秋日天空就是一整片阴沉密封的景象。歌德会喜欢这“无瑕的云朵”的。而“不期而见的蓝”无可挑剔。真美。的确,这就是秋天。
加布里尔:你还想要更多的秋天的诗吗?
大门上铁百合锈迹斑斑,从门口有鸟群飞离,飞往被遮盖着的草地而其他鸟儿在门柱上瑟瑟发抖从中空的花朵之瓶中啜饮雨滴。
还要再来一点吗?
我们寻觅没有阴影遮覆的长椅—我们在悠长柔和的光芒中振奋如新,我们心觉感激,当簌簌轻响之际从树冠间有光亮之痕滴落身上,而凝然注视并倾听,当那些成熟的果实时不时地将大地敲击。
克莱门斯:我求求你:要么就读完整整一首诗要么就干脆不读。
加布里尔:你想要冬天的诗吗?你想要夏天的诗吗?想要夏天那四处冒险的欲望?夏天的沉郁忧伤?夏天的清晨?夏天的黄昏?
我们漫游的这座山丘,已卧在阴影中,另一侧的此刻却还在明光中生气弥漫。
只是当白色的微云飘浮,月光才洒上它柔软的绿色席毯。
绵延至远方的街道渐趋灰淡,漫游者因为一阵低语而驻足:那是山间一泓无法为人所见的水,还是一只鸟儿在将它的眠曲呢喃?
只是当白色的微云飘浮,月光才洒上它柔软的绿色席毯……克莱门斯:我看到了我童年时代的一片风景。这似乎是一本美好的书,这本《年岁》。到底为什么是“灵魂之年岁”呢?我喜欢简练的标题。
加布里尔:我也喜欢简练,正因为此我才觉得这个标题如此出色。因为这里是一种秋天,又不仅仅是秋天。这里是一种冬天,又不仅仅是冬天。这些季节,这些风景,无非是另外一些的承载者。
难道那些感觉,那些朦胧的感觉,我们的内心中最普遍而最深挚的状态不正是以最奇特的方式与一种风景、一个季节、一种空气的特质、一抹气息交织在了一起?你从高高的车上跳下时的一个特定动作;一个了无星光的郁热夏夜;房屋过道里的潮湿石块的气味;喷涌的泉中冰凉的水冲刷你的手时带给你的感觉:你拥有的全部内在与这样的数千个尘世之物联结在一起,你所有的激奋,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沉醉莫不如此。不仅仅是联结:你的内在以其生命之根牢牢地与它们错结生长,如果你用刀将它与这一土壤割断,它就会溃塌萎缩,从你的手间消失于无形。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自我,那我们就不可沉入我们的内心:在外界才可找到我们自己,在外界。正如并无实质的彩虹一样,我们的灵魂跨浮于存在那不可阻挡的下坠之上。我们并没有拥有我们自身:它从外界拂入我们。它从我们逃遁已久,在一股气息之中回归了我们。虽然这是—我们的“自身”!这一个词是如此的一个隐喻。过去曾经在这里筑巢的激灵回归于此。可它们还是当时的它们吗?难道这些回归的不更像是当年离去者的后代,不更像是被一种幽暗的乡思所驱使才回到这里的后辈子孙?总而言之,有一些东西回归了。而有一些东西在我们心中与另一些相遇了。我们无非就是一个鸽棚。
克莱门斯:真奇特,你的思绪居然会走到这样一条路上。而我所想到的却是沿着另一条思路,完全不同的一条思路:很难不去怀疑,在人性的禀赋中是否有某种实质存在。而可怕的是,我们要对外在性的强力进行斟酌:写一个剧本必然是无以复加的艰难,而审判一个凶手必然是无以复加的艰辛。
加布里尔:可是奇妙的是,我们的存在所具有的这种结构与诗歌是如此契合:因为它可以不再拘囿于我们心灵的狭室里,而是居住在渺然阔大、无穷无尽
相关推荐
-

俄耳甫斯诗译丛~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全新广州
¥ 23.87
-

俄耳甫斯诗译丛~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全新嘉兴
¥ 23.27
-

俄耳甫斯诗译丛~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全新广州
¥ 22.57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北京
¥ 28.33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北京
¥ 28.29
-

俄耳甫斯诗译丛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
全新烟台
¥ 34.02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北京
¥ 28.37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泰安
¥ 32.10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佛山
¥ 26.40
-

风景中的少年:霍夫曼斯塔尔诗文选(俄耳甫斯诗译丛)
全新南昌
¥ 23.98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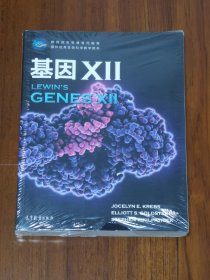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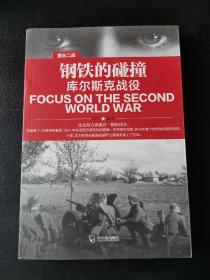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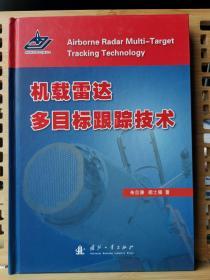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