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地风雷(1995-1997刘庆邦短篇小说)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1.48 5.4折 ¥ 40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刘庆邦
出版社上海文艺
ISBN9787532163663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0元
货号30213682
上书时间2024-05-25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目录
新匪
三月春风
兄妹
小呀小姐姐
人生序曲
泥沼
群众演员
远足
离婚
心事
阳光
人畜
鞋
少男
种高粱喂鸽子
平地风雷
五月榴花.
红果儿
野烧
打手
灵光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这套书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编年卷,一共是6卷,这是第3卷。按照年代先后,选取了作家1995到199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仍然在煤矿题材和乡村题材两类上努力。并继续在极善和极恶的两端,对人性做着充分的挖掘。这一时期的小说可谓题材多样,不拘一格,风格多变,可以看出作家这一时期在不断夯实自己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在挑战和开拓着自己,向着各种故事和人物进行着深入的开掘,因而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被困在井底的老马,内外反差极大的打家劫舍的土匪,等等。
精彩内容
\\\"平地风雷这地方把杀人说成做活儿。你把他杀了,就是把他的活儿做了。我要杀你,就是准备做你的活儿。大家称赞某个人杀人杀得好,一般也不使用杀这种直白的字眼,只说那人好手段,活儿做得干净漂亮。
村里人传说,货郎要做队长的活儿。
天还黑着,队长就把吊在他家门前刺槐树上的那只铁钟敲响了。钟吊得很高,驴性器样的钟锤子下端有一个铁鼻,鼻眼儿里拴一根长绳子,队长就是通过拉动那根绳子,让钟锤子敲打在钟壁上,对全村人发号施令。黑暗给人的感觉是实在物,似乎可以阻挡钟声传播,实际上它不但不能使钟声有半点减弱,还媒体似的帮着钟声共振,使高空下来的金属的声响如同直接击打在每个人耳膜上。男女社员很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了,他们往尿罐里放了一通黄水,头不禁摇了摇,胳膊下夹着工具,就出门去了。这里那里相继响起开门声、咳嗽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时值初春,早晨的天气湿中带寒,村街上晃动的灰人影都缩巴着,伸不开腰。早起不吃饭,掰开眼就下地干活,这是老辈子人传下来的规矩。这样一天下来可以干三场活。先干活,后吃饭;一场活,一顿饭;干了活,好吃饭,一切顺理成章,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几乎成了铁定的法则。今日的活儿队长昨日就派定了,捣粪。饲养室门前的院子里有一大堆湿粪,人们把粪堆扒开,捣碎,晾干,就可以拉到地里,给将起身的冬麦上一遍苗肥。在黎明前那段不短的时间里,粪堆黑得像一座小山,而围绕粪堆蠢蠢而动的人们恰似一群蚂蚁,在做“蚂蚁搬山”的工作。
货郎今天给人的印象与往日没什么不同。上工时,他习惯性地把工具搭在肩窝,双手交叉揣在袖筒里,把工具的把柄搂在胸前,没有一点心存杀机的迹象。他虽然骨架高大,由于年少时跟着父亲挑货郎担压驼了背,显得有些畏缩。他头上那顶脑油味儿十足的一把捋黑棉线帽子,也破得耷拉下来,差点遮住眉眼。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稀松平常,不像个一朝便有大作为的人。不过,社员们见他来出工,眼神儿还是有些兴奋。昨天收工时队长当众宣布过,不许货郎今天出工,因为大队要办他。所谓办他,就是办他的学习班。他偷偷地挑起货郎担到十几里外的村庄游乡卖货,这是第三次被队长抓到了。每抓到一次,大队就要办他的学习班,第一次办一天,第二次办两天,这次当然是办三天。办班的事货郎领教过了,大队干部把他往一间小黑屋里一锁,不管也不问,不给吃也不给喝,什么办学习班,其实就是蹲班房。货郎明白,他出去卖货的事大队里不会知道,都是队长存心跟他过不去。队长给大队干部递了烟,就顺便把大队干部的手借过来整他,肯定是这样的。这次他不想去大队“蹲班房”了。
队长觉出好多人在看他,乱用亮亮的眼神儿向他打报告,告给他货郎不听话,又上工来了。队长现在一见货郎就来气。村里有人给他递话,说货郎跟他结了仇,要做他的活儿。起初他不相信为人谦卑的货郎敢出此狂言,后来好几个人都极神秘地提醒他小心,都说货郎要做他的活儿,这些人当中有张三爹,有李四嫂,还有说话挺占地方的王二爷,他不相信也由不得他自己了。货郎那个熊样儿,一点刚性也没有,他想象不出货郎怎样做他的活儿,难道冲他扔货郎鼓不成!他想,货郎也就是嘴上说说解解恨而已,借给他一颗豹子胆,谅他也不敢动手。可就是嘴上说说,队长也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按他的脾气和在村里说一不二的威严,在货郎没做他的活儿之前,他真想把货郎的活儿做了算了,免得他信口雌黄。
队长叫着货郎的名字,问他谁让他来上工的。货郎站住愣了一下,没说话。队长又严厉地质问了一句,他明知货郎说不出谁让他来上工的,偏要这样问他。货郎不回答不行了,说没人让他来上工,是他自己来的。队长嗤之以鼻,说:“你以为自己可以当自己的家,鸡巴毛,你什么也不顶,有人要当你的家。回去吧,大队干部等着你呢!”社员都停止扒粪,瞪大眼睛看着队长和货郎的一举一动。粪堆那边的人赶紧转过来了,他们担心粪堆挡住视线,会漏看一些动作性很强的细节。没有一个人说话和咳嗽,场面有些静。只有一个社员很快地瞥了一眼东边的启明星,像是通过记启明星所在的位置记下本村重大事情即将发生的大致时间。
货郎果然没有像队长命令的那样“回去”,他不紧不慢地把工具从肩上卸下来了,顺在了手里。他的工具跟今天所有到场的社员使用的工具一样,是一把三齿的铁制钉耙。这种钉耙跟猪八戒使用的铁耙子有些相似,只是铁耙子是多齿,钉耙是三齿。而且钉耙的铁齿要长得多,粗得多,非常适合农用。当地一般农家都备有两三把钉耙,它正使可扒,反过来可砸,翻地,刨草根,收红薯,砸土坷垃等,都是用它。钉耙分六斤、八斤、十斤三种,人们根据自己的性别、体力和习惯,选用不同重量级的钉耙。货郎使用的是最重的那一种。他提着钉耙向粪堆走去。若搁往日,货郎会绕开队长走,比如队长在粪堆这边,他就会到粪堆那边,让粪堆把他和队长隔开。既然队长看见他就起厌,他躲开队长还不行吗!可今天不知怎么的,他冲着队长就过去了。
看来今天有戏!大家在心里有些惊喜地暗叫。
队长也看出货郎拿钉耙的架势有点不同寻常。须知每样带柄的农具都是武器,不管是镰刀、斧头,还是铁锨、钉耙,可以用来做庄稼活儿,也可以用来做人的活儿,乡下好多人命案,里面差不多都牵涉一两样顺手的农具。队长想喝令货郎站住,想到那样做社员们会小瞧他。凭着他年轻力壮的剽悍劲儿,要是货郎敢动手,他三下两下就会把驼背的货郎整得四爪朝天,屁滚尿流,他怕什么!于是他把钉耙拄在手里,故作轻松地看着向他走来的货郎。
挨在队长旁边的张三爹和李四嫂开始往一边闪,他们担心货郎和队长动起家伙来会溅他们身上血。
然而货郎把钉耙扒在粪堆上了。他扒下一块湿粪,在地上一点点捣碎,接着又扒下一块。他低着头,干得很专心的样子,一点也不考虑社员同志们对他的期望和关注。别提社员们多泄气了,他们退回自己的位置,面对粪堆继续捣粪。有人无所指地骂娘,以发泄心中的不满。有人叹气,觉得一切都太无聊,太沉闷。粪堆扒开时冒着微微的白气,浓浓的粪味扑面而来。这里没有哪一个人嫌粪的气味难闻,发过酵的粪肥里饱含着庄稼所需要
的营养成分,他们甚至从中嗅出一股酸甜的气息。可粪毕竟是腐烂物,而不是庄稼,它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它带给人的是烂糟
糟的感觉和心情。这时队长又训了货郎几句,大概意思是货郎干也白干,队里不会给他记工,而货郎连个屁也没敢放,这更让大家失望。要是村里没有那个日甚一日的传说,大家不抱那个希望,也就罢了,现在火候明明差不多了,货郎当做的活儿不做,老是像闷一堆粪那么闷着,闷得久了,无非是一摊烂脏臭,没一
点稀罕可看。有人后悔,不该对货郎期望值过高。这好比货郎是一个演员,观众期望他有上乘的表演,锣鼓家伙已经打得很热闹了,他却连个蹩脚的表演都没有,这难免引起一些观众的反感和埋怨。货郎没有挨在队长身边捣粪,他和队长之间还隔着两个人,一个是张三爹,一个是李四嫂。这两位都是好眼色,他们刚才怕血溅身上闪开了一点,很快发现无血可溅,他们便不露痕迹地各就各位。张三爹是希望不灭的一个,相信后面会有好戏看。
他是货郎家的邻居,对货郎家的底细比较清楚。在他看来,货郎已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货郎的老婆前年病死了,货郎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货郎对操持家务是无能的,他喂猪猪死,养鸡鸡瘟,家里时常穷得连买盐和买煤油的钱都没有。没有咸盐时,他就和孩子吃淡饭。没有煤油,他家就不点灯。没盐没油的日子可以凑合,可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不好赖账的。另外还有女儿的穿衣问题。女儿今年都十四岁了,身体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往大里长。开春后,女儿该脱棉换单了,可女儿连一条可换的单裤都没有。女儿自己把粗布棉裤拆了,把里面的烂棉花掏出来,缝缝补补,把棉裤改成了夹裤。不料,夹裤刚穿了一天,后面麻花的地方就撑破了。女儿想翻出一块补丁再补,翻遍屋里所有地方,竟找不到一块结实的补丁。货郎听见,女儿躺在床上拿被子蒙上头哭了。张三爹知道了货郎家的窘迫情况,撺掇货郎挑起货郎担,再去游乡做生意。货郎家的货郎担是现成的,一头是祖传的货箱,一头是竹编的花筐,油光光的桑木扁担上挂着一只货郎鼓。货箱里未卖完的货还有一些,大针小针顶针儿,甘草糖豆弹球儿,还有头绳儿网子烟袋锅儿等。货郎只要外出把货郎鼓一摇,一天下来给女儿挣个买裤子布的钱当不成问题。可货郎不敢去,他一挑起货郎担外出,就算是“走资本”,队长就要帮助他,把他拉回来。前两次队长帮助他的办法就是开会批判他,扣他的工分,还让他去大队蹲黑屋。事不过三,如果再犯事,受罪受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觉得丢不起人。张三爹不这么认为,他说什么叫丢人,丢人多少钱一斤?古代到今天,有买就有卖,为孩子挣点钱没啥丢人的,孩子没裤子穿那才是真正的丢人。这时李四嫂也来了,李四嫂对货郎有所指责,问他这个爹是咋当的,闺女这么大了,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李四嫂把裤腰摸了摸,说她只有身上这一条裤子,但凡有一条能替换的,她立马把裤子脱给货郎的闺女穿。李四嫂还说货郎真是个没种货,要是她,只要队长不砍断她的腿,她就要游乡卖货。看来闺女没娘是不行,没人疼。货郎当时一直苦着脸,没说去,也没说不去。张三爹估计,货郎会去的。半夜里,张三爹听见货郎家门响,隔着院墙一瞅,见货郎正挑着担子轻手轻脚往外走。张三爹脖子一缩,不禁有些乐。
太阳出来时,粪堆矮下去不少,人们踩着软泥泥的沤粪,继续向粪堆“蚕食”。新阳光照在社员们的脸上,每个人脸上都像有了黄病色,显得相当枯燥。货郎将功补过似的干得很卖力,脑门上出的汗把帽边儿都浸湿了。队长眉头拧着,一直不松开,他显然在考虑“走资本”还是“走社会”这类大事,对捣粪这等琐碎事不感兴趣。张三爹左右溜着眼把他二人看了看,向队长提出,他要到镇上卖点醋。他会做醋,家里还有半缸水醋没出手。
这是个好话题,张三爹说的声音也大,社员们都听到了,马上有好几个人附和,也要赶集卖点东西。有的社员无东西可卖,也在小声嘟嘟囔囔,不知说的是什么。队长一听就明白,这是群众对他有意见,嫌他对货郎太手软,就用这种办法将他的军。那天货郎趁着夜色外出去“走资本”,刚走一会儿,张三爹就去敲他的门,挺神秘地从门缝里告诉他,货郎屡教不改,又偷偷地拿起货郎鼓到外面摇“资本”去了。他表示知道了,张三爹还站在门外不走,磨磨叽叽说他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做生意谁不会。言外之意,这次如果不对货郎严加惩治,群众就得对队长的威信打个问号。队长说“放心,饶不了他”,张三爹才走了。那天王二爷也
藏头露尾地暗示他,猴子怕见血,想让猴子听话,就得杀只鸡给猴子们看看。队长想,在如何严惩货郎的问题上,看来群众的呼声是很高的。他接过张三爹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谁
外出也不行!”他表面上是对张三爹说话,眼睛却瞅着货郎,继续说:“就你好搞特殊,怎么,你比别人尿得高些?”说着使劲把钉耙往地上一蹾,不捣粪了,从衣服兜里摸出一张纸片和碎烟,卷了一支“炮筒子”安在嘴上。别人见队长吸烟,也停止捣粪,很嘴馋地看着队长吸。队长要大家往一块集中集中,开
个会。
社员们马上就猜到了,队长要开的会是斗人的会,大家的眼
神儿又有些活跃。那年大家斗过队长,后来队长就一个一个斗别人。开斗人的会虽然不算什么稀罕事,可斗习惯了,不斗斗总觉少点什么。社员们以队长为中心聚拢了一下,把钉耙齿子朝下趴在地上,屁股坐在钉耙木柄上,准备斗人。
货郎没敢坐。明知要斗的人是他,他坐下去还得被喝令起来,不如不坐。粪场转眼变成会场,参加会的人差不多都坐下了,只有货郎和队长站着。货郎觉得很不得劲,就低着头用脚擦钉耙齿上粘的粪泥,三根钉耙齿上的粪泥很快被他擦干净了,尖利的钉齿闪着凛冽的青辉。为了耐磨损,钉耙的齿子都是加了钢的,并淬了火,硬度很好,宁折不弯。从钉耙齿子的光洁度来看,货郎不是一个懒人,懒人的工具一般都是锈迹斑斑,而货郎的工具一点锈迹都不见。他自我掩饰似的把钉耙提起来看了看,接着又擦,在有的人看来,他这么干有点打磨家伙的味道。
队长让货郎“坦白吧”,“你都到哪儿卖货去了?一共赚了多少钱?你要老老实实,不然群众是不答应的。”货郎不擦钉耙了,胳膊和头都垂下来。他觉得头有些晕,脚下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他赶紧扶住钉耙把,才没倒。他这次卖货比较倒霉,一个村庄的队长带着几个人出来,把他卖货的钱悉数搜走不算,还把他的全副货郎担及货扣留了。他好话说尽,百般央求人家发还祖传的货郎担,不料那队长和这队长说的话一个腔调,原来天下的队长都是一样啊!那队长着人把货郎担弄到队长家去了。他蹲在队长家门口不走,天黑了他还不走。他老是想,货郎担是他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要是在他手上弄丢,他连祖宗都对不起。后来那队长发话,要货郎回去,让他们村的队长领着他来,他要问一问他们的队长怎样教育的社员,才能把货郎担还给他。货郎怕的就是让队长知道他外出卖货,他哪里还敢让队
长去帮他讨回货郎担。队长问他为什么不坦白,是不是哑巴了。周围不少声音乱糟糟的,都在帮着队长说话,敦促他坦白。
货郎听出给队长帮腔的有张三爹,还有李四嫂。他的货郎担被外村人扣留的事张三爹和李四嫂是知道的,那天晚上他空手而归时,这两个人还同情过他,在他家里骂队长不是人,现在他们也让他坦白,这不是在他伤口上抹盐吗!家里男孩子交不起学费,女孩子没裤子穿,唯一能生点活便钱的货郎担被人夺去了,队长还揪住他不放,看来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人是没法活了。货郎抬头看了看天,说话了,他说的是:“队长,你要是不想让我活,干脆把我打死算了,我不算个人……活着也就这样,不如死了干净……你手里不是有钉耙吗,要打你就照着头上打。”他把头一俯,意思是交给了队长。
货郎的话引起周围一阵莫名的哗笑。队长马上指出他这种说法是耍赖,是对抗,是态度不老实,“谁不让你活,是你自己往死胡同里钻。我来问你,你在村里放风,说要做我的活儿,你说没说过这话?”货郎摇了摇头,说没说过。队长让他再想想,有好几个人可以证明他说过,现在先不让证明,让他自己说。
货郎撮起眉头,像是使劲在想,还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张三爹对他说过,“人都有一口气,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要死也得拉个垫背的。”王二爷对他说过,“欺人不能太甚,别说是人,兔子急了也咬人。”李四嫂说得比较露骨,“给狗日的队长开一次瓢儿(指头颅),狗日的就舒坦了,也算给平地风雷全村人除一害。”货郎承认,他们的话听着都很顺耳,很入心,也很受鼓舞,并且知道对队长有意见的不止他一个人,有好多人站在他这一边,在背后给他撑腰打气。可是他听了这些话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更没说过要做队长的活儿,这话到底是谁说的呢?他再次否认说过那样的话。他还赌了咒,说他要是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死他。
队长当然不会相信他,队长的意思是,赌咒不灵,放屁不疼。队长坚持认为,货郎一定说过那样的话,他当众连讽带骂,狠狠羞辱了货郎一顿。比如他指着货郎说:“撒泡尿照照你那熊样儿,腰弯得跟屁眼儿里生的豆芽儿一样,自己还把自己当成一根会动的蛆哩,我连屙都不屙你。”货郎如同被人连续抽着嘴巴子,脸一赤一白。他的头轰轰的,像是一下子充满了血,涨得五升斗一样大。又像是血全流尽了,只剩下点点滴滴的冷汗。接下来,队长又让好几个人“帮助”他,他都没听清那些人说的是什么。直到队长命令他“滚蛋吧”,他打了个冷战,才发现大家又开始捣粪了。他没有滚蛋,找不着方向似的原地转了一圈,又接着捣粪去了。他隐隐觉得,捣粪是一种待遇,队长已经取消了他的这种待遇,可他一时又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的确有点晕头转向了。
太阳升到了河堤上方,变得越来越白,照在人身上有些热燥。社员们都饿了,肚皮前墙贴到后墙上。他们等队长宣布下工,有一下没一下地扒着粪,都变得懒散起来。饲养室周围有一圈干坑,社员们一个又一个下到干坑里去了,手上解开裤腰带作撒尿状,眼睛却越过坑沿四处张望。他们希望看到一点动静,比如狗撵兔子或鹰抓小鸡之类,可田野里空荡荡的,都是尚未起身的麦苗,连一个挖野菜的老奶奶都没有。货郎没有去撒尿。这个软蛋,不光没有血性,连点尿性也没有了。大家原想着,即使他不做队长的活儿,和队长打一架或骂一架也是好的,也算给沉闷的日子添点动静,没让大家白等一场,他可好,连一摊粪泥也不如,粪泥扒开还能臭臭人,他连臭人也不会。大家似乎有些发愁,觉得这个村里的人真是完了,提不起来了。这个村历史上也曾有过壮烈的一幕。那年秋天,一干子土匪攻打邻村的寨子。土匪知道这村的人办有演武堂,不少年轻人会武功,要这村的人不要多管闲事。这个村有一帮血性汉子,觉得眼看着邻村受攻打不出来干涉不够意思,结果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呐喊着就出动了。那次这村的人损失惨重,被土匪活活打死四条汉子。有的汉子拖回村时,肠子肚子都流出来了。有一个汉子的头被土匪削去,找不到了,埋葬时只得打制了一个铁头。这件事已过去近百年,村人也换了好几茬,可大家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件事,一谈起来就兴致勃勃,感叹不已。从那以后,村里再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值得称道的事。前年,有一家马戏团到村里来玩老杆,一个演员在几丈高的老杆上做动作。不知为何,村里人都觉得那家伙会从老杆上掉下来,要是掉下来,一定像摔没扎毛的老鸹儿子一样,死得透透的。有意思的是,那演员还真的从老杆上摔下来了。亲眼目睹者奔走相告,无不为之夸耀。然而,那演员拉到医院经过抢救又活过来了。他们本以为这件事会成为历史性话题,人一活过来,大家顿时觉得无话可说。他们一直纳闷,那家伙从那么高的高处摔下来,怎么可能不死呢!有人甚至怀疑那家伙耍了花招,用轻气功之类的玩意儿,骗得大家空欢喜一场。
平地风雷事情陡转急下,是因为王二爷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一点促进作用。队长到坑底去撒尿,王二爷也跟着去了。王二爷把残余的尿液用手甩着,自言自语似的对队长说,货郎硬着不去大队参加学习班,别人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队长说:“谁说没办法,治不了他,我这个队长……哼!”他回到捣粪场就对货郎勒令:“吃过早饭你就到大队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他又点了两个基干民兵的名字,要他们准备一根绳子,如果货郎赖着不去大队,捆也要把他捆到大队去。两个民兵很踊跃地答应了。他们提了一个问题,要是货郎反抗怎么办?队长说:“他反抗,还反天呢!你们是干什么的!队里给你们出着工分,我不信两个大小伙子治不了一个罗锅腰。反抗好说,我就怕他不反抗。”说着很鄙薄地斜了货郎一眼。
这时货郎的动作仍然是扒粪,捣粪。他离队长很近,队长的话他不会听不到,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觉出全粪场的人都在看他,他却低着头,谁也不看。他握钉耙的手有些抖。为避免抖,他狠劲握紧钉耙。这样一来,他扒粪的动作显得有些生硬,偶尔还有所停顿。明眼人不难看出,他是在某些事情上走神了,抑或是对某项重大决定还有些犹豫。货郎终于提着钉耙退出了扒粪的行列,来到队长的身后。张三爹感到,这回货郎大概真的要动手了。这次张三爹没有躲开,还跟队长说了一句关于天气的话。李四嫂也没躲开,她相信冤有头债有主的说法,相信货郎不会把钉耙扒在她身上。她还往队长那边靠了靠,似乎对货郎的动作有所掩护。然而货郎这次仍没动手,他把钉耙往队长身后的湿粪上一立,也到坑底撒尿去了。撒尿回来,他的双手一直在衣服下面的裤腰带上摸摸索索,仿佛裤腰带老也系不紧。
事后人们分析,货郎系裤腰带的动作是装出来的,其中至少有两个用意,一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他要在衣服下面把手藏起来,以免暴露意图。二是通过这种办法麻痹队长,让队长觉得,一个还没系上裤腰带的人能会有什么大的行动呢。
队长是麻痹了,他一点也没想到货郎会要他的命。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大概在判断时间,马上就要宣布下工了。他看完太阳,若是当即宣布下工,也许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愿意想到自己是个队长,愿意和大家作点对,别人越是估计他看完太阳就该宣布下工了,他越要故意拖延一会儿。就在这个时候,货郎抡起钉耙,往前冲了一步,突然把钉耙扒在队长头上了。队长正弯腰低头捣粪,货郎在他背后,扒起来很方便,钉耙的落点也比较准确,正好扒在队长的天灵盖上。货郎用劲老了些,钉耙吃得很深,三根钉耙齿都钉进队长的头颅里去了。 队长受到突然袭击,还未及喊叫,就一头栽在粪堆上,闹了个嘴啃粪。这时队长的思维大概还保持着,他苍白如纸的脸上粘满粪泥,两只眼珠子瞪得十分骇人。他双手还抓着钉耙的柄,似乎要爬起来加以抵挡。可他的脚一蹬,后面的粪就一滑,滑了两次,他的腿就抖得蹬不成了。他的嘴还在动,像是在恶狠狠地骂人,只是谁也听不见他骂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他没有流血,三根钉耙齿钉进去的地方都没有出血。
货郎想回过钉耙,再给队长补一下子,既然做了队长的活儿,就做彻底算了。可队长的头把他的钉耙齿子吸住了。他取了两次都没取下来,他一取,就把队长的头带起来了,像带一块红薯一样。他本想像扒红薯时做的那样,上去用脚蹬住“红薯”,把钉耙取下来,或者举起带着“红薯”的钉耙在硬地上摔一下子,把“红薯”摔烂。可队长的头毕竟不是红薯,队长瞪着的眼睛使他有些害怕了。
货郎用钉耙做队长的活儿,在场的其他人差不多都看到了,但没人说话,也没人出来制止。眼尖的李四嫂看见有一缕血从队长的耳孔里流出来了,血流得很细,像一只红色的小虫子在爬动,李四嫂把它指了出来。张三爹、王二爷马上据此作出判断:队长完了,没救了。
货郎放弃取他的钉耙,退出粪场,翻过干坑,向田野走去,一走进麦田,他就跑起来。
不知谁喊了一句,“别让他跑掉,打死他!”这话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对,打死他!”“杀人偿命,打死他个活狗日的!”大家齐呼乱叫,举着钉耙,卷地一般向货郎追去。
一时间,全村的人都得到了消息,男女老少都跑出来向货郎追去,手里拿什么家伙的有,木棒、镰刀、铁锨等,没有长家伙的就边跑边从厕所的墙上揭下一块砖头。这村的人好久没有这样群情振奋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叫着,像是过大年,像是围猎,又像是举行武装起义,有些干旱的麦田里腾起冲天的尘雾。
货郎跑着跑着就不跑了,他停下,转过身,对着激昂的人群微笑。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有人抓了一把土朝货郎脸上撒去,趁货郎揉眼的工夫,人们蜂拥上去,一顿乱器,把货郎打倒了。货郎没有叫喊,更没有反抗,人们一打,他就表现很好似的倒下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情绪,仿佛谁不打一下就吃了亏了似的,凡跑来的人都在货郎身上下了家伙,不一会儿,货郎就被整得烂糟糟的,像捣碎的一摊红粪。
货郎的女儿穿着破裤子也跑来了,她哭喊着不让人们打她父亲的头。她的哭喊像是对人们有所提醒,其结果是,她父亲的头破碎得几乎找不到了。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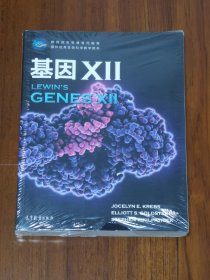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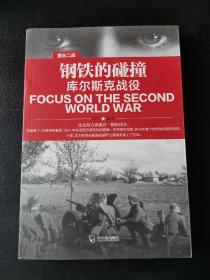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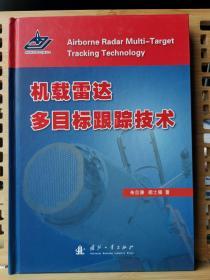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