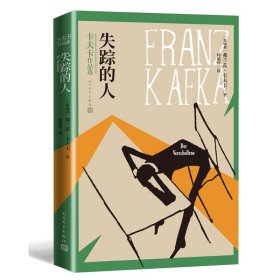
失踪的人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2.06 5.5折 ¥ 40 全新
库存5件
作者(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58911
出版时间2021-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0元
货号31298724
上书时间2024-05-1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在布拉格读德国文学和法学,获,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1922年因肺病离职,1924年逝世于维也纳郊区的疗养院。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中短篇小说集。生前在德语文坛鲜为人知,死后其遗著陆续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深刻影响了莫言、余华、残雪等中国当代作家。
译者简介:
韩瑞祥,北京外国语教授,中国德语文学学会副会长,“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德语文学评委。重点研究现当代奥地利文学,出版专著三部,译著二十部,主编《卡夫卡小说全集》《施尼茨勒作品集》《迪伦马特作品集》《彼得·汉德克文集》等。专著《20世纪奥地利瑞士文学史》获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2000)。译著《上海,远在何方?》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2014)。
目录
目次
一 司炉
二 舅舅
三 纽约郊外的乡村别墅
四 去往拉姆西斯的路上
五 在西方饭店里
六 罗宾逊事件
这汽车停了下来,……
清晨,……
残章断篇
1 布鲁纳尔达出游
2 卡尔在一个街口……
他们行了两天两夜……
内容摘要
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安东尼·伯吉斯小说的主人公罗斯曼从一开始就是其生存环境的牺牲品,不断地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卡夫卡式的迷宫里而无所适从。
——韩瑞祥长篇小说《失踪的人》是“卡夫卡作品选“系列之一,是卡夫卡未竟之作,写于1912至1914年间,1927年出版。讲述的是少年卡尔·罗斯曼的故事,他因被女仆引诱而被父母赶出家门,孑然一身流落异乡美国。
精彩内容
译者前言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地位。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鲜为人知,死后却引起世人广泛关注,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在布拉格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同时也造就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后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1908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1924年肺病恶化,死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
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尤其对歌德的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钻研颇深。与此同时,他还涉猎斯宾诺莎和达尔文的学说。大学时期就开始创作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职以后,文学成为他惟一的业余爱好。1908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司炉》(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第一章,1913),以及《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1—1922),但生前均未出版。对于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很少表示满意,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在给布罗德的遗言中,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罗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从1935年起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万别,无论有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但卡夫卡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他只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首先,卡夫卡的作品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在他的笔下,神秘怪诞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那近乎无诗意的,然而却扣人心弦的冷静。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生存经历,但这些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卡夫卡对他的朋友雅鲁赫说过:“那平淡无奇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不过是把它写下来而已。”其次,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于矛盾层面的表现中。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所面临的困惑。卡夫卡所表现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卡夫卡独辟蹊径的悖谬美学就是独创性和不可模仿性的完美结合。
未竟之作《失踪的人》写于1912年至1914年间,它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作者生前发表了其中的第一章,也就是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司炉》(1913)。1927年,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编辑出版这部小说时取名“美国”。根据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记载,德国费舍尔出版社后来出版的校勘本则采用了作者在其中多次提到的“失踪的人”这个名称。这也是卡夫卡研究界迄今普遍所认可的。
小说《失踪的人》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岁时因被一个女仆引诱而被父母赶出家门,孑然一身流落到异乡美国。罗斯曼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卡尔的轻信,他常常上当,被牵连进一些讨厌的冒险勾当里。罗斯曼要寻找赖以生存之地,同时又想得到自由,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从主人公的坎坷行踪里,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比较具体可感的社会现实;美国是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但卡夫卡却从未到过那里。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无疑是其对自身生存现实感知的镜像。
与卡夫卡后来创作的两部小说《审判》和《城堡》相比,《失踪的人》在叙事风格上比较接近传统的叙事,读者从头到尾可以追踪到一个连续不断的情节链条。评论界向来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卡夫卡甚至在他的日记里也表白了罗斯曼与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主人公的因缘关系。尽管如此,无论从人物命运的表现,还是从叙事方式来看,卡夫卡在这里已经开始了独辟蹊径的尝试,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和叙述者的直叙交替结合的方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现代小说多姿多彩的叙述层面,形成分明而浑然的叙述结构,为其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小说的主人公罗斯曼从一开始就是其生存环境的牺牲品,不断地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卡夫卡式的迷宫里而无所适从。小说第一章“司炉”就已经为罗斯曼的卡夫卡式的命运做了必然的铺垫:受到家庭女佣的引诱,他被父母亲毫不留情地发配到美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他怀着一颗天真的公平正义之心踏上了那个以自由女神著称的国度。他在轮船上遇到了那个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司炉,为其境遇愤愤不平。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义愤填膺地扮演起了一个律师角色,挺身为司炉主张公正。可面对以船长为代表的权力世界,他徒劳无望的所作所为显得幼稚、荒唐和可笑。实际上,这个呈现在“司炉”一节的主题贯穿于小说表现的始终。罗斯曼试图在美国找到一种公正的生存,但却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令他心灰意冷,甚至绝望。刚一抵达美国,从天而降的幸运让他莫名其妙,因为他在船上与素未谋面的富翁舅舅邂逅相遇,初来乍到就进入了美国的上层社会。然而,他生活在上层社会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却一筹莫展,无所适从,森严的等级观念让他难以适应,他很快就莫名其妙地被舅舅赶走了。
不言而喻,舅舅在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丝毫也不能容忍任何违背他的意志的行为。无家可归的罗斯曼不得不继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他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酒店里当了电梯工,但似乎又陷入了一个任人摆布的迷宫里,他时时处处受到监视,生存如履薄冰,无妄之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操作现代技术显然成为一个非人的工作,它迫使人像机器一样运转,使人成为被操纵的工具;罗斯曼在此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他仅仅离开了工作岗位两分钟,便又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这无疑是卡夫卡笔下所有的人物始终要面对的惨无人道的严酷。这个酒店因此看上去就如同《审判》和《城堡》中的权力机构。虽然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是罗斯曼工作的地方,不像那些权力机构那样似真似幻,难以捉摸,而且其权力承载者都是些活生生的人,但罗斯曼生活在其中所感受的压抑和困惑则更加显而易见,更为直接,更为刻骨铭心。
在这个陌生的美国,无论是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还是现代化酒店上上下下的人,或者与罗斯曼同命相连的流浪者,他们的行为无不受到统治欲望和邪恶的驱使,真正的仁爱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不复存在。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最终罗斯曼甚至成了他曾经帮助过的两个流浪者的牺牲品,被迫沦为必须俯首听命的仆人,遭受着种种难以摆脱的折磨。世态炎凉的生存环境使得罗斯曼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自由,他无力应对生存,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充当任人肆意蹂躏的对象。实际上,罗斯曼的命运与卡夫卡其他人物的命运如出一辙。
小说《失踪的人》是卡夫卡整个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部分,体现了“卡夫卡风格”形成的端倪,为全面研究和认识卡夫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见证。这部小说问世近百年来始终是评论界争论不休的对象,但时至今日依然是卡夫卡研究者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也是广大读者很喜爱的卡夫卡作品之一。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失踪的人》单行本之际,译者对收录在《卡夫卡小说全集》中的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作为喜欢卡夫卡的读者,译者在此愿与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同仁继续共勉。
韩瑞祥2019年4月于北京一司炉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他那可怜的父母发落去美国,因为一个女佣勾引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当他乘坐的轮船慢慢驶入纽约港时,那仰慕已久的自由女神像仿佛在骤然强烈的阳光下映入他的眼帘。女神好像刚刚才高举起那执剑的手臂,自由的空气顿然在她的四周吹拂。
“多么巍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该下船了。一群群行李搬运工簇拥着擦他身旁流过,他不知不觉地被推到了甲板的栏杆旁。
“喂,你还想不想下船?”一位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年轻人走过他身边时喊道。“我这就下去。”卡尔微笑着对他说,随之把行李箱扛到肩上,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目送着那位稍稍挥了挥手杖便随着人群离去的相识。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他急忙上前求这位显然不大情愿的相识帮他照看一会儿箱子,匆匆地看了看眼前的情形,看好了折回去的路,便一溜烟似的跑去了。到了下面,他懊恼地发现本来可以供他走捷径的一条通道现在关闭了,这大概是因为所有的旅客都已经上了岸。于是他不得不穿过数不胜数的小舱间,沿着拐来拐去的走廊,踏着一道接一道上上下下的扶梯,艰难地寻找着那间里面仅摆着一张写字台的空房间。这条道他仅仅走过一两次,而且总是随着大流走的,他最终完全迷了路。他一筹莫展,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只听见头顶上响着成千上万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和那从远处传来的已经熄火的机器最终呵气似的转动声。他开始四处乱撞,随意停在一扇小门前,不假思索地敲起门来。“门开着!”里面有人喊道。卡尔急不可待气喘吁吁地推开门。“你干吗这么狠狠地打门?”一位彪形大汉问道,几乎看也不看卡尔一眼。一丝微弱昏暗的余光从上层船舱透过某个天窗,映进这寒酸的小舱室里。室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靠背椅连同这个人拥挤不堪地排列在一起。“我迷路了,”卡尔说,“这条船大得惊人,可我在旅途中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是的,你说对了。”这人带有几分自豪说,依旧忙着修理一只小箱子的锁;为了听到锁舌咔哒锁上的声音,他用手把锁压来压去。“你进屋来吧!”这人接着说,“你可别老站在门外呀。”“不妨碍你吗?”卡尔问道。“啊呵,你怎么会妨碍我呢!”“你是德国人?”卡尔试探着要弄个明白,因为他听说过许许多多关于初到美国的人遭受无妄之灾的事,尤其是爱尔兰人作恶多端。“是,是的。”这人回答说。卡尔依然迟疑不决。这时,这人突然抓住门把手,狠力一拉,迅速关上了门,卡尔被拽进了屋里。“我无法忍受有人从走道上往里面看着我。”这人说着又修理起他的箱子。“无论谁路过这儿都往里面看看,这让人受得了吗?”“可这会儿过道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卡尔说着紧紧巴巴地挤在床腿旁,心里不是滋味。“我说的就是现在。”这人说。“事关现在,”卡尔心想,“这人可真难打交道。”“你躺到床上去吧,那儿地方大些。”这人说。卡尔一边尽力往里爬,一边笑起自己刚才企图纵身鱼跃的徒劳。可是当他刚要爬到床上时,他却突然喊了起来:“天啦,我的箱子给全忘了。”“箱子放在哪儿呢?”“甲板上,一个熟人照看着。只是他叫什么呢?”他说着从母亲给他缝在上衣里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鲍姆,弗兰茨·布特鲍姆。”“这箱子你非常急需吗?”“当然啰。”“那你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我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我是跑回来取伞的,不愿随身拖着那只箱子。我哪里想到会迷了路。”“就你一个人?没人陪伴?”“是的,就我自己。”我也许应该求助于这个人,卡尔思考着,我一时上哪儿去找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你连箱子都丢了,我根本用不着再提那雨伞了。”这人说着坐到靠背椅上,似乎卡尔的事现在赢得了对他的几分兴趣。“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失。”“信任会带来幸运。”这人边说边使劲地在他那乌黑浓密的短发里搔来搔去。“在这艘船上,道德也在变化着;不同的码头就有不同的道德。要是在汉堡,你的那位布特鲍姆也许会守着箱子,可在这儿,只怕连人带箱子早就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得马上上去看看。”卡尔边说边看看怎样从床上爬起来。“你就呆着吧。”这人说着用一只手顶着卡尔的胸膛,粗暴地将他推回床上。“为什么呢?”卡尔生气地问道。“你去顶什么用!”这人说。“过会儿我也走,我们一道走好吧。你的箱子要么是让人给偷走了,找也无济于事,你到头来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要么是那个人始终还在照看着它,那他就是个傻瓜蛋,而且会继续看守下去,或者他是个诚实的人,把箱子放在原地。这样等船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再去找它岂不更好。还有你的雨伞。”“你很熟悉这船上的情况?”卡尔狐疑满腹地问道;他似乎不敢相信等船上的人走光后就会更方便地找到自己的东西,觉得这种本来让人心悦诚服的想法中埋藏着某种不测。“我是这船上的司炉。”这人说。“你是这船上的司炉。”卡尔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仿佛这事完全超越了所有的期待。他支起双肘,凑到近前仔细打量起这个人。“恰好就在我同那些斯洛伐克人住过的那间舱室前有一个天窗,透过它就能看到机房里。”“对,我就在那儿工作。”司炉说。“我向来就着迷技术工作。”卡尔固守在一成不变的思路上说,“要不是我迫不得已来美国的话,将来会成为工程师。”“你干吗非得来美国呢?”“啊呵,那就别提啦!”卡尔说着手一挥,抛去了那全部的故事。这时他笑嘻嘻地瞅着司炉,好像在恳求他谅解那讳莫如深的事。“这其中想必会有什么原因吧。”司炉说,可谁也说不准,司炉说这话是有意要求还是拒绝卡尔说出那原因。“现在我也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现在对我父母来说,我无论干什么差事,全都无所谓了。”“我这个位子要空下来了。”司炉说,他完全有意这样说,两手插进裤兜里,那两条裹在褶褶皱皱的、皮革似的铁灰色裤子里的腿往床上一甩伸了开来。卡尔不得不挪到墙边。“你要离开这条船?”“是的,我们今天就离开。”“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这工作?”“对,事情就是这样,不总是取决于你喜欢不喜欢。另外,你说的也对,我是不喜欢这差事。你可能不是决意想当司炉,但要当非常容易。我可要劝你千万别干这事。既然你在欧洲就想读大学,干吗在这儿就不想上了呢?美国的大学无论如何要强得多。”“这很可能。”卡尔说,“可我哪儿有钱上大学呢?我虽然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有那么一个人,他白天给人家打工,晚上读书,最后成为博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而且当上了市长。可是这得有锲而不舍的劲儿,你说不是吗?我担心自己缺少的就是这股劲儿。再说我也不曾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说真的,中途辍学,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格。我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想,这里的人准会对外国人抱以偏见。”“这等事你也听说过?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是他乡遇知己了。你看看,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艘德国船上吗?它属于汉堡—美洲海运公司。为什么这船上不全都是德国人呢?为什么轮机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叫人想不通。而这条癞皮狗竟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负德国人。你可别以为,”——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打了个迟疑不决的手势——“我只是为抱怨而抱怨。我知道说给你也不顶什么用,你还是个穷小子。可这也太过分了。”随之,他一拳接一拳狠狠地敲打起桌子,边打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拳头。“我在那么多船上干过,”——他一口气连说出二十个船名,就像念一个词似的,卡尔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向来干得都很出色,处处受到赞扬,总是船长得意的工人,而且在同一商船上一干就是好几年。”——他说着竟挺起身来,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而在这个囚笼里,无论干什么都受到约束,一点欢乐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我在这儿是个无用的人,始终是舒巴尔的眼中钉,成了懒虫,只配被扔到外头去,靠人家的施舍过活。你懂吗?我就是弄不明白。”“你可不能这样忍着。”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眼下处在一个陌生大陆的海滨旁,踩在一条船上那摇摇晃晃的舱板上。在这司炉的床上,他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你找过船长吗?你在他那儿讨要过你的权利吗?”“咳,你走吧,你最好还是走开吧!我不想让你呆在这儿,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反而还给我出主意。我怎么会去找船长呢!”他又疲惫地坐下来,双手捂住脸。“我不可能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喃喃自语说,甚或觉得不该在这儿出些让人家看不起的主意,倒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当父亲把那只箱子永远交到他手里时,曾戏谑地问道:它会跟你多久呢?可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失去了。惟一让他宽慰的是,无论父亲怎样去打听,也不会得到他现在一丝一毫的消息。同船的人能告诉的不过是他到了纽约。卡尔感到很遗憾,因为箱子里装的一切他还没有享用过;要说他早就该换件衬衣了,但没有合适的更衣地方也就省去了。可是现在,正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时,他多么需要衣冠整洁地登场,却不得不挂着这件污迹斑斑的衬衣来亮相。这下可够瞧的了。不然的话,就是丢失了箱子也不至于那么糟糕;身上穿的这套西装比箱子里的那套还要好些。那一套只不过是拿来应急用的,就在他临行前,母亲还要把它补了补。这时他也想起箱子里还有一块佛罗纳色拉米香肠。这是母亲特意给他放进去的,可他仅仅只吃去了一丁点。他在旅途中压根儿就没有胃口,统舱里配给的汤就足够享用了。此时此刻,他真盼着拿来那香肠恭奉给这位司炉。因为像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拉拢过来,只需施点什么小恩小惠就是了。这一招卡尔还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就凭着给人家递烟拉拢那些跟他在生意上打交道的低级职员。卡尔现在可奉送的还有带在身上的钱,但他暂且不想动用它,即使他也许丢失了箱子也罢。他的心思又回到箱子上,他眼下真的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旅途中一直那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箱子,多少个夜晚不敢合一眼,而现在却把这同一个箱子那么轻率地让人拿走。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他始终猜疑那个矮小的斯洛伐克人在打他箱子的主意。这人就躺在他的左边,隔他两个床位,一味暗中窥视着卡尔随时会困倦得打起盹来的时刻,趁机会用那根白天总是在手上舞弄或者演练的长杆子将箱子钩到他跟前去。白天,他看来够纯真无邪,但一到天黑,就时不时地从铺上起来,垂涎欲滴地朝卡尔的箱子瞅过来。卡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儿或那儿不时地会有人随着移民的哄哄嚷嚷,不顾船规而点起一盏小灯,借以试图去琢磨移民局那难以理解的公告。当这样的灯光在他近旁时,卡尔就会迷迷糊糊地打个朦胧。一旦这灯光离他远些或者四周昏暗暗的,他就必须睁着眼睛。这样劳累简直折腾得他精疲力竭。可是,这一切现在也许全都付之东流了。这个布特鲍姆,要是卡尔有机会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话,非得让他瞧瞧厉害不可。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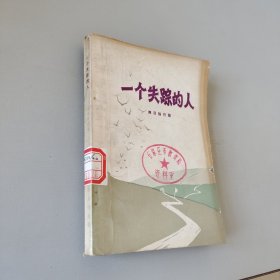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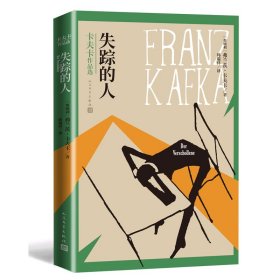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