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9787532184484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40.38 5.2折 ¥ 7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4484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1587826
上书时间2024-12-29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 作者简介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美国有名文学史家、莎士比亚研究者,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特聘教授,《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主编,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亚当夏娃浮沉录:一千个哈姆雷特》《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大转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莎士比亚的自由》等书。 ◎ 译者简介 吴明波,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西方古典学。 李三达,文学博士,湖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理论与视觉文化。
目录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致 谢
说 明
前 言| 塑造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
导 论
1 大人物的餐桌前: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
2 机械复制时代的圣言
3 怀特诗歌中的权力、性别和内在性
4 塑造绅士:斯宾塞与安乐窝的毁灭
5 马洛与绝对戏剧的意志
6 权力的即兴表演
后 记
尾 注
索 引
内容摘要
本书是对16世纪的生活和文学的探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研究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文学人物——莫尔、廷代尔、怀特、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的自我身份的结构,他论证了,在现代早期,支配着身份生产的知识的、社会的、心理的还有审美的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对该时代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是文学史、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文本,无论是对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生来说,还是对所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批评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都是一本必读佳作。
主编推荐
作品看点 * 重读《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我在这本书中感受到了这个迷茫的时代的许多痕迹。是在我目睹强势的邪恶力量决定碾压所有反抗之时;在我试图阐释,他们以陌生人为目标,操纵后者所感受到的威胁,由此巩固权力之时;在我不安地感知到,那些反对这种权力的人亦体现了它的某些突出特征之时,这些痕迹十分明显。——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本书主题是从莫尔到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作者起初试图理解“人类自主在建构身份时扮演的角色”,但终无奈屈服于一个福柯式的论断:“人类主体本身……是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莫尔是教会的产物,廷代尔是国家的拥趸,怀特臣服于主义国家;斯宾塞拥抱国家,马洛在对权力的不懈反抗中构建自我,莎士比亚则表达出对的颠覆服从。此而言,自我塑造亦是自我毁灭。或说,他们热切地融入制度与,由此塑造自我认同,但这般努力终往往取消了作为个体的自我,因此造成了自我的丧失。 但无论是作者格林布拉特还是本书关注的六位人物,他们都明白:“我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是一种无法放弃的幻觉。即使自我被认作一种虚构,放弃自我塑造是放弃追求自由,是放弃自己固执地坚持的自我,是死亡。 *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开山之作 “人类学的解释必须更多关注社会成员对其经验的解释建构,而非习俗和制度的机制。与这一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它的地位是解释,它的目的是将文学理解为组成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不管多么难以实现,它的正确目标是文化诗学。”文学“并不通向内在生活,而是作为内在生活而存在”。
精彩内容
◎《大人物的餐桌前: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这就是莫尔在那个危险而又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世界中的漫长职业生涯的精华,他观察君王和主教的本质:膨胀的虚荣、贪婪的胃口、愚蠢。眼前的景象使他既反感又着迷;他永远不会让自己仅以神圣的义愤之名放弃这个世界。与此相反,他让自己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成功表演者:1490年代早期他在莫顿大法官(LordChancellorMorton)家里担任年轻的侍从,在法律、外交、议会政治以及法庭方面工作四十年后,1529年,莫尔作为沃尔西的继任者成为大法官——这个领域的最高职位。然后,似乎为了证实他对权力和特权最黑暗的思考,他的地位在国王离婚的压力下迅速下降。1532年5月,为了保全自己,他以身体健康为由辞去大法官职位,但他太重要而且太引人注目,因此不可能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退休。他拒绝发表最高权威宣誓(OathofSupremacy)的行为——即拒绝承认国王为英格兰教会首脑——让他于1534年身陷伦敦塔,并于1535年7月6日上了断头台。本章将描述莫尔的生活和作品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self-cancellation)复杂的相互影响,描述他对公共角色的塑造以及内心深处希望摆脱精心塑造的身份的欲望。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这一场景,莫尔坐在大人物的餐桌前,在这个特殊的氛围中,他有野心也有讽刺意味的消遣,有好奇也有厌恶。他似乎正在观看一场虚构的演出,他同样被整个表演的不切实际和它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力量打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安慰的对话》(DialogueofComfort)这部作品的核心感受,这种感受披上无尽的伪装,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一个幻想刚被埋葬,另一个又冒出来,接着又被抓住、击败,直到整个世界,人的希望、焦虑以及目标的整个躯体,像海市蜃楼一样闪烁,引人入胜、顽强,又全然虚幻。
◎《机械复制时代的圣言》……但是,我们必须用廷代尔的作品提供的东西来平衡这种观点:在印刷文化早期,书籍可以有种独特的呈现,这是手抄本没有的。诸如廷代尔的作品的书籍拒绝正式的耳边忏悔和司钥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自我塑造的主要来源之一。废除(unmaking)与置换(displacement)形成对称,它们占据了忏悔册的结构位置,但是它们拒绝这种似乎控制了中世纪对内在性的体验或至少控制了对内在性的再现的制度框架。这种框架坚持认为,内在性应当从属于私下的口头交流(verbaltransaction),并被嵌入教堂这种可见建筑中的忏悔和赦免仪式。在廷代尔的《服从》以及新教徒有关内心生活的类似指南中都没有这种目的;印刷文字并不是为服务于口头言说而存在的,它有种绝对性、完整性以及不可变更性。与手抄迥异,生产数量相对较多、传播到远离作者和印刷商地方的机制拒绝服从仪式化的口头交流,缺乏灵韵——所有我们可以称作早期新教徒印刷书的抽象性(abstractness)的东西——这些赋予印刷书一种强度(intensity)、一种塑造的权力、一种强制的要素,而这些是中世纪后期的忏悔手册所没有的。30就此而言,像《服从》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后一个世纪印刷或抄写的作品对内在生活的描述。在17世纪的精神自传中,内在生活在外在话语中得以再现;亦即,读者会接触到对一些事件的记录,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被记录下来并且被人从黑暗带入书页的光明。在16世纪早期,还没有这样清晰流畅且持续的内在声音(像一种戏剧性的独白)被记录下来。出现在《基督徒的服从》的书页中的文字是内在生活的一些方面,它们笨拙却有说服力,半成形,或者说正在形成。这些言辞没有见光,相反,它们注定会进入相反的进程:他们会被无数的个人历史所研究、吸收、内化以及歪曲。这就好像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看到了事物本身,这些事物不是被再现的(represented),而是以它原来的最初形式被呈现的(presented)。我描述的这种现象——具有同一性的书面文字的呈现(presence)——在蒙田的散文和《哈姆莱特》的独白中散发出它最后的辉煌,《哈姆莱特》的独白是通过从手书回到声音的转换而得以实现的,而且这些言辞并不通向内在生活,而是作为内在生活而存在。这些言辞的特性——不同于现代的试图记录内在性的话语——在于它们的公共性,也就是说它们的修辞结构和表演方式具有明显的非个人化倾向。如果说对哈姆莱特内在思想的揭示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论辩(quaestio),即关于存在与不在(beingornonbeing)的问题,是直接面向众多的、户外的、公开的聚众演讲,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回忆像《服从》这样的作品来理解这种特殊习惯的力量,这些作品中明显的非个人化色彩的修辞塑造了读者对自己最亲密的感觉。
◎《塑造绅士:斯宾塞与安乐窝的毁灭》对于处于怀特的处境中的人而言,角色扮演似乎无法避免,不管是宫廷内的权力集中还是新教徒的意识形态,都导致了身份意识的增强,人们越加关注对身份的表达,越加努力地塑造和控制它。对自我的塑造被提升到一个问题或计划的地位。身份所带来的压力——意识和权力的压力,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身处其中的社会中——具有深远的文学影响,我们在检视前面三个人物时已经对此有所知晓。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关注第二个三人组——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现在会更多地聚焦于特定的文本而更少地聚焦于作者和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缩小焦点是出于艺术具有独立性的巨大幻觉,也是由于我们必须在完全为人所意识到了的虚构世界中思考更复杂的、看上去更自主的角色。我们已经在莫尔、廷代尔和怀特那里看到了自我塑造的压力,它已经超越了更高层次的意识艺术(consciousartistry),而16世纪后期的文学则变得越加擅长在高度个性化的情况下塑造人物。另外,至少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可能把文学当成他们的主要活动:当我们的对象从斯宾塞变成马洛,再变成莎士比亚,对艺术创作的职业身份的重视愈发凸显。因此,我们更容易在个人作品内讨论这种身份的形成和削弱,而不需要正式将其与创造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种明显的内在性依赖于一种自我塑造文化的鲜活经验。在转向斯宾塞之前,我们会尝试简要概述一下这种文化的显著特征。
◎《马洛与绝对戏剧的意志》马洛既远离正统也远离怀疑论;他质疑文学和历史是重复的道德训练这一理论,他质疑他的时代拒绝这些训练的独特模式。但是,他如何能够理解他自己的角色的动机,那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行为的力量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答案在于他们都想要自我塑造。马洛的主角们奋力创造自我;用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话来说,他们站立着“就仿佛,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创造者/不知道还有其他亲族”(5.3.36-37)。莎士比亚的特点是让他笔下的马洛式主角伸手抓住了他母亲的手;在马洛的戏剧中,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QueenofCarthage),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很少听说过主角的父母。帖木儿是无名的“低贱的”斯基泰人的儿子,浮士德有着“卑贱的父母”(parentsbaseofstock)(12),而巴拉巴斯,据我们所知,没有父母。(即使在《爱德华二世》中,马洛强调家世似乎不可避免,但也很少提到爱德华一世)。家庭是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大多数戏剧的中心,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在马洛那里,家庭是可以被忽略、轻视或者违背的东西。马洛的两个主角杀了他们的儿子却没有懊悔的迹象;大多数人都更喜欢男性友谊而非婚姻或者亲属关系;所有人都坚持,亲密关系应当自由选择。在他父亲死后,爱德华马上叫来了加维斯顿;巴拉巴斯选择了伊萨默尔而不是阿比盖尔;浮士德黏着他亲爱的梅菲斯特;另外,比起与奇诺科拉特一起的爱情场景更充满激情的是,帖木儿赢得了特瑞达马斯热烈的忠诚。
其后果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常情况下决定身份的神圣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结构瓦解了,这使得主角们实际上自生自灭,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给出。的确,自我命名是这些戏剧中的一件要事,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就好像主角只有不断地更新他们有意志的行动(actsofwill)才能继续存在。奥古斯丁曾经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如果上帝从现存的万物中收回我们所谓的他的‘建构权力’,那么这些现存的万物就不再存在,就好像他们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并不存在一样。”35马洛的世界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中立性,这种“建构权力”必须存在于主角自身当中;如果它在某一瞬间消失了,那么他可能会堕入虚无,用巴拉巴斯的话来说,变成“一块无意义的泥土/会被水冲洗成尘埃”(1.450-51)。因此,主角被迫重复他的名字和他的行动,马洛将这种受迫与戏剧联系在一起。主角的再次呈现(re-presentations)随着戏剧不断重复的表演而逐渐消失。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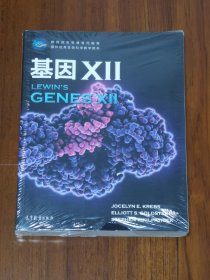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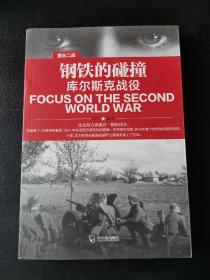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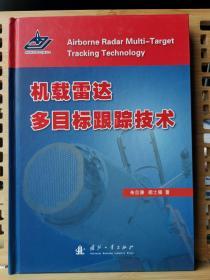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