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伯特·弗罗斯特校园谈话录
正版新华书店直发可开发票,支持7天无理由
¥ 23.9 6.8折 ¥ 35 全新
仅1件
江苏无锡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著;(美)爱德华·C.拉什姆(Edward Connery Latham) 编;董洪川,王庆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50257
出版时间2015-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1201181305
上书时间2024-05-0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位罕见的文学大师,在他的世纪里,只有威廉·福克纳能他比肩。他是二十世纪很受欢迎的美国诗人,曾获得4次普利策奖,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
目录
序言
坚持己见
诗自何处来
巧用修辞
“文科之隐忧”
一切皆有书指引
不是摆脱束缚,而是拥有自由
谈谈快速阅读及我们所称的“完整”
不能让自己惊奇的,怎能让别人惊奇
带着“编织物”前行
世间万物,正反相随
弗式诙谐
谈谈“优选的忧虑”
信念如何铸成
生活必有所依,直至被代替
某种赌博――无法确定的事情
世界的未来
慢慢求索,直到有所感悟
当写诗的时候,我想自己在做什么
论“选举者”与“当选者”
一见钟情
谈谈归纳
“站在新的起点”
某种莫名的焦虑
关于思考和在闪耀中毁灭
优雅地关注美好的事物
让我们勇敢地说出――诗歌价值无限
听我说――我的人生足迹
编者后记
引用文献出处
译后记
内容摘要
《罗伯特·弗罗斯特校园谈话录》收录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三十多所院校授课或谈话的文稿,时间跨度达三十年之久,是了解和研究弗罗斯特的难得资料。这些谈话内容由《罗伯特·弗罗斯特诗集》的编者E.C.拉什姆选编,并由获普利策奖新闻记者 D.M.谢里布曼作序。书中充满了智慧与洞见,犹如山涧的清泉,汩汩涌动。
精彩内容
序 言
戴维?M.施里布曼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著名诗人,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是所有美国诗人中获得该奖项次数最多者。1963年,诗人辞世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讣告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弗罗斯特是美国最著名最受人爱戴的文学家,”并在编者按中专门强调,他在英格兰享有的声誉,使我们在悼念他时“感到仿佛是失去了一位本国文学大师”。美国总统这样评价,他的去世让“美国精神留下了空缺”:“虽然他的离世使我们精神空虚,但是他已经给美国人民留下了不朽的诗歌宝藏,美国人民将永远从他的诗行里获得快乐和理解”。就在一年前,英国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在英国版的弗罗斯特最后一部新诗集的前言中宣称:“真实情况是,坦诚地讲,弗罗斯特是位能被称着世界级大诗人的美国人”。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中——从1914年出版部诗集到去世——弗罗斯特作为一位诗人和文学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他是一位罕见的文学大师,既赢得了大众的赞誉也获得了学者们的认同。他的另外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在他的世纪里,只有威廉?福克纳能与之匹敌:一个拥有高雅艺术的作家深深根植于一个地区,但又无可争辩地代表了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
他是一位乡村小路诗人,那时他的国家正在建设城镇和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他是一位具有闲情逸致思想的祭司,而那时他的国家四处充斥着商业崇拜;在工业化的浪潮里,他的焦点始终在农业和乡村况味。在一个全世界都在未来的祭坛面前跪拜的时代,他确乎是一位过去的坚定的维护者。在一个谎言被粉饰得完美无瑕的时代,他却道出了巨大的真实。
然而,弗罗斯特,一个城市化时代的乡村人,一个新文化时代的老古董,却又是一个与“早报”一样跟随潮流的人,在拥有着最为广泛的大众市场、大众文化的国度里,心中装满了大众的诉求。他出现在纯文学刊物的封面如《大西洋月刊》、《星期六评论》,他也出现在大众流通的杂志封面如《时代》、《生活》。两个圈子的读者都敬重他、热爱他。
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他被授予了四十多个荣誉学位,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学位,在他之前仅两名美国人同时获得这两所大学的荣誉学位,那是十九世纪的H.W.朗费罗和J.R.洛威尔。在他的故乡弗蒙特州,一座山依他命名。在其七十五岁和八十五岁生日时,议会一致通过,向他正式致敬,并在1962年他八十八岁生日时向他颁发特别金牌。对这样一个人而言,所有这一切,正如一首诗“锈迹斑斑”中所言,都“不如你/集体的爱/那么温馨/而这爱,正轻轻拂过现代世界。”
虽然弗罗斯特时常回到农场,但他并不是一名隐士。渐渐地,他成为了一位公众人物——一位名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接受了大众而大众也接受了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提到他存在的“公众性”——这个词为他独有,恰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但是这“公众性”并不是仅仅在他慈祥的老年时才获得的(实际上,无论是青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弗罗斯特身上都有一种并不单纯慈祥的东西,因为他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世界)。然而,作为公众人物,也许1958年被聘请为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顾问强化了他的角色——相当于美国选定的桂冠诗人——后来又担任国会图书馆的人文荣誉顾问。
1962年3月,正是弗罗斯特戏剧性地担任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演说嘉宾后一年多一点的时候,诗人告诉一位弗罗里达的采访者说:“这一年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名了。这使得我全部暴露在公众视线里。很多人给予了令人温暖的关怀。但是出现在公众里,那不是你写诗的地方。”
对于一个潜心于内心世界和拨动公众心弦的人,站在公众视线里是一种讽刺,而且他自己也被许多这类讽刺所伤害。1962年,他前往苏联。在苏联,他与赫鲁晓夫举行了广为周知的一对一的历史性见面。(以前他也曾以文化友好使者身份,受国务院派遣,到过许多国家如巴西、英国、爱尔兰、以色列和希腊。)后来,诗人在艾默斯特学院对听众谈起他的苏联之行:“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老师,被苏联之行几乎把我废掉了。最近我碰到的所有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我去过苏联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书。”
弗罗斯特的诗歌在其身后广为流传,而且名声与日俱增。他在为诗友E.A.罗宾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曾写道:“优选的愿望是写几首能永世相传的诗歌”。十分显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弗罗斯特的诗歌抱负,已经相当完美地实现了。
但是,迄今为止,读者并不知道弗罗斯特——也无从知晓——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即作为教师和演讲者。事实上,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无论是美国教室、讲台或者舞台最伟大的存在之一。尽管很多年乃至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在学院、大学或者小学——弗罗斯特,无论是演讲智慧还是演讲形象,仍然是魅力独具、生动难忘。他经常周游全国,在城市或者乡间,面对特殊群体或者普通大众发表各种演说。不过,他最喜欢的听众还是知识群体。
他自己从大学离开了——如所周知,上本科时他就曾逃离了达特默思和哈佛。(“达特默思是我主要上的大学”,他在1960年告诉一位采访者,“也是我逃离的所大学。后来我也从哈佛大学逃了,但是达特默思是个”。有时,正如1961年在在康涅狄格学院那样,他还会补充说,“从达特默思,我逃离了并开始了我的事业”。)可是,他也跑回过大学,承认那里才是美国诗歌的氧吧。在1954年,他对大学里的听众略带夸张地说:“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甚至也不会有我的存在,如果没有大学的庇护。在美国,我们没有王公贵族或者贵妇人来庇护诗人,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大学以及大学提供的听众。依我看,在世界上,最好听众就是居住在大学城里的城镇居民与大学师生。是他们,给予我生命,给予了我生活。”
对于自己的文学生涯,弗罗斯特曾经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概括:四处吟游的诗人。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概括术语,即使有一点不经意的自嘲味道但也有一点儿自视太高的意思。于弗罗斯特而言,四处吟游,正是诗人之所为——他曾走遍美国,有时还跨洋吟游。四处吟游,这使得他与传统相接。1962年,他曾对乔特中学的学生说:“大家知道,这是诗人四处乞讨的谋生方式。从荷马开始,我们就是乞丐。”他还引用托马斯.希伍德的诗行:“七个富裕的城镇在争论荷马的死亡,/而这些城镇正是或者的荷马乞讨的地方。”然后,他坦言道:“我乞讨的地方远不止此,正如有人所言,我吟着这些诗句,到处乞讨。这是一种很好的美国行乞方式啊。”
即使弗罗斯特要向听众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典型的开头往往是,像一场歌剧那样,以随意性的谈话方式拉开序幕。恰如1960年他在迈阿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首先我给大家即兴朗诵一首诗歌,这样开头……是一个不大的主题——有时是政治的,有时是宗教的,有时是历史的。反正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东西。”同样地,1959年在爱荷华大学,他这样对听众说:“我往往以这种漫谈方式开始,这是我唯一的自由诗。但我从来不写自由诗。我只是即兴地谈论自由诗。”但是,即使是他即兴演说,他也总能够娓娓道来,如同圣贤的书面表达。
多少年来——在教室、在演讲厅或者在报告厅——无论听众是来自某一课程的班级还是来自四面八方,身为教师的弗罗斯特已经成为一位显赫人物。(在1962年11月份的底特律大学,八千五百多听众见证了诗人在讲台上的最后荣光。)他是一位善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或者爱出风头的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约翰?西尔迪在《周六评论》上这样描述弗罗斯特:“事实上,他是一位专业高手:他知道如何提起听众的兴趣,也知道如何控制局面。”
但是,并不是所有场合都这样。对于弗罗斯特而言,讲台他是逐渐培养起来的情趣,也是逐步获得的技巧,来之不易。早年,他曾为面临听众而倍感恐惧。正如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劳伦斯?汤普孙所描述的那样,弗罗斯特的生平故事中有一段是描写1892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中学告别演说时发生的窘迫情形。汤普孙这样写道,弗罗斯特“极度紧张”,在他即将开始演说前冲下讲台,跑下演讲厅后面的楼梯,把手巾浸泡在水槽,把脸泡在冷水里,在演讲厅的走廊上不停地来回走动,然后缩头缩脑地回来——站在讲台上,几乎周身都在发抖,极度痛苦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还有两次,大约是在1906和1907年,在新罕什布尔州的德里公理会教堂,弗罗斯特应邀为男人联盟朗读自己的一首诗,他由于极度紧张,最后不得不由牧师替他朗读。在1909年,他应邀为他的一群教师同事演讲,他事先再鞋底放些小石子,希望以此能分散注意力而不至于过分害怕。此外,汤普孙还细致描述了几年后发生在弗罗斯特身上的另一个窘迫情形,那是他刚从英格兰返回不久,也刚刚出版了最早的两本书,他面对一群波士顿的听众:
“他决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窘境,也要通过在公众场合露面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声望,他尽自己优选努力去展示自己的勇气、胆识和果敢。然而,当他站在作家俱乐部的听众面前时,手还是不停地发抖,以至于他担心自己手里的书会掉到地上。在他还没有说话之前,他感到嘴唇在不停地颤抖,而他说话时,声音确实在明显地颤抖。他看到一些听众都在为他捏把汗。”
弗罗斯特从来就没有在讲台上镇定自若,最多只是控制得好些而已。三十多年后,他在一封写给《艾默斯特研究生季刊》编辑的信中附言里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我走向讲台的唯一原因是展示我的勇气…我这样做,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像一位真正的英雄一样直面飞来的子弹那样的经历。在演讲前后,我受的折磨比演讲时还要多得多。”
但是,一旦他克服了怯场,他努力使讲坛成为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圣坛。他在讲坛上找到了灵感,而在许多时候他在讲坛上的表现给人极大灵感和启发。在讲台上,如同他拿笔写作那样,他的能够发掘出他所谓的“语词的细微之处”。在讲台上,正如在山巅一样,他有时滔滔不绝,正如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一首诗《不愿意》中所说的那样,象“登上极目之处/纵览一切景致,然后,信步走下。”他的一生注定就是“向世界诉说”,虽然他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准确地知道他该说什么。他在讲台上就是这样,无可比拟,令人难忘。
弗罗斯特在讲台上的从容镇定,与他在谈话中的从容镇定如出一辙。他不再冥思一个给定的题目,而是随性而谈。无论他是被邀请去发表一个专题演讲还是去参加毕业典礼演讲,他都随意而谈,没有准备讲稿或者哪怕是一点提纲之类的东西。在演讲中,他从不克制自己漫游的思绪,总是随兴所至,任意发挥,侃侃而谈。
有些时候,弗罗斯特为自己的演讲准备了一个题目,但是他讲的却与题目完全无关。一次,是在1954年春天,他应邀去谈论一个大学课程设置的题目“科学的自然与超自然边界”,他这样开始他的演讲:“你们都知道了讲座的题目,现在我想,你们大概应该猜出了该讲什么,所以我还是谈点别的东西。”他就是没讲那个问题。1960年在华盛顿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白眼,我跟谁讲什么都总是一个秘密。只有今年,他们邀请我去俄亥俄、哥伦比亚,希望我给他们三个题目选择。我没有三个题目。没有选择,他们只好接受我给的题目……”
尽管有时看起来表现得风趣十足或者漫不经心,但是弗罗斯特从来没有怠慢过他的任何演讲。1938年,H.培根.卡拉莫对一位邀请诗人演讲的人说:“弗罗斯特先生在演讲前特别希望能独处”,“换句话说,如果你邀请他在晚上演说,他喜欢被安排去某地休息而不与任何人说话。他演讲前往往简单吃一点晚餐,譬如一杯热牛奶,一两个生鸡蛋……他特别讨厌有人在演讲前为他安排晚宴,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得不与人谈话。这样他会特别沮丧。”
不过,虽然演讲前的数小时有点烦躁,而演讲过程本身却又是典型的平静。对于诗人来讲,这种转变过程是漫长的。在早期,他在公共场合演讲总是焦灼不安。1950年,诗人向塔夫茨听众这样描述他1915年在一所大学向学生联谊会朗读他的两首诗时的感受:匆匆逃离“生命的恐惧”,“象兔子一样急急逃离……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在做什么,只是想逃命。”
然而,一旦诗人从一位慌张的朗读者转变为一位沉着冷静的演说者,听众们将会听到诗人对自己作品丰富的阐释,而不仅仅是即席的解读。虽然他说的东西并没有写下来,但也并不是真正的即兴之说。他是显得随意,但并不是临时拼凑。他可能显得好像是一位思维流的演说者,但其演说确是静水流深,不仅如此,他的演说技巧也是一流的。他的友人雷金拉德?库克曾多次参与诗人面对不同听众的演说。他在1956年曾写道:“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可能使得首次听他演说的人认为,弗罗斯特对待演讲非常随意。然而,结论其实恰恰相反。”
诗歌,当然是用来说的,也是用来朗读的——弗罗斯特在他的“吟游”历程中总是告诉他的听众,他想“说”一些诗——听他大声说他的诗,以及阐释他的诗,有一种特别的情趣。但是,除此之外——作为补充或者丰富——就是听他的“自由诗,即兴之说,这样开始”这种演说序幕,听他的阐释、评论,点缀他的“说诗”,也是别具风趣。
诗人带给听众最典型的盛情邀请包含在几个字里:“你也来了。”这是他的《波士顿之北》中一首诗“牧场”的一行诗(这首诗被诗人用作他所有综合诗选集的引子)。
这般热情的邀请,吸引了更大范围的听众主体——正如他在一本诗集的献词中所言“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扩大到了政府和宗教群体”。而其中表达的含义正是确认一种弗罗斯特所谓的“语言的纲性规则”——如其诗“大山”所言——“所有的情趣来自于你如何言说一件事情。”
马克?吐温,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和作家(正如弗罗斯特一样,既是一位文人也是一位公众人物,在英美广受民众喜爱),曾如此区分演讲与漫谈(speeches and talks):“演讲能够被印制成文,而漫谈不可以。”他断言,演讲由认真推敲的句子和思想的圆熟表达准确地与人沟通,而漫谈则不可能。他认为,“漫谈的灵魂”在于“行为”而不是言词——“行为”包括手势以及声音的变化;“思想的无声表达”——所有一切都是一位速记员在记录演说时无法捕捉到的东西。
虽然吐温这样说,但是收集和印制一些演说者的“漫谈”确实有很高的价值。漫谈并非都是廉价的,常常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当漫谈主体是写作和演说大师时,恰如吐温和弗罗斯特那样(他们的漫谈事后都已印制出版)。在即兴的表达中——抑或是真正的即兴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即兴——它不仅包含了说话者想什么,而且还显露出他如何想。漫谈不单是思想的产品,它还富有启示地展示了说话人的思维过程。
罗伯特?弗罗斯特冷静地思考,也把他的思考谈出来。很清楚,从很早的时候——可以回溯到他青少年时代,在1920年代——他就考虑把自己的一些谈话记录下来。1932年,他给友人西德尼?卡克斯写信,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想法——出版一些可能的以谈话为内容的文稿:“我想告诉你,我对于你想与我签订合同的真实想法。目标是我所曾经关注过的一切。我的很多想法已经在诗歌里了。但是,在漫谈中我有一些临时的想法,我担心我绝不会写出来,因为我惰性太强,不想动笔写散文。我觉得,那些想法大多与我的教学相关,是一些关于教育的想法,更确切是说,是一些课程内容。这正是我希望你付出努力之处。我想,如果不太影响你的工作,你肯定愿意为我俩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一年半以后,诗人再次给卡克斯写信:“多年前,我建议你记叙我在漫谈中表达出的但又懒得动笔写下的关于学校、人生、艺术的一些想法,这是很不慎重的。我的想法其实并不是你设想的那样。你以为我是想为自己立传……而我却完全不是出于个人原因。”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尽力回避写前言,这点你也清楚。偶尔,我也希望有朋友来为我作品做阐释。这并不费事,而且如果依靠我的平常漫谈,那比依靠与我进行的专门谈话要好得多。”
弗罗斯特在世时,出版了一些他的漫谈,有的是他授权的,有的没有获得授权。在艾默斯特,这是诗人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四十年代晚期的学术基地,《艾默斯特研究生季刊》曾刊载了他的两则漫谈,发表前他都亲自修改。在这两个漫谈发表之前(1931年),他首先对每个漫谈二十二页的速记文本进行了修订,许多地方修改幅度很大,然后,他又对最初的修改文本进行了大量的增删。1948年出版该谈话时,他这样对《季刊》的编辑谈论他的文本修改:“修订做的超出了你的预计,我是希望这样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篇什。然而,这样恐怕对曾来听了讲座或漫谈的人不够公平。他们会感到十分困惑。我没有直接清晰表达我的观点,这很让人沮丧。”
实际情况是,弗罗斯特总是发现使自己修改演说文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 修订出版1936年他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系列的合同,他就没有完成。哈佛大学出版社寄发给他的这些系列讲座的速记文稿包,他显然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劳伦斯?汤普森甚至猜测诗人最后就把那速记文稿一把火烧了。二十年后,即1956年,共和国基金会成功促成他的允诺,即把他当年在沙拉劳伦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以小册子方式印行,取名为《与学生们漫谈》。在授权书中,诗人强调:他的言谈只能是“漫谈”,没有注释,是“非书面的文章”。
在诗人晚年的时候,曾有那么一次,他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自己一次演讲的全面修改中。这次演讲他为获得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爱默生-梭罗奖章而做的,时间是1959年。他讲的是爱默生,一位他内心极为敬佩的人。他的演讲重点,毫无疑问,是他对特别崇敬者的评价。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表演——“表演”这个词,并不是随意拈来的,在大家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他之前,他就是“一位表演艺术家”——他的表演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能给大家带来听觉享受。恰如库克在1956年题为“作为教师的弗罗斯特”所言:“说话,当然是演讲最主要的构成要素,”总是伴随着各种手势、频频点头、面部表情的不断变化,甚至脚上的步伐。(所有这些也都根据听众的感觉而移动,一会儿靠向他们,一会儿又后退几步。)声音、手势、表情、着装——所有这些人性化的考虑都是那么自然得体,令人印象深刻。弗罗斯特一贯言行一致。在他身上,你永远看不到一个矫饰诗人的影子,也永远听不到不是诗人的声音。
他的听众,无论多和少,都十分清楚,他们在亲身感受一位重要人物的“自然表现”。而这种在演说者和听众两者之间的共识,形成了最初的联结。这种联结在每一个演讲会结束之时,都会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弗罗斯特总是要求把演讲大厅的灯打开,以便他能清晰地看到听众的表情,所以这种联结被强化了。
当他在对听众发表演说时,他总是欲言又止,常常又非常谦卑。他经常在演说中间插入一些旁白。他说话的速度随着自己思考的速度而调整。在这个方面,彼得?斯丹利斯曾参加过诗人多种场合的演讲,也是诗人的好友,他在为诗人的《弗罗斯特百年文集》其中一卷中如此写道:“他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从一点到另一点,乃至从一个短语到另一个短语,他总在思考、即兴地调整,而显然诗人又在不断挖掘内心的东西,希望能从内心深处被遮蔽的某地寻找到一个原创的观念、意象、抑或是类比,但是当这些观念、意象、类比在他内心涌现出来并通过他的嘴说出来时,从说出的过程也能明显地看出诗人在努力寻找直接向每位听者表达的准确词汇和声调。这一切,都真切地反映在他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中。”
伴随着这种融洽的氛围、复杂的思想和信手拈来的惯用语,诗人常常运用一些方言,把“because”缩读为“cause”或者“them”读为“em”,或者把“so as”读为“so’s”——或者说“gotta”,“tis”,“tis’nt”等。为了效果,他有时直接使用分明是俚语的表述,如“That don’t mean……”,“Ain’t it hell……”
简而言之, 他的风格就是一种谈话式的。因为谈话是一种听觉媒介,而不是书写媒介——当与谈话对象面对面时,也是一种视觉媒介——因而弗罗斯特谈话的真实文本,以及他谈话的整体效果,根本无法完全捕获,在书写文本中不得不有所遗漏。马克?吐温在一百年前在口述自传中所谈的完全正确。漫谈编辑毫无疑问常常有机会遭遇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弗罗斯特在六十年前的谈论修订时就说了:“我没有直接清晰表达我的观点,这很让人沮丧。”
作为一位把谈话内容编辑成为文本并出版的编者,他不可能到处都加括号添注释(如给演员的对话脚本那样)说明什么是怎么被说的:认真的,随意的,玩笑似的,等等。一个清楚的例证来自于本选集一个演讲,那是诗人1956年应邀在俄勒冈大学做的演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误释的表述。在他评论的开始,他非常简略地谈到他的教书哲学,以及写作哲学,然后他补充了一些话,这些话对读者好像有点古怪、刺耳:“说起那些各式各色人们,他们装得象我一样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例子,以及其他很所例子,文字稿根本无法复制说话时的情景,包括语调与脸部表情,而那个四月旁晚在尤金的听众都清楚明白诗人这只是一句诙谐的自嘲话。
以印刷文本的方式也根本无法完全展示弗罗斯特演说时的幽默方式。1960年诗人的一次演说(也包括在本书中)中,诗人与他的一位有点醉意的诗友互嘲——诗人模仿诗友含糊不清的说话(“我模仿他说话的方式”),带给听众无比的欢乐——但在文本中无法展示。
本书后面选取的是诗人弗罗斯特在三十二个学校的四十六次演说,时间跨度从1949到1962年,也就是诗人人生最后的十四年。其中,诗人在达特默思(马萨诸塞州南部一个镇——译者注)做的演说数量最多,部分原因是那时诗人在每年学院著名的大讲坛之前都会出现在那儿,而所有演讲都会被录音。尽管录音后来变得很普遍,但在当时,其他地方却是比较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罗斯特的演说每每总是征引很多其他诗人的诗句,包括英国和美国的诗人,而他的征引完全是凭记忆,且准确度很高。读者在后面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诗人会在逐字背诵诗句时偶有疏忽。(在1955年七月一次与面包英语学校的学生谈话中,他问道:“有些诗句沉入你的记忆,与你完全融为一体,最后它发生了某种变异,你们曾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吗?”)
偶尔,诗人对自己写的诗句也会支吾其词,甚至连他非常熟悉的诗歌“桦树”也是如此——1955年他在国会图书馆告诉听众:“我完全能背诵,我对它太熟悉,有时我在中间就忘记了……上次我说这诗时就说错了。”他也熟悉爱默生的诗歌,但有时他也把“给予爱一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开头“Heartily know……,”说成了“Verily know……”
另外,他有时在谈到相关出版物的题目时也有遗忘或者不够严谨,这在后面的文稿中会有不少地方出现:把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变成了《贫穷与进步》,把“联邦论”变成了“联邦论文”,把“空心人”(原文是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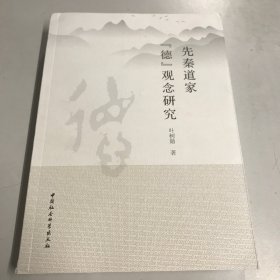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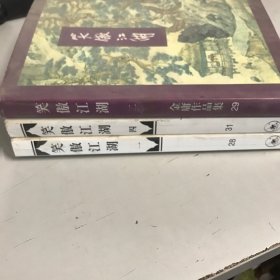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