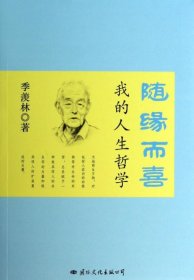
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 季羡林 9787512506640 国际文化
当天发货,全新正版书。
¥ 9 2.8折 ¥ 32 全新
库存104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国际文化
ISBN9787512506640
出版时间2014-04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定价32元
货号162484
上书时间2024-05-2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研习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是季羡林先生作为学界泰斗的生活态度和作为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人。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其问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录
第一章 随缘而喜
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清塘荷韵
槐花
表的喜剧
我的猫
喜鹊窝
神牛
神奇的丝瓜
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朗静山先生
雾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大觉寺
第二章 随遇而安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满洲车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轰炸
山中逸趣
梦萦红楼
翻译《罗摩衍那》
逛鬼城
鳄鱼湖
人间自有真情在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我的座右铭
第三章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论正义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漫谈撒谎
毁誉
世态炎凉
趋炎附势
漫谈出国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成功
缘分与命运
牵就与适应
谦虚与虚伪
走运与倒霉
有为有不为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反躬自省
第四章 思维的乐趣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应多学习外国语言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青年的使命
开卷有益
藏书与读书
三思而行
一寸光阴不可轻
哲学的用处
第五章 悠游一百年
晨趣
时间
回忆
老年谈老
新年抒怀
长寿之道
百年回眸
老年十忌
在病中
死的浮想
笑着走
后记: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内容摘要
《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是季羡林先生作为学界泰斗的生活态度和作为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天地萌生万物,对生命赋予惊人的力量,一花一树,一
只猫,一个路人,一场雨……在季老的眼中都是因缘而生的,他皆以喜乐的态度来看待,随缘而喜;回首百年沧桑,走过阳关大道,行过独木小桥,面对生命中一切无常与得失,季老皆秉承“不喜亦不惧”的态
度,随遇而安,从容应对;关于为人处世的素质与哲学,季老坦言一个老知识分子心声:出于对人类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人还是要有一点信仰,一
点主旨,一点精神;年逾耄耋,面对老病死,他选择“笑着走”……《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感悟生命,体悟人生,季老的文字,平实无华中透露出深刻的人生
哲理,你的心境将因之更加纯净而美好。
精彩内容
小友兼老友唐老鸭(师曾)自南极归来。在北大为我举行九十岁华诞庆祝会的那一天,他来到了北大,身份是记者。全身披挂,什么照相机,录像机,这机,那机,我叫不出名堂来的一些机,看上去至少有几十斤重,活灵活现地重现海湾战争孤身采访时的雄风。一见了我,在忙着拍摄之余,从裤兜里掏出来一
个信封,里面装着什么东西,郑重地递了给我。信封
上写着几行字:祝季老寿比南山南极长城站的植物,每100年长一毫米,此植物已有6000岁。
唐老鸭敬上这几行字真让我大吃一惊,手里的分量立刻重了起来。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株长在仿佛是一块铁上面的“小草”。当时祝寿会正要开始,大厅里挤满了几百人,熙来攘往,拥拥挤挤,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这一株小草。
夜里回到家里,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一株“仙草”拿出来仔细玩赏。第二天早晨才拿了出来。初看之下,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之处,这不就是一
棵平常的“草”嘛,同我们这里遍地长满了的野草从外表上来看差别并不大。但是,当我擦了擦昏花的老
眼再仔细看时,它却不像是一株野草,而像是一棵树,具体而微的树,有干有枝。枝子上长着一些黑色的圆果。我眼睛一花,原来以为是小草的东西,蓦地变成了参天大树,树上搭满鸟巢。树扎根的石块或铁块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大山,巍峨雄奇。但是,当我用手一摸时,植物似乎又变成了矿物,是柔软的能屈能折的矿物。试想这一棵什么物从南极到中国,飞越千山万水,而一枝叶条也没有断,至今在我的手中也是一
丝不断,这不是矿物又是什么呢?
我面对这一棵什么物,脑海里疑团丛生。
是草吗?不是。
是树吗?也不是。
是植物吗?不像。
是矿物吗?也不像。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认为它是从南极万古冰原中带来的一个奇迹。既然唐老鸭称之为植物,我们就算它是植物吧。我也想创造两个新名词:像植物一般的矿物,或者像矿物一般的植物。英国人有一个常用的短语:atone'swits'end,“到了一个人智慧的尽头”,我现在真走到了我的智慧的尽头了。
在这样智穷力尽的情况下,我面对这一个从南极
来的奇迹,不禁浮想联翩。首先是它那六千年的寿命。在天文学上,在考古学上,在人类生活中,六千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是,在人类有了文化以后的历史上,在国家出现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中国满打满算也不过说有五千年的历史。连那一位玄之又玄的老祖宗黄帝,据一般词典的记载,也不过说他约生在公元前26世纪,距今还不满五千年。连世界上国家产生比较早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印度,除了神话传说以外,也达不到六千年。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株“植物”开
始长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国家。说是“宇宙洪荒”,也许是太过了一点。但是,人类的国家,同它比较起来,说是瞠乎后矣,大概是可以的。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再想到人类的寿龄和中国朝代的长短,更使我的心进一步地震动不已。
古人诗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过去,人们总是互相祝愿“长命百岁”。对人生来说,百岁
是长极长极了的。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在一百年内只长一毫米。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是周代,约有八百年之久。在这八百年中,人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动呀。春秋和战国都包括在这个期间。百家争鸣,何等热闹。云谲波诡,何等奇妙。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却在万古冰原中,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约八毫米。周代以后,秦始皇登场。修筑了令全世界惊奇的长城。接着登场的是赫赫有名的汉祖、唐宗等等一批人物,半生征战,铁马金戈,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一直到了清代末叶,帝制取消,军阀混战,最终是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千头万绪的史实,五彩缤纷,错综复杂,头绪无数,气象万千,现在大学里讲起中国通史,至少要讲上一学年,还只能讲一个轮廓。倘若细讲起来,还需要断代史,以及文学、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民族等等的历史。至于历史人物,则有的成龙,有的成蛇;有的流
芳千古,有的遗臭万年,成了人类茶余酒后谈古论今的对象。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悠久的岁月中,赤县神州的花花世界里演出了多少幕悲剧、喜剧、闹剧;然而,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两厘米多一点。多么艰难的成长呀!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
我们的汉语中有“目击者”一个词儿,意思是“亲眼看到的人”。我现在想杜撰一个新名词儿“准目击者”,意思是“有可能亲眼看到的人或物”。“物”分动植两种,动物一般是有眼睛的,有眼就能看到。但是,植物并没有眼睛,怎么还能“击”(看到)呢?我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诗意的说法,请大家千万不要“胶柱鼓瑟”地或者“刻舟求剑”地去推敲,就说是植物也能看见吧。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是万世师表,万人景仰。到了今天,除了他那峨冠博带的画像之外,人类或任何动物决不会有孔子的目击者。植物呢,我想,连四川青城山上的那一株老寿星银杏树,或者陕西黄帝陵上那一些十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古柏,也不会是孔子的目击者。然而,我们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是有这个资格的,孔子诞生的时候它已经有三千多岁了。对它来说,孔子是后辈又后辈了。如
果它当时能来到中国,“目击”孔子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能力了解,这一株“植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向唐老鸭问清楚:在南极有多少像这样的“植物”?如果有多种的话,它们是不是都是六千岁?如果不是的话,它们中最老的有几千岁?这样的“植物”还会不会再长?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我眼
前的这一株“植物”,身高六厘米,寿高六千岁。如
果它或它那些留在南极的伙伴还继续长的话,再过六千年,也不过高一分米二厘米,仍然是一株不起眼儿的可怜兮兮的“植物”,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今后的六千年却大大地不同于过去的六千年了。就拿过去一百年来看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做到了;过去认为是幻想的东西,现在是现实了。人类在太空可以任意飞行,连嫦娥的家也登门拜访到了。到了今天,更是分新秒异,谁也
不敢说,新的科技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一百年尚且如此,谁还敢想象六千年呢?到了那时候人类是否已经异化为非人类,至少是同现在的人类迥然不同的人类,谁又敢说呢?想到这一切,念天地之悠悠,后不见来者,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我只能惊诧得瞠目结舌了。P26-27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