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见日曹军庆北京十月文艺9787530220917全新正版
¥ 24.73 4.3折 ¥ 58 全新
仅1件
作者曹军庆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
ISBN9787530220917
出版时间2020-1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1037647
上书时间2024-11-0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商品简介
《会见日》是涉及吸毒与戒毒题材的作品。“会见日”指每个月的15日是强制戒毒所的会见日,它既是本书首篇故事的篇名,也在后面的篇章中多次呼应。一系列“会见日”的故事即一系列的人物传记,真实地展现了当下戒毒人的生活群像,勾画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在戒毒前后内心跌宕起伏,自我救赎中痛苦与心酸的生存状态。
小说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因此具有生活的深度。作者希望讲述和还原人物与事件的真相,曾选择在当地一所强制戒毒所体验生活,观察和采访,同时,作者的创作又充满虚构和想象,通过形形色色吸毒病人的离奇经历,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镜像世界,令《会见日》在饱含生活真实的同时获得艺术真实。
作者简介
曹军庆,生于1962年,现居武汉。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向影子射击》等。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曾获十月文学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储吉旺文学大奖等。
目录会见日
读词典的人
耳鸣症
在美容院楼上
假发套
吹牛者
小镇兄弟
应有之义
纸上的父亲
外科手术
猜忌
一封没有寄送地址的信
去往济南的路上
线人
木头镇曙光肉联厂
卧底
前妻之间
大同小异的故事
本命年
天上的街市
内容摘要《会见日》是涉及吸毒与戒毒题材的作品。“会见日”指每个月的15日是强制戒毒所的会见日,它既是本书首篇故事的篇名,也在后面的篇章中多次呼应。一系列“会见日”的故事即一系列的人物传记,真实地展现了当下戒毒人的生活群像,勾画了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在戒毒前后内心跌宕起伏,自我救赎中痛苦与心酸的生存状态。
小说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因此具有生活的深度。作者希望讲述和还原人物与事件的真相,曾选择在当地一所强制戒毒所体验生活,观察和采访,同时,作者的创作又充满虚构和想象,通过形形色色吸毒病人的离奇经历,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镜像世界,令《会见日》在饱含生活真实的同时获得艺术真实。
精彩内容这段时间我在一个隔离强制戒毒所里体验生活。那个戒毒所的地理位置是这样的:它的东边是火葬场,南边也就是它的大门正对面是一座监狱,西边是刚刚开发的一所花卉度假庄园,北边也就是它的背面则是大片农田。我在强戒所的办公楼里有一间住房。每天早晨叫醒我的是火葬场的哀乐和鞭PAO声。我在这混响声里起床,拿着饭盒到后面院子里的食堂去吃饭。后面的院子才是戒毒学员住宿和做手工的地方,前面的院子则是办公区域。要走到后面院子里去,我必须穿过空空荡荡的前院。东边的火化炉正挨着强戒所的院墙。我抬起头来,一边往后院走,一边望着烟囱里冒出的淡淡黑烟。火葬场上空冒出的黑烟和工厂里冒出的黑烟有什么区别呢?我想象着某个死者正在融入天空。
每月十五号是强戒所的会见日。这天我看见一个女人来探视她的儿子,我在他们会见之前采访了她。她在南方打工,一个月收入三千五百块钱。出租屋的租金八百块钱。她是个白血病人。她儿子二十一岁,因为吸毒进了强戒所。她强调了好几遍,对我说她儿子是个吸毒者。儿子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前夫(对了,她离婚了)也是个吸毒者。他好像还犯了另外的事情,被关在监狱里面。关押她前夫的地方就是强戒所大门对面的那座监狱。她前夫在她之前还有另一任前妻,他和另一任前妻有个女儿。那女儿是她儿子的同父异母姐姐。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也是个吸毒者,他姐姐所嫁的男人也就是她儿子的姐夫也是个吸毒者。女人很羞怯地对我说,你明白吗?我儿子只能依靠我。我是我儿子唯一的依靠。因为化疗,女人的头上已经没有头发。她掀掉头巾,让我看她的脑袋。她说为了儿子,她现在要好好地活下去。她还要多挣钱,每个月给儿子打一千块钱零花钱。打在他卡上,她说,卡上有钱他才可以每周在内部超市里买点东西。这个故事我后来改头换面,写成了《前妻之间》。
会见日的第二天我离开了强戒所,我想找个地方独自静一静。强戒所里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会慢慢写出来,但是现在我要离开那些故事。那么去哪里呢?我想到了白龙山,白龙山上有个白龙寨遗址。如果白龙寨遗址可以过夜的话,我倒是愿意住在那里。即使不能住在那里也没关系,那地方人烟稀少,现在我只想到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去。去那里干什么呢?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我就需要这么一次旅行。我想远离那些吸毒者。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生活才是破败的生活,但是我至少还可以见证另外的事情。去一个遗址。据说白龙寨里曾经出现过某种很奇怪的文明。有一篇题为《装在蛇皮袋子里的手稿》的小说,讲述过那里的故事。
我开着车来到飞沙镇。这镇子的一半像是乡村,另一半则像是城镇。街道和房屋混杂不堪。没有指路牌。房屋的门脸上也没有门牌号码。有人在大门口——也有人在马路牙子上摆开桌子打麻将。我问一个人去白龙山怎么走,那人站在路边。他像是这个镇子的旁观者,嘴上叼着烟,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你去那里干什么?”他说,“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说,“我想去那里看看,走走。”
“随便你!”他随后给我指了一条路,“你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可是去白龙山不能开车上去,那只是条羊肠小道。”
“走到山上有多远呢?”
“不远,也就十几里地吧。”
看来我只能先找个旅馆,把车停在镇子里,徒步上山。从山上下来后,我还得在这里住一晚上。镇子上的旅馆倒是有不少,我入住的那家旅馆现在想起来非常像是一家屠宰铺。睡在罗爷楼梯下面的小屋里,我闭着眼睛也能回忆起旅馆的院子里杂乱无章。它的名字就叫拖拉机旅馆。招牌是一块小黑板,旅馆的名字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面。房间的价格也用粉笔标在上面。院子里到处都是废弃的等待清理的杂物。角落里甚至真还停放着一辆报废的手扶拖拉机。叫拖拉机旅馆就一定要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实物吗?旅馆的老板也太实诚了吧。我之所以说它像是屠宰铺,是因为我怀疑这个院子很适合吊挂白晃晃的动物尸体。我可能刚做了一个梦。那些在我梦境里被屠宰完毕的猪狗或牛羊或猫或狗在大木桶里煺完了毛发。然后吊挂在木杆上开膛破肚。院子中央果然就有几根这样的木杆子。木杆子之间平素里也可以拉上铁丝或绳索,晾晒旅馆里洗过的衣被。等到屠宰的时候,就可以吊挂动物尸体了。地上污水横流,从污水里很容易辨认出动物的粪便或血迹。我那辆又旧又破的黑色别克车就停在那些杂物的缝隙里。
旅馆的男人看上去有些蛮横无理,他说:“我姓杨,你就叫我杨老板吧。”
杨老板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证。我从钱夹里掏出身份证递给他。他拿着我的身份证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好几遍,样子就像是超市里的收银员收到了一张怀疑是JIA币的钞票。可我的身份证不是假的。杨老板这时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这上面的照片是你吗?”
我说:“是我呀。”
“你怎么比照片上的人老了那么多啊?”
我不知怎么回答他,这算什么话。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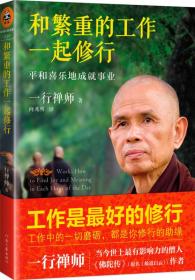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