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二手]昨日的世界 9787108003263
¥ 49.5 ¥ 18.6 八五品
仅1件
浙江杭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奥)茨威格(Zweig, SteFan)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03263
出版时间1996-0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485页
定价18.6元
货号a003
上书时间2016-12-07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8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 商品描述
-
【图书描述】:
本书作者围绕个人的经历,回顾了从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和奥地利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风貌。着重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社会的变化和希特勒的崛起及1横行欧洲的历史见闻。
【内容简介】:
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作者简介】:
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20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感觉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茨威格在诗、短论、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写作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尤以小说和人物传记见长。茨威格对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作品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他的作品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销售量高达数百万册,是当今拥有读者最多、最受读者喜爱的奥地利德语作家。
【目录】:
序言
太平世界
上个世纪的学校
情窦初开
人生大学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我的曲折道路
走出欧州
欧州的光辉和阴霾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在欧州的心脏
重返奥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西山
希特勒的崛起
和平的垂死挣扎
译后记
【文摘】: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跟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尽管我同样赞赏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优美的散文、《安德烈亚斯》的片断(这部未完成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束缚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稚气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粹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那种描绘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魅力。我们以一种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青年一代中,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不会重演。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一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土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小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
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昧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会儿,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似的借助地下铁道和各种汽车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浑身冒着热气、肥壮的马匹牵拉的厢式豪华马车。诚然,从这类宽敞的豪华马车的第二层上,即从车顶的座位上,或者从同样不是急驶的敞篷马车上观光、巴黎,是最方便不过的。不过这样一来,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十分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那些传闻讲:有一些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却从未到过塞纳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却从未见过图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门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在大巴黎内部替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乡土色彩。所以对一个外地人来说,选择何处下榻,得下一番决心。拉丁区对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逗留时,我一下火车就向那里奔去。第一个晚上,我赫已经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并且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酒醉时老是用自己粗实的手杖怒气冲冲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给我自己增加些体面。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这个不喝酒的诗坛小跟班还曾喝了一杯苦艾酒,尽管我觉得那种发绿的蹩脚酒一点都不可口。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这拉丁区里烙守法国抒情诗人们的仪式。按照当年的时尚,我最愿意住在梭尔邦区的一间六层楼上的阁楼里,以便能比我从书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实地领略拉丁区的“真正”风采。可是当我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不再觉得那里显得十分古朴和富有浪漫色彩。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居住区太国际化了,太没有巴黎味了。再说,我替自己选择一处长久的住所,
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种文人的怀古情绪,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十分经心地四处巡视。我觉得,从有利于工作这一点讲,香舍丽榭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附近就更不合适。——所有那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馆约会,除招待员外,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绪尔比斯教堂周围的清静地区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也曾喜欢在那里居住;就我的愿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联结塞纳河两岸的圣路易河心岛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个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处更美的地方。当我在罗亚尔宫的画廊里溜达时;我发现在由“平等”公爵于十八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当年鹤立鸡群的高雅府第现在已降为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给我看了看里边的一间房,我十分惊喜地注意到,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正好看到罗亚尔宫的花园,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花园已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也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犹如远方海边的波涛不断拍击的声音。塑像在月光下闪耀,清晨,风儿有时会把附近“厅堂”里的浓郁的菜肴
香味吹来,在罗亚尔宫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中曾居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们。在罗亚尔宫的街对面是那幢玛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居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常在这幢房子里攀上成百级的狭窄梯阶,到阁楼里去造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罗亚尔宫是卡米耶?德穆兰号召人民群众向巴士底狱进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闪耀着冷酷无情的光辉,罗亚尔宫里那条铺着地毯的走廊曾经是一群并不十分崇尚伦理的夫人们悠闲散步的地方,那个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群妇人中间为自己寻找过一位女恩人。总之,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叙说着法国的历史。此外,只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便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绘画的罗浮宫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也都不远。我终于住进那个最合我意愿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是法国的脉搏、巴黎的心脏。我今天还记得安德烈。纪德有一次来看我的情景。他对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清静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国人来向我们指出才是。”说真的,在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最热闹的市中心,除了这一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以外,我再也无法找到另一处既具有巴黎的风格、同时又非常僻静的地方了。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于事。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正版二手]昨日的世界 9787108003263](https://www0.kfzimg.com/G00/M00/44/B3/oYYBAFbrCneAYGvzAAAvdThOb8g675_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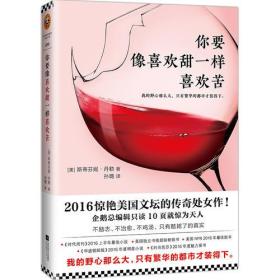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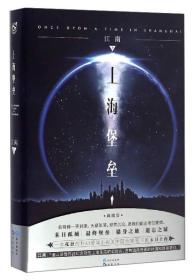


![[正版二手]昨日的世界 9787108003263](/dist/img/error.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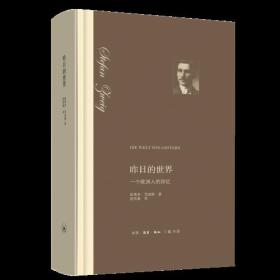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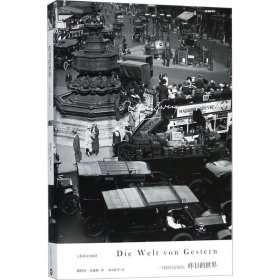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