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如诗
¥ 9 3.5折 ¥ 26 九五品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李岩 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
版次1
印数1千册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4-12-0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李岩 著
-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8-01
- 版次 1
- ISBN 9787510866470
- 定价 26.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228页
- 字数 154千字
- 【内容简介】
-
李岩,收藏家和飞行爱好者。海南省海口市人,1962年生,1995年起经商至今,2007年被海南省发改委授于“海南省服务业优秀创业家”称号。中年开始写作,散文《俞老师的教鞭》,发表在《散文时代》上,从此走上创作之路,在《华文月刊》上发表了诗歌《汽车旅馆》。著有《腐乳》《电视机》《百花岭》《驮一麻袋钱的人》等百余部散文和小说,另有诗歌多部。
- 【作者简介】
-
李岩,收藏家和飞行爱好者。海南省海市人,1962年生,1995年起经商至今,2007年被海南省委授于“海南省服务业很好创业家”称号。中年开始写作,散文俞老师的教鞭,发表在散文时代上,从此走上创作之路,在华文月刊上发表了诗歌汽车旅馆。著有腐乳电视机百花岭驮一麻袋钱的人等百余部散文和小说,另有诗歌多部。
精彩内容:
每天八点后我已经惯了作息,吃早餐后下楼来散步。这,太阳偏西,照在小区里一个个向西的楼宇间,影子像块印花布摊在绿的草坪上。我曾听南宁朋友说快步对身体好,他说不叫散步叫健步。我听他的话双腿一前一后快速交错着,仿佛自己是匹千里马,正扬鞭走在小区里的林荫小道上。
走过游泳池,来到会所的北面,绿的草坪上种着几棵我叫不上名字的树。前天我见到它们刚换下春天的戎装,夏里的叶片在枝丫上随风摇曳,像一把把遮阳的伞亭亭玉立在阳光里,映在地上类似一把把伞影,这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我站在树下,往上看阳光在嫰叶上,叶里的筋脉一条条清晰可见,很好看。可现在的我被眼前的事情吓着了,也可说是生气了,纠结中又怕自己多管闲事,可我的正义感放不过自己,我在忐忑不安中选了几个对角拍完相片,锯树的“吱吱”声和那烧油的机器仍在吃力地“嗡嗡”叫,只见一个工人双手握住长柄电锯在锯汽车入处的大榕树上的枝杈。一个脑袋光滑得像机场跑道的人,正面向着锯树的工人,左手腰,右手在指挥着他锯哪棵枝杈。锯着的枝杈经不起“牛顿的苹果定律”,在“吱吱嘎嘎”声中痛苦地掉在地上,像是人的胳膊在外力作用下迫不得已离开了自己的躯体。我见他是物业的人,便上前责问:“现在是五月天,哪来台风?长得这么好的树被你们锯得只剩下赤裸裸的树干了。”我边说边指给他看眼前的树,像条条电杆竖在我们跟前。
他被我突如其来的责问吓住了,转过身来。他一看,知道我是小区里的业主,心里有点慌,像是做了坏事的顽童。他的目光随我的手去看刚才锯的那几棵树和搁在草坪上锯下的枝丫。我指着他的头说:“你怎么把这几棵树锯成了秃头?”
他不让我指他的脑袋打比方,闪到一边去。他指着树下的草坪说:“树长得太密了,才锯了的,”停顿了一下,看我的反应,“影响地上的草坪成长。”
我不想一针见血地捅破他,让他下不来台,因为大家都在小区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靠小道上的一棵长得优选的树下,前几天才补种草坪,那么其他的树下都长得茂盛像块绿的地毯般的草坪,难道是因为树长得太密了?
我转移话题去说树也有生命,有生命的东西会有灵魂:“树也是有灵的,你对它好它对你好。”他抬头看我,好像在听自己的父亲给他讲童话故事。“你信否?”他在点头认可,我接着趁热打铁引导他说:“我听到树在哭泣,你听到了吗?”见我这么认真地问他有点慌张,侧耳,好像他也听到树在抽泣,心里纠结了。我接着说,“你不应该叫人搭梯子上去把树顶也裁了,树顶是树的脑袋,修整枝丫可以了。”
他好像觉得有理了,说:“这树长得很快。”
我见他还钻牛角尖,说:“这是五月天啊!拿什么遮阳?”
看来和他说下去也是白说了,因为树已经被他们毫不留情地锯下来了,我怕下面的那几棵大榕树受到他们同样的“毒手”,想起我公司门前的那一排种在人行道上的“印度树”,前年也是被园林公司裁剪枝丫。
“经理,有人在我们公司的门前砍树。”我随声音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前台的人员指着门外让我看。我见自动门外有人手持电锯,锯得枝丫“嗷嗷”响,我赶紧走出来,见他们围着门前的一棵树,像围着猎物,锯得枝丫一支支地垂坠下来,重重地抛在地上。我见旁边的一棵树被他们当作“顾客”被剪成秃头了。这还了得?行人用什么遮住夏季里的太阳?我赶紧上前去制止他们的行为,要锯也不能锯到一叶不剩的地步。可他们坚决执行上司的命令,叫我去找他们的。听了我的话有理,叫他的手下留情。
我把这事简单地讲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认可,像我所说的“”去制止他的手下对树留情。到我和他说拜拜时,他突然觉醒似的,对我说:
“谢谢你!我今后在这方面注意,再也不这样了。”
我见他如做错事认错的,便对他说:“这对了,”我边说边走在小道上,“树会感谢你的。”
当我走回来时,见他和那个工人已无踪影了,大榕树呈金字形,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我站在它的前面像个卫士,它的枝丫在抚摩我的脑袋,我想它在笑,我心里也甜甜的。
无巧不成书。从东莞来了一对我三十多年没见面的兄妹,哥哥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可说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那时候我们年轻,正赶上春天的脚步,谈情说爱的季节。她的身段仿佛是婆娑画的一幅画,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该纤细的地方纤细,肥臀细腰。她早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红了山峦,很招人的眼热。我们家和他们家相隔一条水泥公路,我一闲下来借找她哥哥玩去,实是自己像地里的泥鳅滑溜溜地爱往他们家钻。多是在厨房里见到她,她家的厨房里的灶台在坎下,我一来坐在坎上宛如坐在几节台阶上看戏,看着她坐在灶台前和她说话。那时候烧柴做饭,她一停下话,弯着身子向灶台里添柴火,我的心管不住自己的眼睛,火辣辣地往她漏光的地方看去。但他哥不同意我们好。
他们一到我家里,屁股还没着沙发,她打乱了我的安排,嚷着要我马上开车载他们去琼中县。他们是客人,我只能听从,我拿着几件换洗衣服放在一个袋子里,他们也拖着行李箱跟我出门。我们在车库里开车出来,建琼,她的亲哥哥坐在副驾驶上见我掏出手机寻号码问我:“不会吧,没熟路去琼中的?”便侧过脸来。他的妹妹叫建妹,她从后座把脑袋伸到我眼前,可惜她老了,白发在淹没她的黑发。
“阿岩哥啊!”她喊我名字还如当年般亲切,“你在找谁呢?”
我把车停在小区的岀说:“在找我妹夫问路,他常去琼中。”
幸好手机在妹夫的身边,他说:“从你家一岀来,从疏港大道一直走是琼中了。”
经他一点我明白了,忙说谢谢。
“岩哥啊,你多久没有去琼中了,连路也不熟了?”建妹为难地问。
我边启动车边看路说:“高速公路刚开通。那天雨天我坐朋友的车从另一条路上高速,去过一次。”
建妹“哦”了声。建琼有点担忧,他转过脸来盯着我说:“你不会走错路吧?我妹下午聚会。”
我逗他:“我加满了油。”
他果然当真了,斜过身来看方向盘下的油表说:“哪加满?”
我不怀好意地说:“路上都有加油站,你们怕什么,大不了你撒一泡尿到油箱里去。”
他哈哈笑了起来,不说了。建妹和当年一样,话特别多,左一声右一声甜甜地叫我名字,岩哥呵,岩哥啊。我只是偶尔应和着。
世界可以改变人,人也可以改变世界。可怎么不能让建妹的话少点呢?她一见我仿佛把我们中断这三十多年的话用渔网捞回来了。她像我家养的八哥鸟站在我肩膀上啄我的脸庞,“叽叽喳喳”影响我开车,可是我又不好开明对她说,只得像舰上的打旗兵,不时在后视镜里用眼睛对她暗示,但她不当回事儿,明知故犯,调皮得很。坐在一旁的建琼看在眼里,可是他也不当回事,任由他妹妹坐在后面“扰”我、摆布我。
在路上,建琼兄妹一路感慨海的变迁,让他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东西南北,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在整洁的街道旁,衬托在绿化景观里。我似乎有些了解他们心中的渴望:要能在这里买套房该多好,将来在这里看海景养老,呼吸海里飘来的新鲜空气。
是什么给他们兄妹洗了脑,终于把他们阻塞的脑筋疏通了?
我侧过脸调侃建琼:“那时候我对妹有意思,你却对我说:‘我妹妹要和父母一起搬回东莞,她不嫁这里人。’”他无言,像老人沉浸在记忆中。我又说:“女人嫁谁是她的自由,谁也管不了。”建妹插话道:“我现在过得也不赖。”他们是知道我的一些事业的,所以不用我道明,谁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建妹,恰好和她眼睛对上,到底是我闪开了,还是她?
高速公路刚开通路况好,车也少。
“啊!我又超速了。”我说。我赶紧松油门按下方向盘上的定速巡航按钮。
建琼不想继续我刚才的话题,他转移话题说:“好车是不知道开车快”
建妹插进来说:“让岩哥被罚钱了。”
我说:“没事,下次注意成了。”
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像溪水流到一棵大树头湾下,逗留回味也是,那是初恋情人的霞光。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匝道,警示牌拦住了去路。我松了油门,定速巡航也停止工作了,车速放慢后我看到路边的路牌:“枫木”。枫木离琼中县城还有30多公里,为什么不让我们走了呢?难道我只好按着路上的警示牌指示的方向把车开去枫木。建琼兄妹慌了,建妹颤抖着下巴在后视镜里看着我问:“岩哥,你不会把车开错了吧?我下午真的有个同学聚会。”
我她焦烦的心,说:“可能前面修路,从这里下高速。枫木有条老路到了大边河也到营根镇了(营根镇是琼中县的县城)。”
建琼胖乎乎的身子让我想起了他的小名肥仔。他像块肉泥摊满在座位上,孕妇般的肚腩随着车颠簸而抖动。肩膀上撑着个见不着脖子的脑袋,像只打满气的气球转向我,双唇一开一合地在笑容里放出声音来。他几乎忘却了海南话,现在正用满粤语腔说着让人似懂非懂的海南话。他说:“你无路(你知不知路)?跑了白跑。”
刚开始我以为他和他妹妹说话,见他凝视我,才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毕竟我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广东人,多多少少也接触过他们的方言,他们的方言像碗里半生不熟的白米饭。我说:“枫木,谁都懂的,有条老路到琼中的。”
他“哦”了一声。
我的车一下匝道上了老路,海渝中线公路。我打方向盘向着南去,南去的终点是三亚,途经琼中县城。这仿佛燃起了他们兄妹的记忆,两人如巢里的麻雀又吱吱喳喳了起来,夹杂着我一知半解的粤语。
“路上长了这么多的树,”建琼触景生情地说,“刚才在高速公路上光秃秃的,现在绿绿的一片。”
我从车里往上一看,山上的树木几乎把快到中午的太阳遮住了,从路边的大叶桉树里照下来的叶影,点缀着蜿蜒在山坡上的柏油路面,像一卷村姑摊开的花布。我们像走在大自然里,走在大叶桉树搭起的隧道里,又好像在一条刚建好的真空管道里奔跑。
我说:“建琼,你还记得吗?我们上小学时老师常带我们去百花岭上砍柴火给群众饭店赚钱做班费。”
建琼反应灵敏,说:“怎么不记得呢,上中学还利用期砍柴火送去学校,否则开学时不给报名。”
那时候,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几乎耗去了我们大部分精力。
这是久远的故事,我们的手、我们的肩膀也老了,再也经不起岁月的蹉跎了。
时代发展变迁太快,我们的车经过湾岭镇这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我们却认不出来,只能凭借路牌才知道。湾岭繁华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到了大边河。我们怎么能忘记我们眼前的这条水泥桥?她依然容貌美丽动人。我们读小学时老师带我们在下走近十公里的路,拿着铲子、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浩浩荡荡地来到河床掏沙子,给建筑工人盖房子。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活像一个个小。我想把车从桥头开到桥下去,可是眼前的路已经被长得比人腰高的野草挡了去路,我只好把车停在边上下来。我瞭望河水,只见清清的河水都快淹没岸边的草了,不见半点沙子。远处的溪水像条绕在树林里的白布练哗啦啦地往河里流,向北去。我想现在县城里的人上哪掏沙盖房子呢?
我一上车,建妹先问我:“岩哥,你看到什么了?”
我边发动车边说:“以前的大边河里面的河水很少的。”我顿了一下,以为他们会插话,可是他们却静静地听着我讲。“现在看不到河床了,到处都是绿绿的树,清清的水。”
他们专注地向车窗外看去,呼吸着外面飘来的泥土气味。建琼说:“这是我的故乡。”
人过中年是在记忆中,我突然想起,说:“记得你离开琼中时发过誓,再也不回来了。”我停下话看他的反应,“现在是什么使你改变了呢?变成了你的故乡。”
我在挖苦着建琼,揭他过去的伤疤。
建琼不好意思了,如道歉地说:“琼中是生我养过我的好地方。”
他的回答简短真挚,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反驳他,只是感叹他念旧。我想他是看到满山的绿的叶子,回想起自己走的时候,这里曾经被我们这一代人前赴后继地过度开荒造田伤害过,现在只有一颗弥补的心,在召唤着自己。我虽然没有听到他催促我把车开快点,他要到琼中县城里去看一看,看他住过的气象局现在怎么样了,可是我感觉到了他的心潮在澎湃,仿佛要去寻根问祖。我们从湾岭起想在路边找饭馆,因为已经十二点整了,想吃点有当地民族特的食物饱饱福。可是我们人生地不熟,一路寻来,都过大边河的水泥桥了还没找到满意的饭馆。我和建琼都是二十世纪虎年生的,建妹我不知道她属相是什么?之我和她哥哥这时候是只老虎,是只饥饿的老虎,在自己曾经“狩猎”过的山里,猎物满山都是,在树林里,我们竟然没有了抓猎物吃的本领?那我们和动物、植物合为一家人吧!谁也不伤害谁,这叫共存。忆起朋友林军老婆说过到琼中时找她请客。我哪能去找人家请客?但想请他们吃个饭,在微醺中好叙旧,叙叙同窗几年的故事。我掏出手机拨了她的手机,长话短说,三言两语搞定了中午的饭局。
我们的车离开柏油路面进入一条六车道的水泥路面,这仿佛是告诉我们要上琼中县城的街道了,街道两旁各有一条人行道在绿化带的边上。棵棵树伞的底下,人行道上铺着红的、灰的砖块,交错形成一个个颇具黎苗族特的图案。绿化带的外面是高楼大厦,大厦间隔着一个个小花园。
建琼是个容易惊喜的人,这和他童年里的生活有关,对没有见过的事物,他都满怀热情的惊喜,不断发出“这这”声。这让我想起电视里头的老外,老公给老婆买个本来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给她,她接在手上一边端详着礼物,一边装作天真女孩惊喜:“哇!哇!我太喜欢了,”并去亲老公的脸上,给他拥抱,仿佛是奖赏,还连连问道:“你上哪儿买的?”文雅地说,这是会经营美满的生活。通俗地说,这叫作会做人,博得人家喜爱。下次她的老公还会记着给她礼物,虽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博得夫人喜欢。
建琼惊喜地问我:“这条这么宽的路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我一看像一条跑道,依山而去,能降波音747了。
我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回他,他的妹妹建妹时是个慢悠悠的人,这时候她的子可急了,也问和她哥哥同样的问题,我不好如实说不知道,怕他们会马上笑话我家离琼中这么近也不回来看看。我在想这条街的年份,见路边沟里有青青的苔,由此我断定这条街的年龄便脱说:“五六年了。”
建琼不信我的话,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想回他的话,因为我认为这是废话。上了水泥路,路上的人车也多了起来。
建妹把脑袋伸到挡风玻璃,她整个身体从我和她的哥哥之间横过,她好像在寻找她的记忆,记忆是在脑海里闪过。
“岩哥啊!这里会不会是什么来着?”我知道建妹在问“零公里”,因为零公里在那个年代里是一个很好有名的地名,仿佛是一个景点,实是一条公路的起点,比如去乘坡从这里去。所以在公路边的草丛里竖着一块长方形的石头,上面刻着的“0”字也格外引人注目,人们以此叫它“零公里”。许多东西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遗忘了,唯有“零公里”这个公里牌像烙印烙在我们这几代人的心里。我不知道,也不去“古”,昔泥土飞扬的公路变成柏油路面,有个漫长的过渡时间。现在这条拓宽了的水泥街道,会不会把原来竖在草地里的路牌像硬盘里的资料删除,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叫那里为“零公里”?之我们永远都记得它,这里有着我们童年的天真回忆。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里,我外婆好不容易从乡下给我们家拎来好吃的,里面有一只加积鹅。琼海人会搞吃食的,我外婆会养牲畜,每当过年前几个月她会和乡里人一样,硬生生地给鹅喂食,往鹅嘴里灌搅着猪油的米糠,一直灌到脖子上,鹅肥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谁料到关在鸡窝里的这只大肥鹅想逛城市里的霓虹灯世界,夜游了。第二天一早我外婆喂鹅时发现它跑了,邻居纷纷为我们家惋惜,说我们的鹅夜间唱歌。我们怨恨快到嘴里的这只大肥鹅怎么不能给我们家留点面子,让我们在春节里多块鹅肉吃。我的父亲不甘心鹅这样丢了,他怕贼如猫头鹰似的夜间叼去吃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动员,让我们四处去找,找到零公里。那时候没车,光靠双腿奔波,觉得零公里好远哦。多后,我们家来了一个久违的朋友,他在饭桌上和我们一起说起过去的事,不知不觉中他讲起了他很快乐的。夜里他走在零公里的路上捡到一只肥鹅,解决了全家人在春节的肉食。他不知道当时鹅的主人一直在寻找这只鹅的去向,仿佛是活着见人死要见尸。他说的时间和地点恰恰和我们当时的“案情”吻合。我妈是个急子的人,她听到这儿热血沸腾,容不了人家讲捡鹅的经过,她要的是结果,问:“你看见鹅脚上绑一根红线?那是我们家丢了的大鹅。”
这位朋友听了好奇了,讲话更来劲了。他刚开始只是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好打发饭局上的时间,以在饭桌上无话而尴尬。他停下话来,把手中要夹肉吃的筷子收回,搁在碗上盯着我母亲看,见我妈要说话似的,又见我们一双双眼紧盯着自己,好像自己三更半夜不是在零公里捡到人家的大鹅,是在零公里的路上偷了朋友家的大鹅。他顿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巧合,赔钱?什么年代了?谁还在乎这一只鹅?
我母亲见他无话可说,便问:“鹅脚上她用红线绑了三圈做记号的。”
朋友连连叹息,说:“是啊,是啊,绑三圈红线,我记得红线也新新的,一看是鹅的主人刚绑上的。”他停了一下,见我们无话,找出几句良心话来我们这烧焦的心:“我们也想找鹅的主人,可是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你们是知道的,老婆和孩子是从乡下来的,没有户,没有肉票,春节里的肉还没着没落”
我要回建妹她的话,她哥哥先说了:“零公里。”我说:“不、不,这里应该是六队还是四队。”然后指给他们看前方看不着的地方,“下面才是零公里。”
建琼说:“我知道了。”他说着又去看窗外纷纷向后移去的楼宇。倒是建妹问我:“岩哥啊,等下带我们去红旗中学看我们读过书的地方。”
建琼一听见他妹妹提起红旗中学,他可来劲儿了,马上转过脸来看他妹妹,纠正她:“听说红旗中学不叫红旗中学了,叫什么来的?”
他的一惊一乍让我一时也想不起来红旗中学的现名,我想安排他们和林军的老婆吃饭后去实现这一愿望。
“我先找林军的老婆带我们去找好吃的,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解决了午饭,然后再去县中学好不好?”我如安慰一个小女孩似的。建妹一听我点到县中学,她好奇地问:“不是去红旗中学吗,为什么要去县中学?”
那时候的政治彩很浓,浓到画笔上都偏红了。
我瞄了一眼后视镜里的她,见她趴在车窗里目不转睛地看外面,好像在找她失落的东西。我说:“县中学是红旗中学。”
她不说了,见我把车停在红绿灯的白线里等绿灯闪起,说:“这小小的县城也安起了红绿灯了?”
我说:“你们别看这个山沟里的小县城哦,它也随着时代而变迁,愈来愈漂亮了。”我边说边看着三个漂亮的女人撑着太阳伞并列走在斑马线上,如走在t台上,美丽的风景,像一波波热浪拍打我的心田,几乎唤醒了我的青春热血。我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琼中县城了,它的人和车一样多了起来。”
这时,一个女人开车停在我的旁边,和我一样在白线里等红绿灯。这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和父母一起回趟老家。那时候只有一趟早班班车,来往于海至琼中。那次,我们没赶上班车,只好了车票拎着笨重的行李,在中途的屯昌县城车站对面的建国旅社里过一个晚上。我的父母借着难得的机会带我们吃早餐后去逛街。现在想起来我们逛的那条古老的骑楼街应该是博爱路,来到文明东路的十字路,有一个交通亭子坐落在靠东北一个墙角根下,在隐约中可见到里面坐着个着装的交警,我认为他是,我有些怕他。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打着桌面上的几个开关。他在干什么呢?会不会掏?会不会我踮着脚尖远远看着他,见他在指挥着十字路上用铁丝垂下来的红绿灯。红绿灯像铁制的灯笼,黑乎乎的,四面朝向,指挥着车来往。小时候我爱玩电,我沸腾了,多么盼望我们县城的十字路也安上交通灯,指挥我们走路。我见到开着拖尾的公共汽车的女司机,羡慕她女人也能开车,开这么庞大这么长的车从我的眼前慢悠悠地滑过,刷着上面耷拉下来的两条电线一边闪岀火光一边“吱吱”叫着远去。过后想起来她戴的鸭舌帽里梳着两条像马尾巴的粗鞭子耷拉到肩下,好像她是印在币上的那个开拖拉机的阿姨,那两条辫子一直荡漾在我的童年世界里。
红绿灯依然没有从红灯换上绿灯,那开车的女人和自己的年龄相仿,她似乎感觉我在打量她,她微笑着,一脚重重的油门跑了。我还在白线里等着绿灯。建妹不满了起来,说:“绿灯了,你还看女人?走了。”
我“哦”了一声,也踩着油门越过白线跟着去了,仿佛越过了人生的半个世纪。我趁机在建琼的面前逗他的妹妹,好像寻他报复30多年前他如五指山上下来的一只拦路虎,拦着我和他妹妹奔向美好的未来。我说:“男人不想女人是不中用了。”我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建琼的反应,看他会不会像核反应堆发生反应般。他是个比较保守的人,对女人似乎是无动于衷。“女人不想男人是的。”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建妹
我慢悠悠地开车向西去,去老街,老街是山城里很繁华的地段,我想与他们尽早分享小城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两旁的商铺一间挨着一间,多是三四层高的小楼,沐浴在阳光下,墙壁上装饰着不同的民族风情的图案,组成了一道夺人眼球的亮丽的风景线,在唤着我点赞。商铺里面的人进进出出。
我们下一个很斜的徒坡,我说:“建妹,这里才是你说的零公里。”我说着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和她哥哥一样,赶紧往外看,在寻找自己的记忆。零公里变化很大,简直像女孩十八变。他们看到右手边上的一个拱门,拱门边上各竖着一个牌匾,白底黑字。我开车我听到建妹“哦——”声长长的音节,叫她哥哥赶紧看。我放慢车速她念着一块牌匾上的字,我随声匆匆瞄了一下知道里面是公路局。公路局像千百年来的故事,一直矗立在那里,目睹着昼夜的车辆穿梭。
下到零公里是一个“丅”字路,我说过从这里有一条路去五七干校、乘坡,我们不走这条路,在等绿灯一亮起直走去城里,也是人们所说的老街。我和建琼兄妹在这座年轻的小城里出生,伴随着小城一起成长。在时候我们离开了它,回到了故乡工作和生活,到了中年才相约回家看看,好比是左手拎着一只鸡、右手拎着一只鸭走在回家的路上,这种心情是愉快的,仿佛是走娘家。
我们的车一过红绿灯路,熟悉的街道像幅凡?高的油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拆迁扩大了路面,街的两旁起了栋栋的楼宇,但我们仍然记得它的原貌,是一条种植着波罗蜜树、杧果树、椰子树的海渝中线公路从这里贯穿过老街的街尾。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父母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某被人家像赶鸭子上架似的,从住在县委的瓦房子里举家带住在五七干校的茅草房里,说是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父母恢复了工作,父亲回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可是母亲再也不能回去了,被调去物资局工作。物资局在这条街道右边的山顶上,有一条水泥路上去。可是我们家住在右边的一个山坡上,有一条水泥砌成的台阶依山而上。
我那时候上小学,很调皮,每当上学时会背着书包蹲在这条水泥台阶的扶手上滑下来,嘴里“嗷嗷”地。仿佛自己是白马王子从天而降。有时把卡其布的裤子都磨成一个个洞,由于没有穿内裤,里面的白肉外面隐约中可看见,只好腾出来两只手轮着去遮盖屁股去上学,不敢回家,怕挨父母的责骂。当然了,我在那段岁月里很好馋,若能嚼上一粒糖果都觉得是品质无比的甜蜜。我们一下台阶会去光顾公路两旁种的水果树,好像走在自家的菜地里。运气好的话见树上面刚打花结了个小指头般的小杧果,自己的嘴便酸溜溜的,小杧果还不能吃,但要是等到果长大了,也轮不到自己,不知会被谁摘去吃了。我们只好先下手为强,爬树摘下吃,爬不动的树从书包里掏出弓或者捡石头打,打杧果吃,这条街仿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迪士尼乐园 - 【目录】
-
青山绿水/ 001
木薯/ 108
婚礼/ 124
腐乳/ 144
杂门街/ 147
清明/ 155
俞老师的棍子/ 192
驮着一麻袋钱的人/ 195
下放老婆/ 206
交际舞/ 218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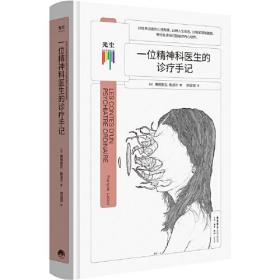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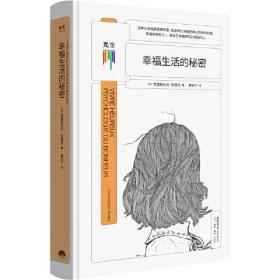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