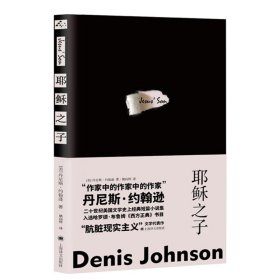
耶稣之子 [Jesus’ Son]
9787532782772
¥ 48.42 ¥ 46 全新
库存599件
江苏扬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丹尼斯·约翰逊,姚向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82772
出版时间2020-0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107页
定价46元
货号12853914
上书时间2024-05-2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丹尼斯?约翰逊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中的作家”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经典短篇小说集 ★“肮脏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 ★入选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书目 ★ 1999年,《耶稣之子》被改编为同名影片,受到影评人广泛好评 内容简介 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以看似混乱的叙述风格,描绘了梦想家、瘾君子和失落之人梦幻一般的生活,映射了美国几个乡镇青年的精神状态。叙述者看似好几个在相同地方出现的、麻烦缠身的年轻人,实则可能是同一个人。故事述及悲伤、惶然、走投无路和救赎、失去、寻找和再度失去。 《耶稣之子》是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著名的小说作品,具有一种天然之美和直击心灵的力量,自1992年出版以来深受文学界和读者欢迎,经常被大学创意写作课程选为范本,对当代许多美国作家有深远影响,堪称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集。 作者简介 丹尼斯?约翰逊(1949-2017),美国作家,以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和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烟树》蜚声文坛。他也创作戏剧、诗歌和非虚构作品。 丹尼斯?约翰逊生于德国慕尼黑,父亲任职于美国国务院。他毕业于艾奥瓦大学英语系,又在该校著名的作家工作坊获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曾师从雷蒙德?卡佛,后又返回作家工作坊任教。丹尼斯?约翰逊19岁即出版第一本诗集《海豹群中的男人》,1983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们》是他的成名作,但真正让他享誉文坛的是199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该书于1999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他也客串了其中一个角色。2007年,长篇小说《烟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普利策奖,201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火车梦》再度入围普利策奖。 2017年5月24日,丹尼斯?约翰逊因肝癌去世。2018年1月兰登书屋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海仙女的馈赠》。 精彩书评 我认为,丹尼斯?约翰逊是自海明威以来最有诗意的美国短篇小说家。他能够通过短语级别的遣词造句,在杂乱中营造美好,在这一方面,他是伟大的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在美国的传承者。在他的作品中,关怀造就了诗歌。黑暗和光明是同一种生命力的不同表现。 ——乔治?桑德斯 《耶稣之子》我读了超过两百遍,写作陷入胶着状态时,读此书有醍醐灌顶之感。 ——恰克?帕拉尼克 我信仰的神,要有丹尼斯?约翰逊那样的声音和幽默。 ——乔纳森?弗兰岑 丹尼斯?约翰逊是丰富的美国声音之集大成者:从他尖刻的讽刺中,我们可以听到马克?吐温,从他重口味的情爱描写中听到惠特曼,从他狠狠地描写自己被掏空、受伤的世界的句子中听到不少达希尔?哈米特。在这一切之外,你还能感受到别的:一个有远见的天使,一个凯鲁亚克,甚至更妙的是,一个看见恶魔、渴望上帝并创造出一种语言容纳两者的威廉?布莱克。 ——《新闻日报》 阅读这些故事就像阅读潜意识里的电报自动记录纸带。 ——《民族周刊》 这些故事强烈、残酷而美丽,具有一种犀利的机智,故意与一个醉汉过分的伤感形成对照。丹尼斯?约翰逊是一个细腻敏锐的作家。 ——玛丽?盖茨基尔 目录 搭车遇祸 两个男人 保释出狱 咚咚 工作急救 肮脏的结合 另一个男人 快乐时间 西雅图综合医院 一双沉稳的手 贝弗利休养所 查看全部↓ 精彩书摘 搭车遇祸 一个销售员和我分享烈酒,睡着了还在开车……一个切罗基人,满肚子波旁威士忌……一辆大众车活脱脱是个大麻烟泡子,掌舵的是个大学生…… 还有马歇尔敦的一家人,一头撞上从密苏里州贝瑟尼往西走的一辆车,永远杀死了驾车的男人…… ……我淋着滂沱大雨从睡梦中醒来,浑身湿透,意识离清醒尚有距离,都怪上面提到的前三个家伙:销售员、印第安人和大学生,他们全给了我麻药。我守在高速公路入口,但没指望真能搭上车。我甚至没心思收拾睡袋,因为我湿透了,谁会允许我上车呢?我把睡袋像斗篷似的裹在身上。子弹般的雨点砸在柏油路上,顺着排水槽哗哗流淌。思绪可怜巴巴地移近拉远。旅行推销员塞给我的药片让人觉得血管内壁被刮了出来。下巴酸疼。我叫得出每滴雨点的名字。我能在所有事情发生前未卜先知。这辆奥兹莫比尔还没放慢车速,我就知道它要为我停车;听见车里 那家人甜丝丝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会在暴雨中出事。 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们愿意一路带着我。 男人和妻子让女儿到前排和他们坐,把婴儿留在后排陪我和滴水的睡袋。“不管你想去哪儿,我都没法开快车,”男人说,“我老婆孩子都在车上,这就是原因。” 你们说了算,我心想。我把睡袋贴着左手边的车门堆在地上,自己往上面一横睡了过去,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婴儿无拘无束地睡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他大概九个月大。 ……然而在发生上述事情之前,那天下午,销售员和我开着他的豪华轿车冲进堪萨斯城。他在得克萨斯载上我,两人发展出愤世嫉俗得危险的铁哥们情谊。我们吃光了他那瓶安非他明,在州际公路上每走一段就下去一趟,再买一品脱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和一袋碎冰。他那辆车两边车门有筒状杯架,皮革内饰是纯白色的。他说他可以带我回家过夜,不过要先停一下,见一个他认得的女人。 顶着中西部犹如灰色大脑的云朵,我们带着轻飘飘的感觉开下高速公路,一头闯进堪萨斯城的交通高峰,感觉像是搁浅了。车速一放慢,同车旅行的魔术气氛顿时消失殆尽。他没完没了地唠叨他的女朋友。“我喜欢这姑娘,觉着我爱上她了——可我有老婆,还有两个小孩,我得承担必要的义务。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爱我老婆。我这人特重感情。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每一个亲戚。”他就这么说啊说啊说,我觉得我被抛弃了,就说:“我有一艘船,十六英尺的小船。我有两辆车。后院有地方挖游泳池。”他在女朋友上班的地方找到她。她经营一家家具店,我在那儿失去了他。 乌云直到入夜也没散。黑暗中我没注意到风暴在积蓄能量。开大众车的大学生灌了我一脑袋大麻,让我在城界外下车时天刚开始掉雨点。之前吃的安非他明都白费了,大麻让我站都站不直。我在公路出口旁的草丛中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雨水积成的小池塘里。 后来,如我所说,我在后座睡觉,奥兹莫比尔——这家人来自马歇尔敦——驶过雨幕,水花四溅。但另外一方面,我梦见我的视线穿透眼皮,我的脉搏一秒一秒标出时间。那个年代,穿越密苏里西部的州际公路基本上只是一条双向道路。一辆半挂卡车迎面擦身而过,害得我们迷失在了茫茫水雾和战场般的隆隆巨响之中,感觉像是正被拖过自动洗车机。雨刷在挡风玻璃上起起落落,可惜只是白费力气。我精疲力竭,过了一个小时,我睡得更踏实了。 我一直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后来男人和他老婆吵醒我的时候,却在拼命否定现实。 “噢——不!” “不!” 我被狠狠地摔在前排的椅背上,撞得很重,砸断了椅背。身体前前后后弹来弹去。我立刻知道是人血的某种液体洒遍车厢,雨点般落在我头上。等碰撞结束,我回到了后排座位上,和先前一模一样。我起身四处张望。车头灯灭了。散热器持续不断地嘶嘶作响。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听见。据我所知,只有我一个人意识清楚。等眼睛适应黑暗,我看见婴儿躺在我旁边,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他睁着眼睛,在用一双小手摸面颊。 没过多久,男人——他软绵绵地趴在方向盘上——坐起来,扭头望向我们。他的脸磕得一塌糊涂,黑乎乎的全是血。光是看着他,我都觉得牙疼,然而等他开口,却好像连一颗牙齿都没掉。 “怎么了?” “撞车了。”他说。 “孩子没事。”我说,尽管根本不知道婴儿情况如何。 他转向妻子。 “简妮丝,”他说,“简妮丝,简妮丝!” “她没事吧?” “她死了!”他说,使劲摇晃她。 “不,她没死。”我现在打算听见什么都唱反调了。 小女孩活着,但被撞晕了。她在昏迷中呜咽起来,可男人只顾摇晃妻子。“简妮丝!”他嚎叫道。 他老婆呻吟起来。 “她没死。”我说,吃力地爬出车厢,拔腿就跑。 “她怎么不醒?”我听见他在说。 我站在外面的黑夜里,不知为何抱着婴儿。肯定还在下雨,但我对天气毫无记忆。我们撞上了另一辆车,我此刻意识到我们肯定在一座两车道的公路桥上。脚下的流水在黑暗中无影无踪。 走向另一辆车,我渐渐听见了仿佛金属摩擦的刺耳鼾声。乘客座敞着门,一个人大半身子悬在车门外,姿势像是用脚勾着秋千架挂在那儿。车横在路中间,被撞得瘪了下去,剩下的空间甚至容不下这个人的两条腿,更不用说驾驶员或其他乘客了。我径直走了过去。 车头灯从远处驶近。我勉强走到桥头,用一条胳膊挥手拦车,另一条胳膊把婴儿紧抱在肩头。来的是辆大型半挂车,减速时齿轮吱嘎碾磨。司机摇下车窗,我对他大喊:“出车祸了。去找人帮忙。”“我在这儿没法掉头。”他说。他让我抱着婴儿爬上乘客座,我们呆坐在车厢里,望 着他车头灯下的事故现场。 “所有人都死了?”他问。 “我看不出谁死了谁没死。”我承认道。 他拿起保温瓶,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关掉除停车灯外的所有灯。 “几点了?” “哦,三点一刻左右。”他答道。 从他的神态看,他拥护的想法大概是按兵不动。我如释重负,热泪盈眶。我觉得事态似乎对我有所要求,但我并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要求。 一辆轿车从反方向驶来,我觉得应该跟他们说一声。“婴儿能留在你这儿吗?”我问卡车司机。 “还是你自己抱着他吧,”司机说,“是男孩,对吧?” “嗯,应该是。”我答道。 经过撞烂的轿车时,我注意到挂在车外的男人还活着,于是我停下脚步,现在我对他受的伤到底有多严重稍微有了点概念,此刻想确定我没什么可做的。他的鼾声响亮而粗鲁。鲜血随着每次呼吸而冒着泡沫流出嘴巴。他撑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但他不知道,因此我低头看着这个地球上一条人命感到巨大遗憾。我指的不是我们凡人终有一死,那不是巨大的遗憾。我说的是他没法告诉我他梦见了什么,而我没法告诉他什么是真实的。 没多久,车辆就在公路桥两端排起了队,车头灯照在蒸汽升腾的碎石上,给这一幕增添了几分夜间比赛的气氛。救护车和警车挤过车阵,因此空气中充满了跳动的色彩。我不和任何人交谈。我的秘密是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从这出悲剧的主宰变成了惨烈车祸的无名旁观者。不知什么时候,一名警官得知我也是车上的乘客,于是找我录口供。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他命令我“把烟掐了”。交谈间我们停了一次,望着垂死的男人被送上救护车。他还活着,还在做他可厌的梦。鲜血汇成一股一股从他身体里逃出来,他的膝盖在抽搐,脑袋胡乱晃动。 我没什么大碍,也什么都没看见,但警察必须要录我的口供,因此带上我去了医院。警车刚开到急诊入口的天篷下,无线电就传来消息说那个男人死了。 我站在铺着瓷砖的走廊里与当地殡仪馆的人交谈,湿漉漉的睡袋收起来靠在身旁的墙壁上。 路过的医生停下,说我最好去拍个X 光片。 “不了。” “还是现在拍一个吧。要是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我好得很。” 妻子顺着走廊走来。她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她还不知道丈夫死了,但我们知道,因此她对我们的影响力才那么大。医生领着她走进走廊尽头有办公桌的一间房间,房门关上,门底下的缝隙射出一横条灿烂的强光,好似钻石正被亿度高温焚成灰烬。多惊人的两个肺啊!她尖叫得像我想象中的雄鹰。能活着听见这声音可真是谢天谢地!我曾为了寻找这种感觉而东奔西走。 “我好得很”——我惊讶于自己竟然会说出这几个字。然而我一向喜欢向医生撒谎,就好像只要糊弄过医生就能代表我很健康。 几年以后,那次我被收进西雅图综合医院的戒瘾病房,我又使出这套伎俩。“听见什么不寻常的响动或说话声吗?”医生这么问我。 “救命啊,天哪,疼死了。”几盒棉球在尖叫。 “也不尽然。”我答道。 “也不尽然,”他说,“呃,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没准备好仔细谈这个。”我说。一只黄鸟扑扇着翅膀飞近我的脸,我的肌肉猛地抽紧。现在我像鱼儿似的扑腾。我闭紧双眼,热泪从眼窝中迸发。我睁开眼睛,我肚皮朝下趴着。 “房间怎么会这么白?”我问。美丽的护士按压我的皮肤。“维生素。”她说,把针头插了下去。 在下雨。巨大的蕨类俯身笼罩我。森林飘下山丘。我能听见小溪在岩间流淌的潺潺声。而你们,荒唐可笑的你们,居然指望我帮助你们。 查看全部↓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耶稣之子 [Jesus’ Son]](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2c22d1f57cfbcc9d_b.jpg)
![耶稣之子 [Jesus’ Son]](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cc217511d9f8a96a_b.jpg)
![耶稣之子 [Jesus’ Son]](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c2f6c10bbadcf9ef_b.jpg)
![耶稣之子 [Jesus’ Son]](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31532cad22f470bc_b.jpg)

![医学专业英语 [Medical English]](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6bc36f591c7dd7b8_s.jpg)








![耶稣之子 [Jesus’ Son]](/dist/img/error.jpg)
![耶稣之子 [Jesus’ Son]](https://www0.kfzimg.com/sw/kfzimg/1585/0131a4378215e45694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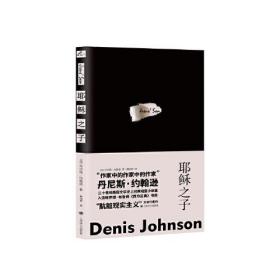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