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
9787532794140
¥ 88.56 6.4折 ¥ 138 全新
库存599件
江苏扬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吴钧陶,西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94140
出版时间2023-10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大32开
页数664页
定价138元
货号13884745
上书时间2024-05-2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 1.高级定制装帧,原味呈现享誉国际出版界的“企鹅布纹经典”形神之美;2. 夏洛蒂?勃朗特的最后一部作品,无论从创作思想或艺术手法上都比以前的作品更为成熟。本书的女主人公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 3.是翻译名家吴钧陶的译作 4.这是一部比《简?爱》更了不起的书,石黑一雄最喜欢夏洛蒂?勃朗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他走上文学道路,也是拜《简?爱》《维莱特》所赐。 内容简介 《维莱特》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一部比《简?爱》更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书中女主人公露茜?斯诺从许多方面来看就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 “维莱特”是"小城“的意思,是比利时布鲁塞尔,从1842年到1844年,夏洛蒂在 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读书并兼任英语教员。在法语、德语和文学修养方面大有收获,同时也与她的老师埃热先生产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最后不得不以分手告终。为了排遣心中的热情感情,夏洛蒂?勃朗特写下了《维莱特》。在小说中,作家本人心中沸腾的热烈的情感和忍受的痛苦的煎熬都幻化在作品人物的身上,使得作品有了比《简?爱》更炙热的情感力量。乔治?艾略特认为“这是一部比《简?爱》更了不起的书”。 作者简介 夏洛蒂?勃朗特,英国女作家。她与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史上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夏洛蒂1816年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母亲早逝,八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一所慈善性机构。15岁时她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最终她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长篇小说《简?爱》,轰动文坛。她另有作品《谢利》《维莱特》和《教师》。 精彩书评 勃朗特优秀的小说 --维吉尼亚-伍尔夫 目录 译本序1 第一卷 第一章布列顿3 第二章波琳娜11 第三章游戏的伙伴们19 第四章马趣门特小姐39 第五章翻开新的一页49 第六章伦敦55 第七章维莱特69 第八章贝克夫人80 第九章伊西多尔97 第十章约翰医师110 第十一章女杂务工的小房间119 第十二章小盒子127 第十三章不合时宜的喷嚏140 第十四章圣名瞻礼日153 第十五章暑假188 第二卷 第十六章往日的时光205 第十七章台地别墅223 第十八章我们的口角235 第十九章克娄巴特拉244 第二十章音乐会259 第二十一章反应285 第二十二章一封信305 第二十三章瓦实提317 第二十四章德·巴桑皮尔先生335 第二十五章年幼的女伯爵352 第二十六章葬礼368 第二十七章克莱西公馆386 第三卷 第二十八章挂表链407 第二十九章先生的圣名瞻礼日421 第三十章保罗先生438 第三十一章树仙451 第三十二章第一封信464 第三十三章保罗先生遵守诺言475 第三十四章玛勒伏拉485 第三十五章博爱500 第三十六章不和的金苹果516 第三十七章阳光535 第三十八章阴云555 第三十九章旧雨新知587 第四十章幸福的一对602 第四十一章克罗提尔德郊区611 第四十二章尾声629 附录夏洛蒂·勃朗特生平大事记635 查看全部↓ 精彩书摘 第一卷第一章 布列顿我的教母住在整洁而古老的布列顿镇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家好几代是那儿的居民,因此,说真的,就以他们的出生地做了姓氏——布列顿镇的布列顿。这是由于巧合,还是因为哪一位远祖曾经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因而把他的姓氏留给了这个地区,那我可不知道了。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每年大约去布列顿镇两次,我很喜欢到那儿去做客。那所房屋和屋子里的人们特别让我中意。那一间间宁静的大房间,那布置得很好的家具,那干净的宽大的窗户,那外面的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似乎星期日和节假日一直在那儿逗留不去,气氛是那么安详,人行道上是那么清洁——这些事物真叫我赏心悦目。 在一个都是成人的家庭里,对于独个孩子通常总是特别钟爱的;布列顿太太对我就是不动声色地格外给予照顾。我认识她以前,她已是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是一位医师,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 在我的记忆之中,她年纪已经不轻了,但是仍然漂亮,身材修长、匀称,并且虽然作为英国女子来说,肤色黑了一些,然而在她浅黑色的面颊上,一直带着健康滋润的样子,在那双美丽的含笑的黑眼睛里,露出轻松愉快的神色。人们感到极为可惜,她没有把自己的肤色传给儿子。儿子的眼睛是蓝色的——虽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得目光非常敏锐——他的长头发,有着正如朋友们觉得难以归类的那种颜色,只是太阳照着的时候,才称为金黄色。然而,他继承了母亲的五官的线条,还有她那一副好牙齿,她的身材(或者说有希望长成她那样的身材,因为他还没有长到定型),以及更好的是她的毫无缺陷的健康,她的那种状态和同等情况的精神,这对于拥有者说来,比一笔财产更好。 在这年的秋天——我正待在布列顿,我的教母亲自来认领我是她的家属,这时候正为我安顿永久的住处。我相信,她这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事情的预兆正在显现,我却想也没有想到,不过关于这事情的微小的疑虑已经足够把不肯定的悲哀传递给别人,并且使我乐于换换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我的教母的身边,时间总是平静地流过——并不是哗哗地、迅速地流,而是平淡无奇地流,好比一条水位高涨的河静静地流过一个平原。我去拜访她,就像“基督徒”和“盼望”“基督徒”和“盼望”都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角色的名字。《天路历程》是英国作家班扬(1628—1688)在狱中写的著名讽喻小说。逗留在一条可爱的小溪边,“绿树排列在两岸,百合花终年装点着青草地。”那儿没有丰富多彩的魅力,也没有小事情引起的激动;但是我那么喜欢安宁,那么不想找刺激,因而在刺激到来的时候,我差不多觉得那是一种烦扰,并且希望它还是远远离开我为好。 有一天,布列顿太太收到了一封信,其内容显然使她惊讶,并且有些担心。我起初觉得信是从家里寄来的,不禁一阵哆嗦,只怕是我所不知道的什么灾难性的信息。不过,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阴云似乎过去了。 第二天,我作了长距离散步回来以后,走进我的卧室,却发现了料想不到的变化。除了我那张搁在光线阴暗的凹处的法国式卧床以外,屋角出现了一张有栏杆的儿童小床,床上蒙着白布;除了我那只桃花心木的五斗橱以外,我还看见一只青龙木小柜子。我站在那儿凝视着,脑子里在想。 “这些东西表明和意味着什么呢?”我自问。回答是明显的。“另一位客人就要来了。布列顿太太准备迎接另外一位客人。” 正要下楼去吃饭的时候,得到了解答。我被告知,一个女孩子马上就要来和我做伴,她是已故的布列顿医师的一位朋友兼远亲的女儿。还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新近失去了母亲;然而,说真的,布列顿太太不久又添补了一句,说这一损失并不像起初看起来可能会有的那么严重。霍姆太太(好像是姓霍姆)过去非常漂亮,但却是一位轻浮、随便的女人,她对孩子漫不经心,又使她丈夫感到灰心丧气。他们远远不是情投意合的,这种结合必然导致的离异终于发生了——是双方同意的离异,没有办过任何法律手续。这一事件以后不久,这位女士在一次舞会上玩得过分卖力,患了感冒,发了烧,病了没有多少天便一命呜呼。她的丈夫天生是一位感觉十分敏锐的人,被这个太突然地传来的消息震惊得不知所措,这时,似乎很难使他不认为他在某些方面的过于严厉之处——某些欠缺耐心和纵容之处——对于加速她的死亡曾经起过一份作用。他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一点,直弄得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影响;医师们坚持要他旅行,试图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这时布列顿太太便提出照看他的小女孩。“我希望,”我的教母在最后加上一句说,“这个孩子可不要像她的妈妈——可不要成为一个疯疯傻傻的小调情者,弄得明智的男人情不自禁地要去娶她。因为,”她说,“霍姆先生正是一个有他自己特点的明智的男人,虽然他并不很讲实际。他喜欢科学,半生都消磨在实验室里搞实验——这是他的蝴蝶般的妻子既不理解、也不容忍的事情;不过,说真的,”我的教母承认说,“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 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教母还告诉我,她已故的丈夫常常说,霍姆先生的一位舅舅是法国学者,他这种科学才能是从这位学者身上得到的。他的祖先似乎是法国和苏格兰的混血种,一些亲戚现在还住在法国,他们之中不止一个在姓氏前加上“德”字,称自己是贵族。法国名门出身的人,一般在姓氏前加一个介词“de”,中文一般译为“德”。 就在这天晚上九点钟,一个仆人被派去迎接我们的小客人预计会乘坐的那辆轿式马车。只有布列顿太太和我两人坐在客厅里,等候她的到来,因为约翰·格雷厄姆·布列顿不在家,他去看他的一位同学,当晚住在乡下。我的教母一面等候,一面阅读晚报。我在做针线活儿。这是个阴雨绵绵的夜晚,雨打在窗玻璃上,风一刻不停地怒吼着。 “可怜的孩子!”布列顿太太时不时地叹息着。“在这样的天气里长途旅行啊!我但愿她已经在这儿,平平安安。” 十点差几分钟的时候,门铃响起来,华润回来了。前门刚打开,我就已经奔下楼,来到厅堂里。地上放着一只大皮箱,几只圆筒形纸板盒圆筒形纸板盒,用来盛放女帽或领圈等物的盒子。,旁边站着一个人,像是保姆,楼梯边则是华润抱着一个用围巾包裹起来的东西。 “这就是那个孩子吗?”我问。 “是的,小姐。” 我本想打开围巾,看一眼那张脸,但是孩子急忙避开我,把脸搁到华润的肩膀上。 “请你放下我,”华润打开客厅门的时候,那娇小的声音发出来,“还要拿掉围巾,”这孩子又说,用一只小手取下别针,以一种过分讲究的、急急忙忙的样子脱掉那堆不像样的包裹。这会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家伙,动作熟练地试着折好那条围巾,可是这件织品太重,太大,那双小手和胳臂可提不起,也舞不动。“请把这个交给海蕊特,”她发出了这样的指令,“她会把它放好的。”孩子说了这句话以后,转过身来,眼睛直盯着布列顿太太瞧。 “来呀,小宝贝,”这位夫人说。“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又冷又湿。来让我在壁炉边使你暖和暖和。” 孩子飞快地奔过来。她脱去了包裹以后,看起来是一丁点儿大,可是小身段却生得匀称、完美无缺,又轻灵,又小巧,又挺直。她坐在我的教母的宽大的裙兜上,只像是个洋娃娃。她的脖子像蜡制的那样细腻,丝线一般的鬈发覆盖在头上,我觉得更增加这种相似的程度。 布列顿太太一面用简短、亲爱的词句说着话,一面擦热孩子的手、胳膊和脚。刚开始,孩子若有所思地呆望着她,但是过了一会儿,孩子便向她露出微笑。布列顿太太一般说来并不是一个善于嘘寒问暖的女人。即使对待她宠爱至深的儿子,她的态度也很少热情洋溢,倒常常是相反。然而这位小生客向她微笑的时候,她吻了她,问道:“我的小宝贝儿叫什么名字啊?” “妞妞原文是Missy,“小姑娘”或“小姐”的意思。。” “除了妞妞之外呢?” “波莱,爸爸这样叫她。” “波莱乐意跟我住吗?” “不一直乐意;不过乐意待到爸爸回家。爸爸出门去了。”她富于表情地摇摇头。 “他会回到波莱身边来的,或者派人来接。” “他会吗,太太?你知道他会吗?” “我想会的。” “可是海蕊特不这样想——至少她认为不会很快来接她。他病了。” 她的眼睛湿了,从布列顿太太手里抽回自己的手,做出要离开她的裙兜的动作。起先没有得到同意,但是她说:“请让我走。我可以坐在小凳子上。” 她终于被允许从太太的膝盖上滑下来。她把一张脚凳拿到光线很暗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布列顿太太虽然爱发号施令,在重大事情上甚至是一个专断独行的女人,然而对于细枝末节的事情却常常听之任之。她允许这孩子自行其是,还对我说:“这会儿可别对她瞧。”但是我却对她瞧着。我看着她一只小小的肘弯搁在小小的膝盖上,头枕在手掌上,发觉她从她小裙子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块一两英寸见方的手帕,接着听见她哭泣起来。别的孩子伤心或感到疼痛的时候会大声嚷着哭,不怕难为情,也不忍着点儿;但是,这孩子却光流眼泪——只有最轻微的偶尔的欷歔声才能证明她动了感情。布列顿太太没有听见,这样倒很好。过了不久,说话声从那个角落里发出来,要求说:“可以打铃请海蕊特来吗?” 我打了铃,保姆应声而来。 “海蕊特,我必须上床睡觉了,”她的小女主人说。“你必须问问我的床在哪儿。” 海蕊特表示她已经问过。 “问问是否你和我一同睡,海蕊特。” “不,妞妞,”保姆说。“你要跟这位小姐同住一个房间,”她指着我。 妞妞没有离开座位,但是我看见她的眼睛转向我。她默默打量我几分钟之后,从她的角落里走出来。 “太太,我祝你晚安,”她对布列顿太太说,但是不声不响地打我身边走过去。 “晚安,波莱,”我说。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译本序 1852年11月里寒冷的一天,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布拉德福市霍沃思村教区牧师巴特里克·勃朗特先生的寓所里,牧师的女儿,这时已经以笔名柯勒·贝尔蜚声文坛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1816—1855)写完了她的小说《维莱特》的最后一行。她搁下笔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后来她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写完后,作了一次祈祷。究竟写好了还是写坏了,我不知道;任凭天意吧!现在我要努力平静地等待结果。” 这时,夏洛蒂年方三十六,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杰作《简·爱》(1847)和颇受欢迎的《谢利》(1849),年龄和事业都是如日方中之际,应该有漫长的锦绣前程等候着她,却不料《维莱特》已是她的绝唱和绝笔了。两年以后,她与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 Bell Nicholls,1818—1906)结婚,结婚前后动笔写小说《爱玛》,未能完成,婚后只九个月便受疾病折磨,留下几章残篇,于春寒料峭的3月31日匆匆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九岁。 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原像多数乡村牧师家的生活那样,是清寒的;如果不是迭遭变故,倒也融融泄泄,乐在其中。但是,夏洛蒂六岁时,三十八岁的母亲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姨母来家照料六个孩子,终未能慰抚孩子们丧母之痛。两个姐姐、夏洛蒂和一个妹妹被送往教士女儿学校住读,学校里恶劣的条件和过分严厉的管教,对幼小的心灵只能投下暗影。还不仅如此,两个姐姐不久以后都得了肺结核,先后夭折。这些,在《简·爱》一书里都有着令人伤心落泪的反映。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辍学回家以后,和弟弟勃兰威尔、最小的妹妹安妮一同长大。弟弟后来一事无成,自甘堕落,浪掷了自己的才华,也辜负了家人的希望。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对于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着共同的爱好,终于都登上文坛,成为杰出的文学家。 三姐妹于1846年用笔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夏洛蒂的《简·爱》于1847年由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出版以后,艾米莉的名著《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也于同年由纽比公司以作者负担一部分费用的苛刻条件出版。第二年,安妮又出版了小说《女房客》。 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顾这一门三女杰的辛勤劳动,让她们可以采摘甜蜜的果实了,却不料从1848年的秋天到1849年的春天的八个月之内,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三人相继在青春年少时死于结核病。 夏洛蒂的《谢利》写到三分之二的地方,正是家中惨祸连连的时候,她不得不暂停写作,过了一阵才强忍悲痛,勉力续完。 在她写作《维莱特》的一年间,可以想见亲人们的死亡的阴影是如何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还要加上一句的是,他们的姨母也早已于1842年死于他们家中。人去楼空,教会提供的两层八间的牧师寓所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爱独居一室的父亲、一个女仆和夏洛蒂三人。在荒原深处,墓冢丛中,教堂对面,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室外狂风呼啸,室内炉火闪忽,夏洛蒂伴着孤灯,形单影只,奋笔疾书,此情此景,该是什么况味!她们三姐妹原来有个习惯,在晚饭后绕着餐桌踱步,一个跟着一个,一面走,一面交流写作心得,互提意见。两个妹妹去世以后,夏洛蒂依然保持这一习惯,绕桌而行但已无人可以交谈,不闻欢声笑语,却只有自己的脚步敲击那石块铺成的冷冰冰的地板跫跫之声了。 这样的写作背景,这样凄凉寂寞的心境,不可能不反映到她的作品《维莱特》中来,何况这部书的内容比起夏洛蒂其他几部小说,带有更浓厚的自传色彩。 《维莱特》的女主人公露西·斯诺从许多方面看来,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真实写照。露西的经历如果说并不完全等于夏洛蒂的经历,却应该说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夏洛蒂的主要经历;同时,露西用第一人称对读者所说的话,应该看做夏洛蒂对世人倾吐的心声。 夏洛蒂把女主人公的姓氏称做“斯诺”是有含意的。1852年11月6日,作者致函出版公司的审稿人威廉斯说:“说到女主人公的姓名,我几乎无法解释,是怎样一种微妙的意念使我决定给她起了一个冷的姓氏……她必须有一个冷的姓氏……因为她有一副冷冰冰的外表。”原来“斯诺”的原文Snowe(=Snow)是“雪”的意思。作者一度曾使女主人公改姓Frost,意为“冰霜”,同样是寒冷之意。参照作者的经历看来,当不仅指她的外表,很可能还指她的遭遇和她的内心。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夏洛蒂还说:“除非我错了,这本书的情调将从头到尾是比较低沉的。……她也许会被看成是病态的、软弱的……而任何人如果过着她那种生活,都必然会变得病态的。” 书名“维莱特”的原文是法文Villette,乃“小城”之意,英国人用这个词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夏洛蒂用这个字暗指布鲁塞尔,正如她在书中用“拉巴色库尔”(Labassecour,“农家场地”或“晒谷场”)暗指比利时一样。原因当是作者要把故事的真实背景弄得模糊一点。从1842年到1844年,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读书并兼任英语教员。这是夏洛蒂一生唯一的一次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大陆。初渡英、法之间的海峡的时候,是她父亲陪送她和艾米莉前去的,费用由姨母资助。不到一年,姨母病故,夏洛蒂和艾米莉奔丧回家。在埃热先生来信盛情催请下,夏洛蒂再次只身返回布鲁塞尔。前后两年,夏洛蒂在法语、德语和文学修养方面大有收获。意想不到的是,在感情问题上,竟然也给她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恋情。她所以要写这部小说,所以要把这部小说叫做《维莱特》,显然是事出有因的。 这一段恋情,当时和后来都鲜为人知。如果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可能会永远湮没无闻。据说,夏洛蒂去世以后不久,为她写出第一部传记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向有关人士搜集资料时,对此事是知道的,但是为了不使尚活在世上的人难堪,为了不使她的朋友夏洛蒂本人的形象受损,故而在传记中略而不提。 事情是夏洛蒂在布鲁塞尔埃热夫人寄宿学校学习期间与康斯坦丁·埃热(Constantin Heger,1809—1896)先生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埃热先生的第一位夫人死于1833年,他的第二位夫人(娘家姓Parent)克莱尔·卓埃(Claire Zo)·埃热(1804—1890)是夏洛蒂求学时的校长。埃热先生主要在学校东隔壁的一所布鲁塞尔王家中学担任文学教授(在比利时,对资深中学教师也称教授),同时也协助夫人治理自己的学校并且授课。埃热先生为人热情,充满活力,学识渊博,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在夏洛蒂和艾米莉初来的时候,给予帮助,特为她们辅导功课。不久,夏洛蒂在学校里学习的同时,还担任了英语教师,并且为埃热先生和他的妻弟补习英语。从现有的材料看来,他们之间不过是如此这般的泛泛的关系。1842年5月,即夏洛蒂和艾米莉到达布鲁塞尔之后的三个月,夏洛蒂给她童年时的学友,后来成为终身挚友埃伦·纳西女士写的信里,这样形容埃热先生:“他是修辞学教师,一个智力雄厚的人,可是脾气异常暴躁易怒,一个矮小黝黑的丑八怪,一张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有时他借用一只发疯的雄猫的模样,有时又借用一头癫狂的狼狗的神态;偶尔,但很罕见,他抛开了这些危险的诱人的表情,采用了一副距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相去无几的风度。”从这些不大恭敬的言词看来,夏洛蒂这时不像对埃热先生有多少好感。但是,过了一年,夏洛蒂在给她的弟弟勃兰威尔的信上,抱怨在这个异乡异国人际关系“虚伪透顶”,不懂什么是友谊的同时,却说:“唯一一个例外是那个黑天鹅,埃热先生。”从“丑八怪”一跃而升为“黑天鹅”,岂不是像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这里,岂不是透露了一点什么信息吗? 另一方面,埃热先生比他的第二位夫人小五岁;那所学校看来又是这位夫人的资产;如此“屈居人下”,如果他感到“压抑”的话,便很有可能主动接近夏洛蒂,引为红粉知己。 当然,不能忘记,当时是十八世纪,当地是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学校。校长埃热夫人矮矮胖胖,彬彬有礼,但是神态冷峻,不苟言笑,一贯以严格的态度领导学校,以不断的监督对待师生。在《维莱特》里,夏洛蒂按照她的模型出色地创造出一位贝克夫人,可以想见埃热夫人管理下的学校的大致的环境氛围。因此,夏洛蒂和埃热先生之间的关系想必不是那种浪漫的师生之恋,而多半如夏洛蒂在《维莱特》里所描写的露西·斯诺和保罗·伊曼纽埃尔之间那种精神上的互相吸引、心灵上的彼此接近和沟通,但事实上是只有绝望和痛苦的那种交往。 夏洛蒂身材娇小瘦弱,但是性格坚韧刚毅,很有主见,再加上长期艰难和孤独生活的磨练,她是一位深情而又不易动情的人。她这时二十六岁,在来布鲁塞尔之前,曾经在家乡拒绝过两位求婚者,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在这样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向一位不适当的对象打开了心扉。恐怕只能说是盲目的爱神向她盲目地射出了一支金箭吧。 尽管夏洛蒂竭力自我克制,尽管表面上维持正常的师生关系,但是既然心中燃起了恋之火,总不免有外露的迹象。勃朗特研究家玛格丽特·莱恩在《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写道:“埃热夫人敏锐地注意到那个英国女教师对教授的反应过分冲动,过分带感情意味。她不喜欢热情,对这种歇斯底里,无疑也有过充分体验。……当然,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无以名状、不知不觉的妒意也在起作用。夏洛蒂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冷淡,正如埃热夫人随时随地都猜疑到对方的不适当的热情。” 大概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处境的尴尬,避免埃热夫人猜疑和冷漠的目光,以及治疗那难以忍受的孤独之感、思乡之情,夏洛蒂于1843年10月向埃热夫人表达了离校回国的意愿。不料,一如夏洛蒂给埃伦的信上所说:“埃热先生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怒冲冲地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不能走。”直到这年年底传来消息,说夏洛蒂的父亲快要双目失明了,这才给了她脱身的充足的理由。 可是一颗动了真挚的感情的心,并不因为它的主人身在何处而情况有什么不同。对于夏洛蒂说来,回到家乡,从此永不相见,反而使思念之情加上生离死别之苦,一如火上加油,而更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书信才能够慰情聊胜于无。这些信必须是可以公开的,因为是写给一位有妇之夫;但又必须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渴念和爱恋,因为这才是写信的真正目的。夏洛蒂以自己非凡的才华尽力这样做,然而纸包不住火,从一些字句,从字里行间,明眼人和旁观者是容易知道此中深意的。不知这些信共有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f09f5f7c910da737_b.jpg)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0977ed25fa83780b_b.jpg)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1acc3a16488ddbb6_b.jpg)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866771d9595bbe2b_b.jpg)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21151719/81754da787646289_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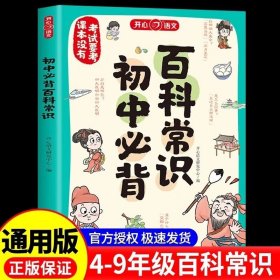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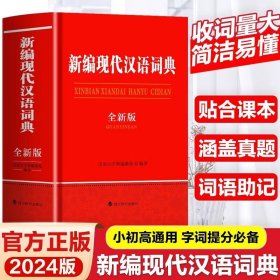





![企鹅布纹经典:维莱特 [Villette]](/dist/img/error.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