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春草堂诗钞
¥ 2160 9.6折 ¥ 2250 全新
仅1件
浙江杭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本社编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0315921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线装
开本8开
定价2250元
上书时间2021-04-05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本丛刊遴选范景中、周小英二教授收藏、校跋之珍贵古籍,以宣纸彩色影印技术仿真再现。原大线装,单独定价。
黄裳先生的书跋,经常托夫人“小燕”之名,实则均出于黄裳先生之手,但依然成为艺林雅事。范景中先生,以译介西方美术史专著著称于世,贯通中西;夫人周小英女史,清代大书家尹秉绶之后人,一手好字,乃是家学渊源。范景中、周小英伉俪净琉璃室所藏的古籍,未必是至善之版本,但却依靠他们自身的德才学识,对书进行批点、校勘、题跋,使寻常之书立升至善本的境界。而他们的批点题跋,乃至钤印,法度严谨又挥洒自如,且善于利用新资料,时常引用文物发掘材料对内文进行印证。这种继承与发扬古代藏书家传统的做法,足可与来燕榭相埒而毫不逊色也。
我的外婆伊相玉,是伊秉缓的后人。按照家谱排起来,大概属于来孙一辈。秉缓先生字组似,号墨卿,家有秋水园,印有“兼茵秋水吾庐”。我有一方闲章,文曰“秋水伊人”指的就是这层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墨卿先生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墨卿先生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里都有传。但在《清史稿》中,不像他所交往的翁方纲、法式善等人那样入文苑传,而是列在循吏传里。这显然是前人更重视他的政绩的原因。《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八)说他“嘉庆三年,出为广东惠州知府,间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废置已久的丰湖书院就是他那时重建的。史书还说他为人侃直,办事公正,因而触怒了上级,被滴戍军台。这引得民情沸腾,数千人为他奔走呼冤。气氛的严重是可以想见的。幸好,墨卿先生的朋友,也是后来鸦片战争中的著名诗人张维屏,为我们记录下了那紧张舞台上的轻松一幕:
嘉庆壬戌,墨卿先生以事罢官,大吏委官看守,在按察司司狱厅。旁人为之忧厄,先生洒然若无事者。腊月十九日,坡公生日,先生招同宋芷湾庶常、阴青原上舍、家贤仲、陈仲卿两秀才,设祀堂,中悬笠展小像共拜之,赋诗饮酒极欢。高士徐爹圃日:噬乎,如伊墨卿者,岂复有世间升沉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
好在冤屈终于得到昭雪,墨卿先生盘桓数月,便在嘉庆八年十月三日由广州花壕解缆北上赴京旅居。《留春草堂诗钞》卷三中有一首诗,题为《腊月十九日与宋芷湾、张贤仲(思齐)、子树(维屏)、陈仲卿祀东坡》,大概就是当时饮酒时所赋。诗中所谓的“良夜卜成文字饮,荒斋寒尽海天春”,的确是达观的。卷四中也有几首诗,是墨卿先生在京城翁方纲的苏斋中为东坡过生日而作,其二似又忆及此事。诗曰:
番禺萧寺柏,铁干风霜苦。隙驹阅斯辰,难虞但怀古。我友宋翰林(芷湾),裁诗力如虎。招来三秀才,各各携酒脯。打门拜公像,我仍为之主。往事戒弗言,欢呼动衡宇。而我更清狂,醉持蔗竿舞。古人不可作,今人隔风雨。
诗中提到的宋芷湾,即乾嘉间岭南的杰出诗人宋湘,他的诗名不仅与黎二樵双峰并峙,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同乡的黄遵宪。他在送别墨卿先生北上的诗中写道:
湖水复何如,公亦去之久。我每过惠州,不敢重回首。惠人昨日来,思公只如母。非我实媚公,父老祝我口。公乎复当来,椎牛面村酒。
后来他到京城又写了三首诗赠给墨卿先生。劈头一句就是“近到京华醉几杯,州民抵死盼公回”。可见墨卿先生在惠州士民心中的位置。
不过,墨卿先生更卓越的政绩,是在扬州知府的任上。嘉庆十年(乙丑年),苏北地方官不顾实情,强开昭关坝,造成下河七邑重大水灾。其患祸之重,我们仅举当时的一些记事诗,便可略见一斑。
泰州邹熊作《大水行》、《米贵叹》、《桃花雨》等诗,记其水灾的由来和危害。
山阳曹镶作《乙丑六月感事》,以“心知有今日,谁是负生灵”,怒责债事河官。
丹徒郭塑作《流丐行》,记苏北灾民就食吴门,地方官闭城不纳,灾民被迫还经京口的逃难景象。
通州李琪作《西门行》,记兴化饥民因官吏扣贩不发,被迫自掠食的情状。
江宁凌霄北行过淮,作《灾民叹》。
安徽方正澎旅扬州,作《水村行》。东台罗怀玉作《乞粥妇》;甘泉许祥龄作《吴陵大水谣》;震泽张士元作《散粥行》;吴县范来宗作《蚕妇叹》;常熟吴兼山作《芦田叹》等等。
高邮宋茂初作《乙丑高邮水灾》诗,向伊秉缓报灾。《清史稿》记述道:
时秉缓方奉微勘高邮、宝应水灾,刺一小舟,栖户枉诸,必亲阅手记。及在任,幼躬率属,贩贷之事,错株必核,吏无所容其奸。倡富商巨室捐设粥厂,费以万计。诛北湖剧盗铁库子辈,杖诡道谁愚之聂道和,它奸猾扰民者,悉严治之。民虽饥困,安堵无惶惑。
墨卿先生的诗集中有《荷花塘》、《姚堤》、《贩灾四首》等诗,就是那场大水灾的实录。“可怜树叶尽充粮,釜能上屋舟入房。房中白发翁与姥,恨非少壮能逃荒。”告哀之声,不忍复听。这是诗集中言愁最工的作品。但却不是个人的一己私愁。
在关于那场大水灾的文献中,我们还发现了林镐的一首长诗。他以对比的手法为我们摄下了墨卿先生的几个镜头。昔日景象如状目前。典型犹存,哲人未远,至今读来,还不禁令人肃然。现引述如下:
清晨发邢沟,薄暮趋秦邮。西风猎猎吹小舟,长年牵缆行且讴。舟中兀坐者谁软?扬州太守查灾黎。灾黎走相告,是为太守心。窃疑往年太守查灾来,楼船万解声喧危。荒村索鸡采,破屋科钱财。上食太守供舆台,敲扑丁役令心哀,苦若巨浸重为灾。今年太守胡为尔,从者三人两人耳。村墟历皆遍,风霜行未己。父老语灾黎,尔辈焉得知。扬州太守今姓伊,政声久从粤海驰。江南大府告天子,命典名郡初来兹。昨闻太守出府时,髯奴悻悻前致词:“官今领大郡,出入须威仪;前船载舆马,后船列放旗;骚路设供帐,州邑争饭遗;既得饱骨隶,兼足充囊资。”太守语髯奴:“尔言何可鄙。我昔被命来,徽屋河之埃。时当夏秋交,暑酷汗如洗。买舟小如瓮,出入波浪里,饥咽脱粟饭,渴饮浊流水。灾区幸周览,遥自恤劳止。何况给郡符,其痛受如己。{兼从人苟多,约束法难恃。岂维索酒食,且复营赂贿。官吏一顿餐,民将竭膏髓;官吏一囊金,民将胃妻子。哀鸿方傲嗽,忍令更出此。”飞符下州邑,谆谆戒令史:“慎勿役丁夫,辛苦负行李;慎勿具盘飨,殷勤奉芳旨。水减民未耕,先为理疆址;岁宴民未食,先为谋矩粉。强梁禁侵暴,底弱救转徙。绘取流民图,郑侠本乡里。行见贩泽施,庶免沟壑委。”灾黎闻此言,感叹同一声。扶攀老与幼,远近纷相迎。争先望颜色,爱戴逾所生。翻愁水涸灾珍息,太守不向村中行。
墨卿先生在知府的任上虽然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从嘉庆九年到十一年的连续三年的大灾却在他手下平息。当他调任河库道和两淮盐运使时,扬州辖区已是风和雨顺,一片丰收的景象了。将近十年后,当他去世时,扬州士民仍怀思不衰,感念其德,把他和欧阳修、苏东坡、王士祯供奉在一起,称为四贤祠,长年祭祀。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此处也许插入一段他在嘉庆十六年秋天重游惠州丰湖的情景是适宜的。当时,他见到邑人僻有伊公祠来赞颂他,他当即速令撤去。《诗钞》卷五《与陈仲卿游丰湖四首》中的“壁上蛟蛇看宛转,庭前香火愧松惺”一联即指此事。
墨卿先生平居端朴,爱民如子,政声郁然,众口一辞,这是他在行为生活中给后人树立的榜样。同样,他在沉思生活中也给后人留下了财富。他的书法刚大充塞,足配道义,笔力千钧,不可禁当,遂令百世之后晶莹不灭,成了我们精神家园中的灿烂星光。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梁章矩曾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中写道:
宋元明三代,隶学几绝,率多以意为之。不特汉隶无传,即学唐隶者亦渺不可得。至我朝朱竹蚝,始复讲汉隶,然如垫角巾,聊复尔尔,已为前人所讥。同时之郑谷口隶书最著,则未免习气太重……此外如林信人、王虚舟,腕力皆弱。直至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未谷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
未谷即桂馥,是著名的说文专家,名声与段玉裁相坍。他比先生大十八岁,与先生可说是忘年之交。《诗钞》中有几首诗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桂氏曾辑有《缪篆分韵》六卷,其中的补遗五篇就是墨卿先生手书上板的。墨卿先生也在文字学上下过工夫,考释文字的心得在函札中屡有所见。可惜,没有专著传世。当代学者金学智先生认为,退庵的话指出了伊秉缓隶起数代之衰的历史地位。其实,这段话的重要性还不仅此。景中告诉我,金石学在清代的兴盛对学术和艺术的影响,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题目。而退庵这段话中所推重的两个人物,恰恰正是清代的学术和艺术中的两个典型。因此这段话的史学意义应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阐发。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所首倡的清代书坛以伊、邓、刘、张为四大家的那种说法,因为它虽然似乎已成定论,但清末的向桑却从另一个角度说道:
墨卿楷书法程哲碑,行书法李西涯,隶书则直入汉人之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
向桑字乐毅,自号抱蜀子,也是一位书法家。他本人对完白山人评价很高。但这里却用来烘托墨卿先生的隶书造诣,是很有意味的。尤其是当梁启超先生把这个意思说得异常明确时就更加不同一般了。因为,自嘉道以降,完白山人在书坛上的地位已固,名声也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书法史上虽然也有“南伊北邓”的称号,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还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前。而且使我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卿先生的艺术就像暗暗黑夜中向我们徐徐飘来的流星,光芒日益强烈起来。张舜徽在《艺苑丛话》中的看法代表了近来的观点。他在那里引用了任公的话,并加以评论道:
论及清代隶书,吾必推伊汀州为第一。梁任公题《伊墨卿临汉碑立轴》有云:“墨卿先生分书,品在完白山人上,有清一代弃冕也。”此乃定评,非任公一人之私言类。伊书劲秀古媚,独创一格。笔画平直,分布均匀;四边充实,方严整仿。融合《衡方碑》、《郁阁颂》、《张迁碑》之长,形成笔力雄健、沉厚挺拔之体。实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故榜书尤冠绝一时。又工小篆,成时名家。楷书、行草,深入颜平原之室,愈小愈妙。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对完白山人和包慎伯的批评。他的论点清晰而又坦率,毫无闪拣其词之处,触及的全是清代书法史上的重要间题。因此,他的意见是应该引起书法史家们的掂量和考虑的。由于这些见解还鲜为人知,在此,我想不顾篇章结构的平衡,详细引述如下:
自从包世臣于《艺舟双揖》中为《完白山人传》,篇题下标明“嘉庆丙寅”,则嘉庆十一年也。包氏时年三十,学识功力,犹未大成。乃于邓石如之书法,推崇无所不至,尊之为清代第一书家,而隐然以第二自居,信可谓不知量炙。论者谓其与邓氏同产安徽,乡曲之私,不免阿其所好,理或然也。自《艺舟双揖》风行天下,而后邓石如书名大张。邓氏存时,固未有人赏重其书而推许之也。平心论之,邓书非无功力,若必张皇过甚,至谓篆隶之工,无第二手,亦太逾其实矣。余平生于完白山人之书法,素所钦迟,尝遇见其篆屏四幅,隶书直幅横幅各一,皆真迹也。然校论其所诣,则篆不逮钱十兰,而隶乃逊伊墨卿。二家学问博赡,下笔有金石气,由泽于古者深也。完白奋自僻壤,闻见加隘,胸中自少古人数卷书,故下笔之顷,有时犹未能免俗耳。顾自嘉道以降,效其体以作书者,目为不桃之宗,影响所及,得固不胜其失也。
这里所谓的“胸中自少古人数卷书”,也不是一家的私言。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就这样说过:“完白以隶笔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两者皆得自冥悟,而实与古合。然率不能济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所谓的少数卷书这个问题,在专业化的现代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甚至还可能认为那些旧时代的先生也太小题大作了。但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心目中向往的是通才,是文艺复兴时代所谓的“universla man",是思想家、学者、艺术家、诗人的洽然综合。仅仅的艺术家是不能束缚住他们的心胸的。而正是书籍,成了他们行为的典范和磨炼性格的砺石。也正是在用书籍所建造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才成了那种我们只能用不世之才或伟人来称呼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墨卿先生受人尊敬的不只是政绩和书法,还有他的理学、教育、法律、军事、金石、诗歌、篆刻等等方面的才能。一言以蔽之,即他胸中的书卷。因此,在谈论他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是乾嘉时代,即一个学术鼎盛时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张先生在评论包世臣时又呼应上面的意思继续说道:
包慎伯在嘉道间,有才名,无学名,固一江湖游士也。而生平好以大言欺人,余往者于《清人文集别录》中既已斥其妄矣。包氏《艺舟双揖》中有《国朝书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神品一人,但列邓氏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但列邓氏分及真书。其他分列姓字,各有等差.若伊秉绩之行书列之逸品下,钱洋之行书、桂馥之分书,钱站篆书,皆列之佳品上。如此衡评,有何绳准?伊氏篆隶俱工,乃至榜上无名。良由门户之见既深,又隘于耳目,未能尽观,故以一己狭陋之见,任意区分高下耳。至于自作品题,乃谓为右军后一人。自信太过,骄亢已甚。自《艺舟双揖》风靡天下,见者无不为其所吓。步趋其后者,流弊乃多。如吴熙载之流,已不能张其军已。平心论之,包氏于书,非无功力。余尝遇见其行草真迹,尽有佳者。惟不宜高自标榜,张皇太过耳。古人云:“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虽于艺事亦然。包氏啤晚一世,悍然欲以主持坛站自居。是非靡准,高下任情。立论虽高,而己之所诣不足以副之也。
张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三中对包世臣的学问所作的评价也大抵如上。包世臣跟墨卿先生有过交往,他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漠视了墨卿的篆隶,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令人费解的。《艺舟双揖》中《记两棒师语》靠后的部分,有几句关于墨卿先生执笔法的评论。那里,也许透露出了一些消息。总之,他对墨卿先生是有微词的。墨卿先生怎样评价他,我们不得而知,好在《留春草堂诗钞》中还保留了两首诗,可供我们推测。其中一首题为《赠包慎伯孝廉》,当时包世臣的名声还未显扬。
年少奇才径县包,醉翁曾以助吾曹。儒干二府资筹笔,贫出千金市宝刀。心盼雕飞边草长,论翻月落海云高。相逢却订深山住,无定时名要善逃。
诗的结句,似乎带有预见或警醒的味道。不仅告诫包慎伯,也警告着百年之下和墨卿先生有着一丝半缕连系的人。我们从历史的画面中所看见的墨卿先生的人格,是不允许别人为他的时名摇唇鼓舌的。墨卿先生的书法是严肃的,它们本身说明了一切。
如果说那些作品激起了杰出的学者和书法家何子贞胸中的诗情,使它奔腾而出,这是不足为奇的。《东洲草堂集》题墨卿书云:
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褚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驰荒醉。不将俗书薄文清,舰破天真辟道眼。
在墨卿先生的后人中,儿子伊念曾,元孙伊立勋都在书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伊念曾不但被誉为能传父隶法,几可乱真,而且还有诗集传世。程序伯诗有云:“自古才人如弃妇,从来名士少佳儿。”这样看来,墨卿先生是幸运的。他曾经给他的儿子写过三十二字的铭言:“方正,奇肆,悠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掘。”这也可看作他本人的创作纲领。他在嘉庆二十年所书的“遂性草堂”四个大隶字下写的跋文“人生也直,即天地之性,无少回邪,径行则正”,也是我们理解他的书法观的很好的辅助材料。他的诗集中有一组题为《书斋四咏》的组诗,其中《端砚》一首写道:“磨人自是同磨墨,正笔应知在正心。”陈石遗认为这两句写得“雄迈浑成”,我们不妨拿来和上引的跋文并置对观。不过,说到底,他还是把做人放在了人生的第一位置上。他虽然称赞过人品不佳的张端图和王觉斯的书法,心中却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近代观念;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他不可能跳过他的时代。
总的说来,他留下的关于书法的话不多。《留春草堂诗钞》中有一些关于碑版法帖的诗,使我们可以从中宛转地看出他书法渊源的痕迹,例如“磨墨兼访衡方竭,吾宗之良均范模”,“维衡与伊氏,同祖商阿衡”之于衡方碑;“溜雨滴石峥,山泽乃通气”之于《华山碑》等等。他和金石学家黄易、翁方纲、张燕昌等人的交往也都在诗中有所反映,例如《小学篇赠黄小松(易)》(卷一)、《题衡方碑阴同覃溪先生寄桂未谷大令》(卷四)等等。有些史料可能就隐藏在这些抑扬起伏的字句之中。还有几首诗可以看作交流史的文献,它们是:《送高丽朴俭书(齐家)归国》(卷二)、《题张水屋刺史(道握)画册送高丽金履度归国》(同上)、《李墨庄舍人出示册使琉球归搓图卷率题其后》(卷四)。这里的朴齐家特别值得注意。他和纪晓岚的交往也很深厚,《三十六亭诗》中有几首就是写给他的。但我读来觉得非常亲切的,是他嘉庆十七年在杭州逗留期间所作的篇章。例如同许乃普等人游黄龙、金鼓、紫云诸洞的七言古诗。由于我家就在紫云洞下,我们也常到这些洞前流连徘徊,吟咏之间,便自然而有往昔先哲凭眺怀古之地,在今有缘寻踪接迹之感。记得仁和魏成宪在《清爱堂集》卷十四中有记先生游杭的诗篇,暇时当检出一阅。
在卷四中有一首题为《明郑端清世子诗》的七律,对我家来说也是别有意义的。景中的原籍旧称河内,有两位乡贤他景仰异常。一个是李商隐,一个便是郑端清世子。这位世子的名字叫朱载峭,是一位大音乐家和大科学家,李约瑟称之为文艺复兴式的人。他写了二十几部著作,其中有部大书叫《乐律全书》,今年正好是这部书出版四百周年的纪念。我家藏有几册郑藩的原刊本。景中常说,要把它献给家乡的朱载靖纪念馆,并且要我把这首颂扬那位世子的诗也恭录在护叶上。
然而我至今还从未抄录过墨卿先辈的诗。江南草长,茶花生树时,我想画上几幅折枝。并工工整整地录上几联墨卿先辈的诗句。他吟咏白茶花的诗“一花开雪后,孤月照宵分;岁宴玉人至,天高白雁闻”,常常在我心中幻化出一种飘渺而又高洁的景象。
《留春草堂诗钞》大概有三个本子。嘉庆十九年(1814)刻于广州板藏宁化秋水园的是第一本,为墨卿先生所自刊。翌年,他便去世,赵怀玉撰有《扬州府知府伊君秉缓墓表》,收在《碑传集》里;张维祯有《哭伊墨卿师长句》,收在《石萝山房诗钞》里;今俱不录。光绪丁酉年(1897)的刻本是第二本。曾见过一部,皮纸初印,很是精美,乃于莲客旧藏;石琴吟馆排印本是第三本,为来孙伊远昭所刊,时在民国庚午年(1930),有伊立勋的题签和后跋。我家的本子即为伊远昭本人所藏过。嘉庆本是后两个本子的底本,文字应以此为准。但是嘉庆本在咸丰以后的印本有补板,这是使用者应该注意的。
除了刻本之外,涵芬楼曾出过一本《伊墨卿先生自书诗》,用林则徐的旧藏本影印。田家英的小莽苍苍斋也藏有一部《伊秉缓诗册》。因未见原件,不知其与影印本关系如何。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默庵集锦》(上下两册),1937年出版的《默庵集锦续集》,1926出版的伊立勋辑《伊墨卿先生真迹》,都收有一些诗作,不但可与《诗钞》对勘而且也可辑佚。另外,叶廷殡在《蜕翁所见诗录感逝集》中还提到了一个选抄本,想已不存天壤。他说:“余囊在颐道堂见云伯先生尝选(墨卿)太守诗一卷,乱后复得之,乃择其尤美者录存三十八首。诗不为前明闽派所拘,亦不沾沾于摹唐仿宋,而性情气息自然近古,真儒本领,因自异于词章家也。”云伯即陈文述,杭州人,嘉庆庚申(1800年)举人。阮元在《定香亭笔谈》卷一中对他很欣赏,说他是杭州诸生中第一名诗人。可惜不知他都选了些什么。
墨卿先生不以诗名,除了《国朝诗人征略》、《石遗室诗话》中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外,其他人的说法大都像上面的叶调生那样,是一些泛泛的赞语。这自然仍是出于对他的人格的景仰。即使在大藏书家叶德辉给《留春春堂诗钞》所写的跋中也未见出显露新意的话。他除了转抄之外只是笼统地说道:
先生早官刑曹。精研法律,出典剧郡,软掌贤劳。于诗本不能如专家用功之深,然风雅性生。吐辞清妙。再至扬州,日与诸名流唱和,未尝以章缓萦心。早随光禄公朝栋侍宦京师,既书大兴朱文正蛙之门,又为纪文达晌延为西席。耳濡目染,闻见异于乡曲之儒。光禄公本以诗名,有《赐研堂诗钞》行世。益之以家学,虽昌黎之于韩农,必卒能成其名而,况先生固有过人之异察哉。
《留春草堂诗钞》凡七卷,前有法式善、吴贤湘二序。后有余正焕一序,陈昙一跋。诗始于乾隆四十七年,止于嘉庆十九年,共收诗七百三十一首。除此之外,散于书轴题跋者,为数尚黔。我仅就手头之便,略作补佚。一首题为《建安亡子歌》,王赦选入《湖海诗传》,这大概是墨卿先生不愿哀入诗集的。另外有两首散落在诗话里,兹录如下,以省翻检。
郭麟《灵芬馆诗话》:余旧居芦墟,去分湖半里。天朗气清,湖光荡目,吴中远山,一痕如黛,因取昌黎“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之句,名楼日“浮眉”。后虽迁移,而其名尚仍而不改。邓江僧序初为之图,刘芙初为作记,伊墨卿太守诗云:桃花新涨渺无津,一株青山染黛攀。侍得纤纤初月上,此楼真合住仙人。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山水扇面,墨卿目题云:无师之画,随笔涂之,以破岑寂,云谷见而取去。此乃生平第二作,真他日笑柄耳。并一绝:白云缺处见山椒,遥指城闺远币嚣。一缕龙涎小舟热,西风吹获晚萧萧。近年出版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法选集》中,有一幅墨卿先生用行书写的五言律诗立轴,属款为:“玉琴先生正,题正希先生像,秉缓初草。”按正希为金声字。金声,安徽休宁人,明崇祯进士,抗清英雄。诗中赞美金声,将他比为宋代的文天祥。这首诗《诗钞》中也未收录。
其诗云:呜咽庐沟水,兵车覆阵云。未容通绝域,聊复整孤军。宗国苞桑计,空江落木声。成仁孝陵侧(用石斋先生语),同配宋家文。
在私家的收藏中,李氏群玉斋有几件墨卿先生的作品很是精美。其中有一隶书扇面,极佳。诗也极明亮高华:
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静重如须弥,深广如大海,无住如虚空,随顺如深水,荣辱如空华,冤亲如梦幻。
诗后有两排行楷小字:“嘉庆癸亥岁九月初七日坐鹿门精舍秉缓书。”落款未说明这是谁的诗,我猜测应为先生所作。即使不是,我们也不妨把它看成是先生人品的写照,而且,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它和纪晓岚先生为他写的扇面系出同一格调。在《纪文达公遗集》中我们读到《为墨卿题扇》:“风露夜清,幽花自吐。与淡泊人,结尘外侣。人本无心,花亦不语。月白空庭,寥寥太古。”
墨卿先生的著作,还有《攻其集》、《坊表录》、《修齐正论》等,惜未见传本。幸运的是,在西伶印社印泉边的仰贤亭里,还能见到墨卿先生的小像。那是张笙所绘、俞逊所镌的刻石。小亭的附近有三径青草,远处是六桥烟水,距我家所居又很近,我们是可以时时瞻拜的。
此文系景中与我合写,由于行文之便,他没有属名。在写作中,得到了穆泽、彭向阳、梁颖诸先生的大力帮助,书此以志雅谊。小英草于丙子年腊月十九日。
文成,又得窦水勇、余辉、林夕三位先生之助,仰感隆情,谨致谢意。又及。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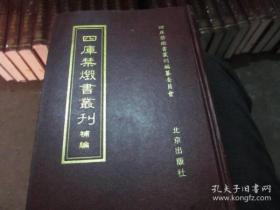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