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自身的外人(拜德雅·人文丛书)
批量上传,套装书可能不全,下单前咨询在线客服!有特殊要求,下单前请咨询客服!
¥ 27.88 4.5折 ¥ 62 全新
库存17件
作者[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著 陆观宇 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4699
出版时间2022-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2元
货号29478422
上书时间2024-11-0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理论随笔,作者从自己作为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出发,由外国人在法国的历史引入,从而引申出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外人”和“自我中的陌生性”是贯穿本书的两个重要概念。作者不仅展现了在古希腊悲剧、《圣经》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文学中的外人形象,还探讨了历史上外人的法律地位,更有力地论证了我们对自我的彻底审视,这一审视始于认识到外人身上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不想在自己身上承认的品质:我们自身彻底的陌生性。克里斯蒂娃断言,只有承认“外人就在我们自身之中”,我们才能开始公平地对待他人。
商品简介
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理论随笔,作者从自己作为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出发,由外国人在法国的历史引入,从而引申出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外人”和“自我中的陌生性”是贯穿本书的两个重要概念。作者不仅展现了在古希腊悲剧、《圣经》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文学中的外人形象,还探讨了历史上外人的法律地位,更有力地论证了我们对自我的彻底审视,这一审视始于认识到外人身上最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不想在自己身上承认的品质:我们自身彻底的陌生性。克里斯蒂娃断言,只有承认“外人就在我们自身之中”,我们才能开始公平地对待他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年生),保加利亚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狄德罗大学荣退教授。克里斯蒂娃为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创立互文性理论与贱斥理论,学术成就卓著,享誉全球学界,屡获人文社科重要奖项与荣誉称号,如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87)、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8)、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2004)、德国汉娜·阿伦特奖(2006)、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司令勋位(2015)与大军官勋位(2021)等。其著作有《符号学》《诗性语言的革命》《恐怖的权力》《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国妇女》等四十余种。
- 译者简介
陆观宇(1998年生),学者、译者,牛津大学罗德学者,现于牛津大学陂柳书院(Balliol College)攻读希腊与拉丁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此前于伦敦大学高等学院瓦尔堡研究院取得文艺复兴文化、思想与艺术史硕士学位,于复旦大学与伯明翰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目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15、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与思想史,亦对文艺复兴修辞史、20世纪艺术史论史、女性主义思想史与中文翻译史有研究兴趣。
目录目录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译者序
我们自身的外人
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
希腊人:在蛮人、迁客与乞援者之间
天选之民:选择陌生
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流亡的良药与朝圣
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
这场“形形色色”的文艺复兴
启蒙与外人
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
实践上……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理论随笔,作者从自己作为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出发,由外国人在法国的历史引入,从而引申出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外人”和“自我中的陌生性”是贯穿本书的两个重要概念。作者不仅展现了在古希腊悲剧、《圣经》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文学中的外人形象,还探讨了历史上外人的法律地位,更有力地论证了我们对自我的彻底审视,这一审视始于认识到外人身上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不想在自己身上承认的品质:我们自身彻底的陌生性。克里斯蒂娃断言,只有承认“外人就在我们自身之中”,我们才能开始公平地对待他人。
主编推荐- 作者简介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年生),保加利亚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狄德罗大学荣退教授。克里斯蒂娃为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创立互文性理论与贱斥理论,学术成就卓著,享誉全球学界,屡获人文社科重要奖项与荣誉称号,如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87)、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8)、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2004)、德国汉娜·阿伦特奖(2006)、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司令勋位(2015)与大军官勋位(2021)等。其著作有《符号学》《诗性语言的革命》《恐怖的权力》《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国妇女》等四十余种。
- 译者简介
陆观宇(1998年生),学者、译者,牛津大学罗德学者,现于牛津大学陂柳书院(Balliol College)攻读希腊与拉丁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此前于伦敦大学高等学院瓦尔堡研究院取得文艺复兴文化、思想与艺术史硕士学位,于复旦大学与伯明翰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目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15、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与思想史,亦对文艺复兴修辞史、20世纪艺术史论史、女性主义思想史与中文翻译史有研究兴趣。
精彩内容- 精彩选摘
译者序
谈起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读者或许熟悉这样一则逸事。1965年,24岁的她获得“戴高乐”奖学金,作为通晓法语的保加利亚学生赴法攻读博士学位。圣诞前夜,飞机降落在大雪纷飞的巴黎,她口袋里只有五美元,在机场没人接应,投奔使馆无门,所幸有贵人相助,才不致露宿街头。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峥嵘岁月,后被克里斯蒂娃记叙在自传体小说《武士》里。
2018年,当这段回忆在公众视野中被重新唤起时,克里斯蒂娃已经是蜚声国际的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理论与贱斥(abjection)理论的奠基人,是巴黎狄德罗大学的荣退教授。是年三月,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即该国秘密情报组织,有媒体将其比作 “克格勃”)档案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数百页的档案,称克里斯蒂娃在1970—1973年,以“萨宾娜”之名,受聘为该组织的特工。据称,她在出国之前签下文件,称“如有必要,会为组织效力”。瞬时,西方学界为之震动,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几日后,克里斯蒂娃严正辟谣称,自己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谍报活动,档案文件没有一份出自她的笔下,均属该部门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而成,诸多内容甚至有悖于她当时的公开立场。七月,克里斯蒂娃于《名利场》杂志撰写长文,自述出国的经历以及此次被诬陷的始末。她写到,自己离开前和当局签下的一份文件,是为了承诺自己不会在巴黎结婚,而她对这份文件也不甚在意。来法第三年,她便与文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年生)结婚。读了档案之后,她才意识到,许多过去的同事和来访的旧友,都是被派来监视自己的棋子,回头便向当局呈交“罪证”;而几年间,自己和先生写给父母的家书,在寄到之前,无一例外地被警方拆阅。她感叹道:“我早就知道自己在法国永远是外国人。这种陌生性,此后倒也成了我的家乡、我的命运。”
外国人的身份,便如此伴随着,甚至是搅动着克里斯蒂娃的人生。早在 1970 年,阐述互文性理论的《符号学》(Séméiotiké)出版后,导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便撰文赞赏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贡献,标题拟为《外国女子》(L’Étrangère)。日后追忆恩师时,克里斯蒂娃表示,出于法国人对传统的敬仰,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不免有被排斥之感;可法国也有像罗兰·巴特这样的人,欣赏学生的研究成果,希望学生有独立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与学界传统大相径庭。因此,她说:“在法国做外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可是]在法国做外国人,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这两句话即出自克里斯蒂娃的《我们自身的外人》(Étrangers à nous-mêmes;下文简称《外人》)一书。该书写于 1988 年,以时而锐利、时而凄楚的文字描摹外国人的境遇,以时而宏大、时而精细的角度梳理外国人的历史,很难说不沾染些许自传色彩。
关于《外人》的出发点,克里斯蒂娃称之为“外国人问题”:在当下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与外国人共存?如何直面他们的存在,既不对他们加以排斥,又不要求他们同化融合?如何处理我们内心油然而生的爱与恨?作者给出的答案触及我们的心理:我们要承认自己内在的奇异性、陌生性;只有在我们将自己视作与自己陌生的人、视作自身的外人之后,才能更好地尊重、接纳外国人,与他们共同生活。
乍看之下,这一论点的效力,甚至是这一论点的核心概念之效力,都受制于法语本身。“外国人”“陌生人”,或是形容词“外国的”“陌生的”,在法语中均作“étranger, -ère”;而“奇特”“怪异”,作“étrange”。大概两者同源于拉丁文 extraneus,演化至今,仅有一字之差。于是,描述性质的名词“étrangeté”既可作“陌生性”,又可作“奇异性”,乃至弗洛伊德处的“怪怖”(unheimlich,法文意译为“令人不安的奇异”)。这些彼此相近的法语词,或许无法用同一种中文译法加以概括;若是新造词语来取代这如此常见的义项,则更为不妥。考虑再三,还是以保留这些词语各自的通俗译法为上。除了难以统一的“étranger”与“étrange”之外,“étranger”一词广泛的意涵本身也为中文翻译出了一道难题。在法文中,“外在于某边界”“让人感觉陌生”的人或物,大都可以用该词形容,如加缪的名作《局外人》(L’Étranger,1942)——主角默尔索是身处北非的异乡人,是现代社会的陌生人,是自身存在的局外人。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étrangers 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政治或文化“边界”,因而中文译法亦根据语境决定: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作“外国人”;在此之前的,如果边界处于地区之间,便作“外地人”;如果边界属于城邦之类的政治实体,便作“外邦人”。在某些段落中,克里斯蒂娃将étrangers视作某种普遍的范畴加以论述,中文译法定为“外人”,算是“外国人”“外地人”“外来者”等义项兼具的折中策略。总之,若是在行文中,“外人”“陌生”“奇异”略显跳脱,往往是因为原文的用词有着直观的亲缘;若是不同章节中 étrangers 的译法前后抵牾,往往是因为语境发生了转变。这些中文译法的权衡之举,还望读者担待。
不过,即使法语的语言特征无法在译文中复刻,奇异与陌生、陌生与外人之间的联系却始终存在着。令我们慨叹奇异的事物,定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而外人的范畴,也正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人、熟悉与陌生的分别之上。只要外人的范畴存在,他们身上的陌生性便无法消解,他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便体现了这个社会对他者、对陌生、对奇异的态度——尤其是外国人,为当代社会中外人的典型。因此,若是读者越过这段语言的藩篱,便一定能体悟作者对外人境况入木三分的剖析。
- 精彩论述选摘
《献给外人的托卡塔与赋格》
外人:扼在我喉咙深处的怒火,将澄澈搅浑的黑翼天使,行迹晦暗,深不可测。仇恨的化身、他者的象征,外人既不是我们慵惰的家庭假想的受害者,也不是带来城邦一切罪恶的闯入者。不是正在进行的天启,不是为了安抚集体而亟须消灭的近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外人栖居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身份被遮盖的一面,是毁坏我们处所的空间,是融洽与同情分崩离析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认出他,我们就不必在他的身上憎恨他。这个被称作“外人”的征状,恰恰让“我们”一词显得破绽百出,甚至毫无可能。他开始于我对自身差异的意识出现之时,结束于我们相互视作亦敌亦友、同属集体的外人之刻。
我们能否既成为外人,又感觉幸福? 外人让我们赋予幸福新的概念。在本原与奔逃之间:一道脆弱的界线,一种暂时的平衡。稳重、尚存,有时显得确凿,这种幸福却是倏忽即逝的,如火一般,只因燃烧而闪烁。外人奇特的幸福,便在于保持这种永恒的短暂、这种短暂的永恒。
人们说,你的笨拙有着魅力,甚至有着肉欲,让追求者争相赞美。没人指出你的错误,以免伤你的自尊;然后错误没完没了,后也没人在乎了。可你发觉这多少也让人不自在:有时候,紧皱的眉头或是盘旋的一句“再说一遍? ”却感觉是在说“你也成不了我们”,是在说“没必要这样”,是在说“我们也不傻”。你也不傻。你只是深信,若是你不辞辛劳、不惜光阴地练习着这门属于他人的语言,幻想着终有一天能够完美地习得它,能够达到天知道怎样的理想水平——而不再因为自己不守承诺的出身,暗中流露自己的失落。
然而,在法国做外国人,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因为你的与众不同不可挽救,永远无法令人接受,你便成为着迷的对象:人们留意你,人们说起你,人们或是痛恨你,或是爱慕你,又或者两者兼具。然而,你并不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存在,不是张三李四。你是问题,是欲望:人们对你或是褒扬,或是贬斥,永远不是中性的。当然,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外国人引发的经济或政治困难都用行政途径加以解决,往往伴随着不可控制的爆发。可是“SOS Racisme”只存在于法国,也只在法国才有对《国籍法》多少还算公正客观的举国反思。
《天选之民:选择陌生》
既然所有人都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爱人如己”的训诫不仅适用于直接的邻人,即同宗同族之人,更适用于“[神]所爱之人”;“正如对以色列人而言,爱邻人如爱自己,此语同样用于外邦人”。
信众吞噬着外邦人,将其同化,融入自己宗教道德法则的保护之下,同化者与受同化者均遵守这一法则。在这些宗教理想之下,吞噬者的幻想秘而不露,而这些幻想可能引起的愧疚之感,也被排除在外。此外,在宗教专属的道德理想的保护下,受同化的外邦人却以“复本”之名,从信徒的自身内部加以影响——永远地让信徒在“低贱”之中、在“过度”之中、在“法外”之中辨识出自己,刺激着他完善自我的动力。如果大卫也是路得,如果君王也是摩押人,那么他的命运则永无平静之可能,而他将永远探求着在自身之中迎纳他者、超越他者。
《凭什么权利算您作外人?》
人权, 还是公民权?
汉娜·阿伦特勾勒出这一冲突的谱系,却也描绘出其堕落——极权主义由此而生;而这一冲突,也体现在现代社会对“外人问题”的解读中。外人问题的困难在于,区分公民与人是在作茧自缚:为了确立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的人民所专属的权利——即使是理性、民主意识的国家,难道不也必须将这些权利与非公民区分开,换言之,与其他人区分开吗?这一举措意味着,我们多少算作公民,就多少能算作人;而不是公民的人,不完全算是人——这是的后果。在人与公民之间,有一道疤:外人。如果不是公民,那外人又能算作完全的人吗? 如果不享受公民的权利,那外人又有人权吗?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赋予外人一切人权, 那么在我们夺去其公民权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呢?
有人会问,蜂拥而至的外来劳工大煞法国郊野的风景,扑鼻而来的烤羊腥膻大倒芝兰之士的胃口,而有色族裔的少年罪犯之多,更是让人将外人与犯罪画上等号,你却要远赴思想与艺术的高阁,归根结底只是为了解决非常实际的,乃至庸俗的问题,这又有什么用呢?
《普遍性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陌生性吗?》
民族自豪感向来不乏《方方郁金香》式的狂热与“吹擂”(gasconnades),在大革命时期更是具备了恐怖主义的特征。我们或许应该思考,这究竟是对卢梭式的民族主义彻底的歪曲,还是它的必然后果。无论如何,《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的爱国主义是从属于人权的普遍性之下的。因此,在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书》(1758)的引言中,他自称“日内瓦公民”,却同样写道:“自由与真理,这是人的首要职责。人性、祖国,这是他首先所爱的。如是有任何特殊的考虑让他改变这个顺序,他便犯下过错。”
就弗洛伊德而言,虽然他只介入精神病学的领域,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他与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联,便无法了解他的贡献。通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内蜷于心理之中的奇异不再被视作病症,而是在人类假定具有的统一性中融入一种既属于生理又属于象征的他者性,而成为同一的一部分。此后,“外人”不再是种族,也不再是民族国家。“外人”不再被颂扬为隐蔽的民族精神,也不再被贬斥为理性礼仪的搅乱者。怪怖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外人——我们是分裂的。
弗洛伊德的意图在于区分由审美经验所引起的怪怖与在现实经验中感受的怪怖:在他着重强调的作品中,正是因为话语塑造的整个世界都是虚构的,奇异性便失去了效果。童话便是如此,被普遍化的艺术手法让我们完全无法在符号、想象与物质现实中做出比较。因此,这种手法便中和了怪怖,而将被压抑者的回归变得逼真、令人接受、使人愉悦。就像是说,的童话——的升华——以及与此相反的的理智——的压抑——是我们对抗怪怖的堡垒。除非它们在为我们免去奇异性的风险与乐趣的同时,也为此带来终结(liquidateur)。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阿凡提的故事·智慧勇敢[彩图注音]](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cdadcbfc/4bba3592386647ab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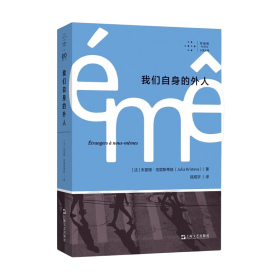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