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
批量上传,套装书可能不全,下单前咨询在线客服!有特殊要求,下单前请咨询客服!
¥ 72.42 6.2折 ¥ 116 全新
库存84件
作者[英]安德鲁·所罗门 著, 理想国 出品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71776
出版时间2020-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16元
货号29139167
上书时间2024-11-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写作本书使我成了一名“专业抑郁者”……我感到,抑郁研究领域里,缺少的是综合。很多学科都分别探讨过抑郁的成因,太多有趣的事发生在太多有趣的人身上,太多有趣的事在被讲述——而这个“国度”里仍是一片混乱。本书的*个目标是共情,真正地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目标,也是对我来说更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秩序,而不是随意用些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我以自己的抑郁开始本书,然后写别人相似的抑郁,再然后是别人不同的抑郁,*后是处于完全不同背景下的抑郁。我让男男女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所面对的战争是本书关注的首要主题……就抑郁进行写作,很是痛苦、悲伤、孤独,令人压力倍增。但每当想到我做的事可能对其他人有所助益,我就会精神为之一振;我也不断获得新知,这也帮到了我自己。
现在苛责制药业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但我的经验是,这行人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利润,但也乐观地相信自己的工作会有益于世界。如果没有制药公司资助相关研究,我们现在也不会有SSRI,这类抗抑郁药挽救了无数生命。我尽可能清晰地描述了我所了解的制药业,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这是一本极度个人化的书。虽然我为一些比较复杂的观点提供了解说和阐释,但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当的治疗。
作者简介[美/英]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1963— ):作家,公共演讲人,关注领域包括文化、心理学及公共权利。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及心理学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为众多刊物,如《纽约客》《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撰稿,已撰写多部书籍,被译为十余种语言;亦担任多所心理机构及艺术机构,如抑郁及双向支持联盟(DBSA)、大都会美术馆等的顾问。
他有近三十年的抑郁症经历。美英双国籍,目前和家人生活在纽约。
目录编者说明 i
献辞 iii
目录 v
题 记 vii
本书写作方法 001
章:抑 郁 005
第二章:崩 溃 031
第三章:治 疗 093
第四章:替代疗法 127
第五章:人 群 165
第六章:成 瘾 207
第七章:自 杀 233
第八章:历 史 275
第九章:贫 困 325
第十章:政 治 351
第十一章:演 化 389
第十二章:希 望 409
第十三章:后 来 433
注 释 499
参考文献 543
致 谢 603
附录1:药品名表 609
附录2:术语表 613
附录3:人名表 617
附录4:其他专名表 631
内容摘要写作本书使我成了一名“专业抑郁者”……我感到,抑郁研究领域里,缺少的是综合。很多学科都分别探讨过抑郁的成因,太多有趣的事发生在太多有趣的人身上,太多有趣的事在被讲述——而这个“国度”里仍是一片混乱。本书的*个目标是共情,真正地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目标,也是对我来说更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秩序,而不是随意用些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我以自己的抑郁开始本书,然后写别人相似的抑郁,再然后是别人不同的抑郁,*后是处于完全不同背景下的抑郁。我让男男女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所面对的战争是本书关注的首要主题……就抑郁进行写作,很是痛苦、悲伤、孤独,令人压力倍增。但每当想到我做的事可能对其他人有所助益,我就会精神为之一振;我也不断获得新知,这也帮到了我自己。
现在苛责制药业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但我的经验是,这行人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利润,但也乐观地相信自己的工作会有益于世界。如果没有制药公司资助相关研究,我们现在也不会有SSRI,这类抗抑郁药挽救了无数生命。我尽可能清晰地描述了我所了解的制药业,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这是一本极度个人化的书。虽然我为一些比较复杂的观点提供了解说和阐释,但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当的治疗。
主编推荐[美/英]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1963— ):作家,公共演讲人,关注领域包括文化、心理学及公共权利。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及心理学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为众多刊物,如《纽约客》《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撰稿,已撰写多部书籍,被译为十余种语言;亦担任多所心理机构及艺术机构,如抑郁及双向支持联盟(DBSA)、大都会美术馆等的顾问。
他有近三十年的抑郁症经历。美英双国籍,目前和家人生活在纽约。
精彩内容- :治疗
一次,我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上见到一个熟人,谈到我正在写作本书。她便说:“我有过严重的抑郁。”我问她为此做了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服药这个主意。我意识到我的问题与压力有关,于是决定把生活中所有压力源都消除掉。”她掰着手指数起来:“我辞了工作,和男友分了手,也不再真去找个新男友。我也不再和人合住,现在自己一个人。我不再去那些开到很晚的派对。我搬去了一个小地方,不再见大部分朋友,基本上放弃了化妆和衣服。”我惊恐地看着她。“听着很糟,但我真比以前快乐多了,也不再那么害怕,”她显出自豪的神情,“而且我没吃药就做到了。”
站在我们这一群中的一个人抓住她的手臂说:“这简直是疯了。这是我听过的疯狂的事。你肯定是疯了,才会这样对待你的生活。”避免那些让自己疯狂的行为,这是疯狂的吗?还是为了维持让你疯狂的生活而服药才是疯狂?我可以把生活降级,少做事,少出行,少交友,也避免去写关于抑郁的书。也许做出这些改变,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我可以生活在能够承受的有限范围之内。我没有选择主要以这种方式生活,但这是个合理的选择。活在抑郁中就像和山羊跳舞时尽力保持平衡—选一个平衡感更好的搭档是完全理智的。可我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复杂性,给了我巨大的满足感,我可不愿放弃。放弃我的生活几乎比任何事情都让我更不愿意。我宁可多服三倍药,也不想把朋友圈缩小一半。“大学航空炸弹客”传达卢德主义的方式是灾难性的*,但他对于科技危险性的见解十分中肯,他在宣言中写道:“想象一个社会,让人屈服于各种令自己极为不快的处境,再给他们药物来赶走这些不快。是科幻吗?这已经在发生了……事实上,抗抑郁药就是一种调整内心状态的方式,好让人可以容忍在其他条件下无法容忍的社会状况。”
- :贫困
强大的意志力通常是抵御抑郁的壁垒,而在抑郁人群中,坚持下去的意志和对创伤的忍耐力常常相当惊人。贫困抑郁者中很多人个性非常被动,到了毫无抱负的地步,这类人是难帮助的。而另一些人,即便身处抑郁之中,也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特蕾sha·摩根是艾米莉豪恩斯坦和玛丽安凯内尔的一位患者,她性格温婉,生活中却点缀着超乎现实的苦难。她住在一所大约两个拖车房宽的房子里,就在弗吉尼亚州白金汉郡的中心,在“信仰通途”圣会以南5英里,“金矿”浸礼会教堂以北5英里。我们见面时,她事无巨细地为我讲述她的故事,仿佛她毕生都在记笔记似的。
特蕾sha的母亲15岁便怀孕,16岁生下她,17岁遭特蕾sha父亲的毒打,不得不爬出家门。特蕾sha的祖父命令她母亲搬出去,躲得越远越好,如果她再回到郡里,或是再试图联系特蕾sha,他就把她送进监狱。“我爸爸那年22岁,所以他才是大混蛋;但以前他们总是跟我说,我妈妈是个fang荡女人,而我会变成她那样的人。我爸爸总是告诉我,单单是我的出生,就毁了他的一生。”特蕾sha告诉我。
特蕾sha很小就被诊断出有一个无法手术治疗的良性肿瘤,这个血管瘤位于直肠和阴道中间。她从5岁生日那天起,每晚都遭到近亲性侵,直到9岁那年,其中一个性侵者结婚搬了出去。她的祖母告诉她,男人统治家庭,而她应该闭嘴。特蕾sha去教堂,去上学,那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的祖母坚信严格规训的效用,这意味着她每天都会挨打,什么家用物品都会用到:祖母用插座延长线抽她,用扫帚柄和煎锅打她。她的祖父是个除虫专家,她从7岁起就花很多时间在房子下面逮黑蛇。特蕾sha八年级时,过量地服下了祖母的心脏病药。在医院,医生为她洗胃,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但祖父说他的家人谁都不需要帮助。
十一年级时,特蕾sha次和男孩约会,那个叫莱斯特的男孩“好像碰到了我的灵魂,我们彼此可以坦诚地聊天。”一次莱斯特送她回家后,她父亲走了进来,狂暴地发火。他身高不到1.6米,但体重超过300磅,他坐在特蕾sha身上(当时她不到1.5米高,重105磅),把她的头撞到地上,持续几个小时,直到鲜血流过他的指间。特蕾sha的额头和头皮至今还布满疤痕,严重得看上去像是烧伤。那天晚上,他还打折了她的两根肋骨、下巴、右臂和四根脚趾。
特蕾sha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她9岁的女儿莱斯莉在和宠物腊肠犬玩耍。后者对这一大堆细节熟悉得很,好似一个熟读《受难》的教徒。但这些细节确实在她心中留下了烙印:听到任何真实的恶行时,莱斯莉都会开始对狗有攻击性。然而,她一直不哭,也一直没有打断我们的对话。
在那次暴打之后,莱斯特邀请特蕾sha搬到他家与他们同住。“前三年都好极了。而之后他就很想让我像他母亲那样,不工作,甚至不开车,只待在家里,把他内裤上那些印子洗干净。可我不想那样。”特蕾sha怀了孕,于是他们结婚。莱斯特以“到处跑”来证明他的独立,留下特蕾sha照看婴儿。“莱斯特以前喜欢我,因为我有想法,”特蕾sha说,“以前我给他讲事情的时候他会喜欢。因为我,他才去听了好听的爵士乐,不再听Lynyrd Skynyrd乐队的那些玩意儿。以前我会跟他聊艺术和诗歌。而现在,他只想让我待在家里,和他母亲一起,因为那是她的家。”
一年后,莱斯莉刚出生不久,莱斯特发作了大面积中风,导致左脑大部分受损。那年他22岁,在修路工程中操作重型器械,这时他半边身子瘫痪,说不出话。之后的几个月,在医生们发现他的隐性疾病(一种导致血栓的狼疮)之前,另一个血栓又毁了他的一条腿,导致截肢,还有别的血栓对双肺造成了损伤。“我本可以离开的。”特蕾sha说。
莱斯莉不再玩了,抬起头来看她,目光茫然而好奇。“但莱斯特是我此生的挚爱,即使我们的感情已经开始经历艰难;我从不轻易放弃。我去医院看他,他一只眼睁,一只眼闭。脸已开始肿起来,开始斜向一边。因为严重肿胀,医生把他左边的头骨取了,直接从他的头上锯下来。但他见到我很快乐。”特蕾sha就住在了医院,教他使用床上便盆,帮他小便,开始学手势,现在他们就是用这些手势来沟通。
讲到这里,特蕾sha停了下来。莱斯莉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照片。“那是你一周岁生日那天,是不是,宝贝?”特蕾sha温柔地对她说。照片里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像木乃伊一样全身裹着布,连着好几台监视器,抱着一个小小的女孩。“那是中风之后四个月。”特蕾sha说。莱斯莉又郑重地拿走了照片。
六个月后,莱斯特回了家。特蕾sha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在工厂剪裁儿童服装。她必须在家附近工作,这样才可以每几个小时就回家看看莱斯特。拿到驾照那天,她拿给莱斯特看,他泪流满面。“现在你可以离开我了。”他用手语说。讲到这里,特蕾sha大笑起来:“但他会发现我没有那样做。”
莱斯特整个人都支离破碎。他会彻夜无眠,每小时喊特蕾sha帮他大便。“我回到家,做晚饭,洗碗,洗几大盆衣服,打扫整间房子,然后我就会睡着,有时候就瘫倒在厨房里。莱斯特会打电话给他母亲,她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呼吸声会打回来,电话铃声会把我叫醒。他以前会拒绝吃晚餐,但现在他总想让我给他做个三明治。我当时一直努力保持喜气洋洋的态度,免得他伤心。”莱斯特和莱斯莉总在争抢特蕾sha的注意力,会彼此抓挠,扯对方的头发。“我开始情绪失控,”特蕾sha说,“莱斯特甚至都不会试着做他该做的锻炼,行动力越来越差,变得超级胖。我想,那段时间我自己也很自私,无法用应有的状态去同情他。”
特蕾sha已经刻意无视她的血管瘤有段时间了,但此时压力导致血管瘤变大,她开始从肛门大量出血。这时特蕾sha已当上工头,但工作还需要每天站立八到十个小时。“体力活加上流血,还有照顾莱斯特和莱斯莉,嗯,我觉得我应该应付得了压力,但还是有点儿疯魔。我们有一把22英寸雷明顿带托长手枪,枪管9英寸。我坐在卧室地板上,拧上枪管,把枪放进嘴里,按下扳机。然后我又按了一次。把枪放在嘴里的感觉真好。然后莱斯莉敲门说:‘妈妈,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了。’那一刻,我放下枪,向她保证我永远不抛下她一个人。”
“那年我4岁,”莱斯莉自豪地说,“那之后,我每晚都来和你一起睡。”
特蕾sha拨了一个自杀干预热线,讲了四个小时电话。“我就那么放声痛哭。莱斯特当时患有葡萄球菌感染。然后我得了肾结石。肾结石让我无比疼痛,我告诉医生,如果他不帮忙,我会把他的脸撕下来。当人身体真的不行了,心智就也想休息。我吃不下东西,一个月都没怎么睡着,躁动不安,痛苦难堪,流血不止,还因此患上贫血。我就这么心怀仇恨地活着。”她的医生带她去见玛丽安凯内尔。“玛丽安救了我的命,这毋庸置疑。她教会我如何再次思考。”特蕾sha开始服用帕罗西汀和赞安诺。
凯内尔告诉特蕾sha,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她做所有她之前做的事,她必须只做那些值得做的。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莱斯特大闹一番,特蕾sha平静地放下了煎锅,说道:“来吧,莱斯莉,拿上几件衣服,我们走。”莱斯特突然记起来特蕾sha是有能力抛弃他的,于是瘫倒在地边哭边求。特蕾sha带着莱斯莉离开家,开着车转了三个小时,“就为了给爸爸一个教训”。她们回家时,他满怀愧疚,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她安排他开始服百忧解。她解释了他们的生活加给她的负担。医生们告诉特蕾sha,如果想防止血管瘤继续出血,她需要停止不必要的走路、锻炼、活动。“我还会把莱斯特抱下车,还会抬他的轮椅。我还会打扫房子。但莱斯特必须很快学会独立生活。”特蕾sha不得不因健康原因辞掉工作。
莱斯特现在在一家洗衣房叠围裙。有一辆残障人士专用公车接他上班,他每天都去工作。在家里他会刷碗,有时甚至会帮助吸尘。他每周的残障补贴和工作加在一起有250美元的收入,一家人就靠此过活。
“我从未抛弃过他;”特蕾sha说。她又突然自豪起来,“人们跟我说我会受不了,但现在我们的关系很稳固。我们可以聊任何事情。他原来是个该死的红脖子,保守的老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已清干净他长大过程中习惯的一些偏见和仇恨。”莱斯特学会了自己排尿,几乎可以用一只手穿衣。“我们从早到晚都在聊天;”特蕾sha说,“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我的一生挚爱,即使对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我都很后悔,但我不会放弃我们和这个家的任何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玛丽安,我只能熬到出血致死,就那样结束了。”
听到这里,莱斯莉爬上特蕾sha的膝头。特蕾sha抱着她前后摇摆,突然激动地说:“今年,我找到了我妈妈。我在电话簿里找到她的姓,打了大约50个电话号码之后,我找到一个表亲,又几经调查[找到了她]。我妈妈接电话时说,这些年来,她一直都在等我,希望我会打给她。现在,她就像我好的朋友。我们总和她见面。”
“我们爱外婆!”莱斯莉宣布说。
“是的,我们爱她,”特蕾sha同意,“她和我都被我爸爸和他的家人虐待过,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特蕾sha说她不太可能有能力站着在工厂劳动了。“有一天莱斯莉能在晚上照顾莱斯特的时候,而且如果医生能让我多活动一些,也控制了血管瘤的话,我会上夜校完成高中学业。我读高中时,在黑人女教师威尔逊小姐那里学过艺术、诗歌和音乐。我会回学校,多读读我爱的作家:济慈、拜伦、爱伦坡。上星期,我给莱斯莉读了爱伦坡的《乌鸦》和《安娜贝尔·李》两首,是不是宝贝?我们从图书馆借的那本书。”她又看着墙上的印刷画说:“我喜欢雷诺阿,别觉得我在矫情,我是真的爱这幅;还有那幅马的画,一个英国画家画的。我还爱音乐,我爱听广播里播的帕瓦罗蒂。
“你知道我小时候在那个可怕的家里想要什么吗?我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去埃及和希腊。和玛丽安的谈话帮我不再犯疯,让我再次开始。我是如此怀念用脑子!玛丽安那么聪明,而我那么多年只和莱斯莉交流,还有一个没读完九年级又不会说话的丈夫……”她走神了一分钟,“天哪,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莱斯莉,我们会去找到它们,对吧,我们是不是会全都找到?就像我们找到了那些诗歌一样。”我开始背诵《安娜贝尔·李》,特蕾sha也加入进来。莱斯莉抬着头,认真地听我和她母亲一起打着节拍背诵这首美国诗歌的前几句。“‘但我们爱上了一种爱,而它不止于爱。’”特蕾sha说着,好似在形容自己的人生之旅。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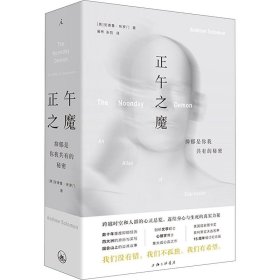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