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货速发】边陲线上
全新正版书籍,24小时发货,可开发票。
¥ 28 4.1折 ¥ 68 全新
库存11件
作者骆宾基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ISBN9787203122104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29444564
上书时间2024-12-2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序言】
好的文字越经过岁月沉淀,才越彰显价值
何鲁丽
骆宾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吉林珲春,山东人的淳朴本性、东北人的豪爽民风,家乡独特的多民族聚居环境和文化传统,特别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都给骆宾基以深深的影响。面对时代的变幻和人生的挫折,骆宾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为人的底线,为艺术创作和金
文研究奉献出毕生心血。
骆宾基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那就是在现实主义细腻描写中交织着浪漫主义,尤其是其中鲜明的地域特色正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他作品扎实厚重的底蕴,使其具有了鲜明的美学特色和艺术品格。除了纪实报告,中篇、长篇小说,他还创作了剧本等。读骆宾基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内心的精神气韵。新中国成立后,骆宾基走进乡村,体验生活,写了一些小说,多角度展现了新农村的面貌。在金文研究方面,骆宾基能独立思考,敢于争鸣,不囿于旧有的金石学理论,自己独创了一套新的。
骆宾基是个爱故乡、爱祖国的战士,是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优秀作家,他专心写作、严谨治学,他有理想,有抱负,他的作品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几十年后看,依然是很有特色、很有贡献的,正所谓“好的文字越经过岁月沉淀,才越彰显价值”。希望年轻的作家,也能传承前辈的精神,从人民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受到民众喜爱的作品。
二○二一年十二月
导语摘要本书为《骆宾基全集》第五卷,是骆宾基的处女作,也是骆宾基的成名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骆宾基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边疆为背景,主要描写了游击队的战斗生活。爱国青年刘强与父亲收租时不幸被抓,刘强历经种种磨难后终于逃了出来,之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作品展现了东北人民走向抗日道路中不同的心理状态,把东北边陲的苍凉与民风的淳朴通过一系列原始而又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现出来,人物命运曲折离奇,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作品语言含蓄、节制,有着契诃夫式的沉着、幽默和微妙。
商品简介本书为《骆宾基全集》第五卷,是骆宾基的处女作,也是骆宾基的成名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骆宾基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边疆为背景,主要描写了游击队的战斗生活。爱国青年刘强与父亲收租时不幸被抓,刘强历经种种磨难后终于逃了出来,之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作品展现了东北人民走向抗日道路中不同的心理状态,把东北边陲的苍凉与民风的淳朴通过一系列原始而又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现出来,人物命运曲折离奇,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作品语言含蓄、节制,有着契诃夫式的沉着、幽默和微妙。
作者简介骆宾基,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等。本册为《骆宾基全集》中的杂文集,共收录作者发表过的杂文《新诗与诗人》《以往和未来》《富饶迷人的黑河》等70余篇,作者为抗日战争所鼓舞,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作品笔触细腻,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从中可以感怀前辈文人干预生活的勇气。
目录【目录】
001 / 上篇
077 / 下篇
164 / 人与土地(章)
187 / 后记
189 / 重读《边陲线上》有感
内容摘要本书为《骆宾基全集》第五卷,是骆宾基的处女作,也是骆宾基的成名作,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骆宾基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边疆为背景,主要描写了游击队的战斗生活。爱国青年刘强与父亲收租时不幸被抓,刘强历经种种磨难后终于逃了出来,之后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作品展现了东北人民走向抗日道路中不同的心理状态,把东北边陲的苍凉与民风的淳朴通过一系列原始而又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现出来,人物命运曲折离奇,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作品语言含蓄、节制,有着契诃夫式的沉着、幽默和微妙。
主编推荐骆宾基,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等。本册为《骆宾基全集》中的杂文集,共收录作者发表过的杂文《新诗与诗人》《以往和未来》《富饶迷人的黑河》等70余篇,作者为抗日战争所鼓舞,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作品笔触细腻,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从中可以感怀前辈文人干预生活的勇气。
精彩内容【试读章节】
二
日头从云隙间射出几道金光。聚焦在树丛中的老鸹,忙乱地吵闹着。四散乱飞的麻雀,时时在空中闪现。是初夏的早晨,气候却像寒带一般的阴凉。
H 城街道是肃静的、冷清的。除了岗警,见不到有行人。东门附近,已不见尸体,只留着业已凝结的血泊,子母壳、刺刀把、破军帽……这一类零散的物件。
火药的残余气味和血腥,已经消淡下去。瓦屋的尖顶上,有飞鸽成群在飞动。
土黄色军用车,驶出了北门,坐在车子四周的日军,拿着上着刺刀的枪支,向外伸着。样子蛮厉而庄重。孤坐在当中的关二虎,脸变臃肿了,一块青的,一块紫的……和美术家的调色板,没有什么差别。他还在发“二虎脾气”,不住地咒骂:
“杂种操的!你老爷是杀猪手不错……专宰你们这些日本猪。……”
“叭!”
在他右颊,又加上块红印。
靠街的铺子里,有人在向街头探头探脑地偷看。稀有的激烈同雄壮气氛立即贯穿了街心。
关二虎一面暴怒地喊,一面寻求他所熟识的人。别人全都知道他:一个屠猪场的家伙,在城里整整失踪了一年。
“?!够朋友的,给弄口棺材呀!”在咒骂声里,他加上这一句。贪婪的黑眼珠,向那后面躲闪着的刘强,盯了一眼。
心儿突然一跳,刘强没敢再瞅那疾驶而过的汽车。他不但知道,而且熟悉——那是一年前的关二虎。
——是他?他这样惊疑着。
从关二虎平淡的脸,宽重的鼻子和配有浓眉的大眼上,刘强都仿佛看出了他的苦痛。刘强觉到有一小块冰,从喉头滑下去——一阵寒栗!在寒栗中他感到悲哀了。
刘强低垂着头,恍惚迷离地到了家。
“我看见关二虎了!”音调是悲楚的,“今天出‘大差’。”
“拿来烟泡没有?”刘房东不关心似的斜眨了他一下。
刘强送上烟泡,哑静地闭住嘴,他十分清楚父亲是浸沉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对于这不会有兴趣的。
“昨天活捉的关二虎吗?”酱紫麻子脸的汉子,侧卧在刘房东对面。
“不是他是谁,一个二虎头,”刘房东烧着烟泡说,“去年时节,想把你侄子‘诓’去,当救国军……早知道他不愿意活了!”
刘房东仰起头,啊呸地吐了口痰,意思是,不愿再说下去。两只枯瘪的手,熟练地捻动着烟枪上的烟泡。
烟灯的灰黄的光,映照在他鼻梁上,画出个瘦瘪的猴子脸:颜色姜黄,没一丝红润,皱纹细密地划在额前,尖削的嘴巴有稀疏的两撇胡子。
“大哥!”麻子脸透着烟枪说,“你知道,刘子章这家伙,‘不善’
哪。‘拉出去’一年多,就来攻城。”他抓了抓头皮,递过了烟枪。“天意。什么都是天意……有前清定规有后清。”刘房东斜瞅了儿子一眼。
“刘强!给我倒碗水。”是酱紫麻子脸说。刘强仿佛停止了思索,木鸡一样呆立在炕下。这时,他也不搭腔,
哑默地送上茶去,然后坐到木椅上。他感到像是生了霍乱病,心在执拗地翻滚。虽然他外形镇静。
桌上有个布包。他知道,那里面有地照、佃农租据。……地下则散乱些碎纸。他更为紊乱所迷惑了。
——杀猪老关知道救国。我呢?……我不能这么地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呀!我……这是逃避。
他又想起了县中的同学。县中是在一年前解散了,现在做了特务机关办公处。
他的臂在胸前交织着,头贴附着墙壁,眼瞳凝止了转动。安然呆坐,相同一座泥塑的神像。
——同学……都跑到救国军里去,只有我——我一个。
“蠢货!卑鄙的东西。”末后,他这样骂着自己。
淡白烟雾,从炕上飘来。一种带有诱惑性的香味,直窜入他的鼻孔。让牙齿咬着厚唇,他还在凝想。
炕上传来了话声:
“年头荒乱那也没什么……日本子这回可完了!”是麻子脸在发挥理论,“不用看‘推背图’,按着‘天干’‘地支’说,甲午年日本子和咱们开仗,那是日旺午时,人家哪能不胜呢!”
“今年你说该到哪步田地?”刘房东吐了口烟。
“今年正翻个‘个儿’。今年岁在癸酉,正正日落酉时呀!”接着,声浪抬高了点,“日本准败。”
“管他娘日落日旺呢!反正老婆孩子送回海南家去了。咱们还怕什么。”刘房东闭住了眼,仿佛在养神。
“那可不。咱们在海参崴,不是混了半辈子吗!那时候穷党和富党,闹得也够凶了吧!”又换了麻子脸的重浊音。
刘强越加厌烦了,神经仿佛在抽搐,——焦躁。心尖似乎沉着颗铅弹,莫名的痛苦,侵袭着他。
纸糊的格子窗,逐渐模糊下去,由惨淡而乌黑。他还交臂在沉思。
“连点灯也忘掉了吗?”刘房东翻了翻眼皮。
刘强方始知道黄昏突然到了,燃起煤油灯来。
“我到关小个子屋去了。”他说了句,就走出去。他知道,这时父亲是照例要睡一会儿的。
“老关。”他敲了一下隔壁的窗。
“干啥?——进来吧!”
“出来吧!”
声音还没完,关小个子闪出来。
“关二虎给毙掉了。”声音低微到听不见。
“那么,尸首呢?”刘强问。
“在‘杀人场’岔道哪,头挂在树上。”
两个人暂时沉默了。刘强的脑间,又映出白天所见的一切景象——汽车、日本兵、枪、发狂大叫的关二虎。……
“我们应该埋掉他。——是个可敬的人。”他仿佛是自语着,他记起关二虎的目光和托付。
“可是没有身子了。”关小个子眨了眨眼。
“哪去了?”这一个吃惊地问。
“谁知道,除非是鬼。”
“头也得埋。——就只一个头吧!”他决定地说,“我们为了证
明城里也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应该这么做——这么做。”
“……”关小个子迟疑地瞧着他。
“走!”是命令式的调子,“拿铁锹去!”
空气仿佛也加强了密度。
“好!……”关小个子掉转了身躯。
刘强心里燃起兴奋的火焰。一种特殊的不安,传遍每一枝神经。胸部起伏着,喘吁。
“走!”关小个子在夜色里握住他的手。并着肩头,走出大门。
黑夜的后街,冷静而宽敞。为了躲避讨厌的盘诘,他们从曲折胡同中绕着弯子。胡同狭窄,黑暗。胶底帆布鞋,轻快地拖动,如同墙角的小鼠吱吱作响。
郊野伸展开来了。远处的山岭,像是屏风,能够渺茫地辨出。周围极其沉寂。沿生在小道两旁,是些矮曲的林丛。
刘强制止紧张的情绪,闭合着嘴,用镇静压伏恐惧。
“就是这棵,你看。”关小个子向一棵树干敲了一下。
树桠上吊着的小木笼,倏地震荡起来。
夜空中散布着的小星,仿佛向幽暗的深处隐去,光力极其微弱。
刘强看不清晰那里的物件。他有些胆怯,没有作声,同时他又感到一阵辛酸。
“我上树,你掘坑吧!”关小个子卖弄着胆大,猴子一样地爬上树腰去。
刘强甩动开铁锹,在松土上挖掘,是急爽而捷速的动作。
“接着!”轻微的一声喊后,抛落下木笼来。
“关二虎……他叫我当救国军去那晚上,还跟我谈了多半夜呢。”
他走近木笼去。友谊的感情,驱逐了他心中的畏缩。
“咱们中学那帮,都和他挺好。因为他在救国军里,非常老实……”
关小个子的脚跟沾住了地皮。
“嗳!”刘强惊愕地说,“头怎么没有了呢?”
他掷下铁锹,胆壮地,从木笼的缝隙,伸入手指去。他触到——
似乎是一个信封样的东西。用绳子缚在木柱上,而木笼失去了底。
“唰唰!”远处传来了脚步响。
“快……走。”关小个子捎着铁锹,慌促地扯了扯刘强。
刘强又惊惧又愤恨,一直跑到了家。
“真险!”关小个子吐了口气。
“……没拿回那信……真是……”
“太险了!要不,我真也想跑到救国军里去混他一辈子。”
“哽!这,你也未免太……”刘强没说下去。和他挥了挥手,走进屋子里去。
刘房东还在睡着。酱紫脸的麻子,惺忪地伸了伸腰。
“呵!这一觉睡得……”他站了起来。
“收拾收拾那没利索的东西吧!不要紧了。今晚可得睡个安稳觉了。”
“回城里吗?大叔。”刘强看着他戴上了瓜皮帽。
“呵!回去。”麻子走着出去。
夜间的凉风,吹散他体中的疲劳。他倒背着两手,摆着魁梧的身材,缓慢地走去。
“KuIa!”
(吆喝意)北门的“加岗”日兵,突然将枪头伸到他胸前,刺刀尖在心窝间,闪着逼胁的光。
他惊讶地举直了两手,向着天空。
“你的叫什么名斯?”日兵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
“我!……”他的嘴角颤抖了。
“他是王四麻子。”一个“满”警说。表示自己挺认识他。
“什么麻斯!——妈个巧比吧!……你的好人?”
“他是好……”警士又想说下去。
“‘KuIa !’你……”日兵逼视了一下“满”警。
“好人,我的。我是凌云阁……经理。”王四麻子有些畏缩。
“‘满洲国’的好好的?”一只大手,在他腰部摸索。
“大大的好。”
“去!”
王四麻子头也不敢回地走开,但心里却想:——日落酉时呀!……日……落……在一个拐角处,黑暗掩没了他的身体。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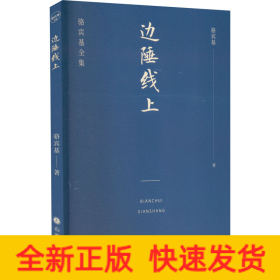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