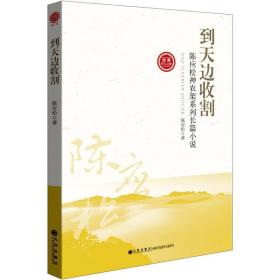
到天边收割
¥ 9 3.8折 ¥ 24 九五品
仅1件
北京西城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陈应松 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8
版次1
印数1千册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4-04-2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陈应松 著
-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2-08
- 版次 1
- ISBN 9787510815911
- 定价 24.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192页
- 字数 207千字
- 丛书 世界华人文库.第2辑
- 【内容简介】
- 《到天边收割》讲述的是一个山区孩子寻找母亲的故事。性格乖戾内向的山区青年金贵,十分想念被父亲的家庭暴力打走与他人私奔的母亲,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历程。可是当找到发财的母亲时,母亲因为金贵长大后酷像其父,多年前恐怖的记忆被唤醒,坚决不认这个儿子。用几千块钱打发了金贵二十多年来渴望的母爱和温情,深深伤害了他。在打工的日子里又因遭人诬陷,挨打而产生了报复心理,于是杀死了仇人,开始了风雪之中的逃亡之路。在老家神农架被追捕跳崖之后,又被女友救活,但最终被女友的父亲举报。在最后时刻,金贵提出想见母亲一面……这部长篇小说文本奇异诡谲,语言浓稠喷薄,以强烈的象征和魔幻色彩,表现了高寒山区的青年为寻求梦想而展开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困境,揭开今日中国种种严重倾斜的社会现实。
- 【作者简介】
- 陈应松,祖籍江西余干,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巨兽》、《陈应松民生小说选》、《陈应松小说》、《陈应松作品精选》、《呆头呆脑的春天》、《暗杀者的后代》、《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车》,随笔集《灵魂是囚不住的》、《所谓故乡》、《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中国瓷器》等40多部,《陈应松文集》6卷。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选刊》小说奖、全国环境文学奖、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人民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湖北文学奖,曾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作品翻译成英、俄、日等文字到国外,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 【目录】
-
娃儿乖,你快睡,
隔山隔水自己回,
虫蛇蚂蚁你莫怕,
你的护身有妈妈……
——神农架民歌
一
这一年,就是春上天气骚怪的这一年,五月,山上的冰还没有融化的意思。冰像铁打的围桶,冒着残忍的、坚定的蓝光。这一天,下了一场冻雨,把我爹余大滚子隔在了山上。那场雨可真是无情,下在身上,立马让衣裳变成了硬壳壳;下在脸上,一抹,全是冰渣子,就好像下的是碎玻璃;我爹正在山上挖竹笋--竹笋埋在山缝里,扎得很深,还没出头。他挖着竹笋,雨就下来了。我爹余大滚子一下子从火热的身子变成了个冰疙瘩,心脏停止了跳动,就跑呀跑啊,跑到一个岩屋(洞),就想,我今天必死无疑了。可走进去,却闻见一股敬佛的香味,就像进了寺庙,就像有菩萨住在里面一样。他知道是什么--好久没闻见这样的香味了,是烧过香柏的香味;香柏就像神仙家的火塘。我爹余大滚子就打燃火机,一照,果真有些香柏的碎屑。不是有些,而是很多,越往里走越多,还有一堆熄灭了的余灰。
“好啊,有人在山上偷香柏!”那个偷树人竟敢把国家二级保护树木砍了,在这山洞里砍成门方偷运出去,胆真大啊!--香柏砍了就去熬一种香精油,然后走私偷运到美国,去制一种名贵的香水。这些年打击了一批又一批,可还是有人铤而走险,胆大妄为。
关于香柏的来历我爹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他要把火燃起来,要救命,救自己的命。他就去烧那香柏的木屑。就算香柏是刚刚砍死的,可香柏含满了油脂,几下鼓捣就燃了。我爹看着火升起来了,不管是香火是臭火,只要能救命,就是好火。我爹看见了火,就像几十年前的穷人看见了共产党,温暖得呻吟起来:哎呀,哎呀!哦嗬,哦嗬!……这时候,心脏恢复了跳动,血气蹿上了脸庞,从一个死鬼变成了人类,从一个冻得像根树棍子的人变成了一条软绵绵的大虫。望着亲爱的火,火的形状五花八门,既不像人,也不像牲畜;既不像我们望粮峡谷的某一处村庄,也不像田地、田地里的庄稼。可是--
我爹坚称那一天他在火里看见了菩萨,看见的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两个都是女菩萨;两个菩萨瓜子脸,小鼻梁,樱桃小嘴糯米牙,柿饼发髻,脖子白溜溜的,手指细尖尖的。
我爹在暖暖的火堆里看见了望粮山人从未见过的菩萨。他先是将衣裳脱下来烤干爽了,发白的洋布褂子终于又露出了本色,泥巴一块一块因干脆后往下掉,那火就像无数只有形无形的手,直往他身子上摸,摸脸,摸头发,摸胸前,摸后背;那火的手加了那香味--檀香味或是别的汹涌香味,异常干净浓烈柔软的香味,就像一阵阵女人的体香,一浪一浪撩拨他。
我爹可能是想起了被他打跑的我妈吧?我妈的一切,在家的一切,在家操持的一切:我妈浆洗的衣裳,我妈做好的饭菜,我妈在深夜的油灯下剁猪草、缝补、烙粑粑或者推磨,甚至走来走去的一切。或是,我爹他可能想到了他的母亲,他死去的母亲,母亲的暖怀,母亲在世的一切。
总之吧,我爹烤着香柏火,竟感动得流下泪来。香柏可是个好东西,我父亲有一种恍恍惚惚重回到子宫的感觉,多好啊,如果--如果我死后睡在一口香柏棺材里,那可就是享福啊。棺材是另一个母亲的子宫,是大地母亲的子宫。为了接受这个香喷喷的菩萨的爱抚,这口棺材,我爹在五十岁出头时,开始谋划自己的归宿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在算计自己的死期。这多么可怕,这个年纪就忽然想到了死亡?
如果你来到我们山区,你就知道一个半老头子想到死亡是很正常的,就是十几岁的少年,经常思考死亡也不是耸人听闻。道理很简单:他们与死亡离得很近。这一点与城里有很大的不同。城里人死后睡的是公墓,与活着的人离得很远,平时看到的全是活灵活现、朝气蓬勃、被广告社会包装得华丽、美艳、万寿无疆的生活场景。确实如此,在城里,人仿佛是不死的金刚,可以活万万年的。假如身边有人死了--那也是在医院死了,就被运到很远很远的公墓里,你永远永远也见不着他了。有时候一想,这个人仿佛是出了长差,某一天还可以回来的--城市的死亡造成这样一种温馨的错觉。可是我们山里呢?一个人死了,我们看着他死去,看着他入殓,看着他埋葬,看着他变成一堆黄土,上面插满了魂幡,春天又插满春条--又叫清明吊子;到了除夕,上面会点亮一盏自制的油灯--这叫送亮。这个人,这个人啊,就在我们身边,变成鬼了--鬼所生活的一切,都每天在我们眼前晃动。那个坟啊,我们出坡干活,放羊牧牛,总是能看见他,他没有走远,死了也还赖在这里,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这就会使活着的人,无论老少都会自然而然想到:这也是我们的未来和归宿啊!这种念头十分强烈。但也没哪个怕死,没有恐惧,甚至连稍微正经点的伤感也没有。为啥?阴间与阳间还是不同的。阴间什么都没有,只会有长眠不醒,没有享受。而阳世间有女人,有温暖,有亲情,可以来回地走动,看日落日出;看鸡上架,狗连裆,看妇人哺乳,少女唱歌跳舞;看小娃出生,老人过世,起新屋,娶媳妇,庆丰收,过大年……
另外,我爹想到了死亡,是因为生活艰难单调,无尽的劳累和饥寒。山里的日子难过啊,爹拖着姐姐和我,把我们拖大了。被他打跑的老婆归来遥遥无期,活着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无望的缠绵。渴望死后的奢华,成了他生命的一个新的兴奋点。于是,这位叫余大滚子的中年人,决定进山伐香柏。
就在他进山的前两天,出现了一件让人闻之变色的事情:
一个从陕西那边过来的采药人,说他在望粮山顶上,看到了天边有一片麦子。
陕西人是外地人,并不懂得当地的禁忌,胡口打哇哇乱说。可谁都没有给他讲这一片天边的麦子曾多次在咱们山上出现过,他咋一来就恰恰瞧见了呢?瞧见了不说,还说出来了。
而这件事是不能说的!
村里的苟家老五在很早前说他望见了那片麦子,后来就失踪了,那一年,雷劈死了村里的两牛两人;王家屋场的一个二丫,割猪草上山也说看见了那片麦子,焦黄焦黄的,还香气扑鼻呢,三天后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她,不知道被什么野物奸了(有说是大青猴),端坐在那儿,眼睛闪闪发光,下身流血,可惜已经死了。那一年,下黑雪,黑豆大一颗一颗的冰子儿,把庄稼全糟蹋了;七十年代一个叫黄春的看见那片麦子后,拿着镰刀就出发了,几年以后回来,已是疯疯癫癫,挥舞着镰刀到处割人的头,后被乱棍打死。那一年最惨,泥石流一夜间埋了七八户人家。今年若有人说看见了那片麦子,我的天,还不知会出什么怪事儿呢!
什么鸡巴麦子呀,哪来的麦子?冰还没化呢,山上像个大石膏头盔罩着,麦子还在冰雪下喘息。我爹余大滚子挺身而出,率领十来个村人,捉住了在山上乱说的陕西人,一顿痛打,打断了他几根肋骨,将他撵出了望粮山。可怜的陕西人疼得吼秦腔,大声说:
“鹅(我)没胡说,鹅(我)讲的全是真话!……”
余大滚子我爹用他的鹰爪手指着西南方向,对十多个刚刚与他一起施过暴的乡亲说:
“你们看好了,哪有什么蛋球麦子?没有,是不是没有呀?”
他启发他们说。那些人分明听见我爹的声音都变了,一双被漫长冬天的火塘熏得如鸡屁眼的眼睛压根儿就不敢往自己手指的天边看。大家也都不敢看,只好顺驴下坡说: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第二天,就是小满。
早晨天气还好好的,就是有点闷,屋子里到处都拧得出水来,水缸上淌着汗,被子潮漉漉的。最早叫开的是乌鸫,只有一只,变幻着七八种腔调,大约也就是在四点多钟。我睁开眼一看,爹在堂屋里晃动。在我的意识中,爹好像半夜就起床了,并在火塘上烤着他的火烧粑粑;火烧粑粑是放在火剪上烤的,翻来覆去,两面就烤得焦黄了;也有烤得糊巴烂灸的。被一阵阵新鲜的火烧粑粑的香味熏醒,又听见了磨刀声。是磨斧头。其实,爹要到深山里砍香柏的计划已经先行透露了,只是不知道他是真是假,何日成行。爹说:“老啦,不行啦。”爹果真要去了,要为自己备一副好寿材。可那天早晨,闻到了从火烧粑粑中爹要出远门的信息,还恍然觉得爹是决定了要去寻娘去的。有时候--每当从梦中醒来,看到厨房里有人操作的身影和响动,我就以为那是娘。这种幻觉每次都会重现,并且愈来愈强烈。
……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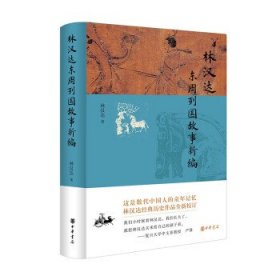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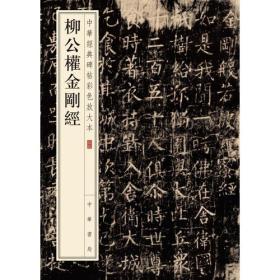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