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宴之前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8.98 4.9折 ¥ 38.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英)毛姆 著;罗长利 译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ISBN9787550294554
出版时间2017-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8.8元
货号1201530155
上书时间2024-11-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毛姆,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出生于法国巴黎。
十岁时,父母已相继去世,遂被送往英国肯特郡,与叔父一起生活。1892年起,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学习医科,同年,发表了首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广受好评,遂弃医从文。靠前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法国红十字会,后受英国军方指派,在瑞士和俄国开展情报工作。曾多次赴南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旅行,许多小说因此颇具异域情调。晚年撰写了许多回忆录和文学批评,至八十五岁时方才搁笔。
目录
万事通先生
教堂司事
患难之交
午餐
红毛
逃脱
珍珠项链
诺言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格拉斯哥的来客
赴宴之前
吞食魔果的人
内容摘要
《赴宴之前:毛姆小说精选集》是一本短篇小说集,精选12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毛姆不善言词,喜欢静静在旁观察人。
他能看进一个人的眼睛里、心里,看穿你的不安、你的虚伪、你的小家子气、你的贪婪。
惊人的是,你读着这些看似在写他人的故事时,内心却频频为之震惊……
《红毛》,三十年后的岛上月亮,是否还如三十年前一般明亮?
《赴宴之前》,女儿从婆罗洲归来,背后隐藏着丈夫堕落、酗酒、自尽的秘密
《午餐》,穷作家与慕名而至的粉丝共进午餐,上演囊中羞涩的内心小剧场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我现在热爱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这是不是一种堕落?
……
整个天堂的水几乎要被倒干,信仰会更坚强,还是干涸?
精彩内容
毛姆是一个聪明的作家,这几乎是喜爱毛姆的读者的共识。
有些作家凭借聪明去显露锋芒,也在无形中制造出与读者的距离,毛姆不会。相比于某种潜心将作品打磨得精致、晦涩的聪明,毛姆其实更像一个生意人。小说是他的一爿店面,他追求的是一种商品化的作品质量,目的是更好地讨得顾客(读者)的欢心。
毛姆是站在读者身边的,他深知读者的喜恶,是一个精明绝伦的故事商。很少有作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些是因为与毛姆的创作追求迥异,追求相仿的作者却往往缺少毛姆一般的天赋。
在毛姆的短篇小说中,他对读者情绪的把控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开篇的两三页,读者便可接近核心的悬念——那个故事中心的黑洞。当然,这仅是浅浅的一瞥。毛姆在设置悬念时,有一丝“润物细无声”的味道,他不会大动干戈地点燃读者的好奇心,只通过描写人物的一个动作、一个小心态,便在读者的心中种下了对悬念的好奇。《赴宴之前》中米莉森特在丈夫离世后从婆罗洲归家的反常,《红毛》中船长登岛前寻找礁石口子的焦虑,《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爱德华后期信件中突然出现的幽默和轻佻……
毛姆像是一位舞台装置家,手中提着一根控制幕布的绳索,他的笔法习惯于一点点扯起绳子,让幕布遮盖的物品渐渐显露在观众的视野中。每一下扯动之前,他会给予读者暗示,供读者猜谜,让他们对接下来展露的东西产生某种预知。阅读毛姆的读者总是处在预知印证前的紧张和预知印证后的快慰之中。
当然,亲近读者的行为,并不代表毛姆是一个二流作家或通俗作者。毛姆在熟稔地掌握小说之“惊心动魄”的同时,文本核心却是一种深刻的嘲讽与深沉的慈悲。
在毛姆与读者之间,有一扇“门”,他总是站在门外,说出一些嘲讽的言语。他的性格不喜欢将人性与命运主题中的无奈与辛酸以更加沉痛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扇门给了毛姆空间。
毛姆不是振臂高呼的意见领袖,也不是温暖治愈的鸡汤先生,他是冷静的,是避免情感混沌的最清醒的洞察者。他在门外,对无奈的困境与悲剧施以嘲讽和揶揄。在他的妙笔之下,这些宏大的主题忽然变得市井起来,轻快起来。只有看得最深的一双眼,才能将这些主题的“大”利落地切分进生活的“小”,在鲜活流畅的故事与玩世不恭的嘲讽中,显现出深刻洞见的锋芒。
毛姆对生活的爱与慈悲,我们通过阅读他的小说便能体会,他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作者,因此他的冷嘲热讽并不会显得残酷或者下作。
毛姆的小说内核,其实是用棉布擦拭刀子。刀柄上华丽的巴洛克式的装饰是毛姆所喜的生活的喧嚣,而棉布擦过锋刃的温和与锐利,才是毛姆文字深处所求的慈悲与深刻。
罗长利
万事通先生
我在见到马克斯?凯兰达之前,就有些不喜欢他。
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远洋客轮的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很难订到客舱,你不得不接受代理提供给你的选择,根本就不能指望有间自己的单人舱。我很高兴订到了一间双人舱,但当我听到同舱旅伴的名字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这个名字令我窒息,一想到将和凯兰达一同度过十四天(从旧金山到横滨),就觉得这会是一次多么糟糕的旅程。我反感这个名字,哪怕同舱的人叫史密斯或布朗都会好些。
当我登上船进入客舱,发现凯兰达先生满是标签的大包小包已被放在床下,那些蠢大的衣柜箱子和外观难看的手提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一进卫生间,我发现他真是个科蒂的优秀赞助商,脸盆架上摆满了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那支乌木的牙刷上还印着镀金的凯兰达名字的缩写。
我一点都不喜欢凯兰达。
我来到吸烟室,叫了一副纸牌,刚要玩的时候,一个男人来到我面前并跟我打招呼。
“我是凯兰达先生。”他说道,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并坐了下来。
“噢,是的,我想我们同住一个舱室。”
“我认为自己很走运,因为我听说你是英国人。能在海外遇到同胞,令人非常开心,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眨了眨眼睛。
“你是英国人?”我有些不得体地问道。
“当然,你不会认为我是个美国人吧?我是个标准的英国人。”为了证明,他掏出护照给我看。
英国有很多奇怪的人。凯兰达先生个子很矮,体魄健壮,皮肤黝黑,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富有肉感的大鹰钩鼻子上方有一双光泽水润的眼睛,一头时尚的卷曲黑发。他在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还伴着丰富的手势。我又仔细查看了他的护照,他确实出生在英格兰,而不是其他天空比英格兰更加湛蓝的地方。
“你想喝点什么?”他问我。
我疑惑地望着他。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绝对没有酒的,当我不渴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要哪种,我不喜欢姜汁汽水或柠檬汽水。但凯兰达狡黠地对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水和干马提尼酒都有,只要你说句话。”
之后,他从两个后裤兜里各掏出一个酒瓶,并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选择了干马提尼酒,让服务员拿来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非常好的鸡尾酒。”我说。
“嗯,我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酒,如果船上你还有朋友的话,让他们一起来分享吧。”
凯兰达先生非常健谈,他谈到了纽约、旧金山,还与我讨论了戏剧、绘画和政治。
他是非常爱国的。
英国国旗是面令人肃然起敬的旗帜,但当它被来自亚历山大或贝鲁特这类人挥舞的时候,不禁使我生出一种它有失威严的感觉。
凯兰达先生很自来熟。
我自然也不喜欢总是端着一副绅士般的架子拿腔作调,但我还是比较习惯一个接近陌生的人在称呼我时,应该在我的名字前加“先生”,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我确定凯兰达先生并没有这样礼貌地称呼过我。我不喜欢凯兰达先生。
当他坐下来时,我把纸牌放到了一边,但是现在,我只想赶紧结束持续了足够久的第一次交谈,我又拿起纸牌继续玩了起来。
“把3放4上。”凯兰达先生说。
当你自己专心玩牌的时候,再没有什么比别人在一边给你指手画脚更加令人懊恼的事了。
“要通了,要通了,”他呼叫起来,“把10放在J上。”
我满心愤懑地耐着性子玩完了这局。
然后他一把将牌抓了过去。
“你喜欢用纸牌变魔术吗?”
“不,我反感纸牌魔术。”我回答。
“好吧,我马上给你演示一下。”
他要我记住三张牌,但我说我打算去餐厅找个座位坐下来。
“哦,没关系,”他说,“我已经给你订座位了,我想我们既然住同舱,那也应该同桌用餐。”
我不喜欢凯兰达先生。
我每天都要跟他住在同一间舱室,与他在一个桌上共用三餐,不仅如此,不论我到甲板上散步还是去哪里,都得与他一起,根本无法摆脱。而且他永远不会意识到与他同行是会令人不愉快的,他以为你如他一样开心。这要是在你自己家里的话,你肯定会一脚把他踢下楼或当面狠狠地摔门把他关在外面,让他知道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很善于交往,没出三天就几乎认识了船上每个人。他什么事都做过:他管理过清洁工作,主持过拍卖,为运动奖项筹过资,组织过掷环和高尔夫球比赛,举办过音乐会,安排过化装舞会。任何地方都有他,他无所不做,自然也成为这船上最招人恨的人。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当着他面也这样叫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赞誉。
他非常健谈,尤其在吃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绘声绘色地高谈阔论,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并且他还能言善辩,他感觉自己比世上任何人懂得都多。如果你提出了与他不同的观点,都会挫伤他那不可一世的自尊心,因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屈从于你,他坚信他对世间一切事物的判断正确、理解透彻,错误思维永远不属于他,为此他会坚持不懈地跟你争论,哪怕是个十分无聊的话题,直到最终把你说服方可罢休。船上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家伙。
一次,我们与一位医生同桌,凯兰达先生一如过去天南海北地说着,医生显得很懒散,而我也一副漠不关心、无所事事的样子。只是旁边那桌被称为拉姆齐的坐不住了,他跟凯兰达一样固执己见,并且非常鄙视自以为是的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激烈辩论。
拉姆齐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他来自美国的中西部,这家伙是个大块头,他一身的赘肉把衣服撑得紧紧的。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他的妻子独自回纽约在家里待了一年。拉姆齐太太俏丽娇巧,十分讨人喜欢,举止得体大方,谈吐幽默。虽说领事馆的工资微薄,她的着装总是很简朴,但她懂得如何打扮自己,她总能穿出独具特色、非同一般的效果。若不是她超凡脱俗的优雅特质和独有的女人魅力,我也不会特别关注她,从她端庄的外表上你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总觉得有朵鲜花绽放在她的衣服上一般。
一天晚上,我们一同用餐时,无意间谈到了珍珠。那时报纸上大量报道了精明的日本人正进行人工养殖珍珠,用于镶嵌。医生说这将无可避免地降低珍珠的价值,如今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将来接近可以以假乱真。凯兰达先生习惯性地奔赴新话题,他讲了很多有关珍珠方面的知识。我不信拉姆齐对此了解更多,但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反驳的机会。只过了五分钟的时间,两人便进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以前我见过凯兰达激动争辩的状态,但从来没见过像今天这样如此亢奋。最后,拉姆齐说了句什么话刺痛了凯兰达先生,他敲着桌子喊道:
“好吧,关于珍珠的问题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正要到日本去谈珍珠生意,我很在行,并且任何一个行家都会认可我对珍珠的认知。我知道所有世界上最昂贵的珍珠,而没价值的也无须了解。”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个新闻,凯兰达先生虽说话很密,但他从来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是去做生意的,大家只模糊地知道他是为了一些商业差事去日本。他得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那些人工养殖珍珠绝逃不过像我这样的行家的眼睛,只需瞟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那条项链说,“拉姆齐夫人,相信我,你戴着的这条珍珠项链的价值将来绝对不会比今天降一分。”
拉姆齐太太那张端庄的脸微微发红,把项链塞到她的衣服里面。
拉姆齐探过身子,他向我们使了个眼色,带着几分讥讽的微笑。
“拉姆齐太太的珍珠项链非常漂亮,对吗?”
“对,一见面时我就注意到了。”凯兰达答道,“哎呀,当时我还在心想,这些珍珠都是真的!”
“当然,这不是我买的。你觉得它值多少钱?我很想知道。”
“噢,在商场里买要一万五千美元,但如果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买的话,三万美元才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听到事实你会惊讶的,这是拉姆齐太太离开纽约前一天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总共花了十八美元。”
凯兰达先生的脸一下红了。
“胡说,这不仅是真的珍珠,而且还是我所见到的这种规格中品相优选的。”
“你敢打赌吗?这是假的,我用一百美元跟你赌。”
“同意。”
“噢,埃尔默,你不能拿你确定的事跟人打赌。”拉姆齐太太的唇边带着微笑,语气温和地说。
“我不能?如果有这样轻易捡钱的机会,傻瓜才不捡。”
“但怎么能证明它是假的?”她接着说,“仅仅是我说的跟凯兰达先生说的不一样而已。”
“让我看看项链,如果它是假的我立刻就告诉你,我宁可失去一百美元。”凯兰达说道。
“摘下来,亲爱的,给这位先生看看,这是他自愿的。”
拉姆齐夫人犹豫片刻,她将手放在项链的钩子上。
“我不能摘下它,”她说,“凯兰达先生,你就相信我的话吧。”
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想不出要说什么。
拉姆齐跳了起来。
“我给你摘。”
他把项链递给凯兰达先生。凯兰达先生从兜里掏出放大镜仔细看了起来,胜利的微笑在他那黝黑油亮的脸上慢慢铺展开来。
他把项链还给拉姆齐太太,正打算宣布结果,忽然瞥见拉姆齐太太面无血色,看上去仿佛就要晕倒,她死死地盯着凯兰达,眼神显得无比惊慌,似乎在不顾一切地向他祈求。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切拉姆齐竟没发现。
凯兰达先生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你几乎能看到他内心的纠结,他在努力说服自己。
“我输了,”他说,“这的确是件非常好的仿制品,其实,我用放大镜已经看出是假的了,我想也就值十八美元。”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百美元,二话没说就递给了拉姆齐。
“我年轻的朋友,这就算是个教训吧,以后别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接过钱。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迅速在船上传开了,凯兰达先生那晚不得不忍受别人对他的嘲笑。这件事也确实是一个笑话,因为“万事通先生”被拆穿了。拉姆齐太太推说头痛,回了自己的特等舱。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后正在刮胡子,凯兰达躺在床上抽烟。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刺啦声,只见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向外看,门外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看见是写给凯兰达先生的,信上的字是印刷体,我把信递给他。
“谁写的信?”他把信打开,“噢!”
他拆开信封,那不是信,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他看着我,脸红了起来。
他把信封撕成碎片交给我,说:“你介意帮我从舷窗扔出去吗?”
我按他说的做了,然后微笑地看着他。
“没人喜欢被人看成傻瓜。”他说。
“珍珠是真的吗?”
“如果我有一个如此娇妻,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一年,而我住在神户。”他说。
此时,我好像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他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将一百美元放了进去。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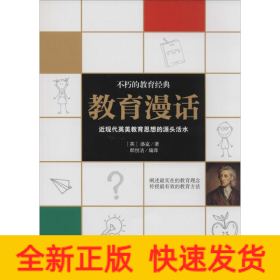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