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小说集(上下)/卡尔维诺经典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3.56 4.4折 ¥ 98 全新
库存10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2261
出版时间2012-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98元
货号1201907739
上书时间2024-06-1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当代拥有有世界影响的作家。1923年生于古巴,1985年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卡尔维诺从事文学创作40年,一直尝试着用各种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手法、奇特的角度构造超乎想象的、富有浓厚童话意味的故事,深为当代作家推崇,并给他们带来深刻影响。“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等达到惊人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意大利童话》优选限度地保持了意大利民间口头故事的原貌,再现了意大利“民族记忆”之深厚积淀。《美国讲稿》是卡尔维诺对自己近40年小说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系统回顾和理论上的总结与阐发。他的作品以特有的方式反映了时代,更超越了时代。
目录
序言
第一卷 艰难的田园诗
大鱼,小鱼(1950)
一个下午,亚当(1947)
装螃蟹的船(1947)
被施了魔的花园(1948)
人们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事(1950)
好游戏玩不长(1952)
去指挥部(1945)
乌鸦最后来(1946)
在路上的害怕(1946)
雷区(1946)
三个人中的一个仍活着(1947)
牲口林(1948)
不可信的村庄(1953)
一家糕点店的盗窃案(1946)
像狗一样睡觉(1947)
你这样下去就不错(1947)
美元和老妓女(1947)
一张过渡床(1949)
猫和警察(1948)
城市里的蘑菇(1952)
市政府的鸽子(1952)
饭盒(1952)
黄蜂疗法(1953)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1953)
好空气(1953)
毒兔子(1954)
和奶牛们的旅行(1954)
长椅(1955)
月亮与Gnac(1956)
车间里的母鸡(1954)
数字之夜(1958)
帕乌拉提姆太太(1958)
第二卷 艰难的记忆
荒地上的男人(1946)
巴尼亚思科兄弟(1946)
主人的眼睛(1947)
懒汉儿子(1948)
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1948)
进入战争(1953)
青年先锋队员在芒通(1953)
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1953)
第三卷 艰难的爱情
一个士兵的奇遇(1949)
一个海水浴者的奇遇(1951)
一个职员的奇遇(1953)
一个近视眼的奇遇(1958)
一个读者的奇遇(1958)
一个妻子的奇遇(1958)
一个旅客的奇遇(1957)
一对夫妻的奇遇(1958)
一个诗人的奇遇(1958)
第四卷 艰难的生活
阿根廷蚂蚁(1952)
房产投机(1957)
烟云(1958)
内容摘要
一首艰难的田园诗,一段艰难的记忆,一份艰难的爱情,一种艰难的生活。在这四卷《短篇小说集》里,卡尔维诺把贫瘠、困窘、苦恼、无法沟通的爱这些艰难沉重的东西,都写成了普通人的瞬间,变成了“一种味道、一道闪光、一声吱嘎响、一种生命的调子”。在小小的快乐、扭捏的困境里,在最无计可施的时候,小说中的人物怀着自欺欺人的侥幸,带着“不得不如此也就算了”的无奈接受了现实状况。
主编推荐
卡尔维诺因为听厌了人们总说他写的东西“容易”“愉悦”,成心写一些 “艰难”的东西。 这些“田园诗”“记忆”“爱情”“生活”轻盈短小,却让人体味到困窘、苦恼、无法沟通的艰难和沉重。
精彩内容
第一版《短篇小说集》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通过对构成本书的这四卷“书”的整理,卡尔维诺在这里收集了前一部小说集《乌鸦最后来》(1949)里的几乎所有的小说、《进入战争》(1954)的三个自传性故事、马科瓦尔多的前十个故事、“艰难的爱”系列中的九次奇遇、杂志上发表过的三部短小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直至此前还未收录成册的零散短篇小说,并把它们归入这本书的四“卷”里。
为介绍这一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此再附上卡尔维诺一次讲话的文字,其中的一部分是未发表过的,这是他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佛罗伦萨的维耶瑟文化中心所做的一次讲座,该文曾被一九五九年一至四月号的《马尔西亚》杂志以“我没写过的短篇小说”的标题刊登过(除前四段外)。
我没写过的短篇小说
对于自己的作品,本是什么都无需说的。让它们自己说,就够了。把若干短篇小说凑成一本书,给它们理个顺序,再归个类,在它们的排列中找出个意义,寻出标题和一些总括性的定义,就已经是对原作品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强是弱)外加了另一种声音,一种解释性的不同意图,就已经是对读者的自由使用了暴力,就已经是去完成那些属于评论家职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则已地超出了作者的任务。妙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作者抢了评论家的活,如果作者想定义自己的作品,评论一点都不反对;人们本来指望着评论会赶紧提出其他的阅读指导、其他的定义、其他的作品和作品间的关系,来加以反驳,然而评论却接受了它被给予的第一个借口,仅仅满足于解述作者的痕迹。比如:在我把我的这本书分成的所有四个部分的标题中,都用上了“艰难的”这个形容词。为什么?因为我早就听倦了人们对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说“容易”,说“愉悦”,说“愉悦的容易”,说“容易的愉悦”。于是,我就到处写下了“艰难的”这个到目前为止人们感觉与我的文章相去甚远的形容词,这种性质,这种生活的意义于我曾显得遥不可及。好吧:行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不眨眼地一致主张,艰难的意义一直就是我小说主要和永恒的特点。我本该为此而高兴,但我存了个疑,如果在这些标题中,我不是用“艰难的”这个形容词,而是用了“容易的”这个形容词,是不是什么都不会改变,所有人仍会同样地接近赞同。于是,我就留在了原地;我对于世界,对于与世界关系的犹疑,如果一切都是艰难的,不管是使人强健的或是使人丧失能力的艰难,又或一切都是容易的,不管是热情的或是失望的容易,我那个犹疑都没有解决,我这种对于世间万象缘由的普遍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而这些,都是徒劳的,需要知道如何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应该是永远无需对自己的作品说些什么的,不能比它们被数出来的词多说一个词,也不能比它们必不可少的词多说一个词,这些词是一个也不能添,一个也不能减。这些东西早在隐逸派时代就已明晓于世了。蒙塔莱的Occasioni里的注释,你们还记得吗?从孩童时候起,每读完一首貌似十分难懂的诗,我就会跑去看书本末尾那少许几页的注释能否提供什么帮助,什么鼓励。然而没有,都是一些吝啬得叫人失望的注释,简洁,患了失语症一般,对那些我们期待的东西是什么都不说,但这正是教给了我们正确的一课,这里也是如此:你要自己去解决它,也许这是我们学会的优选一课。
现在我们属于一个不同文学的时代,现在的文学更轻率,更倾向于评论文学,谈文学,把文学当作一种话题。
可文学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关世界现实,有关隐秘规律、图案、生命节奏的话题,一个从也没有结束过的话题,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感到有必要反复重新提起的话题,因为我们与现实产生联系的方式在不断改变。
你们将要好心地加以关注的这本小说书,只是想成为一种证据,证明在那些于一九四五年开始自己文学实验的人中,他们中的一个,从其时到如今,是如何追随那个去捕捉一种味道、一道闪光、一声吱嘎响、一种生命的调子的幻想的。那是些对于世界的伟大哲学解释并不适合的时代,同样对于伟大的小说也是不适合的;我们尝试过在好比蚂蚁一只眼睛的无数刻面中,在人们企图据以重建整座庞大恐龙骨架的化石脊柱中,去捕捉宇宙的秘密。
当我刚开始的时候,写作是容易的。在词语和东西之间,在事实的力量和风格之间,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是没有差别的。生活在用我们周边的故事迅速繁殖。我和其他人写的很多小说,都是在游击队员的露营地中,在一战后的三等车厢里的tales of hearsay,听别人讲出来的故事。那时,有种要诉说,也要选择那些诉说方式和形态的集体驱动力。当然,我再也写不出来当时是怎么样的了,不只是因为我那时还年轻,所以事情于我看来都很容易。那种允许用相当有限的方式来表现事实的张力,是一种历史的张力,是早在个人的写作艺术之前,就存在于事物和时间之中的。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一种易逝的财产,我不久就能将其掠劫一空、消耗尽的财产。那个时候,我仍能相信这种财富是与“经验”相符的:游击队时期的经历被剥削完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滋补我们的叙述?曾经有一个学派,也就是我们后来定义为叙事学的美国学派,提出一种能肯定获得成功的方法:丰富经验,旅行,亲临正在发生动荡事件的地方;那么写作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在我开始写作的年代里,这种思维形态正值其巅峰。那么,既然战争已然结束,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还想写作的话?追随已经迫在眉睫的新冲突爆发,去西西里参军、和朱里阿诺的独立主义分子混在一起,或者是去巴勒斯坦跟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作战?可对于既不是西西里人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我们,那只会是种纯粹的冒险。而在全世界乱转的毫无理由的冒险,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如果这我不是自己明白的,还有切萨雷·帕维泽反复对我们说,只有从那些不带着文学动机而经历的东西中,才能生出诗来,只有那拥有真正根系的地方,才能冒出树叶与果实。
另一条路是求助于现实的宝藏,这种现实是由自己的地域,由地方的、通俗的、取之不竭的场景构成的:正是在那些年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有回归地区唯真主义的明显倾向。但地区唯真主义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地方主义永远要晚于历史一拍,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与历史同步的东西,但同时也要从自己的根源出发,立足于一片土地,拥有一种经历。
我曾参与的政治一派,企图在文学中描写出一种人民,这种描写会把纪实性的客观与积极情绪的富足和说教的热情混淆起来。但是社会现实主义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在革命运动中,我对一种早已众所周知的道德的解释从来也不曾感过兴趣,也不会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那种历史逻辑的荒谬机制。我在政治报刊上登载的小说在慢慢地失去现实的体积,但增添了叙述的线性成分,增添了能够获得一致的对称,增添了像寓言或童话般精准的几何学,而这正好发生在——您请注意好了——其时的政治理念最能来滋养我那些小说的时候。直到如今,我仍以为,如果不是想像的,讽刺的,乌托邦的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文学,我仍以为,“现实主义”经常携带着一种不信任历史进程的因素,携带着一种对过往的偏爱,这种偏爱但愿是高贵地反动的,并且即使在保守这个词的最积极的意义上也是保守的。
所以,是那种加强小说中理性的和故意的因素,加强秩序与几何学的需要,把我推向童话的。童话和想像叙述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一条任性与简单的路途:如果太过偏向纯粹的超现实无理由,可就糟了,如果不得不遵循一种局限于体现狭义道德历史的准则,那也很糟。为了避免成为一场纸做的舞台背景,想像必须要充满了回忆、必要性,总之,充满了现实性。
现实,于是——在我的最早的那些短篇小说的时期,现实好像如此简单和直接——就越来越成为一条不可捉摸的白鲸。如果我想抓住它的骨架,则必须要感到现实在越来越稀薄,直到它变成童话或是芭蕾舞蹈,而如果我想抓住它无限庞杂的整体,则需要对准一种在空间和时间里尽可能确定的叙述,一种麇集、细致、密布的叙述,就像用极细的针脚织成的网。而这里,我不得不去面对自己过去的一切;因为刚从浸满了直接经验的亲身经历中脱离出来,这网的针脚会扩张,缺口和脱漏也会打开,而现实的意义就会缺失。我寻找的现实也不存在于自传主义和心理反省中。对于人类灵魂的自传和描述会偏向于不定形,偏向于无限的接近,偏向于每一个人类存在的内心混乱;而我却总是偏向于构建一种有意义、有矢量线条图解的故事,偏向于把现实的刀片往每次选择出来的不同方向磨尖。
当然,只有从记忆,还有从我们曾直接卷入其中的经验出发,才能获得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一种不冷也不假的描写。但我寻找的现实,也肯定不存在于对意大利社会描写的现象学中,也不存在于对习俗的记录和批判中。当没有别的形式来了解,来表现这些事实的秩序时,文学有这种功用是合理的;而现在,我们有相当活跃的新闻业,也有在环境和现象方面都颇具实况效果的电影艺术。文学于是就有了另一项任务:揭示历史转折点,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一步跳跃,而不是今天那种滴答声。
我看到,我能向你们说出的,不是我已经写出的那些小说的故事,而是我慢慢地拒绝写出的那些小说的故事。至于那些我写过的小说,它们在那里,在书中,我希望,它们的故事能由它们自己讲述出来。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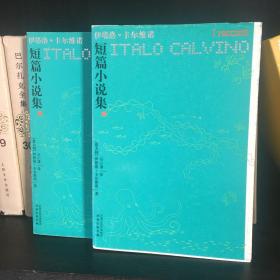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